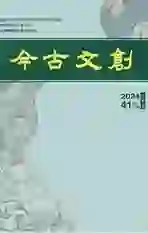明代中后期基层赋役改革的横向互动
2024-11-21叶再兴黄子萌
【摘要】明代中后期湖南基层赋役制度弊窦丛生,官民达成共识后,合力推动了一场赋役改革。在湖南茶陵州、攸县及善化县的赋役改革过程中,借助官员流动和官绅交往网络等媒介,邻省南昌县的赋役改革有益经验成为茶陵州的重要制度资源,而茶陵州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创制《便民正规》复被邻县攸县所借鉴。在攸县清丈中,地方官员通过合理利用官绅交往网络,使跨省界田清覆难题迎刃而解。基于湖南的例证可知,明代中后期的基层赋役改革不仅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还呈现出跨区域横向互动的特点。赋役改革经验的跨区域传播是这一横向互动的核心内容,而官员的跨区域流动和官绅之间良性的交往网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赋役改革;横向互动;官绅交往网络;明代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7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21
明代赋役制度研究自梁方仲发表《一条鞭法》以来,学界已展开卓有成效的研究,相关成果极为丰硕。①以往研究大致循两条路径推进,其一为侧重对制度规定层面的分析与阐述,多取传统制度史与全国性视角;其二为侧重对制度实践层面及其所引致之社会变迁的分析,多取社会史与区域性视角。②与此前历代自上而下的赋役改革不同,明代中后期的赋役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对此,学界已有辨明。③其实,明代中后期的赋役改革不仅存在一个自下而上的纵向互动过程,还存在一个不同地区之间的改革互相影3jGHKqvpHTDkuoyjrw838pBhRwtlrY+RAlXf8ktnqK4=响的横向互动过程。对此,学界却多未论及。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仔细剖析明代嘉万年间湖南长沙府的赋役改革实践,初步总结明代中后期湖南基层赋役改革中的横向互动模式及其特点,以期进一步丰富对明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
一、赋役改革经验的跨区域传播
在明代,长沙府位于湘江中下游流域,东界江西袁州府,西、南、北则分别与湖广辰州府、衡州府、岳州府接壤。长沙府下辖茶陵州、长沙县、善化县、湘潭县、攸县等一州十一县。其中攸县在长沙府南三百六十里,东界江西安福县,北界醴陵县,西界衡山县,南界茶陵州。[1]1266-1268茶陵州则在攸县之南,东与江西相邻。攸县、茶陵州地处罗霄山脉中,境内多为山地丘陵,很多居民自称明清时期从江西迁来,当地方言与江西较为接近。④
明朝定鼎之后,明廷以鱼鳞图册及黄册互为经纬,并创立里甲、粮长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重建赋役制度。但经过百余年的演变,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湖南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的赋役制度已弊窦丛生,或则诡寄田地而飞洒税粮,或则征收无度而逋赋严重,或则徭役签派之权操诸官吏里胥而卖富差贫。嘉靖年间,刘应峰谈到攸县清丈时即指出:“今天下田赋浮诡之弊萌滋久矣,故豪宗右姓之所磐石率多无税之田,而沉痛茹苦空输无田之税者倍在畸门窭子辈焉,积岁累世,固根深穴,虽强察吏莫之诘也”[2]467-468。又如《茶陵州志》载:“(茶陵州)均徭……旧例以一七甲、二八甲、三九甲、四十甲、五六甲一年一审,分别上中下银力二差,中间卖富差贫者多”[3]211,“旧志当年里长审定官丁,轮流拨差,十户九逃”[3]212。长沙府茶陵州、攸县赋役制度的败坏使得民不堪命,于是苦于赋役繁乱的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改革诉求。与此同时,茶陵州、攸县的州县地方官出于为民纾难及个人政绩的考量也有着较为强烈的改革冲动。到嘉靖年间,随着官民逐渐达成共识,一场官民合力推动的赋役制度改革在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拉开序幕。
嘉靖三十三、三十四年间,茶陵州知州刘高针对茶陵州田赋浮诡之弊议举核田,希望通过核田来清理田赋。然因举措不当,“约田程功,一切驱以苛峻”[2]468,致使“群役惴惴受事,如赴汤火”,“事未就而讼牒起”[2]468。由于遭到吏民抵制,刘高的改革最终失败。刘高的改革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为随后的改革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嘉靖四十四年,黄成乐就任茶陵知州,黄氏有感于茶陵赋役制度的败坏,于隆庆一、二年间再次推行改革。鉴于刘高改革的失败,黄成乐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他积极争取地方士绅的支持,接纳地方士绅刘应峰参与改革。刘应峰曾于嘉靖三十五至三十七年出任江西南昌县知县,在任内推行赋役改革,成效显著。据章潢《新修南昌府志》卷十六载:
刘应峰,字绍衡,茶陵人。由进士宰南昌,邑当会省,事难综核。公以镇静处之,一不为劳。均丁粮以签差役,省工食以覈机兵,开十限以定追徵,均铺行以苏偏累,革民船以省差扰,政绩为一时之最。[4]314-315
刘应峰后来因政绩卓越被擢为吏部主事,历江西参议疏乞终养。此时已回到家乡茶陵,成为一位究心理学,著述自娱的乡绅。在黄成乐的虚心邀请下,刘应峰再度涉足自己曾取得傲人成绩的赋役改革领域,将自己丰富的赋役改革经验献诸桑梓。在黄成乐与刘应峰等的合力谋划下,最终于隆庆年间议立《便民正规》。《正规》“仿江右一条鞭法,凡本州一应钱粮、均瑶、公费等项,岁当输于官者均派于概州丁粮”[2]504,“征银入库,随时支用”[3]214。由于得到刘应峰等拥有丰富赋役改革经验的士绅的协助及地方民众的支持,黄成乐的一条鞭法改革得以较为顺利地推行。
茶陵州借鉴江西的改革经验成功完成一条鞭法改革,直接推动了攸县的一条鞭法改革。茶陵州的一条鞭法改革取得成功之后,邻县攸县民众“鸣诸上台,求仿行焉”[2]504,表达出强烈的改革诉求。于是攸县知县徐希明顺应民意,引入茶陵知州与地方乡绅合议的《便民正规》,开始一条鞭法改革。
徐希明在《平赋役序》中详细记载了攸县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的情形。据徐希明记载,攸县民众见茶陵州议立《政规》 ⑤后顺利推行赋役改革,乃请求仿照茶陵州进行赋役改革。这时适逢湖南抚台下达赋役改革公文,徐希明遂召集地方士民在公所商议赋役改革事宜,最终达成三点共识:一是额办、派办和京办等项目维持原数;二是比照原颁会册与茶陵政规,如果原颁会册所载关乎攸县风教、解运、民瘼等公费较少,则相应增加;三是与攸县官府有关的公费,就算茶陵政规有所改革,也全部依据湖南原颁会册,不敢予以增加,以免让人觉得官府进行一条鞭法改革是为了谋取私利。[2]504
据上所述,攸县的一条鞭法改革有三点颇值得注意:第一,徐希明在“公所” ⑥召集地方士民商议赋役改革事宜,由此可见地方官员不敢轻视地方权势对赋役改革的影响。第二,改革过程中,地方官员注重结合邻州已有的成功改革经验及地方士民的诉求,折衷损益,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执行上级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条文。第三,改革者通过将赋役改革项目划分为不同部分,即与地方官府有关的公费全部依照湖南原颁会册,与民间事务有关的公费则借鉴茶陵的改革经验予以增减,实际上是划分了地方官府与地方士民之间的权力边界。由此可见,攸县一条鞭法改革是攸县官府、上级政府和地方士民三方势力合力推动,折衷损益的结果。
由于攸县知县徐希明悉心谋划,积极争取地方士民的支持,其一条鞭法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徐希明也因此获得后人很高的评价,《攸县志》称其“万历中由举人知攸县,莅任数年,丈田清赋,贫者无无田之粮;清江西界田,豪民无无粮之田”[2]257。
在茶陵州及攸县的赋役改革过程中,邻省南昌县赋役改革的成功经验通过退休官员刘应峰这一重要媒介而成为茶陵州改革的重要资源,进而茶陵州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创制《便民正规》又被邻县攸县所借鉴。可见,当基层赋役改革的经验经由官员的流动和官绅社交网络在地区间传播时,赋役改革的跨区域横向互动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明代中后期湖南基层赋役改革过程中,赋役改革经验跨区域传播的案例尚有不少,下面试再举两例。
据上文可知,徐希明在攸县知县任内,借鉴毗邻茶陵州的赋役改革经验,在攸县成功实现一条鞭法改革和田亩清丈。徐希明卸任后,董志毅接任攸县知县。董志毅后来又赴湘潭县任知县,并在湘潭县任内推动湘潭县一条鞭法改革。据李腾芳《征丁议》记载:董志毅赴湘潭县后,清查丈粮册,想改变赋役征派的办法,让每五石粮兼出一丁之银,从而废弃旧的征派办法,以为这样可以用私惠取悦于没有田的人。但是湘潭县的民众不肯遵行新的赋役征派办法,最终导致新的方案被束之高阁几近五十年之久。[5]599
董志毅将其在攸县任职期间所获得的赋役改革经验用于推动湘潭县赋役改革是不难想见的。
万历二十八年,善化县知县陈弘乘在推动善化县驿传改革时也借鉴了湘阴的改革经验。对此,陈弘乘的《善化官马议》记之甚详:
“今日之最为民累者无如马递一节……合无比照湘阴事例,除长善两县量存马数匹为县马,余总合两县之马,通付付临湘驿走递为官马,不惟马数多而易于应差,且马属于官而乘骑者亦知所顾恤矣。”[5]592
二、官绅交往网络与攸县清丈
丁粮、徭役及公费等项的摊派,是湖广省原颁章程及茶陵《便民正规》主要关注的领域,而田亩清丈尚未涉及。赋役摊派领域的改革固然可以做到既有负担下的相对公平,但难以解决税赋虚浮造成的民不堪命,可谓治标不治本。因此,徐希明在推行赋役摊派一条鞭法改革的同时,于万历三年进一步主持了田亩清丈,以期从更为根本的层面上解决攸县的赋役问题。
明代嘉万年间,攸县的豪宗右族兼并土地,当值的粮递在征收押解田赋的过程中也上下舞弊。[5]619徐希明就任之初,询问民事,为虚粮所苦的民众每天纷集于庭下[2]468,徐希明乃决定清理攸县的虚粮。开始,徐希明想根据原有册籍逐都清查,但很快意识到田契之内的虚粮可以查到,但田契之外的虚粮无法查到;留存有户口版籍的虚粮可以查到,但是没有户口版籍的虚粮无从查到[5]619,要从根本上清理虚粮问题只有清丈一途。其时,恰逢都民洪邦里等连名具告,恳请清丈田亩,徐希明乃借机召集攸县士民商议田亩清丈事宜。邑中士绅多表示赞同清丈,然亦有反对者,徐希明“独毅然抗论,谓能身冒议端,毋令重吾民困也”[2]468,核田之举由此敲定。
万历三年十一月,徐希明率领民众在城隍庙发誓,随后开展清丈活动。清丈的时候,每个都推选十名公正的人来监督清丈行为,再推举两个人负总责,与地报、知识人等一起对清丈用的绳罩进行编号,以防止民众作假。[5]619徐希明也时常亲往监视,以确保田亩清丈的顺利进行。[2]468攸县田亩清丈之事历时七个月,丈毕,将逐都田地细数登记刊印之,家给一册。[5]619在清丈过程中,徐希明还顺利清覆了攸县与江西安福县之间的界田。
在攸县与安福县交界处,居住着杨氏大家族。杨氏买了攸县民众的田地而逃避田税,攸县部分民众亦趁机隐逸自己的赋税,并诡称是杨氏所逸。此前攸县官府误以为赋税全部为杨氏所逸,于是让攸县民众代为输纳。[6]235。杨氏所逸之税皆由攸民代输,必然加重攸民的负担,最终造成“(攸县)四十八都之粮名存而实亡者积百五十石,当年粮递因之破产流移者不啻十之四五”[2]467的严重后果。本来,横跨两省的界田清覆因牵涉不同政区管理者的协作,更牵扯到地区间的税赋利益博弈,往往不易处理,所谓“以吴楚势悬隔,无能焉”[6]235。但是,徐希明善于利用官员与地方士绅之间的交往网络,借助当地颇有影响的士绅之力,使清覆界田一事迎刃而解。
安福杨氏有一位姻亲叫刘元卿,乃当世名儒。刘元卿因忤张居正,科举之路被阻,于是居乡讲学。但他不忘经世之志,对于“邑大便利,无不为当事言之,动中款会”[6]1551。因此,刘元卿颇得地方长官敬重,以致“县大夫至者,皆就而问政可否、缓急之宜”[6]1551。在此次清丈中,徐希明在命令约正张思乃“檄谕诸杨”的同时,鉴于刘元卿在安福杨氏中的影响力,写信给刘元卿,希望他出面劝诫杨氏配合界田的清理。刘元卿接到徐希明的委托后,乃“与清泉(即杨氏族人)户晓家喻”[2]467之。在姻亲刘元卿的劝诫和知县徐希明的谕令之下,杨氏在族人杨子孝的带领下,冒暑雨履亩清覆。最终“凡攸之田,悉属丈明,登册以报”[2]467,共得所逸之税四十七石,杨氏表示愿为输纳。⑦安福杨氏将逃逸的赋税上报后,徐希明当即宣布杨氏归附正义,因为他们的倡导而成就了攸县清丈的美事,并赠送“尚义”的门匾给杨子孝,以表彰他的首功。[5]611。界田清覆之后,徐希明担心杨氏后人可能再次逃避输纳赋税的义务,于是算明赋税额度,拔田给四十八都,让该都各甲分种,以其收获充缴赋税,永远不许买卖,并树立碑石,以垂不朽。[2]467
由于徐希明举措得当,攸县清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首先,此次丈田清理出大量的逸税田亩与人丁,从而使官府所掌握的财赋来源大增。据徐希明《固本楼记》载,攸县原有田地三十五万亩,清丈后增至七十五万余亩。[2]471清雍正五年(1727),攸县知县陈文言也提到明季徐希明丈田后,攸县田亩数定为七千二百九顷零。[5]620由此可见,徐希明确实清查出比原额更多的逸税田亩和丁数。其次,由于清丈后税基扩大,且秉持“田有沃瘠不等而科粮均以一则,俾滑胥积算不得操赢缩于其间”[2]468的原则,在税赋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攸民的税赋负担明显减轻且更趋公平,所谓“及考其成籍,粮无溢额,邑人获减损者十之七八,而间有一二稍增益者,亦寂无譁语”[2]467是也。
攸县核田之举,也获得了当地绅民的认可。缙绅庶民无不欢呼雀跃,认为清丈之后确立的新赋税征收办法非常方便,于是谋求立碑来记录徐希明的功德。[2]468攸县庠生龙尚宝、刘腾生、谭阶及陈制⑧请求茶陵州的刘应峰撰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徐氏也因其丈田清赋之功,得以荣列“名宦”,名垂青史。
攸县的界田清覆横跨湘赣两省,更牵涉到地区间的税赋利益,本不易解决,攸县知县徐希明通过合理利用其与刘元卿等地方士绅之间的交往网络,使这一棘手问题迎刃而解。由此可见,官绅之间良性的交往网络不仅可以促进赋役改革经验的传播,还可以在跨区域的纠纷调解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三、结论
有明一代,赋役改革几乎贯穿始终,而以中后期之一条鞭法改革及万历清丈为高潮。明代嘉万年间,湖南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与国内很多地方一样税粮虚浮、徭役繁重,再加上胥吏里甲舞弊、豪强劣绅侵凌,逋赋逃役时见,民不堪命。因此,官民双方都萌生了强烈的改革赋役制度的冲动。嘉靖年间,茶陵州知州刘高导夫先路,隆庆、万历时,茶陵州知州黄成乐、攸县知县徐希明追踵前贤,最终在绅民的支持下实现了赋役改革目标。通过仔细剖析明代嘉万年间湖南茶陵州及攸县的一条鞭法改革及田亩清丈,我们大致能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已表明,明代中后期的赋役改革表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湖南长沙府的赋役改革实践的分析可知,明代中后期的赋役改革不仅表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还呈现出跨区域横向互动的特点。赋役改革经验的跨区域传播构成了这种横向互动的核心内容,而官员的跨区域流动和官绅交往网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其次,以往的研究多强调基层行政中官绅勾结而导致徇私枉法,欺压良善的一面,而较少关注官绅之间的良性互动对基层行政的推动作用。来自攸县田亩清丈的案例表明,良性的官绅交往网络在处理某些地方行政时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官绅之间的互动似不可一概而论。
最后,在基层赋役改革中,地方官员往往是倡导者和直接领导者,他们根据已有改革经验、上级政策和地方实际折衷损益,探索适合地方实情的改革方案,表现出较大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地方社会尤其以士绅吏役为代表的地方权势的改革诉求与人心向背往往能左右改革的走向与成败。因此,官民之间是否存在通畅高效的协商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说,成功的基层赋役改革往往是官民共同推动的结果。
注释:
①参见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相关研究数量众多,不一一列举,可参阅赖惠敏《明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载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出版组1993年版。
②前一路径可以梁方仲、唐文基为其代表,后一路径可以刘志伟、郑振满为其代表。梁氏在《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初稿)》中指出,其所著《一条鞭法》《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释一条鞭法》及《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多半侧重在制度方面的分析和阐释”“至于历史方面,除在第二篇及第四篇的一部分外,都无暇多说”。《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初稿)》虽侧重历史方面,但终究与刘志伟、郑振满等试图从社会史和区域史的视角来研究明代户籍赋役制度改革旨趣各异。唐文基关于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参见氏著《明代赋役制度史》。刘志伟、郑振满关于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分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及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③参见万明《明代赋役改革模式及其特点初探(上)——从海瑞的县级改革谈起》 (《河北学刊》2016年第3期)及《明代赋役改革模式及其特点初探(下)——从海瑞的县级改革谈起》(《河北学刊》2016年第4期)。万明在其论文中指出明代的赋役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并试图从县、府、省级改革及其官员群体出发对明代赋役改革模式及其特点做出初步探讨。
④具体可参见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编》,载《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载《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⑤即茶陵州知州黄成乐所编定之《便民正规》。
⑥在明代,公所一般是商人或地方人士集会议事的场所。
⑦安福县致使攸县四十八都之粮名存而实亡者,积百五十石,杨氏自报逸税四十七石,剩下的一百零三石,或另有隐匿之情弊,则未可知也。
⑧陈制乃刘应峰姻亲,在攸县一条鞭法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茶陵《便民正规》很有可能是陈制从刘应峰处获得。
参考文献:
[1]薛纲,吴廷举.(嘉靖)湖广图经志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2]赵襄等.(同治)攸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3]福昌等.(同治)茶陵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5.
[4]范涞.(万历)新修南昌府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5]吕肃高.(乾隆)长沙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6]刘元卿.刘元卿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叶再兴,男,湖南醴陵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
黄子萌,女,湖南武冈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近代中国户政制度建构研究”(项目编号XSP22YBC06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