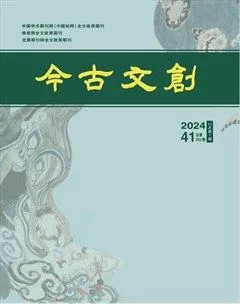符合论 : 普特南真之理论的变中之不变
2024-11-21李子哲
【摘要】普特南认为,实在论者通常都相信真理符合论。尽管他多次改变他的实在论立场,但他始终在实在论阵营中。在科学实在论时期,普特南在组合映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符合的真理论”,即一个真句子是与语言外事实和语言的其余部分有某种符合关系的句子。在内在实在论时期,他从达米特的辩明思想中得到启发,将真理解释为理想化的辩明。在自然实在论时期,普特南受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影响,开始捍卫常识意义上的符合论。在普特南哲学发展的三个时期,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符合论的思想。可以说,普特南真之理论的变中之不变就是符合论的思想内核。
【关键词】符合论;三重符合;理想化辩明;常识意义上的符合论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7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20
普特南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他一生笔耕不辍,在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等领域成就斐然。因其学术成就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他在美国具有罗素式的知识分子地位。普特南的学生科南特认为,普特南在哲学家中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多次改变他的基本观点。[1]16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普特南坚持一种较强的科学实在论。遭到达米特等反实在论者的激烈批评后,他试图走出一条中间道路,转而主张一种较弱的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反思,又转向为“自然实在论”。他的一些批评者给他贴上“移动的目标”的标签。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巴斯摩尔直言,“写关于普特南的哲学,就如同试图用鱼网捕风一样。”[2]707但是,在普特南哲学思想从科学实在论转向内在实在论,再从内在实在论转向自然实在论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如何为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普特南一直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真理问题一直是普特南研究的核心问题。普特南在批判和借鉴其他研究者真之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自己对真理问题的认识。在实在的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直接影响到真理观,实在论者坚持认识与外部实在相符合的传统真理观。普特南在转向“内在实在论”立场后,并没有完全接受反实在论的真理观,而是保留了实在论的观点。
不能将普特南粗暴地划入反实在论阵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普特南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坚持“实在论者”的真之理论,认为“真在于命题与事物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之间的一种符合关系”[3]210。
一、科学实在论时期的符合论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通常被称为普特南的“科学实在论”时期,他在该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论述集中在几篇论文中。1960年普特南在《真的断定符合实在吗?》一文中首次对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进行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真之理论。
塔尔斯基通过语义学理论的研究,对真理做出了定义。他认为,断言某个句子是真的或假的,只能作为某个特定语言的部分而言,如果一个句子断言某个句子是某个语言中的真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本身不能是语言中的一个句子,而必须属于某个元语言。普特南认为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存在以下问题:
(1)塔尔斯基所宣称的形式化的“真理符合论”,并不能说明一个句子是真的,当且仅当它与语言外的事实有某种可指明的关系,而只能说明我们必须定义“真”,以致“真”在某种语境中是可以消除的。
(2)像“‘蛇鲨是一种可怕的怪物’是真的,当且仅当蛇鲨是一种可怕的怪物。”这样的T语句,向我们传达的仅仅是“当且仅当”的左边和右边的句子是以某种方式相等的,即任何人只要接受了其中一个就有义务接受另一个。但它并没有提供一个符合关系C,使得一个真句子恰恰是对应于某个语言之外的事实处于关系C之中。
(3)塔尔斯基的理论没有为我们构造出一个说明,即某些断定(或具有断定语法形式的句子)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4]71普特南对塔尔斯基基于语义学理论对真理下的定义没有在这篇论文中明确提出。
在批评了塔尔斯基后,普特南提出了自己的真之理论。他认为,传统符合论的错误之处是会漏掉引号中的“以及语言学的”。他提出了一种策略,代之以试图直接地刻画所谓的真句子与“事实”(或“实际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刻画语法上的句子与其投射于可能世界的集合的范围之间的关系。他假设“存在一个唯一的句子的自然地投射于可能世界的集合;并且对应于一个真句子的集合永远包含着实际世界,而对应于一个假句子的集合不包含实际世界。”[4]74
因此,他在“组合映射”的概念上阐述了这样的符合观点:“一个真句子不是与语言外事实有某种关系的句子,而是与语言外事实和语言的其余部分有某种关系的句子。(‘符合’是三重的而不是两重的)。”[4]82这样,回到自然语言,就能够使某些“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句子有意义。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对传统真理符合论的改造。
普特南在《语言与实在》中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虽然他想通过自己的实在论直觉,即人类经验只是实在的一部分,实在不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或全部,来否认传统外在主义的符合论。但他承认,在没有相反证据出现之前给予肯定判断的原则和理性的无知原则都是以指称概念为前提的,而指称是语词与世界的关系。任何将语词映射到事物上的关系(当局限于一种特定语言时)都是语词与世界关系。普特南提出,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指称概念的作用是指定世界的参数化,并将其与语言的参数化联系起来,以这样一种方式,接受的句子倾向于与实际获得的事态相关联。
现实中,我们使用的语言在不断发展,语言与世界间的联系愈加复杂,因此,难以在句子或思想与其指称的对象之间寻找任何一种统一的联系;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指称概念看作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家族,因为这样会把语言与实在间关系的本质忽略掉,“这种关系的本质是语言和思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渐近地与实在相符合的。”[4]290也就是说,指称理论就是关于所讨论的符合关系的理论。因此,毋庸置疑,普特南在科学实在论时期所持的真之理论是真理符合论。
二、内在实在论时期的符合论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有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由于争论中的每一方都有其缺点,人们很容易试图将实在论论点与反实在论论点结合起来,以获得更好、更温和的立场。普特南试图持有实在论的真理概念,但他拒绝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和实在论的语义学。“为从‘上帝之眼’回归人类之眼,普特南提出内在实在论,以区别于外在实在论。这里进而提出关于‘真’的内在符合论,以区别传统的外在符合论。”[5]
普特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不再把真理看作“判断与其对象相符合”,他引入了一个认识论上理想化的概念,把真理看作一种“理想化的辩明”,旨在试图在不滑入形而上学的实在论的前提下,为真理的强大客观性奠定基础。
普特南认为,“真理是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与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的观点是外在论观点。为了进一步揭示外在符合论面临的困境,普特南对钵中之脑实验进行考察,他认为,钵中之脑的故事不是从世界上有感知能力的生物角度出发,所以,它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一种上帝眼光的真理观,也就是没有人的眼光的真理观,把真理看成是与观察者完全无关。他运用假言条件句的否定后件式对“钵中之脑”这个假设进行反驳,普特南的论证如下:
(1)如果我们真的是“容器里的大脑”,那么我们就不会想到自己是“容器里的大脑”,也就不可能合乎逻辑地具有真和指称所依赖成立的这种符合关系本身。
(2)事实上,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具有真和指称所依赖成立的这种符合关系本身,能够设想自己是“容器里的大脑”。
(3)所以,我们不可能是“容器里的大脑”。
钵中之脑的思想试验说明了概念与事物之间并没有神秘联系,同时指称与所指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普特南证明了并不存在我们能知道或能有效设想的上帝之眼,存在着的只是现实中的人们的各种想法。而他捍卫的观点是内在论观点,“在内在论者看来,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是我们的诸信念之间,我们的信念同我们的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6]55
合理的可接受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融贯论思想,同时带有了浓厚的相对主义的色彩。在某种语言使用者的共同体内部,相对于同一个概念框架之内的命题与特定对象之间是可以谈论符合关系的。普特南认为,主张真理符合论是最自然不过的理论。
康德以前,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持真理符合论。“虽然指称的相似性没有生命力了,但我们为什么必须放弃断定真理的符合论呢?即使我们的概念与它们所指称的东西之间有‘相似性’的想法无法成立,难道不可能有某种抽象的同构性,难道不可能有概念向(独立于心灵的)世界上的事物的某种抽象的投射?难道不可以把真理定义为这样一种同构性或投射吗?解决这个问题的难点不在于词或概念与其他实体之间不存在符合,而在于这种符合太多了。如果存在抽象的符合,那么集中不相容的理论就都可能是真的。”[6]79-80形而上学实在论者在承认存在抽象的符合与强调唯一的真之理论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悖论。而内在实在论者的真理观展现了向着真之多元论发展的趋势。普特南在此对抽象的符合论展开论述,也就为符合论的存在设置了真之条件。
普特南在1983年《论真理》一文中指出,真理概念的哲学问题不能通过去引号概念,或者真理的语义概念,或者这两者的某种结合,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他再次对塔尔斯基的理论进行批评,他指出,塔尔斯基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人们只能站在整个语言构架之外去构造存在于这个构架之内的陈述。普特南直指塔尔斯基真理理论的弊病,塔尔斯基试图仅仅通过添加一个“去引号方案”就把一幅唯我论的画变成一幅实在论的画的做法是荒谬的。[7]327
普特南赞同达米特对塔尔斯基真理论的看法:塔尔斯基和戴维森的命题只能是逻辑形式自洽,而不具有解释真理的功能,在哲学上是中性的。但在哲学中我们需要这种与塔尔斯基的真理形式一致的形式化刻画。达米特将真理与辩明等同起来,普特南从达米特的观点中获得启发,将真理视为理想化的辩明。普特南认为,真理不能简单地成为辩明,真理应该是一个陈述的属性,不能丢失,而辩明可以丢失,辩明是一个程度问题,而真理不是。
在普特南看来,如果一个陈述在许多种类陈述的认识论理想条件下被辩明是正确的,并且如果我们有点像物理学中的“无摩擦平面”,那么这个陈述是真的。普特南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许多种类的陈述,我们不可能真正达到认识论上的理想条件,即使我们能够达到,我们也不可能在某一天不得不改变主意的理论可能性之外确定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些条件,无摩擦平面也不可能真正达到,然而,他的这个比喻是有用的,因为谈论无摩擦平面具有实用价值,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近似它们。同样地,我们可以对许多种陈述的认识论上的理想条件进行高度的近似,并且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是寻求合理的实用价值。
普特南在探讨指称和理解的关系时,再次对实在论与符合的关系进行阐述。普特南认为,虽然在关于“使用”的叙述中,没有任何关于词语和事物之间,或句子和事态之间的符合。但这并不能由此得出这种符合不存在的结论。但是,“使用语言的程序”的好坏很可能取决于语言的单词和事物之间,以及语言的句子和事态之间是否存在适当的符合关系。[8]99-100
综上所述,普特南的初衷不是完全放弃符合论,普特南真正想抛弃的是上帝的眼光的观点,是“作为唯一的真理论的符合”,他试图在带有人类面孔的实在论立场下寻找一种可以与符合论相容的真之理论,也就是多元的符合论。
三、自然实在论时期的符合论
普特南在内在实在论时期想走一条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中间道路,但这一时期的真之理论存在矛盾,他一方面把真理与合理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真理是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理性可接受性是一种取决于认知美德的标准,它可以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化,这就默认了真理是可以发生改变的;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真理是超出当下合理性的一种不变的性质。
从根本上说,内在实在论自相矛盾的原因是没有真正克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路径依赖,自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形而上学预设,即在我们和世界之间设置一种分界面,我们的认识无法直接达到世界本身,也就无法表征分界面之外的世界,不能构成与外部世界的认知关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普特南开始寻求清除分界面的理论方法。1994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杜威讲座上正式进入到自然实在论立场,“实在”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事实”,它并不是存在于生活事实之外的另一个形而上学实在,否则不是陷进形而上学,就会导致相对主义。这种认识论的转变导致了他所认可的真理观的重大变化。
普特南摒弃了以往将真理视为理想化的合理可接受性的认识论概念,在詹姆斯、杜威的影响下,回到生活,回到常识的观点上来。他坚持了一种真之多元论的观点,即真理在不同的话语领域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普特南将真理等同于许多不同事物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有多少种真命题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东西,一个命题可能为真的领域就有多少个:经验的、数学的、逻辑的、伦理的、法律的、宗教的等等。简而言之,真理不是一个,而是很多。
普特南认为,“理解一门语言在于能够使用它(或把它翻译成一种可以使用的语言)的说法是目前该领域唯一的说法。”[8]97也就是说,我们对“黄金”或“电”的理解完全取决于我们对“黄金”或“电”这些语词的用法。他认为,我们在谈论对象或实在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某种外在于我们的语言的东西,而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我们的语言。
普特南试图表明,我们所谓的真理与指称对象本身的存在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为同样为真的陈述完全可能是指称完全不同的情况,即我们的一切描述都相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相对于我们的概念框架。普特南把这种“概念的相对性”作为他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和论证内在实在论的有力武器。当我们说一个陈述为真是相对于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强调对说出这个陈述的语言的理解决定了这个陈述的指称和真,也就是决定了我们的世界图景。正是在强调概念相对性的过程中,普特南开始从内在的实在论转向实用主义的实在论。
普特南意识到,过分夸大概念相对论就会走向一种扩大了的“唯我论”的相对主义,而文化相对主义者也可以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者。他指出,我们的概念在文化上是相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使用这些概念所说的话的真假仅仅是由文化“决定”的。[9]98
普特南通过支持自然实在论,改变了自己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观点,从而接受了真之多元论,即真理在不同话语领域中的作用不同。他对原先分裂的本体论做出重大的改造,自然实在论完全放弃了对世界和实在的幻想,而是从人类的现实活动出发,以实践的原则重新构造了我们视野中的世界。
普特南对真理的解释在此发生很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他对塔尔斯基真理论述的态度上,普特南从科学实在论时期对塔尔斯基“去引号”理论的强烈驳斥,转变为接受塔尔斯基的某些观点。这种转变表明,正是人和世界一起完成了事实的构建过程,事实与实在之间并不存在经验与超验的对立,而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当一个命题符合我们所断言的事实时,这个命题才被我们认可,这些事实就是实在本身。因此,与事实相符合就是与实在相符合。至此,普特南完成了他对符合论的再认识,其真之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结语
尽管普特南的实在论立场经历了两次转变,但对其实在论立场起决定作用的真之理论中有一个不变的思想内核,即符合论。
借用罗蒂对普特南真之理论的评价,普特南仍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实在论直觉”,尽管他对千篇一律的比喻的否定让他无法将这种直觉用语言表达出来。[10]普特南自己在《意义和知识》中开头就阐明了这种“实在论直觉”,即无论实在论者说什么,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相信“真理符合论”。[8]18
塔尔斯基的语义学真理定义真理符合论没有关注外部世界的事实,而仅仅认为是元语言与对象语言层面的符合关系。普特南对塔尔斯基这方面的批判是正确的。同时,由于证实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等对符合论的质疑,当代主要实在论者在对传统的真理符合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真理做出了更加多元的解释。
普特南对真理的解释也变得多元,他把符合论与理想的合理的可接受性、理想化的辩明和实践等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常识意义上的真之理论。从根本上,普特南的思想的一个不变的特征是确信“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和思想‘钩联’世界的方式问题”,其中隐含的观点是,对真理的正确理解既能给“钩联”一个抓手,也能抓住“钩联”的东西。这可能是因为,无论我们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真理解释,直觉上,当一个命题为真时,真理可以被用来表明该命题与它所涉及的那部分实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11]
无论是科学实在论时期的三重符合的真理论,还是内在实在论时期对真理的解释——理想化辩明,抑或是自然实在论时期常识意义上的符合论,普特南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符合论的思想,这位哲学巨人为何始终与符合论纠葛在一起,并难以真正放弃。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理论的探讨,沿着这个方向,重新考察历久弥新的符合论,并分析在符合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真理多元论,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Conant,J.and Chakraborty,S.Engaging Putnam[C]. Berlin,Boston:De Gruyter,2022.
[2](澳)约翰·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M].洪汉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英)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M].牟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Putnam,Hilary.Mind,Language and Reality[M].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5.
[5]陈晓平.真之符合论与真之等同论辨析[J].哲学分析,2014,5(1):118-130+199.
[6](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7]Putnam,Hilary.Words and Lif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8]Putnam,Hilary.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M]. Boston:Routledge,1978.
[9]Putnam,Hilary.Conant,James.(ed.).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0]Rorty,Richard.Putnam on Truth[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2,52(2):415-418.
[11]Dell’Utri,Massimo.Putnam’s Conception of Truth[J].European Journal of Analytic Philosophy,2016, 12(2):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