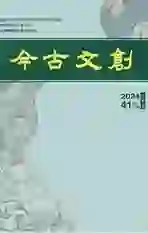《孙子兵法》功利战争观研究
2024-11-21阚尉航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使孙子对战争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其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中表现出国家本位的功利主义战争观。“利战”思想是《孙子兵法》的主体思想,具体表现为“安国利主”的功利战争观,“非危不战”的理性战争观,“上兵伐谋”的谋略至上思想。从根本来讲,无论是慎战备战的理性思想,还是用势用间的重谋思想,其最终目的都是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孙子兵法》;战争观;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6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18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兼并盛行,战争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频繁的战争刺激着中国古典兵学的萌生发展,战争观也在战争实践中逐渐深刻化,系统化。可以说,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战争观的基本特点就已初步成型,确定了后世战争观的发展方向。《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兵家的开山之作,表现出兵家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独特战争观。
一、“安国利主”的功利主义战争观
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战争都与“利”密不可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争夺是战争的主要驱动力。周朝以前,由于缺乏伦理道德的束缚,为争夺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而频繁爆发的部落战争常常是血腥暴虐的,黄帝擒拿蚩尤后“(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充其胃以为鞫(鞠),使人执之” ①。后羿被寒浞等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 ②。部落首领们为了鼓舞士气,常假借神的旨意彰显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如天降预兆、战前占卜算卦,以鬼神天命掩盖本质上对“利”的追求,这一时期所谓的“天命战争观”实际上是以争夺经济与政治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功利战争观”。
周公制礼作乐后,提出 “惟德是辅”的敬德保民思想,在兵事上规范了战争的基本伦理道德,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在礼法的束缚下表现出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从根本来讲,无论是“尊王攘夷”的口号,还是“奉旨勤王”的旗帜,都只是给不义的争霸战争披上一层尊礼守法的外衣,其本质仍然是以逐利为目的的暴力战争。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诸侯霸主们纷纷撕下“礼法”的外衣,在利益的驱动下频繁发动兼并战争,毫不掩饰对权利的追逐和渴望。尽管有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家们四处奔走,宣扬“仁政”“王道”的民本主义思想,但有战争实际操纵权的君主将领们,显然更倾向于实行“霸道”的功利主义战争观,以雷霆手段派遣士兵四处征战,兼并土地,扩大领土。即使嘴上说着“抚民”“保民”的话,也只是把它当作“劳民”“驭民”的政治手段,以免造成民心不稳,国家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局面。因此,思想家们的“民本战争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未得到实现。
“利”作为战争的价值核心和实际驱动力,始终主导着中国古代战争的兴起、发展和结局。无论战争的发动者们借着天神的旨意还是披着尊王的外衣,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利”。在中国古代军事战争史上,最先肯定功利主义战争观,宣扬“利战”思想的是春秋末期的兵圣孙武。孙武直言:“兵,利也,非好也”[2],承认“利”是战争的首要目的。其军事思想著作《孙子兵法》虽然篇幅不长,但精练地反映了孙子理性的功利主义战争观,“利战”作为中心思想,起到统领全书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中“利”共出现52次,“军争为利”[2],“兵以利动”[2],“非利不动”[2],“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2]等言论反复强调“利”的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中“利”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和君王,表现出“国家本位”与“君王本位”的功利主义战争观。有学者将“民本”作为《孙子兵法》的主体思想,认为《孙子兵法》“把‘仁’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③,其中爱卒、爱民、善待战俘等观点“闪烁着人本思想的光芒” ④。但联系上下文整体分析,以上这三种行为无不以“利”为前提,表面上是以民为本,归根结底其内核还是以利为先。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2]是军中将领驭下的手段,“爱而不能令……不可用也”[2],爱卒的根本目的是令卒、用卒,关心爱护士兵,获得士兵的尊重与爱戴的根本目的,是在战场上能更好地命令、指挥士兵,是能驱遣士兵“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2]。让士兵完全服从于将领的命令,为战争的胜利,国家和君主的利益付出一切。为激发士兵的潜能和勇气,可以将士兵“投之亡地”“陷之死地”[2],以此提高战争的胜率。由此观之,在孙子看来,战争取得胜利的价值远高于士兵的价值,无论用什么手段,最终目的都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实际上是以取胜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
“民”在书中共出现10次,《始计》篇“令民与上同意也”[2]一句,之所以是“民与上同意”而非“上与民同意”,是在令百姓去主动顺从君王的意志,听从君王的旨意,服从君王的调遣,百姓的意志与意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主的命令与决策,百姓只需要无条件服从君主的一切决策,实际上是在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威性。“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2]这句话突出的是懂得用兵规律的将领在战场上的重要性,将领的优秀与否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负,决定了百姓与士兵的生死,决定了国家的安危存亡。将领的才能往往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2]。将领承担着国家和百姓安危的重担,只有掌握用兵作战的规律,做好全胜的准备,才能保护士兵和百姓,才能保全国家,保住疆土。“胜者之战民也”“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2]中的“民”都不指百姓,而是指士卒。“爱民可烦”[2]是说爱护民众的将领往往会被民众牵制,给敌人可乘之机,“爱民”在这里显然是被否定的,孙子认为将领应当时刻保持理智与冷静,以战争的胜利为一切决策的前提,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将领可以舍弃一切,包括士兵和百姓的生命,战争的胜利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2]中的“人”也指民众,保护民众而有利于君主的将领是国家的珍宝,“唯人是保”的前提是要符合君主的利益,是要“令民与上同意也”,最终目的还是落到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上。
“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2]的“善俘”行为,常被认为突出表现了孙子以民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从《作战篇》的整体结构来分析,善俘的出发点还是“利”。开篇孙子列举军队出征前的庞大军费开支,“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2],尚未出征便日费千金,军队出征后,行军路途与作战时所耗军费更甚,为避免面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2]的窘境,孙子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速战速决的“速胜论”,作战时间拖得越久,对国家的损耗就越大,“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2]行军打仗最忌拖延迟缓,在外耽搁一日,国库的负担便加重一日,战局便有可能出现动荡,因此速战速决有利于节省国家钱粮,增加军队胜率。其二是以战养战,取用于敌的计策。孙子认为粮食可以从敌国获取,“智将务食于敌”[2],“因粮于敌”[2],从敌国获取敌军的粮草,既减轻了本国军费开支的压力,同时也缓解了本国粮草长途运输的压力,减少运输途中人力物力的损耗;战车也可以从敌国抢夺,“车战得车十乘以上”“取敌之利者”[2]要加以奖赏,以此类推,“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2],敌国的战车可以抢夺并收编到我军战车中,敌国被俘的士卒也可以加以善待,并收编到我军士卒中,提高我军战斗力,“是谓胜敌而益强”[2]。因此,整体来看“卒善而养之”在这里强调的并非是孙子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是以战养战,取用于敌的国家本位功利主义思想。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孙子始终将国家的安危排在首位,国家的生死存亡高于一切。为达到“安国利主”[2]的目的,将领可以使用一切诡道计谋来获取战争的最终胜利,表现出兵家区别于儒墨道的功利主义战争观。受到周礼敬德保民思想的影响,孙子的战争观也不同于原始时期的血腥暴力战争,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色彩。
二、“非危不战”的理性主义战争观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出,《孙子兵法》表现出区别于道家和法家的“对待人生世事的极端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所谓理性态度,就是“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智的判断和谋划” ⑤。兵家较之原始部落和周礼,对战争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不再受鬼神观念的束缚,重视战争中人的作用。
孙子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2]君主和将领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要事先探明敌情,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对方的详细情况,如粮草存量,士兵状态,调兵部署情况等。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对敌方动态情况的了解越详细,我方获胜的概率就越大。但敌情的获取,不能依托于祭祀鬼神、占卜、祈祷等迷信手段,也不能根据日月星象草草推验而得,必须“取于人”,从了解敌情的人身上获取情报。而了解敌情的人,即由我方培养,送到敌营中获取情报的间谍,间谍在两军作战时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敌军的驻扎位置,行军路线,军队情况,甚至于军队布防,将领谋划,都可以通过间谍之口得知,预先布防应对,大大提高我军的胜率。在鬼神观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孙子明确指出战时占卜祭祀的非理性特征,以及可能对国家生死存亡造成的严重后果,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决定性作用,表现出理性主义色彩。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2],孙子的理性主义战争观还表现在他对战争危害的清醒认识。“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2]兴师远征是个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十万的军队不仅需要劳动七十万百姓荒废田地,沿途运输物资,而且“日费千金”,这样算来一年就是几十万金的花销,有时甚至要“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2],军队长时间在外奔波驻扎,衣食住行皆要消耗国库钱财,如此计算,耗费在战争上的钱财简直难以估量。这样劳民伤财的兴兵作战,若是幸运地取得胜利,收缴敌军物资,开拓我国疆土,还能稍微弥补战争的损耗。可往往情况是“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2]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打造攻城器械,又牺牲掉三分之一的士卒去攻城,城池却依旧攻不下来,平白耗损资源不说,如此大规模劳民伤财却毫无所获,沉重地打击了国家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
为趋利避害,减少战争对国家的危害,孙子提出“慎战”和“备战”思想。“慎战”即君王和将领要谨慎发动战争,“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2],是否发动战争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胜率和形势,没有利益不要行动,不能取胜不要用兵,没到危急关头不要轻易发动战争,时刻以国家根本利益为主,三思而后定。君主和将领必须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切不可暴躁易怒,情绪激动起伏大,所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2],主帅在情绪的刺激下草率发动战争,不仅会使士卒大量牺牲,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亡国不可以复存”[2]的巨大灾难。孙子的“慎战”思想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国家本位基础上的利战思想。
如果说“慎战”是站在战争发动者的角度分析战争的最佳时机,那么“备战”就是站在战争承受者的角度,思考敌军发动侵略战争时,我军如何打赢保卫战,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孙子认为,赢得保卫战胜利的秘诀就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2]只要能做到“有以待”“不可攻”,国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所谓“有以待”“不可攻”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要提高警戒,做好敌军随时入侵的准备,时刻保持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要安排好士兵巡逻,即使在休息时也不可彻底放松警惕。要充盈国库,储蓄钱粮军械,以备不时之需。其二要不断提高国家军事实力,增强我军威慑力。士卒要勤加操练,做到能征善战,训练有素,随时能上阵杀敌;将领要勤习兵法,有勇有谋,做到“通于九变之利”[2],在战场上气定神闲,指挥若定。要预先备好作战方案,“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2],随时根据地形地势特点和政治外交形势调整作战方案;君主要励精图治,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使城池坚固,国库充盈,装备精良,具有“先为不可胜”[2]的实力,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2]。
孙子的理性主义战争观,突破了原始天命观的束缚,强调将领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警示君主和将领谨慎发动战争,战时要始终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非战时要做好备战工作,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三、“上兵伐谋”的谋略至上战争观
中国古代兵书大致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 ⑥治兵与治国不同,治国是长期持久的工作,要以正当合理的统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兵事往往是成败一夕之间,因此战场上讲究权谋,要出奇谋以致胜。《孙子兵法》是兵权谋类军事著作,其中示形任势、虚实奇正、用间先知等思想都表现出谋略至上的战争观。
“形势”是兵力的部署与运用,将领在战场上要灵活机动地运用“形势”,取得胜利。分开来讲,“形”是军事实力的建设,“势”是在“形”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军事实力以取得战争的胜利。钱基博注:“形者,量敌而审己,筹之于未战之先。势者,因利而制权,决于临战之日。” ⑦“形”是战前根据敌方情势,做好我方军事建设,“强弱,形也”[2],军事实力强弱是确定的。“势”是战时根据战场上利害得失,做出及时决策应变,“勇怯,势也”[2],士兵表现的是勇是怯是随机的。“形”有先定之数,形胜在己不在敌,战事未始,以敌我双方之“形”就能基本判断出战争胜负,具体来讲“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2],田亩数量决定粮食产量,粮食产量决定兵员多寡,兵员多寡决定军队战力,兵多粮足者胜,这就是战前可见之“形”。孙子将“形”巧妙地解释为“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2],在山涧上积水是“形”,决水就是“势”。将领在战场上管理士兵,分配部署兵力,指挥作战,士兵以“激水之疾”“鸷鸟之疾”[2]向敌方迅速猛烈发起进攻,这就是“势”。孙子将“势”比作“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2],从高山上滚落的石头速度极快,威力巨大,战场上善于借“势”的将领,往往能使军队如滚石般势不可挡,一战而胜。
“形势”又可分为“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四种,前两者是治兵方法,管理很多人如同管理很少人,指挥很多人如同指挥很少人。后两者是用兵方法,兵力部署要奇正相生、虚实相生、变化无穷。李零先生认为“奇正”和“虚实”的区别在于,“奇正”是点上的兵力配置,“虚实”是面上的分散集结 ⑧。中路走大军“形以应形”,侧路出奇兵“无形以制形” ⑨。即为“奇正”之法,调动大军避实击虚,隐实示虚即为“虚实”之法。孙子认为,对敌军要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我军要隐实示虚,千变万化,使敌人“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2]。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虚实并非一成不变,“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2]因此,将领要掌握并运用战争规律,敌众我寡时,使“我专而敌分”[2],逐个击破。要抓住瞬息万变的时机,“攻其所必救”“乖其所之”[2]来扭转战局,掌握主动权。
如果说“形势”侧重军事实力的建设与运用,那么用间与先知就是对军事情报的探查与利用。孙子认为间谍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2]不了解敌我军情就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战前探察军情不能求神问卦,要依靠间谍,间谍探得的情报能使我军料敌于先,谋敌于前,占得先机,极大提高我军胜率。孙子将间谍分为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类,介绍了不同间谍的不同用法,并对用间的君王和将领提出条件和要求,只有“圣智”“仁义”“微妙”的人才能用间,对待间谍要坚持“亲”“厚”“密”[2]的原则。“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2]善用间谍是“兵之要”[2],是“人君之宝”[2],孙子对间谍与情报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智”与“谋”的重视,准确的情报可以大大减少士兵的损耗,巧妙使用计谋远胜于一味蛮力进攻,所谓“上兵伐谋”[2]者,谋略的使用往往可以大幅度提高作战效率,实现我军利益最大化。
四、结语
《孙子兵法》是孙子在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对战争本质和规律的独特认识,表现出不同于原始战争的理性色彩,和区别于儒墨道等学派的利战思想。“利战”思想是《孙子兵法》中其他一切思想的最终指向,慎战和备战思想的提出在于减少国家损失,形势与间谍等谋略的使用在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归根结底,《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孙子国家本位的功利主义战争观。
注释: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
③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④孙喆:《略论〈孙子兵法〉中的人本思想》,《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6期。
⑤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⑥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⑦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⑧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参考文献:
[1]孙武,曹操,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银雀山汉墓简竹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3]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5]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6]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7]李零.孙子古本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8]杨丙安.孙子会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9]施芝华.孙子兵法新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0](日)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11]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12]褚良才.孙子兵法研究与应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13]郭化若.孙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4]龚留柱.《孙子兵法》战争观诸说驳论[J].滨州学院学报,2010,26,(05):57-62.
[15]龚留柱.《孙子兵法》与先秦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J].滨州学院学报,2010,26,(01):1-6.
[16]程远.先秦战争观研究[D].西北大学,2005.
[17]李桂生.先秦兵家研究[D].浙江大学,2005.
作者简介:
阚尉航,女,汉族,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