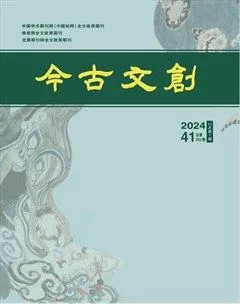浅论晏子辞令中的重礼思想与民本精神
2024-11-21周诗易陈彦辉
【摘要】晏子是春秋行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辞令善用譬喻、刚柔相济,充满浩然正气,是春秋行人辞令的典范。他对礼乐的推崇可以反映春秋时期上层贵族重礼的社会风气。晏子重视礼制,对礼制中蕴藏的“中和”之美的推崇体现了典雅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他“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是儒学民本思想之滥觞,这种理念也催生出了其独特的忠君爱国观念。
【关键词】晏子;辞令;礼制;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61-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17
春秋是一个讲求辞令的时代,行人是创制辞令的主要群体。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承担着政治谈判交涉的重要使命,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要求行人不但需要具备卓绝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觉察能力,亦需要他们在交际时言谈风雅委婉、表述灵活准确。行人辞令是经过行人精心撰写、修饰、润色过的文字,春秋行人因此是一个与文学关系极为密切的群体,春秋时期的郑国子产、子羽、鲁国叔孙豹、齐国晏子等都是杰出行人的代表。晏子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其辞令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晏子名晏婴,又称晏平仲,春秋时齐人,齐国大夫晏弱之子。他历佐灵公、庄公和景公,执政时期长达五十余年。他执政时,齐国已经失去齐桓公时期的霸主地位,但他凭借自身的才识和机敏,使各国不敢轻视齐国。晏子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史记》和《晏子春秋》等文献之中,他是春秋时期贤臣的代表,不仅学识深湛,熟谙礼乐,而且善于论谏、工于辞令,通过其辞令,我们可以探求晏子的思想特征,如重视礼乐、爱国爱民等。
一、晏子辞令的论说特点与策略
“辞令”,在春秋时期一般指应对宾客或议论政事时所用的经过文饰的言词[1]6,又称“辞”或“辞命”。并非所有的士大夫言词都可以称之为辞令,只有经过精心修饰的,优美且富深意的言词,才可称之为辞令。孔子曾表示辞令的制作至少需要经过“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四个步骤或流程[2]185-186,这一方面说明辞令制作的复杂,另一方面表明时人对辞令重视程度之高。辞令不仅指外交场合的外交辞令,也包括用于本国君臣、臣子之间经过文饰的言辞。
晏子思维敏捷,善于辩论,将语言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作为齐国上大夫,晏子常为本国君主建言献策,多次参与外交活动,《晏子春秋》和《左传》中保留了晏子的大量辞令,通过这些辞令,我们不但可以认识晏子含蓄与直白兼善、雅言与俗语结合的语言风格,了解到晏子忠正的品性,也可以照观春秋时期贵族的言谈举止,更清晰地把握春秋上层社会的交往习惯。下面就晏子辞令的几个特点略加品评。
首先,晏子善于引用前人事例,使辞令摆脱枯燥乏味的说理,激发听者的兴趣。《晏子春秋》卷二记载的晏子劝谏齐景公饶恕伐竹者之事便是该类辞令代表。齐景公作为一国之君,看见有人砍伐自己的竹林,便亲自驾车追赶砍伐竹子的小偷,并要治罪,这显然会遭人非议。为了维护君主的声誉必须让国君收回成命,晏子马上求见齐景公,给他讲述齐国第二任君主齐丁公讨伐曲沃善待百姓的事迹:“丁公伐曲沃,胜之,止其财,出其民。公日自莅之,有舆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视之,则其中金与玉焉。吏请杀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众图财,不仁。且吾闻之,人君者,宽惠慈众,不身传诛。’令舍之。”[3]108让齐景公认识到作为国君应该像自己先祖一样“宽惠慈众”,最终齐景公改变不当行为,马上释放砍伐竹子的小偷。晏子这里的劝谏辞令最大的特点就是引用先君的具体事例,将所有想表达的道理都融合在历史故事之中,易于为听者接受,能够顺利达到自己劝谏的目的。又如齐景公欲于春夏之交田猎,且欲修筑大台。晏子便利用对比的手法,引用周文王不沉迷田猎和楚灵王大兴劳役建台之事进行劝谏,周文王与楚灵王一明一昏,一正一邪,形成强烈的反差张力,令齐景公认识到田猎与修台的弊病。
其次,晏子好用譬喻。他在送别曾子时以“直木”“和氏之璧”和“兰本”作譬喻。直木被做成车轮后,便再难变直;和氏之璧被雕琢后,成了传国之宝;兰本浸泡在苦酒恶臭难当,而浸泡在麋肉酱中则足以换取一匹好马。这三者必须经过外在环境的重塑才能够发挥本身的能力,晏子将常人比作它们,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希望曾子能够选择合适的环境,择优而交。当他出使楚国,面对楚王“齐人固善盗乎”的刁难时,晏子又以橘为譬:“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3]392不仅回击了楚王的言语,且讽刺楚地水土不佳,难育贤才,令楚王只能自嘲致歉,这足见晏子所用譬喻之奇巧有力。
再次,晏子在劝谏或批评时常常直言不讳、造语犀利。他不喜阿谀奉承,遇到不当之事,立即出言批驳,并不容情。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4]1292
齐昭公与晏子似论房屋,实议国事。春秋诸侯企图以厚德自饰,齐昭公也不例外。当齐昭公问“其谁有此乎”时,表明已有自矜之意,后自问自答“吾以为在德”。可见齐昭公自认是有德之君。晏子明白齐昭公之意,可他不称齐昭公为有德之君,反夸赞陈氏善待百姓之举。并表示,若陈氏未灭,而齐昭公后人稍有懈怠,齐国便会被纳入陈氏囊中。这番辞令十分尖锐,直言齐国有易主之危。晏子不仅在面对本国君主时直言不讳,面对他国君主时一样态度强硬。晏子出使吴国时,吴王问他如何做才能让国家威严强盛时,晏子回答:“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彊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不以众彊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此长保威彊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3]256由于不满吴王专行霸道、穷兵黩武的做法,晏子表示国君对内应该先考虑百姓利益而后满足自己称霸的私欲,令强大、尊贵、富有之人不欺凌弱小、贫贱和穷困之人,使得百姓和乐、政治太平;对外不能凭借威武强大压制他国之君、兼并他国土地,无论是使用刑罚还是动用士兵,都应为民众福祉考虑。晏子对吴王所作所为直接提出批评,丝毫没有照顾吴王颜面,导致吴王气愤不已、勃然变色。
最后,晏子深明刚柔相济之术,并非一味直言批驳,而是将直率与委婉相结合。鲁昭公三年,晋齐两国联姻后,晏子与晋叔向曾展开过一次颇具深意的交流:
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4]1071-1072
晋国叔向和齐国晏子都是春秋时期名臣,晏子如晋之时,二人谈论了齐、晋两国公室衰微,士大夫强大的局面,话语中流露出对公室前途命运的忧虑。晏子识见渊博,不刻意追求谈吐上的雅致,论事时不避浅陋,反而更能见出他对平民苍生的关注。他抓住“豆、区、釜、钟”这四样贴近齐国百姓生活的量器进行论述。陈氏将自家所用的四种量具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容量,百姓贷粮时,用自家的量具贷出,还款时却仅需按照齐国原本规定的量具标准还回。陈氏不要利息,反而“贷厚而收薄”。不仅如此,陈氏卖给百姓的木材、鱼盐等物,也均以成本价售出。在齐国王室治下,年老者忍饥受冻,市面上鞋履便宜而假肢昂贵,可见齐王室的无能腐败、刑罚严酷,百姓自然更加爱戴并支持陈氏。晏子恼怒齐君的无道,又碍于外交礼节,未在他国臣子前直斥本国君主,只通过委婉的方式向叔向表达自己的态度,他见微知著,提前预见了田陈代齐的结局,可见晏子的远见卓识。
又如《晏子春秋·内篇》记载的“金壶丹书”也是晏子将直言和委婉劝谏相结合的典型范例:齐景公到纪地游玩,偶然获得金壶一只,金壶内藏丹书曰“食鱼无反,勿乘驽马”。齐景公认为丹书之义是:不将鱼翻转是因为厌恶鱼腥味,不乘驽马是因为难以远行。而晏子对于丹书的解释与景公大相径庭,他认为这句话是指:“食鱼无反,毋尽民力乎!勿乘驽马,则无置不肖于侧乎!”[3]336即强调要怜惜民力,远离奸臣。对此齐景公很不理解,他认为该丹书的含义很简单,没有那么深刻的哲理,纪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治国之道,否则它就不会灭亡。晏子认为正是由于纪国将丹书置于壶中而非悬挂于门上的做法才造成了它的灭亡,非常圆满地解答了齐景公的困惑。晏子并无大段论述,言辞精致简洁而发人深省,前后逻辑毫无纰漏。虽然丹书中的内容本意或与晏子的解释不同,但晏子顺利将话题引入到爱民与理政上,借此规劝齐景公。纵观其各类辞令,大多是劝谏君主重仁爱民之辞。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5]75 “浩然之气”是需要自身长期努力而后形成的道德修养,是言辞能够说服他人的关键。晏子为人方正、仁义为先,博学多才、能言善辩,他本身的浩然正气成了其辞令的基础,在论说己见时自然能够无往而不利。
二、晏子的重礼思想与“中和”审美理念
西周时期,“礼”是社会秩序的主导,重礼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上层社会的共识。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诸侯以及卿大夫僭越礼制的情况不断出现,宗周礼乐制度面临崩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仁人志士为维护周礼,开始就“礼”的正义性、合理性、内核和社会作用等问题进行揭示和阐发,在春秋时期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礼学思潮。虽然无法改变礼制最终衰颓的结局,但这种重礼的思潮反映了春秋士人对社会的观察与反思,对社会政治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埋下了伏笔。
晏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是治国安民的重要手段。《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对“礼”做了如下阐述:
“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4]1292-1293
这是齐景公与晏子在路寝之台议政时的对话,齐景公问晏子怎么才能阻止陈氏势力不断扩张,晏子认为只有发挥“礼”的作用才能实现。因为在晏子看来,“礼”是国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只有依靠“礼”,才能让社会的各个阶层保持平稳安定的状态。同时,“礼”也是国和家的枢纽,在“礼”的黏合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关系均能得到很好的维系。晏子对“礼”的解释十分具体,在晏子那里,“礼”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落实到政治生活的客观存在,他对“礼”的认识并未流于表面。
出于对“礼”的重视,晏子才能勇于劝谏国君尊礼守礼。齐景公曾向晏子表示自己不想通过复杂的射礼来选拔勇士。很明显,齐景公没有理解射礼的真正含义,在他看来,有一系列仪式规则的射礼只是表面文章,对挑选孔武有力、杀敌制胜的勇士没有什么帮助。对于国君的错误想法,晏子毫不客气加以反驳:“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3]170晏子用“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这句非常犀利的话来说明“礼”对于人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指出,一个有勇有力而不知礼之人,会对国君的性命构成很大的威胁。最后指出“礼”对国君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价值是为其驾驭百姓,这么好的工具,国君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礼”既是社会运行的基础,同时也是个人应当遵守的准则。晏子认为区别君子与庶人的重要标准即是否知礼,正是秉着这样重礼的态度,他对自己也有着严格的遵礼要求。昭公三年,晏子出使晋国后,景公为其更换住宅,晏子回国后认为这么做不符合君子守礼的规范,坚决要求拆除新舍,他坚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4]1074晏子将“礼”视为行为处事的原则,一切都需依礼而行。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春秋时的诸侯依然遵守礼乐、重视信义[6]585,春秋时期周天子虽然式微,但诸侯仍然需要假天子之名依“礼”行事,“礼”在春秋时期依旧不可或缺。春秋多结盟活动,必须依靠“礼”才能维持共处关系,而讲求信义,又是各国重“礼”的外在特征,“信”与“礼”也是不可切割的。晋栾盈受其母栾祁谮害,被迫流亡楚国,后又到齐国谋求生计。栾盈无辜遭谮,齐庄公收纳栾盈似无不妥。但在晏子看来,商任之会中,齐国已受命于晋国。栾盈为晋所逐,齐国若留栾盈,无异于撕毁盟约,此为不信之举,所以晏子力谏齐侯不能失信,不可收留栾盈。不失信是维系各国间“礼”的先决条件,反对失信,同样是晏子重“礼”的表现之一。
晏子的重礼思想也对其审美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晏子直接表明自己审美价值与理想的文字并不多,但根据他与旁人的交谈,我们不难总结出他对美学的理解。《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4]1237-1238
景公认为“和”与“同”是相等的概念,晏子却指出二者有异。首先,他以烹调为例,烹调需配以不同的食材,又必须使这些食材浑然一体。“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即是说味道不足时则增加佐料,味道过重时则反之,最终使得菜品达到一种中和的味道。其次,以音乐为例,气息的流动、舞蹈的刚柔、音调的高低、风格的多变需相辅相成,音色的清浊、节奏的快慢、情绪的起伏、结构的周疏必须相济有度,这样才能形成中和之音。最后,指出“和”是谐调应合之义,而并非相同一致。齐国大夫梁丘据的观点与景公完全一致,便如同烹饪时“以水济水”,演奏时“琴瑟专一”,使得菜品与音乐了然无味。晏子形象地指出了“和”与“同”的具体差别,分析了“和”的作用与“同”的缺陷不足。晏子对“和”的理解体现了儒家精神,孔子所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179正与此不谋而合。
另外,晏子在以音乐论“和”时频繁地利用对立的概念来阐释“和”的内涵,如“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等。两种对立的事物交融后形成不偏不倚的状态,又可以称之为“中”。这种对音乐艺术性的深刻见解反映了晏子的审美理念,也反映出儒家艺术精神的内核。晏子认为音乐的美好,在于相对的元素能够彼此颉颃,最终形成一种典雅中和的状态。这种求“中”理念起源于上古社会,且不局限于艺术领域。《尚书·商书·盘庚中》语:“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7]241孔安国释此句为“群臣当分明相与谋念,和以相从,各设中正于汝心。”[7]241可见商代时期,“中”已被视为个人评价的正向标准,有“中正”之义。春秋时期,“中”被视为创制周礼的准则,孔子在谈“礼”时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8]1383子思对此有详细解释:“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8]200说明周礼需确立一个无论是“过之者”还是“不至焉者”都能够通过努力达到的适中的标准。
作为重视礼乐、依礼行事的贵族,晏子自然对礼制中蕴含的“中和”观念产生高度认同。庞朴在《中庸·平议》中将古典文献中表现求“中”理念的句子归类为四种形式:第一,A而B,以对立方面B来济A的不足;第二,A而不A,强调的是泄A之过;第三,不A不B,要求不立足任何一边,表现出毋过毋不及的主张;第四,亦A亦B,指明双方的相互补充。[9]83-87四种形式中的A与B是一组对立相反的概念,上述的四种形式实际上都是表达A与B保持中正且不偏颇的状态。依据这四种形式,我们不难从晏子的言辞中发现晏子对“中”的追求。如晏子在与景公交谈时中曾言:“是以贤者处上而不华,不肖者处下而不怨”[3]203即是“A而不A”的形式。贤能之士处上位而不慕荣华,缺乏才能之人处下位也能没有怨憎,他认为盛君治下的社稷,人们无论地位高低,都能够保持内心的中正平和。又如叔向问晏子:“君子之大义何若?”晏子立即用了一系列“A而不A”的句式进行回答:“和调而不缘,溪盎而不苛……和柔而不铨,刻廉而不刿,行精而不以明污……此君子之大义也。”[3]283-284他列举了君子与人和谐但不顺大流,明察秋毫又不过分严苛,平和温柔却又不卑微自贱等优良的中和品性。再如齐景公欲为晏子在宫内建造房屋,晏子以“隐而显,近而结,维至贤耳”[3]419作为推辞。该句为“A而B”的句式,晏子认为至贤之人能做到隐居时名声显赫,靠近君王时能有所节制,而自己尚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在晏子论述治世、君子和贤人这种理想的物和人时,时常涉及对“中”的理解和追求,“中”于晏子而言是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所保持的一种积极状态。
三、晏子“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忠君爱国精神
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西周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发展,最终在汉代基本定型。《尚书·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7]177的说法,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2]14、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5]387和荀子认为的“君舟民水”[10]152-153都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在治国理政方面颇有建树的晏子,他提出的“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叔向曾向晏子请教过民众与道义的关系,在他看来民众与道义似是分割的、对立的,民众与道义难以共存。晏子的观点恰与叔向相反:“婴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3]282他认为民众与道义是统一整体,二者不可割裂,其关键在于“以民为本”,只要把握住民这个根本、中心,就不会出现叔向的疑惑。晏子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谈,前文所引的晏子与叔向对齐国未来的探讨便可作为这一结论的直接论据:齐国陈氏爱护百姓,齐国王室虐待百姓,而尊崇道义、行为正直的陈氏则获得了百姓的拥护。晏子将“以民为本”视为治国基础方略,向齐王提供了一系列有惠于民的建议,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减轻赋税。如晏子劝谏齐景公不要修建大钟:“既筑台矣,今复为钟,是重敛于民,民必哀矣。”[3]123齐景公乃止。第二,减免徭役。如晏子见齐景公对道路上的死尸不闻不问,于是批评:“饥寒冻馁,死胔相望,而君不问,失君道矣。”[3]72齐景公于是免除了方圆四十里百姓一年的徭役。第三,减轻刑罚。如晏子劝谏齐景公不可因为野人惊吓了自己欲射之鸟而杀之。晏子的治国理念将“以民为本”作为基本纲领,并且积极主动地以此纲领进行改革或劝谏,反映出晏子为苍生请命的正义感和仁政爱民的政治品格。
对民众百姓的强烈关怀也使得晏子形成了前卫且独特的忠君观念。齐国大夫梁丘据曾嘲讽晏子一人侍奉三君,既然三位君主并不同心,在治国理政的观念上就必然存在不同。梁丘据认为晏子能做到顺应三君,心思自然也不专一,不可算是忠于国君。晏子对此反驳道:“婴闻之,顺爱不懈,可以使百姓,彊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3]290他并未对自己侍奉多位君主的事实有过多辩解,而将重心置于百姓上,只要顺应国君、爱护百姓,就可以让百姓听从命令,若是残忍暴躁、不忠于国君,那么连一个人都指挥不了。他认为,忠君的目的是能够使百姓顺服,只要最终能达成这个目的,即便一人侍奉百位君主,依然只是一心而已。晏子所理解的“忠君”“一心”并不是对某位君主的绝对忠诚,而是忠于“爱民”的崇高理想,即使效忠的君主不同,只要“爱民”的目的不变,便不可算是不忠。这种思想超脱了狭隘的君臣观念,使对君主的忠从属于对民的忠,晏子已将“民”的地位置于“君”之上,是否爱民也因此成为其区分君主的重要标准。他大致将君主分为贤君、堕君和暴君,面对三种不同的君主,臣子应采取不同态度。“婴闻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逮则退,不以诬持禄;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3]273-274侍奉明君当竭尽全力,侍奉惰君当不显露自身,若是力所不及便应离去。“是以君子不怀暴君之禄,不处乱国之位。”[3]255事从惰君尚可“优游其身”,面对暴君就应该立即离开。晏子反对愚忠,强调臣子自己选择君主的必要性。当景公询问晏子臣子应该用什么来报答君主时,晏子回答:“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3]238 “择君而事”与“忠君”这两个命题看似矛盾,实则均指向晏子重民的思想。
尽管晏子在与他人交谈时对自己的“忠君观”有着明晰的阐释,但当实际面临抉择时,晏子也会陷入怀疑与反思中。当崔杼弑杀庄公后,《左传》记载了晏子的反应:
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4]948
骤然面对君主被弑,他陷入了茫然无措,表示自己既不愿为君而死,也不愿逃亡,更不愿就此还乡。晏子曾评价齐庄公:“君自弃也,弗能久矣!”[4]921他素知庄公自暴自弃,非贤明之君,即便如此,晏子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辅佐庄公,庄公被弑后更发出“将庸何归”的感叹,似乎与其“择君而事”的观念相悖。他的言行并不总是一致,反映出政治家在情感与思想观念相冲突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晏子在庄公被弑后的言行还反映了他的爱国理念。他不赞同臣子与君主同生共死的观念,强调臣子作为独立个体,有其本身独立的工作和任务,其自身命运不必与君主绑定。只有当君主为国而死,臣子才应当随其赴死,若君主为自己私利而死,臣子则无需追随。换句话说,国事与民事皆比国君更为重要。晏子明白地阐述过国与民的关系。当齐景公问晏子国家何时才说得上是安定时,晏子在回答中提及:“上有礼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可谓安矣。”[3]253君王造福百姓,且百姓在其治理下安居乐业,是国家实现安定的重要条件。百姓是国家的主体,君主则是为这二者负责的主要个体。晏子的治国方略和忠君爱国思想均由其“以民为本”的理念出之,民本主义思想实际上是晏子思想理论的基础。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在后世儒学中得到了继承。比晏子稍晚的孟子和荀子都提出过与“以民为本”近似的主张,从重民角度来说,晏子可能是儒学民本思想的先驱。
综上所述,晏子的辞令是解读晏子论说方式、思想理念和人格魅力的关键所在。其辞令雅俗兼善,既富有论辩技巧与艺术气息,还充满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通过对其辞令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晏子对礼制的重视和“中和”的审美理念。此外,根据晏子与君臣间的论辩与自我剖白,我们还可以从中体悟晏子浓厚的民本主义理想,他将“以民为本”的思想与国家结合,并由此劝谏君王施行一系列的惠民政策,提升了“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晏子的这些思想和举措对后世的儒学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A]//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吴则虞撰.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5]赵歧注,孙奭疏.孟子注疏[A]//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7]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A]//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A]//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庞朴.“中庸”平议[J].中国社会科学,1980,(01).
[10]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作者简介:
周诗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陈彦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辞令比较研究”(GD22CZW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