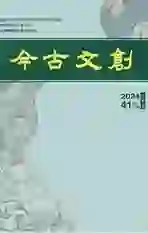萧红文学的现象学研究
2024-11-21高雪洁
【摘要】从现象学视角看待萧红文学的本质,其文本中的女性意识独特性、向死而生的生存哲学,以及独特的小说形式变易特征,均可解释为是一种意向性活动的结果。作家的生活真实与创作真实之间在文本世界里达成彼此渗入的状态。同时作品为现象逗留、真理显现自身提供基础,通过主观重塑时间和空间比例,作品成为大地澄明的场域。
【关键词】现象学方法;意向性;萧红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4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12
“胡塞尔起初的目的在于建立一门哲学的方法。‘哲学方法’——这是指通向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一个过程。” ①现象学追问的真理是关于原本性的,进一步说就是万千世界的经验都依据这个原本性被给予一定的方式。而“所有在‘直觉’中本原地(可以说是在其真实的现实中)展现给我们的东西都可作为自身被给予之物接受下来” ②,每一个经验对象与其被给予方式的原本性之间的独特性都有可以被操作的具体方式。胡塞尔提出了“意识的意向性”功能,即所有的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识具有权能性。人通过映射将对象作为被给予方式加以透视,从而获取对象所指。
海德格尔认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置造事件为大地与世界的争执提供场域。所谓事件即胡塞尔说到的对象多样性现实的一种,也就是在“直觉”中本原地(可以说是在其真实的现实中)展现给我们的东西。具体而言就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呈现。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呈现或凸显为人物、细节,或是场景、情节。而大地即真理,就是一切存在的本源性,世界就是大地即真理的原本性被给予的方式、在事件中获得表达的具体物。
萧红文学世界的独特性是通过特定事件确立的:包括以蘸满颜料点染和泼墨的后花园中的自然生灵,冰封的呼兰河被北风席卷的冰面和弥散在空气中的雪沫,也包括每一段人物与食物纠结的细节,直至被拉长时间、推到眼前的生死挣扎的描绘。萧红文学的语言呈现明显携带着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语调:沉重、低回、坚韧。在时而细腻婉转,时而锋芒锐利的话语中,勾勒、渲染出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的革命风暴和裹挟在风暴里的向死而生的个体或群像。
与这样鲜明的历史语调并存的,还有一种萧红个体生命经验的情绪情感,这种情绪情感来自萧红在世界历史时间上所经验到的、却直触普遍时间中世界生命体验的本源意味,因而萧红文学既是历史性的,同时也是现象学式的。
一、萧红文学作品的现象学表现层
生和死本是生命的两面,生之意义的获得在于对时间的尽力占有,死亡则是占据所有与死者相关、存活下来的人的思想,由此世间亿万生命的意义连贯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些对生存和死亡彼此互为镜像的表达,就是萧红作品的独特事件,此类事件共同置造出萧红文学的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中,生命的大地意义得以澄明。
(一)生存和死亡互为镜像的叙事
萧红文学创作的时间背景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布满生死挑战的时代。民族危亡和抗争爆发出强大的生命意志。这促使萧红的文学创作将重心自觉放在社会历史的本质层面,将生死主题放置在一个浮雕作品凸显的部分。带有鲜明日常书写色彩的萧红文学,清晰地写出了在人与人之间无暇顾及活着的彼此时,人的生存和死亡的意义。
在萧红笔下,活着往往在慢节奏里显露出死亡的逼迫(小团圆媳妇的活),在鲜活的开场里预演着落寞的散场(王阿嫂的命运)。然而同时也有在死亡面前用拼命嘶吼表达出的生命倔强,在静静消亡处(翠姨的死)呐喊出生命的悲壮意义。萧红笔下特定历史时代东北大地上普通人的生存总被死亡窥视着,而同时死亡也被顽强生命的执着挑战着。萧红笔下的生存和死亡叙事具有“存在者之存在成了与对象性相同一的东西”的现象学内涵。
生命的表层是千变万化的个别,这些个别是萧红式的生存之原初性的被给予方式:它们是被饥饿威胁的口腹之欲刺破道德坚守的堡垒,是被本能驱使的繁衍行为击碎的爱情幻象,是被无知和贪婪玩弄的高尚意义,是被死亡随意性考验的生之脆弱和无辜;是向世间冷漠抗争的倔强和顽强,向日常无聊投掷的盲目逃脱……一场场生死搏杀酣畅淋漓地上演,它们都是获得生命对象被给予方式的过程。萧红对生与死镜像关系的塑造,使得作品充满无限的生命张力。
(二)消除性别的女性立场
萧红文学创作中的现象学观照除了尽力为生命以各种形式赋能和赋形,尽显生命的丰富与深刻外,还有某种既明显又隐秘的女性视角。之所以说萧红文学的女性视角体现得明显,在于萧红的人物叙事聚焦于各种女性的生存现实:月英、金枝、王婆、小团圆媳妇、翠姨、芹、王大姐等形象总体上具有特定历史时期东北农村妇女被迫害者的统一特征,但细节处每一个角色都努力破除女性悲剧命运形成的当下现实。萧红作品准确揭示了女性被迫害的命运之源深及传统文化的痼疾:父权、夫权、族权的威压。
值得深思之处在于萧红塑造女性形象时淹没了她身为女性的主观性。消弭作家个人的性别主观,便达成一种作家与世界灵魂触碰的意向性写作。在意向性写作中作家与创作对象同时被释放、获得自由:作家不被意图支配,文学形象亦不受作家支配。此种意向性创作产生的文学形象既可能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也可能是一种隐喻结构 ③。现象学意义上的女性角色绝不满足于引发读者的哀叹和悲悯,破除女性作为弱势存在的社会学意义,她们不仅作为被父权、夫权、族权三座大山压垮的被动符号,她们还与男性以及自然草木虫鸟一样,作为袒露生命未知与蛮荒、人性自觉与麻木的主动符号。对萧红作品女性形象的阐释除了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对女性形象意义赋值外,更为直观与深切的是直逼小团圆媳妇被害过程的惊惧,在冯歪嘴媳妇死去中渐渐察觉的解构意味,以及翠姨死亡里低吟的冷漠、月英死亡前嘶吼出的对救赎的渴望。
(三)小说形式的变易
萧红小说“以舒缓的抒情笔致写自我主观感受,着重写意境、写氛围、写印象、写感受” ④。小说叙事中浓重的散文化、诗化特征是萧红将她现实生存体验升华为文本叙事的极限方式,小说叙事的虚构与散文叙事的真实,以及诗歌语言的蕴藉在同一个文本里完成本源性真实的统一。如同海德格尔眼中凡·高的画作《鞋》,海德格尔在画作《鞋》中看到画中劳动妇女世界及其脚下的大地,这与萧红小说中人物用面包蘸盐充饥折射的生死无期,二者都是现象学层面的艺术真实。
小说《呼兰河传》中写道:
“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的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
而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也写道:
“父亲打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向着窗子,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后花园》中写道:
“六月里,后花园更热闹起来了……那简直是干净得连手都没有上过。”
作为小说人物的祖父是有力量的,是“我”的依靠。散文中祖父是无力的,仅是萧红相依为命的伴儿。小说中的后花园是人物的活动地,散文中的后花园是萧红家园一角,萧红笔下的后花园是如诗般的精神栖息之地。冰封的呼兰河是故事里一座城的坐标,呼兰河在散文中是萧红离家后回望辽阔的乡土,呼兰河亦是萧红在香港弥留之际诗意向往的灵魂归处。
萧红的小说完成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众生图存的语言、心理、行为的虚构想象,那些熟悉的场景也是记刻萧红生活色彩、明暗、线条、轮廓格调别致的版画,这幅版画是萧红的文学文本“置造”的那个统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地”的力量得以显现。
二、萧红文学作品的现象学意义层
“现象就是作为自显现的东西显现自身者。这首先意味着:它作为它自身在此出现,并不是以某种方式在场或处于间接的观察中,而且不是以某种方式重构。‘现象’是某物的对象存在的方式,而且是一种突现的方式:一个来自其自身的对象的当下存在(Präsentsein)。所以,这首先根本没有规定有关事情的内涵(Sachhaltigheit),这里也没有任何规定事情的领域的指示,‘现象’的意思是对象-存在(Gegenstand-sein)的突现方式。” ⑤现象学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的面相不是无差别的平均在时空中的一切行动原封不动地刻录,文学作品通过语词提炼出现实生活中行动的典型突现,而不对其加诸任何规定性内涵的流露,只是为现实生活本身的显现与无差别的现实平常区别开来,由此使现实生活的本相显现。这些在萧红文学作品中可概况为三个方面。
(一)与世界建立的意向性关联
萧红坚持创作要面向全人类的愚昧,这便需要萧红具备一种能力,使她的创作能托举这个形而上的主题。萧红通过现实生存考验获得了这种能力,即与世界建立的意象性关联。萧红意向性思考和表达的客观世界不是纯粹自存的客体,而是萧红的“完全的意象客体” ⑥,在意向性生存实践中萧红自我与世界融合为一个整体,“感知与被感知之物合乎本质地构成一个直接的统一,一个唯一具体的思维的统一” ⑦,这便是其创作最本源的动机和文本意义形成的基础。萧红从何种角度可以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发现了世界和人类,而又在何种层面上认为自己的创作写出的恰恰可以表现这个世界和人类?这中间起到转化作用的是萧红的意向性创作活动。
“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地钻出了土皮。”“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
这段描写中世界本来的存在仍在,带着萧红视角的万物色彩和叙述力度的世界也在。自然世界的质料就是风、草、树的无声生命之力,自然世界的质性就是壳破芽长的暴动,人之于自然亦深藏着同样的血肉之质料,而那如春的暴动就是人之质性的显现。
与自己所在的世界建立一种意向性互动模式,促使萧红创作把生活的现时感留置在了艺术虚构中,萧红的生存体验在文学语言里被反复琢磨并映射其中,作家自我与角色经验向时空投射的情感和意志保持着原本的一致。进而形成文学创作成为作家与生存现实世界意向延展与升华。家庭意象、亲人形象既是作家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更是她笔下被意向性还原了的世界代表。作品中的后花园是作家精神世界的镜像反映,作家在现实生存与文学世界之间的调和过程充斥徘徊、挑战甚至妥协。作品语言显现作家用思想抵达痛苦当下和幸福目标边界的方式,使文学创作获得真正面向全人类愚昧的本质力量。
(二)让大地澄明的文学世界
按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解释,大地是存在自明的独有,是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浑然整体的寂静所在,是最直接在眼前的也是隐约不在眼前的部分共同组成的向外释放的信号。在追赶大地的脚下是无数自我和他者共同面对的众生面孔,是时空中每个生命喘息的声音,是无形的灵魂在万千双眼中闪烁的叩问波光。大地处于遮蔽的状态,文学世界通过事件使大地澄明。文学事件是由文学语言建构起来的一切文本有机组件,包括故事情节、典型人物、场景环境,甚至是文学语言本身,而文学事件构置的独特性就是作家文本风格的独特性。
萧红的文学世界多以行动单线、语言简约的人物对比、大量密集的环境和场景描绘构建起来,环境和场景的变数巨大而不可控,凸显生命存在的艰难,个人生存于这个背景中的主观能动性被弱化,舍弃个人生命的精神和理性力量的驱动,消弭叙述者对人物的判定,为生命大地的本源呈现去除预设的羁绊。与设法让生命本质涌现和敞开相比,萧红更能从艺术作品本源的隐退一维即大地一维塑造她的文学世界。小说《呼兰河传》众生浮世对生命之大地本源意义的呈现靠的是将众生编织在呼兰河岸的广袤土地上。面对自然海德格尔曾提出“回退步”的思想,“回退步在方始想要到达的东西面前回退,赢得同它的距离。对距离赢得是一种间离(Ent-Fernung),是对有待思想的东西之自行切近的开放” ⑧。
呼兰河用自己的广博和原始凝神注目这片土地上每一个被叙述者,以此完成对这座城的生命表达:生命大地本源的秘密被人物木然执拗地施暴宣告着,像生命广阔海面上汹涌的浪波,使未来的不可知性陡增。死去者像大地的长嘶,留存者失去了施虐对象,余下的只有无尽荒凉,二者共同唤起了生命自身的悲悯和等待救赎。
注释:
①(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②(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③彭依伊:《论萧红小说的“女体书写”》,《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67-75页。
④沈巧琼:《从〈呼兰河传〉看萧红小说的散文化、诗化特征》,《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年第2期,第183-186页。
⑤(德)海德格尔著,何卫平译:《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84页。
⑥(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⑦(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⑧倪梁康等:《现象学与实践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参考文献:
[1](德)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唐小林.论萧红小说中的日常经验书写——从《旷野的呼喊》《呼兰河传》到《马伯乐》[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9,(01).
[3]沈巧琼.从《呼兰河传》看萧红小说的散文化、诗化特征[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02).
[4](日)平石淑子.萧红传[M].崔莉,梁艳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5](德)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M].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作者简介:
高雪洁,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审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