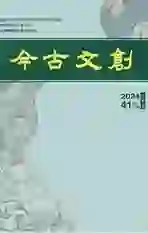论黛玉别号 “ 潇湘妃子 ” 的深层意蕴
2024-11-21唐彩妮
【摘要】林黛玉在《红楼梦》中有“潇湘妃子”的别号。此号除了与她居住的地方叫潇湘馆,以及和她本人爱哭的性格与“湘妃涕竹”神话有关外,其实还具备着更深层的意蕴。比如“还泪”和“涕竹”之间的联系,“竹”这一意象和黛玉的关系,还有“湘妃”本为两人,用在黛玉身上,是否影射在黛玉之下,还有另一位“湘妃”与之密不可分。
【关键词】林黛玉;潇湘妃子;竹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3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11
一、林黛玉与竹
“湘妃”与“湘妃竹”这两个意象从古至今都是密切相连的,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甚至可以互通。提及“湘妃”,首先想到的就是她们泪洒斑竹的事迹,想到斑驳的湘竹。因而林黛玉被冠以“潇湘妃子”的称号,其内涵不仅囊括了“湘妃”事迹,与“湘妃竹”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竹”的意蕴也息息相关。
(一)湘妃涕竹和绛珠还泪
“湘妃涕竹”来源于娥皇女英的神话故事。晋张华《博物志》中记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在《红楼梦》中,这一神话被曹公巧妙化用,湘妃涕竹不仅与黛玉爱哭的性格相勾连,更与黛玉的前世“绛珠仙草”还泪一说所联结。
绛珠仙草因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在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下凡造历幻缘时一同前去欲偿还恩情,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所以作为绛珠转世的林黛玉,就被赋予了爱哭的特点,尤其是在面对贾宝玉或是与贾宝玉有关的事情时,更是频频泣泪。而关于黛玉还泪和湘妃涕竹神话之间的联系,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第三十四回。宝玉在遭贾政笞打之后担心黛玉伤心,托晴雯为黛玉送了两张帕子,黛玉拿到帕子后体贴出了宝玉的心意,往上题诗三首,其三便是“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在湘妃涕竹的神话中,我们能看到千年之后从书中走出的黛玉身上同样为情执着的特质,同样为情而垂泪的身影,那么,这一故事又是如何与“还泪”一说相联系的呢?根据欧丽娟老师的观点,她认为林黛玉的还泪以及最后泪尽而亡的结局,并非直接来源于娥皇女英的神话,而是经由李白改造之后的《远别离》才最终将这一意蕴得以延展和丰富。原神话中只有湘妃涕泪,以及涕泪之后所形成的湘妃竹情节,却并没有关于“泪尽而亡”一说的内涵,但在李白的诗歌中,清楚地写道:“苍梧山h0yQEurJQdDUbRO7flJMMQ==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此处的“苍梧山崩”和“湘水绝”,从表面上看,是作为外在自然景观的山与水的消亡,深推敲下去,这种消亡,又可以象征一切形体的消亡,包含天地、个人,甚至是存在于世间的所有事物,而当个人的形体真正消亡时,眼泪才会随之泯灭,情才会由之飞散,这样,便使得形体消亡与泪尽之间,搭建出了一条有机的桥梁,即“形体”与“眼泪”共生共灭。而这一内涵,在《红楼梦》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书中第四十九回,黛玉对宝玉说到自己最近的情况:“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从书中种种线索以及脂砚斋的批语来看,可以推断林黛玉应该逝于钗玉成亲、贾府真正没落之前,不管是一百零八回之说还是一百二十回之说,此情节在书中都处于近一半的位置。而这时的黛玉眼泪已经是一年比一年少,且并不多了,再根据绛珠仙草要将自己一生的眼泪还给神瑛侍者的说法,可见此时黛玉正在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死亡,而当她的眼泪真正流尽,灌溉之恩偿还尽之日,就是她真正逝去之时。
(二)竹绿:黛玉生命的色彩
周汝昌先生在他的《红楼艺术》中说:“盖红者,实乃整部《红楼》的一个焦点。”在《红楼梦》全书中可以找到不少关于“红”的身影。如下雪时众人穿的斗篷是红色,贾母簪在发间的菊花是红色,宝玉、凤姐爱穿的衣服颜色是红色……但在这一片红色之中,黛玉却以她“绿色”的身姿伫立于其中。黛玉初进贾府时,与邢夫人坐的是“翠幄青紬车”,贾母将她安置的地方叫做“碧纱橱”,甚至就连她的名字,“林”字和“黛”字,本义也关合绿色和青色。于是,这样一位与“绿”和“青”息息相关的女子,在搬入大观园时,自然而然就选择了与自己生命相洽的一年常青的潇湘馆。
《红楼梦》中对潇湘馆的描写着墨凡多,但每次提及时都无不在强调它的清绿。贾政与众人初次游览潇湘馆时,写到这里“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宝玉为之题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当贾宝玉顺路走到潇湘馆时,入目是“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看到“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黛玉自己在潇湘馆行卧起居时,“只见满底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窗外竹影映入纱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翠竹深深,丛丛掩映,寂寂无声,因而鼎中飘出的轻烟才会是绿色,手指触碰到棋子才会觉得分外幽凉,也只有这般幽深寂静,“苔痕上阶绿,竹色入帘青”的苍翠深远,才不负黛玉平昔临窗读书的悠闲宁静,堪配她不流于俗世的满腹才情。正如写出“淡极始知花更艳”的宝钗,象征冷静与自持的白色是她性格的本质颜色,同样,绿色也是黛玉的生命色彩。它象征着生命力,正如黛玉会在死气沉沉的封建教条下常常流露出自己鲜活的叛逆;它代表着宁静,恰似曹雪芹描写黛玉时说她“娴静时如姣花照水”,在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纷攘攘的尘世之中,黛玉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和心境。
(三)竹德:黛玉高雅的品质
《诗经·淇奥》写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中借绿竹的挺拔、青翠来歌颂君子的高风亮节,由此开创了以竹喻人的先河,从此,借“竹”来赞颂文人雅士道德品质的传统延续至今。
妙玉住在玄墓蟠香寺时,山上有漫山遍野的梅花,居于大观园栊翠庵中时,庵中亦有灿如胭脂的红梅。曹公深知,读者深知,只有孤削如笔,清瘦舒朗的梅花梅枝,才符合妙玉清高孤傲、洒落洁净的品性。同样,只有如黛玉那般的清华澹泊、傲骨凌霜,才配得上潇湘馆满院的萧疏。铮铮翠竹,是黛玉至坚至真的写照。面对王夫人的陪房周瑞送宫花的做法,她可以直白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当着薛姨妈这位长辈的面,也完全可以借与雪雁说话来暗讽宝玉;当刘姥姥游玩大观园,之后再连吃喝带打包带走一车东西后,她仍可以谈笑自若戏谑一句“母蝗虫”。
李贽在他的《童心说》里说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黛玉的情、黛玉的性,全都源于她的本真,而这份本真,便是出自她的一颗“真心”,这种真心,让她为人做事皆能保持坦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黛玉是完全符合李贽笔下具有赤子之心、完整人格的人。她可以活得就像一株竹子,不需要像藤蔓那样依石攀援才能勃发,也不必像柳絮那样凭风借力才可以直上青云,黛玉只需要做自己,傲然挺立,坚贞不移,纵使雪压枝头,霜欺枝叶,也自有自己的不弯和苍翠。
二、名虽一个,暗合两人
为黛玉起“潇湘妃子”的别号,其依据除了来自她本身所居的潇湘馆,以及她与湘妃、湘竹共同的特质外,还需值得深思的一点便是:湘妃原指娥皇女英二人,现将“潇湘妃子”一称置于黛玉一人身上,是否影射在这个称号下,除了黛玉还另有一位“湘妃” ?并且二人关系是否如同书中的甄玉与贾玉一样具有显隐之分,或者是存在某种相似或对峙的关系?
根据《红楼梦》文本、脂砚斋批语等线索脉络,再结合诸位红学家的观点看法,可大致推断出在黛玉背后的另一位“潇湘妃子”或许应为薛宝钗、史湘云、妙玉三者中之一。
(一)宝钗之说
在《红楼梦》“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一卷中,开篇脂批便提到:“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并且在第二十二回之中,写到贾母出资为宝钗庆生,批语对曹公为何不写贾母为自己所溺爱之黛玉作生辰,却反而特意去写宝钗这一奇怪的现象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此书通部皆用此法……不写而是写也”“将薛、林做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家。”《红楼梦》的残缺使得读者无缘看到黛玉逝后宝钗是何模样,因此也就无法探究脂批所说的钗玉实乃一人是否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黛玉和宝钗的关系,绝对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看到的对峙那么简单。
先从钗黛之间的关系来看,《红楼梦》中曾多次将林黛玉与薛宝钗并举,使得二人呈现出双水分流、两峰对峙之势。《枉凝眉》中写道:“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古往今来的通俗观点都是:“阆苑仙葩”是指黛玉这株绛珠仙草,“美玉无瑕”则是贾宝玉这块玉石,所以这支曲子实际上是宝黛二人的爱情悲歌,其实并不然。与其说《枉凝眉》是在怅恨宝黛的情深缘浅,不如说是在嗟叹钗黛的不幸命运。书中开卷第一回提到神瑛侍者居住的地方为“赤瑕宫”,瑕乃玉有病也,是瑕疵之义,因此,作为神瑛侍者转世的宝玉实际上是“瑕疵品”,是有瑕之玉。而“阆苑仙葩”中的“葩”,本义是指花之丽采美盛,而非在说草,书中又提及过宝钗和黛玉二人一人为姣花,一人为纤柳,所以,如果我们把“美玉无瑕”看作是在形容黛玉,而“阆苑仙葩”是在指射宝钗,那么解释会更合理一点。另外,脂批曾评“黛玉为十二钗之冠”,而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中,宝钗抽到的花签又是“艳冠群芳”,且后来黛玉抽到芙蓉花签后,签上还注云:“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在《红楼梦》里,“钗”指代女子,“群芳”同样是指女子,二人同为冠首,故其地位齐等。
再从钗黛与宝玉的关系来看。第五回贾宝玉在太虚幻境时曾与警幻仙姑之妹兼美行以云雨之事,对于兼美的描写,书中说道:“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脂批亦评“兼美”乃是“盖指薛林而言也”。又有第六十二回描写宝玉生日的情景:“宝玉正欲走时,只见袭人走来,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洋漆茶盘,里面可式放着两钟新茶……说着自拿了一钟。”后来另一钟则被同在一处的宝钗和黛玉分饮完了。在婚俗之中,“吃茶”,意味着许婚,指旧时女子受聘于男家,凤姐就曾对黛玉开过玩笑:“你都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而关于“两杯”,则暗合“合卺”。在《礼记·昏义》中有:“以一瓠分为两瓢,谓之卺。壻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酳,故云‘合卺而酳’。”这里虽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瓠两瓢,但一盘两茶,各拿一杯,同样也呈现出了“合卺”的意味。两杯之中,一杯为宝玉所执,另一杯为钗黛二人共饮,在加之《红楼梦》通篇所呈现出来的“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纷争,不难看出宝黛钗三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明确的婚恋纠葛,甚至可以说是如同娥皇女英二女那样“共嫁一夫”的关系。
(二)湘云之说
如果说宝钗是因为和黛玉之间存在着似对峙又似统一的关系,且与宝玉都有着不可割裂的姻缘纠葛而被认为是另一位“湘妃”的话,那么史湘云则是缘于她和“湘”本身的不解之缘而被我们推断为“潇湘妃子”背后的另一位“湘妃”。
“湘”,本义是指湘水、湘江。湘云的判词中有:“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关于她的曲子《乐中悲》中也写到“终究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无论是湘云的名字,还是她的判词、曲子,我们都可以知道,“湘云”的“湘”字,暗合的是湘江之义,并且“水涸湘江”一句,更是直接化用了娥皇女英的典故。《列女传》中开篇记载道:“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娥皇女英在舜死后最终死于湘江,而湘云的结局,也应是在“云散高唐”,也就是夫妻离散、恩情断绝之后,孤苦漂泊在湘江附近。
同时,黛玉和湘云之间还存在着相似的处境。黛玉父母相继而亡,于是在贾府之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湘云也同样如此。“襁褓之间父母违”,湘云还在襁褓之中时,便父母双亡,然后由叔叔婶婶养育长大,虽然是出身于四大家族中的史家,但却过得并不如意。同样的“寄人篱下”,同样都有点“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意味,而湘云也几次对黛玉说起“我也和你一样”。
湘黛两人,都与湘江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都有着孤苦无依的身世处境,作为与黛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湘云,的确可以说她是黛玉身旁的另一位湘妃。
(三)妙玉之说
妙玉与黛玉,二人皆以“玉”为名,似乎从名字上看来就想让人猜测二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事实上的确如此。
妙玉第一次出现在书中是林之孝家的向王夫人回禀她的身世:“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从林之孝家的描述来看,其实不难看出与黛玉家世相仿的影子。黛玉祖籍是姑苏,而姑苏本就是苏州的别称;林如海乃前科探花,林家祖上曾袭过列侯,到了林如海又袭了一代,书中说林家是“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黛玉身有不足之症,从会吃饮食起便开始吃药,却皆不见效,三岁时赖头和尚提出要化她出家,因她父母固是不从才作罢。她二人都是一样的来自苏州,家中皆是读书仕宦之家,又一样的自小多病,不同的是,黛玉并未因为多病而遁入空门。但无论从出身,还是境遇来看,黛玉和妙玉以前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黛玉和妙玉都生性好洁,妙玉之爱洁甚至更胜一筹,她们又都富有才情。诗社写诗联诗,黛玉屡次夺魁,其《葬花吟》《桃花诗》,都在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妙玉为湘黛二人的联诗续尾,黛玉称赞她为“诗仙”,《世难容》一曲中也说妙玉“才华阜比仙”。种种类似,我们不妨大胆地说,妙玉便是遁入空门之后的黛玉,而黛玉,便是留在红尘之中的妙玉。
综上所说,无论是宝钗也好,湘云也罢,又或者是妙玉,我们推断她们是黛玉“潇湘妃子”别号之后的另一位“湘妃”都各有依据。而为黛玉取“潇湘妃子”一号,或许也并不是仅仅来源于她所居住的地方叫潇湘馆,以及和她性格多愁善感、爱哭有关。与“湘妃”密切联系的泪水、翠竹等意象,甚至湘妃有二,为何却用在黛玉一人身上这一问题,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探究“潇湘妃子”这个称号背后所含意蕴的内容。
参考文献:
[1]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周宝东.《红楼梦》“二人共用一杯”文化意蕴考释[J].明清小说研究,2022,(04).
[3]魏颖.《红楼梦》与湘楚文化——从“潇湘妃子”到“芙蓉花神”[J].美与时代(下),2017,(02).
[4]王晓明.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潇湘意象群之建构与拓展[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
[5]何丹.林黛玉别号“潇湘妃子”意蕴分析[J].才智, 2014,(33).
[6]刘金荣.林黛玉与《诗经·淇奥》[J].红楼梦学刊, 2013,(05).
[7]喻言.论林黛玉形象外绿内红的艺术张力[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8]王晓洁.林黛玉与潇湘馆研究综述[J].红楼梦学刊,2010,(01).
[9]刘颖.浅谈“潇湘馆”环境描写与林黛玉性格的统一融合[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09).
[10]章惠垠.神女神话与林黛玉——黛玉原型初探[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1).
[11]姜葆夫,黎音.略谈“潇湘馆”的环境描写[J].红楼梦学刊,198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