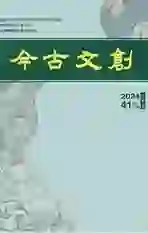爱伦 · 坡哥特小说中的物叙事研究
2024-11-21冯雅兰
【摘要】在爱伦·坡的哥特小说研究中,物因其阴森、诡异等特点通常被认为是恐怖、惊悚的源头,而在思辨实在论的视域下,这些物制造恐怖的手段并非仅仅是它们的外在表象,深层缘由需要向内探求,抵达物本身。爱伦·坡将物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主体,反对人类将其视为客体他者并沦为空洞的文化符号或只作为一种渲染恐怖氛围的工具或手段,这种本体性力量颠覆了人的理性大厦,消解了人类的主体性神话,颠覆了人类本体论上的优越感,通过呈现某些未知的神秘力量来彰显物的施事能力,并且达到极致的恐怖效果。通过彰显物的本体性力量和恐怖效果,人可以重新反观自身,以更加谦虚、包容、富有想象力的姿态和视野重新认识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爱伦·坡;物叙事;思辨实在论;本体性;恐怖效果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3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09
一、物叙事及其在爱伦·坡小说中的体现
自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以来,认知世界的方式从主体去适应客体变成了客体依赖于主体的经验而存在,主客体之间的秩序颠倒了,物开始在主体的参照下书写自己的命运。同时,主客体二者之间的对立也就越发明显。到了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这里,如果主体的意向性未能捕捉到客体,那么外物就是一片黑暗和混沌。这是人对世界认知模式的巨大改变,并且随着现代性的加剧,主体的地位越发重要,优越性也越发显著,客体完全沦为被把握和被凝视的对象,被赋予意义、内涵、作用等。
思辨实在主义(Speculative Realism)则是要颠覆这样一种主客秩序。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1967—)
将自康德以来的总是将物和人联系在一起并在人的视角下对物来进行观照的哲学称为“关系主义”(Correlationism),
这种关系主义哲学强调物与人——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陷阱要么否认物自体的存在,要么认为物自体存在于人的理性之外,无法被认知,人在认知物自体的过程中起到的只是中介作用。而思辨实在论恰恰要提出反对意见:它相信物自体的存在,因此是“实在的”,它相信通过想象(而非理性)可以抵达物自体,因此是“思辨的”。[1]
在以人文主义诉求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学传统中,物很长时间以来被当作他者、客体,承载了主体的意志和情感,成了主体观照自身而凝视的对象,文学研究中的物转向则要求重新开始寻找物本身的非附属于人的意义与价值,物在叙事中的作用被重新解读。在后人文主义的整体思潮下,国内对物叙事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三类:1.关注物的社会政治含义;2.关注物与人是如何交互并推进叙事的;3.关注物自身的叙事模式。[1]尹晓霞、唐伟胜在《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中认为物叙事承担三种功能:1.作为文化符号,映射或影响人类文化;2.作为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作用于人物的行动,并推动叙事进程;3.作为本体存在,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的表征,显示“本体的物性”。[2]在具体的小说文本中,物所承担的话语作用或叙事功能往往是融合式的,对物自体的关注是为了以一种更谦逊、更富有想象力与包容性的思想和精神去认识主体以外的世界,甚至“突破人类的理性极限”[1],因此,物的本体性存在和价值被凸显,人通过这种谦逊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
在爱伦·坡(A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哥特小说中,物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的本体性存在,不仅仅是用以渲染恐怖氛围的手段,而且作为一种独立于人和人之意志的存在,其本身就具有一种消极、恐怖或邪恶的力量,与主体——人进行对抗,挑战着人的理性和思想,故而产生惊人的恐怖效果。因此,在爱伦·坡的哥特小说中,对物的描写不仅从外部环境渲染了恐怖阴森的氛围,也从更为深刻的精神层面解构了理性带给人的安全感,从而实现了双重的恐怖效果。
比如,在唐伟胜的《爱伦·坡的“物”叙事:重读〈厄舍府的倒塌〉》[3]中,作者从小说中对物件的描写出发,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厄舍府里的物件都具有一种消极的力量,与高贵的、理性的罗德里克(Roderick Usher)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终于在长期的对峙中战胜了罗德里克的理性,使其患上精神病且最终走向死亡,并且摧毁了整个代表“思想的圣殿”的厄舍府。作为主体的人正是通过理性认识世界,将世界作为客体进行观察和把握,而物件在《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中拥有自己独立的力量,它不作为依附于人类的客体而存在,在物与人的关联中,物不再属于被动的一方,反而积极地挑战人的理性殿堂,使得人类在这种存在危机下被迫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
二、《红死病的假面具》中的物叙事
《红死病的假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城堡内和城堡外,空间上的二分化使得两种物占据了各自的营地:城堡内的物承载了人们关于和平健康的美好愿景,城堡外则是红死病的主场。城堡内的物虽为主体(亲王)之创造,但背叛了主体的意志,衍发出某种邪恶、恐怖的力量,将造物者主体置于间断性的恐惧感之中(城堡里的钟声)。而城堡外的物(红死病)则是主体生命意志的威胁者。
人将自己囚禁于自己造就的物的内部以获取安全,然而这巨大的城堡以自身的主体性之创造对人所形成的反叛,处处彰显着死亡与恐怖的气息,与外部空间的红死病“合谋”将人这个主体置于巨大的生命和精神危机之下。
(一)内部空间:城堡的颠覆性力量
“城堡”是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物”,开篇爱伦·坡就写道,这是“一座非常偏远的城堡式宅院”“宅院四周环绕着一道坚固的高墙。大门全用钢铁铸就。亲王的追随者们带来了熔炉和巨锤,进宅院之后便熔死了所有门闩”[4]46。城堡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场域,“所有的快乐和平安都在墙内。墙外则是红死病的天下”。墙的隔断,使得城堡处于一种孤立无援、封闭幽森的空间内,“那是一座宽敞而宏伟的建筑,是亲王那与众不同但令人敬畏的情趣之创造”[4]46。显然,城堡的物性应是来自亲王的授予,但是该物性实际上向主体呈现的效果却是相反的。
在城堡内的第七个房间中,四面墙壁、地面被黑丝绒帷幔和黑丝绒地毯完全包裹住,本应与饰物的色调一致的窗户却是“殷殷猩红,红得好像浓浓的鲜血”[4]47。鲜血本应是生命的基石,然而在第七个房间的玻璃所影射出来的“殷殷猩红”,却如死亡般恐怖,物以其与文化表征之间的错位来揭示自身的真相以及物与人的真实关系,以反叛自身创造者的方式对强加在自身的文化赋意进行反拨,城堡以自身的力量避免成为空洞而无力的文化符号。与前六个房间都不一样的是,这个黑色房间从色彩到配置都很特别,火光从外部透过玻璃照亮其他房间,全都产生了绚丽斑斓、光怪陆离的效果,然而黑色房间中的效果却“可怕到了极点,凡进入该房间的人无不吓得魂飞魄散,以致宅院中几乎无人有足够的胆量进入那个房间”[4]47-48,这个细节就证明了物不仅可以被人创造出来以满足实用、审美等功能,还具有削弱他者力量的能力。
被亲王创造的城堡房间显然背叛了它的缔造者,它以恐怖的面目恐吓众人,以此展示自身的施事能力和本体性。
在黑色房间中,还有一座巨大的黑色时钟,这个巨大的黑钟虽在物理空间上占据优势,但是其色彩和靠墙的位置使其仍被人所忽略,因此只有通过声音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恐慌。“人们能对这乌檀木时钟视而不见,却没法对洪亮古怪的钟声置若罔闻。”[5]每一个小时就会响起的钟声,使被忽视之物变成一个幽灵,比物本身的物理尺寸放大成千上百倍,充斥着整个城堡的空间,不容人的拒绝和无视。
爱伦·坡在这里对钟声的描写很细致,他先写“钟摆伴随着一种沉闷、凝重而单调的声音左右摆动”,紧接着又写“从巨钟的黄铜壁腔内便发出一种清脆、响亮、悠扬、悦耳但其音质音调又非常古怪的声音”[4]48。钟表和时间都是人依托理性科学的认知所构建出来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然而这种理性、精确的机械造物所发出来的声音却是“沉闷、凝重而单调”的,这或许是爱伦·坡对科学理性的一种质疑。而钟声之所以“古怪”,则全在于人的感官体验了。“清脆、响亮、悠扬、悦耳”与“古怪”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容放在一起修饰钟声,物本身发出的声音和人感受到的声音出现了差别,实际上这是人和物的两种感官体验的错位交互,是本体性之间的冲突。人们对这种非常规的体验感到仓皇失措、面色发白,然而钟声一过,人们依旧在城堡里自欺欺人地间歇性逃避,等到余声寂止,人们才恢复轻松愉悦的交谈。
事实上,人的恐惧感其实源自物对人的主体性底线的试探,一种对自身所创造之物的莫名的畏惧感,无法用科学进行合理的解释。理性不可触碰、不可阐释的场域便是人的主体性无法占领之地,“他们还彼此低声诅咒发誓,下次钟声响起时绝不会再这样忘情失态;可在六十分钟之后……黑色巨钟又一次鸣响,于是又出现和前次一样的仓皇失措,神经紧张和沉思冥想”[4]48。人们的恐惧感如阴影一般挥之不去,循环往复,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是人的理性被击溃的边界,物以非理性的事件挑战着人的理性世界。这是一种间断性的刺激,每当人们快要忘乎所以完全陷入狂欢的愉悦中时,恐怖就要出现打断这种激情,定时挑拨人们的神经,这就是物对自我本体性的宣扬和炫耀。而一次比一次加长的钟声更是宣布了人的无力,无法用科学理性进行解释的无力感,只会不断加深这种恐怖效果,因为人们永远不甘屈服于未知,且不愿接受主体对世界的认知是一种徒劳或幻想的可能。
(二)外部空间:红死病的入侵
在“墙外的瘟疫最猖獗的时候”,普洛斯佩罗亲王(the Prince Prospero)带领着众人狂欢,“举行了一场异常豪华的假面舞会”[4]47。这里有两个细节体现了物的力量:第一,“最猖獗”“异常豪华”,物的狂欢与人的狂欢形成相互观照,彼此在各自主宰的世界达到高潮时刻,同时为自己的主体性欢呼庆祝。第二,人们举行的假面舞会中,人们扮成各种怪异样式,理性世界以狂欢和模仿的形式试图将非理性、未知的世界涵盖进自身,以此抵消物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殊不知红死病已经悄悄潜入了城堡内部。
理性带来的极度自信使得主体低估了物的力量。在《红死病的假面具》中,红死病伪装成的那个物,不仅不受到亲王(即主体)的控制,反而以主体未知的方式出现在它本应被主体所驱逐的场域,因此带来混乱和恐怖。主体的理性始终相信主体以外的客体世界是缺乏能动性和施事能力的,因此红死病在被揭开真面目之前一直是以“陌生人”的角色存在的,它被认为“太过分了,居然装扮成红死病之象征”[4]50。也就是说,狂欢者们认为面具背后存在的真实主体仍然是人,而他足以乱真的面具和装束细节使得人们大为不满。因为红死病是被明确排除在城堡外部的物,而且是被视为客体的他者之物,因而这种装扮刺激着主体的理性神经,即使是假扮的也被视为一种不祥。后来人们对他的情感从不满、惊讶逐渐变为惊恐、畏惧和厌恶,由于过分逼真,人们已然感受到了来自物本身的威胁。
在小说中,普洛斯佩罗亲王是最强大的理性主体的象征,红死病的出现不仅挑战了他的权威,同时也让他意识到眼前的物不会臣服于自己。有关亲王对红死病伪装的入侵者的反应,爱伦·坡是这样描写的:亲王“一阵猛烈地颤抖,说不出是因为恐惧还是厌恶”“当普洛斯佩罗亲王看见这个幽灵般的身影……他显然大为震惊。开始只见他一阵猛烈地颤抖,说不出是因为恐惧还是厌恶;但随之就见他气得满脸通红”[4]50。一种被冒犯和无视后的尊严扫地,亲王代表的权威走向跌落。
显然,物已然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成了“施事者”,“‘物’不仅可以促进或阻碍人类计划,而且还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天性”[2]。红死病不仅中断了舞会的进行,还“如入无人之境”[4]52地从亲王身边走过,走过每个房间,最终与第七个房间融为一体。至此,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实现了物与物的融合,实现了物对人的反向统治。
在《红死病的假面具》中,物几乎始终是以有形的、可知的样态呈现,直到结尾,红死病在面具被揭开后才展现出其本身的虚无形态,体现出物的“引退性”(Withdrawn)特征。这个概念是思辨实在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1968—)提出的,哈曼认为,物所具有的独立于人类的实在性是无限的,而且是“引退的”,因此物不可能完整被把握或再现。[3]也就是说,物所能被人看见、观察和把握的外显特点或给主体产生的感觉与其实在自身之间始终存在着修辞性的巨大鸿沟,导致人类只能从服装或语言等修饰层面对物进行一种捕捉,但当人类想进一步揭开表征的面纱从而触碰到物的本质时,只能发现“死死抓住的那块裹尸布和僵尸般的面具中没有任何有形的实体”“每一个人死后都保持着他们倒下时的绝望姿势”[4]52。正是这种必然存在的距离宣告了人的理性无法跨越之地,因此带来极致的恐怖效果。
表面上来看,人的理性似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假面具的揭露,人们才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主体性谎言中,于是迅速步入死亡。“其实死神一直都在人们身边某个角落,只不过当十二点到来,生命的时间慢慢耗尽之时,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达到极值之刻,对于象征死亡的红死魔,人们才有了最清楚的察觉和认知。”[5]是主体忽视物的力量的自大,最终导致了恐怖和自身的死亡。
三、结语
在亲王创造的城堡内部空间中,人自以为安全可靠,物却以自身的本体性力量颠覆了人的控制,刺激人的感官,强化恐怖效果,而作为城外世界之主宰的红死病通过对城堡这样一个封闭空间的神秘入侵极大地彰显着自身的施事能力,冲击着人的理性神经,最终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二者共谋从内外两个空间包围人类世界,揭示了理性神话的局限性,扯开了巨大的主体性谎言的面纱,强调物的本体性价值和意义。不过,在爱伦·坡以《红死病的假面具》为代表的众多小说中,物的本体性存在始终表现出惊悚、恐怖的效果,这正体现出人类以往对物的本体性认知的缺失。对物自身的关注是一种更为谦虚、更富有想象力和包容性的姿态,从爱伦·坡的哥特小说中人类可以重新认识物曾被人忽视的神秘力量,并且重新对自身的主体性神话进行反思。
参考文献:
[1]唐伟胜.思辨实在论与本体叙事学建构[J].学术论坛,2017,40(02):28-33.
[2]尹晓霞,唐伟胜.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J].山东外语教学,2019,40(02):76-84.
[3]唐伟胜.爱伦·坡的“物”叙事:重读《厄舍府的倒塌》[J].外国语文,2017,33(03):6-11.
[4](美)埃德加·爱伦·坡.乌鸦[M].曹明伦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5]陈谊,田轲宇.场景与意象:“死亡”效果的呈现方式——读《红死病的假面舞会》[J].名作欣赏,2011,(18): 27-28+31.
作者简介:
冯雅兰,四川大学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