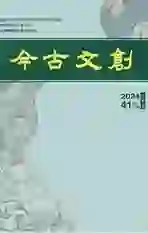《榆树下的欲望》中的创伤与复原
2024-11-21李秋卉
【摘要】尤金·奥尼尔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是美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代表作《榆树下的欲望》被誉为“美国第一部伟大的悲剧”,同时因为奥尼尔在创作时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悲剧性经历融入了剧本中,《榆树下的欲望》也是一部无意识自传作品。本文通过创伤理论视角,结合奥尼尔生活的时代与个人经历,分析剧中主要人物的创伤与救赎,揭示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和畸形发展必然会带来难以磨灭的创伤,导致伦理的丧失、人性的毁灭,而爱与联结可以使人类获得拯救。
【关键词】尤金·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创伤理论;创伤复原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2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07
一、引言
创伤(trauma)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指外部原因造成的身体创伤,后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被赋予更多的内涵。19世纪德国神经学家阿尔贝特·尤林博格首次从心理学角度描述负面生活事件对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造成的影响,由此创伤概念产生了一次由身体创伤向心理创伤的转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先在其著作《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中运用精神分析法中将创伤概念引入心理学,指出深入灵魂的惊恐,即心理创伤,是真正的致病因素,开创创伤研究理论化的先河。此后很多学者都对心理创伤概念进行了界定,大致可以总结为极度强烈的冲击对人类心理所造成的影响深远的伤害。19世纪8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将创伤描述为经历或目睹涉及死亡、严重破坏和威胁,并且使人感到恐惧、厌恶或无助的事件,并将“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纳入诊断手册,从此心理创伤在诊断规范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解释。精神创伤从受创主体来说可以分为集体创伤和个人创伤,个人创伤关注的是个人所经历的打击、痛苦,而集体创伤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解释心理创伤为弥漫在一个社会群体间的,破坏人们之间联系纽带的创伤现象,集体创伤和个人创伤相互联系、影响与转化。
《榆树下的欲望》创作于美国爵士时代,尤金·奥尼尔意识到当时沉湎于物质社会的精神世界的空虚,试图通过老卡博特一家的故事警醒当时的美国人民,并且同时在《榆树下的欲望》中还可以发现奥尼尔本人原生家庭亲情创伤的印记。在剧中,老卡博特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压榨与奴役,给埃本、爱碧等造成了一种集体创伤,同时埃本与爱碧在集体创伤中引发的畸形欲望和个人创伤,使得埃本和爱碧一步步走向弑婴的悲剧。
二、创伤极其根源
(一)膨胀欲望造成集体创伤
《榆树下的欲望》出版于1924年,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但是这些并没有将人们带到美国梦的天堂。相反,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发展默默地摧毁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信仰,物质欲望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却无法填补人们精神的空虚。这一时期的美国民众越来越迷恋金钱和权力,变得贪婪和虚伪。在这个纸醉金迷的时代,最初注重精神追求,强调人的价值和劳动的重要性的美国梦产生了异化,获得巨大的财富与权力成为美国人民的强烈追求,美国也逐渐为物质主义所驱动,美国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热情善良的品德逐渐变为自私贪婪,畸形膨胀的欲望,人们对权力金钱的痴迷逐渐毁灭了人的本性之美和精神世界,同时这也导致人们逐渐失去了与彼此之间的联系纽带和集体感,造成了一种集体创伤。卡博特一家的故事,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缩影,奥尼尔借此对沉湎于物质主义的美国社会提出了质疑,警醒人们畸形发展的欲望是对美国梦的背离,并且最终会给美国人民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
老卡博特是本剧的主角之一,最鲜明的人物特点便是他永不满足的欲望。戏剧伊始,便可以从卡博特三兄弟的对话中对老卡博特的人物形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老卡博特作为一家之主,在新英格兰拥有一个农场,但是这并不能使他满足,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和金钱,他的妻子和儿子们被迫在农场上像奴隶一般劳作,他的前两任妻子因不堪劳作重负都被折磨致死,而关于农场的所有权,老卡博特坚持强调,为了让其他人不能占领农场,他甚至会放火烧农场,当他考虑谁可以继承他的农场时,老卡博特则回答道:“我老婆不是我本人。儿子才是我,我的血肉,我的。我的东西该留给我的后代,留给了他们,这些东西才仍旧是属于我的。即使我在六尺之下还是属于我的,你懂吗?”因此在老卡博特看来,他的妻子对他来说只是生儿子的工具,并不属于他,但是儿子的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脉,儿子是他的延续,所以在他死后,如果他把农场留给儿子,农场就会仍然属于他。老卡博特的物欲使家庭关系异化,给家庭成员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集体创伤,本应该父慈子孝,夫妻和睦的家庭关系为一种严酷的雇佣关系所取代。西蒙和彼得对父亲充满怨言,他们咒骂老卡博特,称其“很快就会上西天的”,还说“咱们得等下去,等到他入地狱之后”,同时,因为老卡博特奴役致死埃本的母亲,更是使得埃本怨恨父亲,伺机寻求复仇,占领农场,并且产生杀害父亲的违背伦理的想法。老卡博特畸形的欲望给家人带来了严重的集体精神创伤,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疏离,情感排斥,而在这一集体创伤下,每个家庭成员又有着各不相同的个人创伤体验。
(二)畸形欲望造成个人创伤
本剧的主人公之一埃本,幼年时目睹父亲将母亲虐待剥削致死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可愈合的个人创伤,自此创伤占据着他的内心世界,支配着他的行动。埃本为了夺回母亲的遗产,与父亲、兄弟争夺农场所有权,而为了报复父亲,埃本采取了很多间接的手段,比如占有父亲的情人,一个名叫米妮的妓女。埃本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俄狄浦斯情结,有着对母亲形象的深刻心理追求,尽管埃本的母亲并未在剧中直接出现,但通过三兄弟间的对话,仍可窥见她的形象——一位美丽且优雅的女性,并且在埃本的生活中始终占据着积极的心理地位,而埃本在受到对父亲的憎恨与对母亲的思念的共同驱使下,试图在继母爱碧身上寻求情感的慰藉与满足,而在情感的纠葛与利益冲突的推动下,最终一步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本剧的女主角爱碧的身世非常不幸:幼年时即沦为孤儿,靠着在别人家里做苦工为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在丈夫和孩子死后,爱碧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家,孤独无助的她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受折磨。荣格认为,安全感是一个人的首要需求。而从小就失去父母的爱碧,毫无疑问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因此她只能企图在无限膨胀的欲望中麻木自己,这也使她一步步走向毁灭,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在剧中,爱碧一到农场便被它深深地吸引了,她双眼贪婪地扫视了房子一遍:“家,真美呀!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正是我的家啊!”,而当老卡博特告诉她“一个家是得有一个女人”时,她反驳道:“一个女人是得有个家。”从她的言语之间,可以看出她对农场的不加掩饰的占有欲望,也暴露出她与年龄足以当自己父亲的老卡博特结婚的真正目的是在其去世后占有这个美丽的农场。当爱碧第一次见埃本时,埃本质疑她与老卡博特结婚的目的,嘲讽她为“买来的娼妓”,爱碧直言“就算我确实需要一个家又怎么样?我嫁给他这么个老头,还会图别的什么?”,并且回击埃本“这是我的田庄——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厨房!”,这些对话表明爱碧已经把农场当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当爱碧知道老卡博特想要把农场留给一个能给他带来新希望的孩子时,她意识到只要她生下一个孩子,她就可以得到老卡博特的全部财产,于是爱碧引诱埃本,生下乱伦得来的孩子,不知真相的老卡博特也十分喜欢这个孩子,准备把农场留给他,但是埃本恨老卡博特迫使自己母亲在农场劳作至死,认为只有自己可以继承农场。利益的冲突使埃本和爱碧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爱碧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埃本,而为了解除埃本对她的误会和恨意,她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孩子。爱碧极度缺失的安全感,埃本怨恨父亲、思念母亲、渴望爱与关怀的创伤记忆在弑婴事件上得到延续,是二人个人创伤的一次集中体现。
三、奥尼尔个人经历与创伤
《榆树下的欲望》的创作时期是美国的爵士时代,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民注重物质生活的丰盈,美国社会中物欲横流,而奥尼尔意识到在这种生活背后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因此通过创作《榆树下的欲望》中卡博特一家的为物欲蒙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异化的生活,映射出现实生活中美国人民面临的精神困境,因此可以说《榆树下的欲望》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缩影。同时众多文学评论家认为《榆树下的欲望》也是奥尼尔的无意识自传作品之一,奥尼尔的原生家庭生活如卡博特一家一样痛苦压抑,而奥尼尔对父母的复杂情感在《榆树下的欲望》中也有所体现。
1888年10月16日,奥尼尔出生在纽约百老汇拐角处的一家酒店。他的父亲詹姆斯·奥尼尔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美国演员之一,在《基督山伯爵》中扮演布索尼神甫近20年。由于演出需要,詹姆斯·奥尼尔经常带着一家人变换住处,因此尤金·奥尼尔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童年漂泊不定的生活。由于没有固定的居所,小奥尼尔就像浮萍未感受到家的温暖,缺乏安全感。尤金·奥尼尔的母亲玛丽·埃拉·昆兰出生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富裕家庭,并且在一个女子修道院中度过学生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与詹姆斯结婚后,埃拉的生活质量迅速下降,她曾抱怨詹姆斯·奥尼尔将她带入了那个不得安宁的世界,婚前浪漫的期待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导致他们产生了分歧,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悲剧。
首先是埃拉和詹姆斯的儿子埃德蒙·奥尼尔因感染哥哥吉米的麻疹而夭折,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严重的打击,为了弥补内心的创伤,奥尼尔夫妇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奥尼尔,而埃拉在生育奥尼尔的时候,又因詹姆斯请来的庸医过量注射吗啡,使得埃拉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对吗啡产生依赖,开始吸毒,精神也常常处于疯癫状态,甚至试图在吗啡的作用下自杀,意识不清的母亲给奥尼尔的童年带来了阴影,而父亲与哥哥甚至把母亲的毒瘾归咎于奥尼尔的出生,使得当时年幼的奥尼尔对母亲也十分愧疚,这也造成了奥尼尔对母亲的复杂情感。奥尼尔的哥哥吉米酗酒,曾带着15岁的奥尼尔一起去酒吧喝酒,奥尼尔从此也开始酗酒,有时一喝就是一个礼拜。1920年8月奥尼尔的父亲去世,临终前给奥尼尔留言:“我很乐意离去,去过一种更好的生活,现在这种生活空虚,腐朽,一切都不好。”两年后奥尼尔的母亲去世,哥哥吉米十分悲伤,于一年后死于饮酒过量。原生家庭的不幸遭遇给奥尼尔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痛苦回忆,而对《榆树下的欲望》的创作,这些痛苦回忆不仅成了奥尼尔创作的素材,并且在创作过程中也成为奥尼尔创伤经历的宣泄口,剧中埃本可以解读为奥尼尔的自画像,而老卡博特则是根据奥尼尔父亲为原型塑造的,埃本与奥尼尔一样,思念母亲,怨恨父亲,充满着抑郁情绪,而老卡博特将前两任妻子虐待致死,也与詹姆斯因省钱请来庸医导致妻子埃拉对吗啡上瘾相似。
四、复原与救赎
众多学者经深入研究后普遍认为,个体在遭遇心理创伤的情境下,写作作为一种可以输出内心感受的表达形式,展现出了显著的心理治疗效用。这一过程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索内心世界的平台,是一个帮助他们逐步揭示并理解那些被埋藏的情感与体验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字的书写,作家可以对创伤事件进行某种形式的叙事建构和历史重建,减弱创伤记忆的力量,逐步释放那些由创伤所带来的沉重枷锁,使心灵得以解脱,情感得以宣泄,并且通过为有创伤经历的角色找到从创伤中恢复的解决方案,自己也能获得从创伤中恢复的力量。因此,写作不仅被视作一种有效的情感表达方式,更被广大研究者和实践者视为一种能够帮助个体克服心理创伤、实现自我疗愈的重要手段。显然,在《榆树下的欲望》中,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在奥尼尔的创作时美国梦破灭等时代的印记,还可以看见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奥尼尔在创作中无意识地重新构建着他的家庭和生活,进行自我修复。
在《榆树下的欲望》中,埃本和爱碧是自我救赎的最佳范例,他们最终通过与彼此的联结摆脱了欲望的蒙蔽,超越了先前创伤记忆,实现了精神上的救赎。弑婴事件象征着对二人违反伦理道德的惩罚,是埃本、爱碧内心深处创伤产生的恶果的揭示,而之后两人的对白反映了二人对自己所犯恶行的忏悔和对个人创伤记忆的消解,爱碧创伤记忆下对安全感和家的追寻与埃本的对爱的渴望与复仇欲望得到救赎,埃本和爱碧因此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罪行的后果,实现了从“欲望”到“爱”的转变。埃本和爱碧经历了从堕落、受罚、忏悔到救赎的心路历程,不仅是对他们个人命运的深刻反思,对创伤的救赎,更是奥尼尔对人性中善恶冲突、欲望与救赎等议题的深入思考,为我们理解并应对生活中的复杂情感与道德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Caruth 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 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2]La Capra Dominick.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2001.
[3]Sigmund Freud.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A]// David Lodge(ed.).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M].London & New York:Longman,1972.
[4]陈立华.从《榆树下的欲望》看奥尼尔对人性的剖析[J].外国文学研究,2000,(02):71-75.
[5]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M].陈良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6]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7]张立.欲望的泛滥与升华——《榆树下的欲望》的宗教解读[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01):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