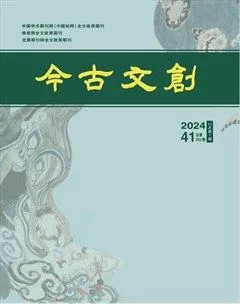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 “ 反文化 ” 群像
2024-11-21王天钦包晨曦 王舒
【摘要】虽然《杀死一只知更鸟》再现的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南方社会,但身处反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夜,哈珀·李身为作家的社会良知促使她以彼时正在酝酿发酵中的反主流文化意识重构大萧条时期的历史叙事,并在小说中建构了一系列具有反文化精神气质的人物形象。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也构成该书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迅速经典化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文化研究视角为棱镜,透视小说建构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人物群像,旨在通过有机融合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创作时代背景,揭橥美国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嬉皮士文化、新左派运动等反主流文化思潮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追索,为当代青年的成长提供价值理性借鉴。
【关键词】《杀死一只知更鸟》;反文化运动;女性主义;嬉皮士;新左派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1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05
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深度危机与骚动,社会结构的动荡加剧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绝望与沮丧,于是一场青年人主导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在美国应运而生。所谓“反文化”,并非自绝于人类文明、目空一切地反对所有文化,而是反叛彼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主流文化,试图建立新的社会规约与价值系统。他们的反叛往往被印上离经叛道的标签,例如以吸毒、滥交、焚烧星条旗等骇人听闻之举闻名的嬉皮士,即是反文化一代的极端例证。然而,根据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这种疯狂的反叛可以被看作是美国青年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试图找到属于自我的“第二世界”的尝试,尽管极尽低俗、猎奇,但其确实具有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内核。正是经由反文化运动对主流价值的解构,女性、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等边缘群体的社会处境开始成为热门议题,妇女解放、黑人平权等一系列民权运动走向高潮。在知识界,也涌现了一批向往乌托邦、反抗权威的知识分子,即所谓“新左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次年即获得普利策奖,并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全球销量逾三千万册,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虽然《杀死一只知更鸟》再现的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南方社会,但身处反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夜,哈珀·李身为作家的社会良知促使她以彼时正在酝酿发酵中的反主流文化意识重构大萧条时期的历史叙事,聚焦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性歧视与偏见,所传达的恰恰是“怀疑多数,反抗主流”的价值取向,与“反文化”一代的叛逆立场不谋而合。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也构成该书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迅速经典化的重要因素。
盛名之下,《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已有研究也已比较丰富,尤其以女性主义视角读解《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研究蔚为大观,如“Sympathetic Alliances:Tomboys,Sissy Boys,
and Queer Friendship in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and To Kill a Mockingbird”中提及了故事叙事人斯库特是一个典型的“假小子”形象:故事中,斯库特一直穿着代表着男孩的背带裤,而不是代表着女孩的裙子,这象征这女性社会地位相对低于男性。[1]Shackelford的“The Female Voice in To Kill a Mockingbird:Narrative Strategies in Film and Novel”从小说叙事与改编电影叙事对比角度进行论述,侧面说明了女性声音的缺失,并指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2]与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相关的研究同样丰富,国内学者王锦塘在《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嬉皮士运动剖析》中指出嬉皮士文化反叛虽然将美国社会搞得得动荡不宁,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但它并非重塑社会底层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只是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反叛,其实质是改良主义。[3]赵林则在《美国新左派运动述评》指出新左派标志着一个人向社会和传统挑战的勇气和决心,但过于偏激的实践样态及其救世主姿态与新左派最初倡导的“分享民主”的政治目标却是背道而驰的。[4]然而,鲜少有人从小说文本的角度出发,解读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黄明华的《〈镜厅〉——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选择了这个角度,通过《镜厅》中三个主人公的不同的生活经历向读者展示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5]本文以文化研究视角为棱镜,透视小说建构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人物群像,旨在通过有机融合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创作时代背景,揭橥美国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嬉皮士文化、新左派运动等反主流文化思潮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追索,为当代青年的成长提供价值理性借鉴。
一、社会性别的弱者
20世纪60年代正值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发轫之时,与此同时,社会性别这一概念逐步形成。根据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坎达斯·韦斯特和唐·H·奇默尔曼撰写的文章《行动着的社会性别》(Doing Gender),性别(sex)是由生物学所描述的东西:如人体、荷尔蒙和生理学等。而社会性别(gender)是一种获得的地位,是一种心理、文化和社会建构。[6]哈珀·李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深知女性在社会的缺位,从社会性别这一方面来说,她1960年出版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非常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小说中斯库特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与身边的人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会导致两种可能性:一是慢慢走向身边人所认同的传统女性角色,成为下一代传统女性,另一极端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套用社会既定的强势群体(男性)的社会特征(包括衣着、行为方式等)作为抵抗的手段,这就必然导致女性个体不得不全盘否认自己的生理特征及心理特质。这种非此即彼的性别操演模式,看似是对传统桎梏的反抗,实则仍囿于传统性别的二元框架中。斯库特便是选择抵抗的后者,她一直穿着象征着男性的马裤而非象征着女性的裙子。“斯库特,我最后一次告诉你,闭上你的嘴吧,不然就给我滚回家!我向上帝发誓,你每天都越来越像个女孩了!”[7]这种表达方式极具讽刺,斯库特本就是一个女孩,却被哥哥杰姆形容为“越来越像个女孩”,这不但是因为其家庭中母亲角色的缺失,更是因为社会根本就不愿承认女性和男性是对等的。在阿迪克斯找来亚历桑德姑母教导斯库特淑女礼仪时,斯库特与传统的女性形象可谓相差甚远。“亚历桑德拉阿姨非常热衷点评我的着装问题,如果我穿马裤,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淑女。当我说穿裙子什么也做不了时,她说我不应该做那些需要裤子的事情。”[7]亚历桑德姑妈作为一位典型的南方贵族女性,她对于女性的社会定位即为男性的附属品,她认为女人只需要作为一个“花瓶”,安安静静地坐着就好了。
事实上,除了自我选择之外,受到社会影响,男性和女性本身也会走向越来越远的两端。西蒙娜·德·波伏娃于20世纪40年代在她的《第二性》中就对女性社会性别作了系统论述:“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8]进入青春期的杰姆对于斯库特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转变:“你最好从现在开始像个女生那样。”这就是哈珀·李文字的奇妙之处,儿时的杰姆带有性别的偏见,但他是男女平等的拥护者;长大的杰姆接触到了更现实的社会,他所说的话传达的却是“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的意思。与之相对的,一直认为自己和哥哥杰姆地位相同的斯库特,也逐渐从杰姆这一社会棱镜中看到了那些本就存在的、她未曾注意的有色眼光,随着年龄的增长,杰姆享有越来越多的优势,斯库特则背上了越来越多的桎梏。
除了主角斯库特之外,哈珀·李还刻画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莫迪小姐、杜博斯太太和马耶拉小姐。莫迪小姐有着先进的独身主义思想;杜博斯太太不惧病痛,战胜毒瘾;马耶拉小姐则是深受男权社会迫害的典型代表。《杀死一只知更鸟》并没有选择以女性主义为议题,而是将其归于一个更大的议题——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的压迫,这也是小说的内核所在。在哈珀·李构建的梅科隆小镇上,女性是社会性别上的弱者,无声地与父权社会对抗。这正是非主流文化运动中女权主义者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女性如何为社会所规约,又要如何修正社会规约与环境,如何与她们所处的世界相抗,又如何与世界相处。
二、自我麻痹的反叛者
在众多对嬉皮士运动的分析中,王锦塘颇具洞见地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系列青年反叛运动是战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历史合乎逻辑的反叛。[3]从经济上看,二战后的美国社会要面临的失业、通货膨胀问题并不小,经济的不稳定让普通民众不由得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从政治上看,工业化带来的官僚主义盛行,黑人领袖遇刺,让统治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显得苍白无力。从文化上来看,新教伦理衰落,导致简朴、节约的生活态度没落,高消费价值观横行,酿成传统价值体系的崩坏。由此,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受到右翼保守主义影响,以吸毒、穿奇装异服、群居却又离群等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的“垮掉的一代”,逐渐转变为60年代的嬉皮士。虽然哈珀·李描绘的并非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也没有直接出现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思想主体与书写主体的哈珀·李身处反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夜,自觉地以彼时正在酝酿发酵中的反主流文化意识重构历史叙事,小说中也出现了颇具嬉皮士气质的人群,他们无能于找寻惨淡现实的突围之道,遂以浑噩的自我麻醉强作逃遁之举。
《杀死一只知更鸟》存在着一批群居的“下等白人”。哈珀·李在书中写道:“用他的话来说,尤厄尔家的人属于另外一个独立封闭的群体,那个圈子里全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这些普通人选择对尤厄尔家族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拥有一些特权,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比方说,他们用不着非得去上学。更有甚者,鲍勃·尤厄尔先生,也就是巴里斯的父亲,还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在禁猎季节设陷阱进行捕猎。”“每个和梅科姆一样大的城镇都有像尤厄尔一家这样的家庭。经济波动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地位——像尤厄尔一家这样的人在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都过着同样的生活。逃学的军官无法让他们众多的后代上学;没有公共卫生官员可以使他们免于先天缺陷、各种蠕虫和肮脏环境中固有的疾病……”[7]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尤厄尔家对于社会是不满的,但他们仅仅只是想不劳而获。一方面,尤厄尔家族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的一大特点十分相像——群居。并非受社会经济影响,而是本身的价值体系使然,所以无论外界的情况如何改变,尤厄尔家都会选择碌碌无为的生活方式。他们痛恨社会,痛骂社会对他们的不公,但从不反省,也不做任何改变。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尤厄尔家找不到奋斗的方向,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奋斗方向是什么都不改变。另一方面,尤厄尔家又是离群的,他们并不在乎法院如何判决,大众如何看待,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声誉。哪怕尤厄尔家族再落魄,他们也认为自己比汤姆一个黑人的社会地位高,所以他们选择诬告汤姆,并且在阿迪克斯为汤姆发声后袭击他的孩子。他们完全脱离了社会斗争大舞台,更有甚者站到了反主流的另一端。
《杀死一只知更鸟》构造的美国南方小镇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正如历史也包容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嬉皮士运动可以看作是一场自我的狂欢与解放,但其更多的是个人的放纵与群体的荒诞行为。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反主流文化运动,但其反作用更甚,放纵吸毒的嬉皮士反而让群众觉得反主流运动是一场胡闹。本文认为哈珀·李抓住了嬉皮士文化这一社会特点,塑造了自我麻痹、冥顽不灵、停滞向前、背离群众的尤厄尔一家,让其作为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恶人,对这种败坏的风气与混乱的伦理秩序发出了猛烈批判,实现了作品内核的多样化。
三、超越时代的先行者
阿迪克斯在小说中的身份尤其特殊,他作为斯库特和杰姆的父亲,又作为梅科隆小镇上的律师,他既是孩子们成长的风向标,又代表着整个小镇的政治风向。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中最强烈的政治问题便是种族歧视问题,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珀·李塑造的阿迪克斯却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者。在教育上,他不会因为性别厚此薄彼,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在政治选择上,他选择了正义而不是群众的偏向,为一个黑人诉讼发声,去打一场不可能成功的官司。本文认为,阿迪克斯的角色塑造同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新左派思想不谋而合,并且阿迪克斯走在了新左派之前。首先,新左派的成员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阿迪克斯身为律师,能够独自养育两位孩子。其次,新左派反对的主要目标不是现存的经济制度而是现存的权利结构和价值系统,赵林先生将这种追求称为“个人分享民主”的社会制度[4]。阿迪克斯的行为与思想理念并不是从根本上对社会结构的冲击,而是一种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角度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的再思考。再次,新左派由于过于强调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它并没有在破坏的同时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体系。阿迪克斯在这一方面上显得十分清醒,他一直都很清楚他所主张的正义只被少数人认可,而不会被社会的大多数接纳,但“他明知会输,也要去做”[7],这正是其与新左派的不同之处。
阿迪克斯是《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有着极为独特和超越时代的特点。阿迪克斯指出了杀死一只知更鸟便是犯罪——有一天,阿迪克斯对杰姆说:“我宁愿让你们在后院射易拉罐,不过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去打鸟。你们射多少冠蓝鸦都没关系,只要你们能打得着,但要记住一点,杀死一只知更鸟便是犯罪。”那是我第一次听阿迪克斯说某种行为是犯罪,于是就去问莫迪小姐。“你父亲说得没错”,她说,“知更鸟只是哼唱美妙的音乐供人们欣赏,什么坏事也不做。它们不吃人家院子里种的花果蔬菜,也不在谷仓里筑巢做窝,只是为我们尽情地唱歌。所以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犯罪。”[7]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杀死一只知更鸟”,阿迪克斯就这样带着他远超同时代的教育理念引出了小说主题——独立进行价值判断,保留对良善的信念。这份理念可以通过小说后文的相关情节体现,无论是为黑人汤姆辩护,还是感谢怪人拉德利,阿迪克斯都始终坚信人性的善,并且坚持人性应当凌驾于法制,对对错的判断也该基于自我的良知而非嘈杂的群众。由此可见,阿迪克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要创造的社会与新左派希望的社会是相似的,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类似现代乌托邦的社会,为社会的不公正发声,为平等、民主发声。相比新左派,阿迪克斯选择的是一种更为高明,社会更愿意看到、接受的做法,即对孩子进行教育,将思想理念传递给孩子。
诚然,正如新左派注定要失败,阿迪克斯的坚持也不会成功。人无往不在社会之中,但是人却要给人贴上各种社会标签。“他们说阿迪克斯在为黑鬼辩护。”[7]哈珀·李善于用最简单地文字展现出群众与个人的意识冲突,从侧面体现了阿迪克斯的思想本身不会被社会接纳。阿迪克斯的伟大在于他的勇敢,他希望通过一场必败的官司,一场无用的控诉多少唤醒群众沉睡的良知。只要能多一个人和他一样勇敢,他的努力就是成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女儿斯库特在阿迪克斯的教育下,甚至更具有新左派的特点——极度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她在看清了社会的龌龊之后,仍然能够回想起父亲的教诲并保持自我,这便是阿迪克斯远超时代的成功。
四、结语
《杀死一只知更鸟》空前绝后的成功离不开它探讨的话题——非主流与主流的对抗。哈珀·李塑造了丰富而多元的“反文化”群像,他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社会性别的弱者如女性和有色人种也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揭示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自我麻痹的反叛者为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选择和行为提供了再思考;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穿越时代呼吁人们不要放弃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正因如此,不要摒弃了不从众的良知,不要杀死歌唱的知更鸟。
参考文献:
[1]Kristen B.Proehl.Sympathetic Alliances:Tomboys, Sissy Boys,and Queer Friendship in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and To Kill a Mockingbird[J].2013.
[2]Shackelford.The Female Voice in To Kill a Mockingbird:Narrative Strategies in Film and Novel[J]. 1996.
[3]王锦塘.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嬉皮士运动剖析[J].世界历史,1993,(03):30-37.
[4]赵林.美国新左派运动述评[J].美国研究,1996, (02):40-57.
[5]黄明华.《镜厅》——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08):30.
[6]Candace West&Don H.Zimmerman.Doing Gender[J].1998:167.
[7](美)哈珀·李(Harper Lee).杀死一只知更鸟[M].李育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8](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美国文学中印第安屠杀事件的历史再现研究”(项目编号:2023SJYB14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