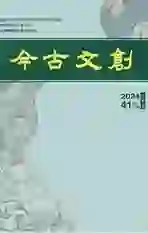从《小珍集》看施蛰存创作风格的转变
2024-11-21刘源
【摘要】施蛰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从现代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他在1936年出版的小说集《小珍集》增加了对真实世界的描摹,显示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呈现出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施蛰存创作的转变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是作者基于自身创作和外部环境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关键词】施蛰存;《小珍集》;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01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其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的10年间。1929年,施蛰存出版了小说集《上元灯》,这部作品标志着施蛰存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小说主要描写“我”对儿时美好往事的回忆,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20世纪30年代初,施蛰存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将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运用到小说之中,创作出了《将军底头》《石秀》《梅雨之夕》等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作品,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心理分析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就在施蛰存的文学事业达到高峰之际,他却忽然停止了对心理分析小说的探索。他在1936年出版的《小珍集》“彻底扫荡了魔幻怪异因素”[1],转而“用哀愁笔调和讽刺手法去描写当代生活”[2],又显示出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最终又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历程。《小珍集》是研究施蛰存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创作转变的重要文本。通过分析《小珍集》中的篇章可以发现,施蛰存一方面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社会现实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小说的创作方法和形式进行探索和发展。
一、《小珍集》对现实主义的回归
施蛰存以往的心理分析小说大多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热衷于揭示人物的病态心理,现实世界则作为次要内容而被忽略。但在《小珍集》中,作者将关注的重点转向现实世界,加强了对真实世界的描摹,并显示出社会批判的意味。
(一)描摹真实世界
在《小珍集》中,施蛰存不再一味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将目光转向外部,表现真实的社会生活。《失业》展示一名银行小职员刘念劬被辞退后的苦闷与颓唐,不愿回家面对妻子的他穿梭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他先是在南京路上闲逛,观察着商品的种类、价格以及各种吸引他目光的事物:“钢扣纺大廉价,每元一丈二,三花牌化妆品盒,三种共售洋五元,‘无敌牌’大赠品,‘拔佳’大削价,$1.75、$1.50、$1.25,百跌不坏火车表每只售洋一元,日本巧克力什锦糖减售半价,提花毛巾浴衣每件一元半……”[3]之后偶遇了老同学,请他在冠生园的冷饮部吃了冰激凌。接着逛到了永安公司,买了一包“吉利”刀片。最后坐着电车到西门的稻香村买了一些瓜子与糖食回家。小说通过刘念劬一天的城市漫游经历,展示了上海的都市景观和小市民的现代生活,描写生动鲜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除了描写上海的都市景观外,施蛰存还对上海周边的城镇乡村展开描摹。《名片》中有一段对西湖的描写:“西湖是百看不厌的,一半勾留为此湖,苏东坡尚且如此,何况马家荣先生?虽然苏东坡时代的湖上有画船箫鼓之盛,但如今虽无画船,却有铜栏杆的划子,或汽油快艇;虽无箫鼓,却有女学生的口琴,或His Master's Voice的话匣子,或RCA无线电。”[3]小说对西湖的景观进行古今对照,从侧面表现出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
(二)关注现实问题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带来都市的空前繁荣,上海周边的城镇、乡村难以抵抗都市文明所带来的冲击,传统的小农经济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施蛰存在《小珍集》中就关注到了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冲击。《牛奶》写老佃户财生的牛奶没有销路,顾客宁愿花费更多的钱去买牛奶公司的牛奶,也不愿意买他的新鲜牛奶,嫌弃他的牛奶不干净。但牛奶公司实际上只是低价收购农民的牛奶,再贴上“卫生牛奶”的商标罢了。这篇小说反映了现代商业制度对农村传统小农经济的冲击。《汽车路》则一方面揭示了城市对乡村土地的侵占,另一方面讽刺了狭隘、愚昧的小农思想。汽车路修到了陈家荡,侵占了农民的大片土地却只给了少量补偿。原本忠厚的农民关林在自己的利益被侵害后,便将一切与汽车路相关的人和事都当作自己的仇恨对象,常常与乡民们一起做些破坏工作,妨碍汽车路的修筑。路修成后,关林帮助出车祸的人推车后得了六角钱的小费。尝到甜头的他开始人为制造事故以牟取利益,最终被捕入狱,只得卖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田地才得以获释。
除了关注在城市文明挤压下逐渐衰落的乡村,施蛰存还将目光投向在都市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通过展示他们的生存状态揭示现代大都市对人身心的摧残。《失业》写了小职员刘念劬被辞退后的状态,他在街上四处游荡,希望能找到新的差事。回家后面对妻子,刘念劬坐立难安,在妻子的再三追问下才敢说出自己失业的消息。刘念劬失业后失魂落魄的痛苦样貌显示了小人物在现代都市的生存压力。《鸥》写银行职员小陆面对日复一日机械枯燥的生活感到烦躁疲惫,甚至对未来充满恐惧,只能从对故乡的回忆中寻求一丝精神上的慰藉,揭示出都市社会经济压力对人性的扭曲。
二、《小珍集》对现实主义的发展
《小珍集》虽然显示出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施蛰存的创作又回到了原点。在《小珍集》中,施蛰存没有完全抛弃心理分析的手法,而是将其运用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之中。与此同时,施蛰存继续探索新的小说形式,尝试创作出用“纯中国式的白话文”的新小说。
(一)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
在《小珍集》的一些篇章中,施蛰存将他所擅长的意识流、心理分析等手法运用其中,大大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鸥》讲述了银行职员小陆在机械枯燥的工作间隙,回忆起故乡的小渔村和自己初恋的女孩。不久后,小陆在上海大光明戏院门口偶遇了自己初恋的女孩,此时的她完全是摩登妇女的打扮,并且成了自己同事的情人。这篇小说揭示了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压抑,同时又表现出对村镇文明没落的失意之情。这类主题在当时的京派和左翼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但《鸥》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小说中的情节被淡化,整篇小说由感觉、联想、想象、回忆连缀而成,角色的心理活动成为刻画人物的唯一角度。小说以主人公小陆意识的流动来组织故事:修女的白帽子引发了小陆对白鸥的联想,接着回忆起家乡、大海和自己初恋的女孩。账簿上40只钢笔画的鸥鸟使小陆想到自己40元的薪水,一下子从幻想被拉回到现实。这篇小说描绘了一个“都市白日梦”,而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确实为读者带来了如梦似幻的朦胧之感。
在创作《鸥》时,施蛰存克服了以往心理分析小说中魔幻怪异的非理性成分。《鸥》中主人公小陆的意识流动基本上围绕着“鸥”这一联想中心明晰而有序地展开,并非是虚无缥缈,而是清晰可知的。正因如此,《鸥》这篇小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没有走向怪异和不可理解的极端。
《鸥》用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了现实主义的主题,正如施蛰存自己所说的:“这篇小说是新感觉派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两边调和了。”[4]
(二)探索新的小说创作模式
作为一位有积极探索精神的作家,施蛰存在回归现实主义创作之后,依然在继续探索新的小说创作模式。他试图“创造一种纯中国式的白话文”,即“评话、传奇和演义诸种文体的融合”“希望用这种理想中的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一面排除旧小说中的俗套滥调,另一面也排除欧化的句法”[5]。于是施蛰存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尝试用“纯中国式的白话文”创作小说。《小珍集》中的《猎虎记》和《塔的灵应》就是他探索新的小说创作模式的成果。
《猎虎记》的主人公郑涛出生于打虎世家,虽说挂着一个“赛武松”的名头,却连老虎都没见过。乱世之下,连山里的动物都已绝迹,猎户们没猎物可打。走投无路之下,一位绰号“汤土地”的猎户提出,不如借“赛武松”家祖传的老虎皮假扮成大虫去偷村民的家禽。村民报官后,“汤土地”进城避风头,不想老虎再次出现在村里。“赛武松”认定这次是真的老虎,拿猎枪打死老虎后才发现老虎是村里泼皮汪二假扮的。发生此事之后,“赛武松”再次被人们奉为英雄,而猎户们先前偷鸡摸狗的丑行也因此被掩盖。《塔的灵应》以位于常州城外的圆觉寺作为故事发生地。寺中有一座宝塔,曾在历史上有过数次灵应。宝塔旁有一放生池,竖立着一个莲花幢,上书:“八功德水沸腾日,七级浮屠堰仆时”。游客们都觉得这个预言不可信,但预言却在一系列巧合下实现了:行脚僧不满老和尚,于是买了生石灰投入放生池导致池水沸腾。两个孩子正好在此时搬动了塔下的础石,宝塔随之倒塌。这两篇小说都运用了传统小说的形式,以情节为中心,按时间顺序组织故事,具有连贯的叙事结构。其故事情节也颇具传奇性,符合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
然而施蛰存在创作这两篇小说时,一味追求使用“纯中国式的白话文”,而忽略了新文学应有的“现代性”,因此有人指责其为“回老路”的作品。虽然这两篇小说在艺术上远不及施蛰存过去的作品,但他为新文学民族化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三、施蛰存创作风格转变的原因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提道:“施蛰存的最后一本小说集《小珍集》彻底扫荡了魔幻怪异因素。他显得像是已经完全屈服于左翼的压力,从他早期小说的都市哥特方向上被完全拨转过来。”[1]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施蛰存难免受到左翼文学主潮的影响。但与其说他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是左翼文学影响下的被动转变,不如说是作者基于自身创作和外部环境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一)主观原因
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部分作家一样,施蛰存也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他在192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江干集》,这个集子里收录的24篇短篇小说都是追随“五四”新文学而创作的,表达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倾向。此后,受到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感染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施蛰存主动投身于普罗文学运动之中,与戴望舒、刘呐鸥、杜衡等人一起创办了“第一线书店”和《无轨列车》月刊。《无轨列车》上刊登的文章超过半数都属于普罗文学,显示出了浓厚的左翼色彩,因此杂志办到第8期就因“宣传赤化”而被禁止,书店也因同罪名被查封。之后,施蛰存等人又创办了水沫书店,出版了《新文艺》月刊这一左翼刊物。可以说,施蛰存称得上当时最为活跃的左翼文学青年之一。除了兴办进步刊物、出版进步书籍之外,施蛰存还积极创作普罗文学。他发表了《凤阳女》《阿秀》《花》《追》等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7]其中《追》描写无产阶级革命故事,还被国民党列入了禁书目录。青年时期的施蛰存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自觉使用文学这一“武器”介入社会现实,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然而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革命的失败使施蛰存逐渐意识到“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加上施蛰存性格中更多具有传统文人的气质,使得他无法适应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自此,施蛰存开始偏离革命的道路,转而开始进行文学形式的实验,并创作出了一系列心理分析小说,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创作之路。
从施蛰存早期的创作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那么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转向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笼罩在日本侵略战争的阴影之中,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身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家,施蛰存无法继续再躲藏于文学象牙塔之中。正如鲁迅先生在《论“第三种人”》中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8]施蛰存身处“战斗的时代”,因此他重新拿起文学这一“武器”,回到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道路上。
(二)客观原因
施蛰存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创作转向现实主义,既受到作家自身社会责任感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有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的中国难以发展这一客观原因。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英国批评家麦尔科姆·布雷特勃雷认为正是“现代化”造成了“现代意识”,而现代派文学就是为了表达现代意识而产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缺乏西方那种孕育现代主义文学的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也不具备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幻灭感。与之相对的,中国的“现实意识”却异常强烈。“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文坛主流。“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中华民族的命运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现实主义文学显示出广阔的前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能够发展现代主义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施蛰存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是难以深入的。施蛰存也体会到了创作的困境,他在《梅雨之夕》自跋中说道:“我很困苦地感觉到在题材、形式、描写方法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了。”[6]因此,基于对现实情况的准确判断,施蛰存开始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最终在《小珍集》中完成了“蜕变”。
综观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历程,他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创作风格。从《江干集》的反封建题材、《追》的普罗文学创作,到《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等心理分析小说,再到《小珍集》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发展。施蛰存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情,不断探索新的小说形式。施蛰存的创作转变显示了他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他从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5]施蛰存.文艺百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6]施蛰存.施蛰存序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7]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J].新文学史料,1985, (10).
[8]鲁迅.论“论第三种人” [J].现代,1932,(01).
[9]王宇平.自杀的“现代派”——论施蛰存后期小说创作的转向[J].名作欣赏,2006,(18):26-30.
[10]黄德志.悖离·整合·归依——论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J].江汉论坛,2000,(01):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