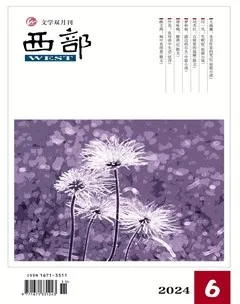失眠症
2024-10-29付一凡
失眠症悄无声息地在人群中蔓延,犹如某种病毒。
凌晨三点钟,人们徒劳地将双眼合拢又张开,像在深海暗处来回翕动的鱼嘴;凌晨四点钟,大脑仍保持亢奋状态,无数奇异的物象从头颅中漂流而过——巨柱般僵硬的蛇、残缺的鹅绒枕头、四蹄粉嫩的战马……
——短篇小说《失眠症》 作者:石姣
在一个与史诗感毫不沾边的星期三,石姣因为写一篇有关失眠症的小说而失眠了。
这是一个坏毛病——缪斯总是挑夜深人静时屈尊降临:具象的细节与画面在大脑中翻滚成海浪的形状;灵感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肾上腺素仿佛一波波向上涌动的地下泉——这一切将头脑冲刷得澄澈清明,如一片结冰的旷野,冰面上每一条裂隙的脉络都清晰可见。
手机屏幕炸开刺眼的强光,时间显示深夜两点。“必须睡了。”石姣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明天有早八(早上八点第一节课的简称)。”
她选择了一个舒适的侧卧姿势,努力抚平大脑中起伏的褶皱。
“向左侧卧貌似会压到心脏。”一个想法鼹鼠似的将头探出洞穴。石姣打了个滚,换成右侧卧。右脸颊痒酥酥的。她突然意识到右耳下那颗前几天冒出的、珠圆玉润的痘。枕头上有什么?在那块枕头大陆的微观世界里,细菌、螨虫与散落的头屑争相蜷曲蠕动。
“我可不想让这痘越来越肿。好吧,那就平躺。”于是她尝试了士兵型(双腿并直,手臂伸直放在身体两侧)、木乃伊型(双臂交叉于胸前)、帐篷型(双腿弯曲,将被子撑起),均无成效。最后石姣把四肢伸展开来,想象自己是一只柔软的章鱼,在海水浮力的支撑下毫无防备地摊开身体。让身体变成一片在铁板上平展的蛋液,她想,对,什么也别想,就这样伴随着铁铲刮锉板面的滋啦声,心甘情愿地凝固……
凌晨三点。
蛋液……铁板烧……这种联想引诱着饥饿感深入胃部。石姣睁着空洞的眼睛,听胃酸在空荡荡的胃里反复涨潮。与此同时,后头皮处绷紧,太阳穴酸胀。
凌晨四点。
完了。
她终于绝望地熬到了近五点。当黑夜与白昼交替时,意识终于如愿以偿地跌进睡眠的深井。
中午,石姣才醒来,打了个缱绻的哈欠,整个过程极其深远漫长,深渊般的喉咙尽数吸去了周围的空气。
“昨天又没睡好?”肖遥把一碟哈尔滨红肠端上餐桌问,“小说还没写完吗?”
石姣擦去眼角泌出的泪,“写到……”话被截断——第二个哈欠半路杀出。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肖遥迟疑地打量那两兜黑眼圈,它们像是眼睛的投影,乌色翅膀似的贴在眼睑下。“算了吧,这又不是啥大事,我本来换床就容易失眠,来你家住,还不是很适应。”石姣懒懒地说。
失眠这件事对石姣来说不陌生。由于经常深夜写稿,为了不打扰他人休息,石姣去年申请搬出宿舍,在外租了一间小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倒也轻松自在。夜深人静时是灵感繁衍的时段,但灵感的到来注定要以睡眠时间和质量做交换。不过石姣会将失眠控制在一周两次以内——对石姣而言,失眠的状态是可控的。但现在貌似有点失控了。
电视机上,一位煞有介事的专家夸夸其谈:“如何形成良好的睡眠状态呢?首先,将室温维持在零上二十至二十三摄氏度。睡前八至十小时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三至四小时避免摄入酒精;睡前两小时避免吸烟……”
“全是废话。”肖遥嘟囔一声。
石姣望着碟中红肠的油光,心跳沉重,在胸腔中擂出闷声,小说的场景浮现眼前——她隐约意识到,自己或许即将成为失眠症的宿主——失眠症从天而降,潜入她的体内,像某种从遥远的边区潜行而来的疫病,又像一颗从星际尽头发射而来的飞星,失眠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续让一个个夜晚倒塌。
Chapter 1
年轻的报社女记者(姓名待定)点开网页,登录社交平台的企业号,查看后台是否有民众的私信反馈。或许又是几条类似“堆在家门口的大白菜被邻居顺走”的消息。接着她开始浏览某知名论坛社会板块的热门帖——在一个“全民记者”的时代,凝聚了民间力量的新媒体平台是一块富含新闻线索的水草丰茂之地。作为“网生代”,女记者进入、退出这些路径轻车熟路。
办公室里各处散落着“啪嗒啪嗒”快速点击鼠标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的味道是这样的:木头泡进了鼓囊囊的油墨,用文火慢煮,泡到木质发软所散发的气味。每个工位都冒出热茶汩汩的白汽,味道顺势渗进白汽中,以一种水乳交融的姿态。
年轻女记者在社会民生中心待了三年了,是被调剂过来的;她的第一志愿是文化旅游中心。新报纸每次热气腾腾地出炉,她首先翻开的不是本部门的“社会民生副刊”,而是由梦想中的部门负责的“非遗副刊”“文旅副刊”和“书评副刊”。女记者二十七岁,青春期还未终结,她喜欢飘浮在半空中的东西,而具象的柴米油盐、脚踏实地的衣食住行对她而言总归差了点意思。所以,那个高校文学院里当讲师的男朋友不仅仅是一个男朋友,还是她梦想的延伸。
“嘟——嘟——嘟——”座机响起。女记者并不抱什么希望地拿起听筒。
去年社会民生中心刚开通了“民生热线”,拨打就能听到:“生活中遇到突发事、新鲜事、感人事、烦心事,都欢迎您拨打《莲城商报》社会民生中心热线电话:XXXXXXX。”来电的多为赋闲在家的老年人,女记者怀疑他们的目的是与人聊天而非所谓的爆料。“儿媳买的‘蜂巢’奶粉结块聚团”——比如这位老太太的控告,披着消费者维权的外衣,剥开皮实为婆媳矛盾。女记者感到自己正逐渐过渡为一个专门倾听老年人心声的电台主播。不过,民众提供新闻的热情愈发水涨船高,总归是件值得鼓舞的事。
于是,女记者柔化声音道:“喂?这里是《莲城商报》社会民生中心。”
“出现了怪事,记者,这绝对是大新闻!”老年男人开门见山,嗓音粗匝匝地磨着女记者的耳廓。
“什么怪事?”她的心陡然一跳,像揣了条伸腰蹬腿的猫。
对面递上答案,仿佛孩子递上满分试卷,着急讨赏: “失眠,睡不着!”
女记者失望了。
但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完颠三倒四的补充:“大家伙儿一块儿失眠!我和一起下围棋的棋友都连续几天睡不好,天天睁眼到凌晨三四点。老感觉像鬼压床,脑门儿上沉甸甸的……还有十四楼的黄伟明家,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人呀,两口子整宿睡不着……”
声音断了,手机像是被夺走了。“记者老师你好。”换了一个人,“他太啰唆,我来说一下情况吧。”
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女记者陡然一惊,突然战栗起来。顺着长长的电线,她察觉到话筒那头浮着乌泱泱的人声——是一群人在来电,对话的是派出的代表。
“我们是XX社区XX楼的住户,大概在一周前,这儿的住户出现了同时失眠的情况,大家几乎凌晨三四点钟才能睡着,而且睡眠质量很差——包括各个年龄段的人。我也问了社区其他楼的人,三分之一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们怀疑附近有某种辐射,或者声波,或者生活中共同使用的某样东西影响了大家的睡眠,比如饮用水。大家多次致电物业,但物业没有正面回应,他们认为我们在无理取闹,想骗钱。”
来电结束后,女记者的视线凝固在多肉盆栽的肥厚叶片上,愣怔许久。噼里啪啦的打字声一次又一次淹没她的思绪,一次又一次退潮,暴露在沙滩上的是一句话——“要保持 ‘新闻敏感’,及时捕捉世界的变动信息,然后给出预判。记者有时与先知承担同一个身份。”这是中心前主任离职前告诉她的话,她曾通过多个在其他主任那里会被毙掉的选题。
年轻女记者是个腾空的人,她相信那些不落地的事。她将没写完的专稿放在一边,联系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她大学时亲密无间的朋友,如今在省广播电视台工作。媒体同行之间,新闻线索的互通有无是行内的惯例。对她们来说,这还是一种巩固友情的闺中私语——类似中小学女生互相交换秘密以加深友谊的行为。“你别说,还真有人来过电。”朋友在外采风,声音断断续续,“但毕竟是个位数的案例,构不成一个选题,当时我没放在心上。”
第二个联系的人已经与女记者冷战了一个月,冰期仍在延续。冷战的发起人是她男朋友——一个在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的讲师(姓名待定)。原因是半个月前她受那位大学密友的邀请参加电视台的聚餐,而男友怀疑她与桌上的电视台民生频道男主持勾连了暗度陈仓的不正当关系。其实年轻女记者仅与男主持有这一面之缘,她记得他梳着饱满平滑的大背头,在酒桌上说了几个三脚猫笑话。声音好听,笑话很冷。不过在场的年轻女孩子都很捧场。太荒唐了,这种轻率的指认就像不入流的小说一样荒唐,像发表在妇科医院宣传册的最后几页、供大众娱乐的小小说里的桥段。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年轻女记者归罪于“非升即走”的规则,男友被这些规则折磨得焦头烂额,睡梦里都在写论文投C刊。所以,他才神经紧绷、猜疑心强——她总在有意无意替他找补,替梦想的延伸找补。或许只想安慰自己罢了。
想到联系他,是因为“民生热线”里提到的事发社区离男朋友任职的高校很近。女记者想咬手指甲,又意识到前几天刚做了莲花图案的美甲,连忙将手指放下。
电话拨过去,没有接。
她又打,这次被挂掉了。
她再打,终于通了。
年轻女记者抿了抿嘴,抿出轻飘飘的问句。
她说:“最近睡得好吗?” 因为压着语气,听着像陈述句。
话音未落,通话被那头毫不迟疑地挂掉,仿佛下一句话一旦公布,潘多拉的魔盒就此开启。
那晚,女记者也失眠了。
Chapter 2(节选)
所有人徒劳地睁着或闭着眼睛,但始终无法进入通向睡眠的那条隧道。
有人索性放弃了尝试入睡的行为。年轻人通过打游戏、追电视剧、看直播消磨时间;老年人刷着一个接一个的视频号,或无所事事地盯着黑暗中的某处发呆。整座城市被不知名的诅咒笼罩,睡美人的故事终究变成了某种反向的启示。
家家户户都开着电视机,生怕漏掉新闻里的每一句话。女音机械地报道最新进展:“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失眠调研工作的紧急通知》,打响了与流行性失眠症抗争的第一枪……一支由精神学、心理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调研专班于近日抵达失眠症最为严重的莲城。”
女记者连续一周都出差。楼下咖啡店的生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店员们的眼睛里鼓着红血丝,将厚椰乳和动物奶油倒入咖啡液里。两天之后椰乳与奶油没有了用武之地——意式咖啡机萃取的浓缩咖啡成了垄断式的宠儿。咖啡的口味、香气、性价比成为退而求其次的标准,能保持清醒和警觉的咖啡就是好咖啡。毕竟,在失眠症流行的年代,过马路都变成高危行为。除了高咖啡因的饮品,咖啡店还兜售一些补品,比如红参饮品、姜枣红糖饮,用于弥补那部分被失眠抽空的精力。
前几天,女记者目睹两个摇摇晃晃的人相撞。他们像两头被绚丽色彩惹毛的斗牛,边甩出脏句子边向对方挥拳。失眠降低了拳头的命中率,几只拳头打向空中,以奇怪的姿态定格,徒然到有些可笑。
失眠让人更愤怒了,催生了新一代的失眠愤青。女记者滑动手机网页。各种媒体平台上,“睡眠”“失眠症”都是讨论最多的热词。网民们根据睡眠立场的不同,自划出两个派别:“基因进化”派以及“拯救睡眠”派。
“基因进化”派似乎更加激进。她追根溯源,发现一篇帖子似乎是“基因进化”派的大本营。帖主ID叫“心河摆渡”,帖中说:“失眠症的流行并非一件彻头彻尾的坏事,其本质上是基因的更新——睡眠的进化表明人类真正意义上摆脱了太阳节律的掌控,或者说,人类真正意义上获得了掌控自己时间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后工业化时代高强度、高效率的生产要求。”
帖子下,一群人将“心河摆渡”视为“预言家”“未卜先知者”,他们在虚拟网络中狂欢呐喊,接龙类似“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的评论。这群人属于社会的少数派,但他们如异军突起,在各种平台上散布言论,试图吸纳更多力量的认同。
“拯救睡眠”派则是传统保守的代名词,认为人类应继续遵从延续了五百万年的自然规律,努力回到正常睡眠的轨道上来。两个派别形成了“睡眠对立”,每天在线上吵来吵去,甚至超过了性别对立的热度。网络像一个发泄口,睡不着的压力、白日昏沉的懊丧、精力不足导致的工作失误,所有归因于失眠的不幸都化为了爆炸般的愤恨和各个平台上的口诛笔伐。
……
接下来要怎么写?
一种治疗失眠症的疫苗被研发,为了争抢疫苗,全球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石姣打开手机,深夜一点。她爬上床,不抱任何期待地合上双眼。半小时后,她认命地承认自己丧失了自然睡眠的能力。褪黑素药丸也抛弃了她,不肯在她体内发挥作用。
于是戴好耳机。耳机里正播放ASMR(助眠声音)的触发声,主播用化妆刷扫动着电容型麦克风的收声网格。
毛茸茸的刮擦音在石姣的耳道里窸窣作响。她想象自己躺在长满黑色羽毛的洞窟中,羽毛变成疯长的野草,缠绕住她的四肢,一层层包裹她的身体。你将变成一具木乃伊……她的潜意识正提醒她。石姣在下沉,往某个临界点下沉。
Chapter 3
没有睡眠接续的性爱会变得粗陋、俗气。一切事都要点到为止,包括性,它需要梦中的回味,睡眠起到的就是一种隔断作用,这种作用与距离产生美的道理相似。如果两人大眼瞪小眼地相处一夜,难免会相看两生厌。
男讲师懒洋洋地半靠在床头,已经一个月没有睡了,酒店的枕头一条软一条硬,硬的那条枕在脖颈处舒适度极佳,像专为失眠起夜的人准备的。
酒店半开的窗外仍传来熙熙攘攘的人声。失眠症大流行后,夜店文化勃兴,24小时制健身房发展得如火如荼。深夜两点,街头游荡的青年比白天更多。仍有人在努力入睡,但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挣扎,逆来顺受地接受了命运施加在人类头顶的新命运。白天,则靠咖啡、红茶等高咖啡因饮品支撑精神——不少人咖啡成瘾,将其当作一种精神活性药物来依赖。
男讲师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眼袋:鼓囊囊的,宛如一只鱼鳔。身边的姑娘突然翻了个身,把白皙的胳膊和大腿压到他身上。刚刚做完两次爱,她睡得很沉。红色皮革裙胡乱扔在床边的沙发上。
男讲师揉了揉眼睛,轻轻叹了口气,没有一丝睡意的大脑里突然浮现出女友的样子——男人果然都是佟振保,有了红玫瑰就想念白玫瑰,并对那几个气头上挂掉的电话感到有一点点后悔。
失眠症还未流行的时候——见面的问候语还没从“吃了吗?”变为“睡好了吗?”的时候,失眠就已经与他如影随形了。那份入校时签订的考核协议也不让他睡安心,教学、科研成果、项目基金申请,他生怕某一项有疏漏,导致自己落入前途未卜的恐惧中。
女友是记者,空中飞人似的,在旷日持久的出差途中为他买了一副遮光眼罩快递回来。她说,光量会决定褪黑激素的分泌量,你的眼睛感应不到光线的时候,松果体就会接到分泌褪黑激素的命令,让你快点睡着。
但是,女友并不知道,他巴不得睡不着。人不睡觉多好啊,几乎相当于拥有了双倍的生命。双倍的时间意味着他可以干更多的事,写出更多的文章,发布更多的想法。失眠是天才的病症,普通人怎么会懂得?每天呼呼大睡的只是还未进化完全的动物罢了。
电视开着,“新闻三十分”又在报道一起凶杀案。时事评论员忧心忡忡地说:“失眠大大强化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焦虑状态和性饥渴,他们急需通过各种非理性方式甚至暴力来缓解焦虑。打架斗殴事件频发,出轨事件急剧增加,离婚率增长了五成。许多人被失眠拖垮了奋斗的意志,他们失去生活的希望,不再工作,沉湎于酒精、性和暴力中。街道上坐满了昏昏欲睡但又无法入眠的流浪汉,迷蒙的眼眸黯然无神。”
“优胜劣汰”,男讲师笃定地想。就像他在帖子里说的那样,这场失眠症流行就是一次自然选择,适应失眠状态的人的基因将被传递,而另外一些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类永远进步。
男讲师感到肚子有些饿,肚子咕噜咕噜叫。晚上点的北京烤鸭外卖这么不顶事儿吗?咕噜声似乎惊扰了半拥着他的美丽女孩,她哼唧了几声,翻了个身,又幡然入梦。
又写不下去了。
“楼上怎么还在装修?明明十点后就算扰民。”石姣把电脑猛地一合,装进了提包里,从肖遥的卧室中走出来。客厅里的装修声更大,像集中了世界上所有歇斯底里的蝉,它们嵌满天花板,密密麻麻、大声齐鸣。
电钻远远地凿着石姣的头皮。她心里一酸,强烈的委屈感直冲脑门,有液体涌上她的肿眼泡。失眠无异于一场强制性的睡眠剥夺,类似历史上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的酷刑。石姣受不了了,今天是她失眠的第四十一天,她正在枯朽。一旁的梳妆镜里,那个人眼睑浮肿,目光呆滞无神。
石姣的心猛然一惊:再写不完这篇小说,她也许会因为失眠而猝死。
她穿上外套,拿起提包,走出客厅,拉开防盗门。
“喂,你去哪啊?”肖遥在后面大喊。
“我出去找个舒适点的酒店,试试看能否睡着。”
“现在都十二点了,周边的环境你也不熟悉……”肖遥的叫声淹没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
石姣只觉得头晕脑涨,一股怒气在她的脉搏中激荡。她头也不回地冲下楼梯,跑到大街上。风的冷冽逼迫她的大脑迅速降温,她终于发现自己做了多么不合时宜的事情。肖遥趁着父母度假,邀请她来做客,她却在人家家里大吵大闹,离家出走。她泪眼蒙眬地走走停停,感觉自己的情绪变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不再受控。
身边不时经过一群嘻嘻哈哈的年轻人,他们从全天营业的快餐店出来,或许要前往另一个酒吧,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办公楼灯火通明,商铺二楼健身房的落地玻璃窗里,一整排动感单车座无虚席。
昼夜不分,这个世界疯了。
在街头的拐弯处,石姣终于发现一家宾馆。它局促忸怩地挤在两家灯牌夸张的足疗店之间,外部的装修风格类似世纪初的招待所。如果不注意看,灰扑扑的墙面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石姣快速地办完入住手续,沿着走廊往房间走时,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人朝她走过来。看清他的脸后,石姣的大脑“嗡”的一声巨响,脊背上的汗毛几乎要直立行走。
是教授文学课的男老师,也是她小说中“男讲师”的人物原型。更吊诡的是,他与另一个穿红皮裙子的年轻女性挽着手臂,两人走进大厅的前台取走“饿了吗”外卖。
石姣转身躲开老师,冲向自己的房间。
这个世界乱套了。
石姣的脑袋乱作一团。很多疑问像春水里的蝌蚪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她无力解答。她唯一确定的是,这篇小说给她生活带来了要命的混乱。再写下去,她要死了。
这样想着,石姣飞速打开电脑,鼠标捉住被命名为《失眠症》的小说WORD文件,将它扔进了电脑桌面上的小垃圾箱图标中。接着,她丝毫没有犹豫,点击“清空回收站”。
——确定要永久删除这一项吗?
石姣点击“是”。
巨大的困倦像飓风一样从半空袭来,石姣栽倒在席梦思厚厚的床垫上。
肖遥哈哈大笑,笑到泪花濡湿眼眶。
“没有,”她说,“你昨晚根本就没有出去过夜。你忘了?你出门没十分钟就回来了。你说周围根本找不到酒店。我打完一把游戏,进屋看你,你早睡着了,睡得那叫一个沉。”
石姣坚决不信,她又讲了与男讲师的偶遇,还有电脑里那篇被永久删除的小说。
“我敢打赌,”肖遥笑嘻嘻地说,“这是你构思的小说情节,被你带进了梦里吧,让你以为真实发生过。”她又补充,“至于你说的那个长得像招待所的宾馆,我跟你打包票,我从来没印象。”
石姣飞速打开电脑,瞪大眼睛,桌面上除了“我的电脑”“回收站”等几个标配图标,空空如也——小说不见了。
后来追根溯源,想起开始写那篇小说的普通夜晚,石姣才确信,她的失眠症的确由此开始—— “失眠症悄无声息地在人群中蔓延,犹如某种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