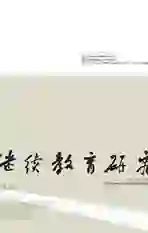中日社区成人教育发展过程比较
2024-09-30李艳华邓湘宁
摘要:通过对中日社区成人教育发展的雏形期、发展期、转化期进行比较,探讨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教育政策、成人学习意愿、政府导向之间的关系。中日政府控制、民众意识及社会控制条件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教育行为,形成两国各自不同的社区成人教育形式。通过比较可知,中日社区成人教育在不同时期,民众行为诉求相同,随着社会变化,个体求知欲增强,成人教育概念的发起行为相同。在教育载体、教育对象的变化、政府角色等方面不同,研究二者的异同,可以探寻符合我国新时代发展中提高优质社区教育资源的因素。
关键词:社区教育;成人教育;政府政策;民众意识;中日比较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4)11-0031-06
一、前言
社区成人教育的本质属性,要求社区成人教育必须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去进行[1]。中日两国在智能时代背景下,社会成人教育理念、目标不断发生变化,“社区”在国家成人教育发展战略中凸显职能作用。结合19世纪美国社区学院的成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区与成人教育进行了萌芽互动[2]。随着社区成人教育发展状态,进一步分析了社区与成人教育融合发展的条件[3]。社区成人教育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探讨了有效联动的策略[4]。不过,中国社区成人教育的理论动因还不清晰。
日本社会教育发展早,重视对成人的职业生涯、终身教育。我国学者对日本社会教育进行了阶段性的梳理[5]。日本以成人为教育对象,在学习论和教育论的特征分析中,将成人教育作为教育对象仍是今后研究的重大课题[6]。日本学者从自然环境、社会系统、人等三者之间的独立关系与相互关系,寻找社会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7]。日本关注社会市场动态,根据社会教育群体特征,不断调整社会教育政策和内容[8]。对于社会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在各领域的普及性、未来发展性等方面的理论说明不充分。
在社区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民众的行为态度、个人规范、行为意向不同,产生不同的参与状态与形式,中日政府政策的制定依据、政策内容的变化、政策执行方式等与民众意向、民众行为、政府期待的行为结果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分析中日社区发展变化,探寻影响中日社区成人教育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从中日社区成人教育发展过程的“政府-民众”“社会背景-个体求知”“社会需要-个人需要”等角度,对中日社区成人教育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教育活动的发起者、执行者的行为因素,梳理人为因素、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模式提供理论参考。
二、中日社区成人教育:雏形期
(一)中国古代社区教育色彩
我国古代“乡校”“乡约”“社学”等赋予社区教化、社区自治、社区建设等社区教育的最初色彩[9]。“乡校”是西周春秋时,设在乡的学校,也是讨论政治的集合地。“乡约”在明代日益成熟,通过价值观引导,使成人在思想意识上与国家对意识形态的灌输吻合,同时又能与社会精英群体的思想活动方向一致,从而保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乡约”的制定,由最初的士绅自主起草到后来政府统筹,由自主治理到官府管理。“社学”兴于元朝,以50家为一社,学习农桑知识、习俗礼节。虽然古代还没有“社区”概念的导入,但是已经出现区域性、统一指导的教育形式,也是士绅提高影响力、扩大思想传播的方式。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通俗教育馆”为培养民众良好生活习惯、遵守社会规则等服务。早期属于民间社会教育机构,民国成立后,教育部积极推动社会教育,主办通俗教育、各地政府主办通俗教育馆,并且建立了民众教育馆,其性质与通俗教育馆无异。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集中工农教育,一些民众馆转为文化馆,教育的味道减弱,更注重文化娱乐。在20世纪90年代,学校为居民开放体育馆、阅览室等设施设备,为成人提供了娱乐、借阅的机会。没有形成专属的社区场所,而是从学校开放的角度,拓宽民众的视野,也是中国社区成人教育的最前身。
(二)日本奈良、平安时代
日本一直没有社区教育的概念,是提倡社会教育国家之一。社会教育形式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奈良、平安时代。“足利学校”的建立是早期的社会教育雏形,兴起于家族学校,后被大力推广,达到繁盛。其主要对武士和僧侣进行教导,以提升其文化修养,除传授学问以外,还讲授孔子儒学“四经”。“足利学校”历经镰仓、室町、安土桃山直到江户时代,一直存续到明治五年,才随着日本教育的全面西洋化而宣告终结。在明治时期,受德国“民众教育”“公众教育”等教育观念影响,日本正式将“社会教育”引入教育体系中。在大量引入外国文化的同时,出现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为了提高民众觉悟,改良社会,增设了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
(三)中日民众非个人意志控制下形成的行为意向相同
中日两国社区成人教育建设雏形期均源于规范社会制度、提高学识的思想。无论我国还是日本在最初形成的教育模式中,都是有能力的家族为了扩大影响力,规范社会秩序,自主选用教学内容,在能力、社会扩充、教育资源储备到位的前提下开展的教育规范行为。日本在教育资源、教育设施设备中,模仿了我国古代的教育形式和内容。
三、中日社区成人教育:发展期
(一)中国社区教育的演进
在我国社区成人教育发展初期,成人教育设置形式多样,如学堂、民校、识字班、业余大学等,随着成人教育不断普及,担负教育责任的机构开始集中。在“社区”概念引入后,社区成人教育不断被明确化、政策化和理论化。国际社区范围没有明确的边界,大范围社区包含一个国家、城市、乡、镇,小范围社区指居家区域。社区最初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以“社区居委会”的形式存在,在城市化程度低的地区以“村委会”的形式存在,到了21世纪,为了使居民委员会更加适合社区服务职能,绝大多数城市将“居民委员会”改为“社区服务中心”等,凸显社区概念和职能,社区范围以行政区域来划分。
“社区教育”是在“社区”概念的基础上,开展各种正式和非正式、促进社区中的个人和团体学习和社会发展的活动,需要建立社区与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设立民众所需、企业和政府所求的高质量知识技能和生活质量的课程。在我国城市,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区域内,面向全体社区居民,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全力推进社区生活质量,改善居民生活内需,提高学历教育。具体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与社区政府部门、教育部代表、街道居民代表、企事业代表、工会代表等组成社区教育委员会,依托调整机构,进行管理。
(二)日本公民馆的建立
公民馆的历史就是社会教育的历史。公民馆在日本社会教育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公民馆的定义如下:为区域居民推进社会教育提供的场所,起到设施推进的主要作用。
1946年,当时的日本文部省在全国区域内设立了人们可以聚集、学习的场所“公民馆”,帮助民众学习新的价值观,配合改善生活各项活动。“公民馆”一经设立,很快在全国普及。其建设宗旨为遵循教育基本法,推行社会教育,将公民馆进行制度化。成立全国公民馆联合会,与社团法人日本联合国教科文协会、财团法人日本联合国亚洲文化交流中心进行合作,共同推进公民馆的发展。公民馆的理想画像,强调了以提高区域居民社会教育为主,自觉支持职业生涯计划,帮助完成生活水平品质提高培训,增加区域内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建立“学校”“家庭”“志愿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三)中日社区成人教育发展期比较
1.社区成人教育概念发起者的知觉行为相同
在成人教育思想中,中日表述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概念界定都受到外国学者对民众教育思路的影响,并且确定各自国家不同界定的词语,不断扩展、延续到现代社会。对于在他国逐渐流行起来的教育方式,当这种教育方式在本国被认可和接受时,其影响力也会不断扩大,并引起思想的共鸣,在社会状态与国际视野背景下,提高了知觉认知,加快了知觉行为。在我国,“社区”一词最早由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家从西方社会学中引入。最初是为解决农村教育底子弱、老百姓社会伦理观不足等问题而展开的教育模式,到民国时期,政府通过颁布《我国教育改革与纲要》建立社区教育组织,并第一次提出了“终身教育”概念。日本社会教育在明治时期之后,概念逐渐清晰,传播度扩大,具有历史性、区域性特征。发起者无论是武士家族,还是政府行政部门,都洞察到教育的重要性,并赋予培养、壮大、强化的责任感,开展了教育实施活动。
2.规范信念形成的载体与时间不同
中国的“社区”和日本的“公民馆”概念不断深化,民众的自觉意识不断提高,政府的目标不断清晰和明确,体现了民众和政府对教育组织产生更强的期望,对“社区”和“公民馆”产生依赖和顺从。
而我国与日本在组织载体建设中,有明显的时间差距。我国在长期的多种教育载体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整合式教育载体,在20世纪80年代,社区教育概念引入后,形成社区概念下的成人教育理念。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公民馆载体之后,不断扩大影响力,强化公民馆的职能,民众对公民馆的规范信念更强。
3.社会成人教育潮的知觉行为主体不同
中日两国在时代变更之际,社会动态稳定,步入大量生产力阶段,而民众的劳动技术、劳动状态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兴起了时代变更后社会成人的教育热潮。
中国政府统一调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从贫穷、落后、无知状态中剥离出来,也为了更好服务新中国成立的宗旨,强调工农子弟兵教育的重要性。推进社会发展,提升成人知识水平,提高社会生产力,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重建,迅速进入社会成人教育阶段。由政府统一调控,自上而下开展扫盲教育、农民教育、干部教育、职工教育。教育初期以识字、文化补习模式为主。
由美国政府主导,日本政府政策执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政策指导、日本国内民主力量推动下,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思潮等进行了全面的资产阶级改变,日本国家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1946年,美国占领当局提出日本民主化改革不够彻底,要求充实图书馆、博物馆、扩大学校的社会教育面,并形成了“重新把日本的智慧性与精神性资源作为新方向”的成人教育计划书,如培养民主思想教育、社会福利工作理论技术等。在美国政府主导、日本政府政策执行之下,日本民众的民主、人权等意识不断强化。
四、中日社区成人教育:转化期
(一)中国社区成人教育的转化
1.终身教育体系
我国在21世纪,终身教育理念全面迈上新台阶。社区成人教育更加受到关注,社会对人才需求提高,对成人教育能力素质要求提高,倡导对民众的全面教育和终身教育,强化了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等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学校以外的继续教育内容,更多是对成人的教育。2012年,教育部成立继续教育办公室,对职工教育、社会成人培训、社区成人教育进行宏观管理。2015年《教育法》的修订,保障了成人教育学习的权利。
2.学习型社会构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了学习型社会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构建多渠道人才培养通道,完善社区内成人教育办学资源,强化职业学校、高校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教育管理。学习型教育理念提升了成人教育内涵式建设,扩大了成人教育范围,对社区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职业教育法与社区成人教育的融合
2022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从法律的角度对成人的职业教育进行了保障,也对社区成人教育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带来新的机遇。从大范围来看,学校以外的教育归为社区范围内的教育;对社区成人教育的内容、形式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在社区成人教育中,强调职业教育、专业知识教育、职业素养培养的重要性;拓宽了社区成人教育的视野,提高了社区全面服务民众的职能。
(二)日本社会教育的转化
1.终身教育背景下成人教育理念的深化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技术革命与经济技术发展新形势之下,提出了“学习化”“终身教育”的概念。日本政府在70年代将终身教育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综合性教育,“一生的学习”“一生的教育”把成人教育理念升级、深化,上升到以人类教育为基础、以培养社会长期适应人才为目标的教育理念。在日本科教兴国、人才急需之下,企业界重视员工终身劳动技能,并把员工培养作为企业发展文化之一,既是终身教育理念落地的具体表现、深化成人教育的过程,也是日本长期终身雇佣制的开始。
2.社会人口变化下成人教育群体的扩大
随着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的加剧,青壮年群体的减少,社会劳动力不得不拓展到老年群体,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同中青年人一样参加社会工作,在新技术的普及、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乐观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工作给社会教育工作带来新的课题。发展更多类型的“成年人”群体,比如妇女、残疾人等,掌握更多的劳动技能,获得更好的劳动资源,提供更多投入社会保障的措施。
3.新自由主义思想下女性学习保障的后退
在新自由主义社会状态下,女性的学习被重视起来。日本推出了“妇人教育”“妇人学级”教育,1970年,相继缩小了地方自治体。1980年在《行政改革》中设置推行了“男女共同参与”政策,1995年在设置225所教育馆中,女性教育设施馆却在减少。在《千禧年开发目标》中提出了“截止2015年,取消男女差异”,在社会教育活动中,女性实际参与占六成以上。能否真正实现取消差异,提高女性学习机会,备受瞩目。
(三)中日社区成人教育转化期比较
1.教育体系辐射度不同
虽然中国社区成人教育概念化时间短,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我国成人学习特点与学习需求,强调要建立全民学习机制和贯穿生涯的终身学习模式。为了不断深化全民学习状态,从多角度聚焦成人教育理念,以职业院校、大学、社区教育机构、企业等多融合的方式渗透社会成人教育,具体解决成人所需所求的课程内容,教育体系幅度大,调动多方资源满足成人课堂。中国政府宏观调控,各教育机构联合执行。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终身教育概念以来,非常重视这一理论。从高中阶段开始安排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授撰写简历、面试技巧等技能,帮助学生作出未来职业生涯决策,将终身教育贯穿在生命周期内不断学习、提升技能和知识,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重视职业技能人才,有凭证上岗的优势,主要渗透在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中。日本政府广泛提供财政、资源,各教育机构行使各自的教育职能。
2.教育对象状态不同
中国社区成人教育对象以职业工作者、社会自由人以及学校体系内成人教育为主,进行职业拓展培养,提升职业技能,从不同教育机构进行专项的职业、兴趣培养。而社区教育具有广泛性,现在将老年教育、妇女教育、残障人教育及社会其他弱势群体的教育纳入其中。从终身教育需求角度,推动成人学习型社会发展。针对不同的教育群体需求,创造不同的教育环境、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是我国社区教育的长远课题。
日本在职业教育需求中,除企业固定人员就职以外,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工作的青壮年群体减少。在老年人老无保障、独居老人常态模式下,为了生存,老年人不得不学习职业技能,外出就业。日本成人教育中老年人职业教育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这是日本成人教育不同于我国的显著特征。在成人教育活动中,女性参与占比大,对教育课程需求不同,而实际教育资源配比、教育内容并没有体现女性特点。
五、中日社区成人教育发展状态比较
(一)社会发展与个体求知意识相同
在中日社区成人教育理念落地、教育群体变化、教育载体丰富、时代背景不断变化中,成人教育的定位和模式进一步完善,形成不同时期、不同思想意识的群体。在社区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时代背景与个人背景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
随着社会局面的变化,民众开始接受教育,个体知觉意识更加敏感,态度更加积极。在我国和日本社会成人教育发展期中,个体的求知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化的,有同样的轨迹特点。
1.中国“文化大革命”后个体自我学习意识加强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耽误大学梦的一代人,出于将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心理,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强烈渴求。成人高等教育是当时高等教育有力的补充,同时也兴起了第一批初等、中等成人教育热潮。改革开放后,我国呈现了以社区教育、成人教育为主的社会教育形式,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潮流影响,民众自我学习意识不断加强。在社会国际化接轨、外来环境的冲击下,激发了民众个体知觉意识,并在周围个体知觉意识变化中,个体自身生长要求、求知意识觉醒。成人教育理念、教育机构、政府政策、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对象不断扩大,教育目标更加具体。个人的人权意识、受教育权意识不断觉醒。国家社会教育素质、能力空前未有。
2.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体自我学习意识觉醒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来,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促进下,民众社会教育意识开始觉醒,但由于美国占领当局没有具体的社会教育指导内容,加之日本民众“团结合作”,出现了社会层面的各种团体培训、社会教育形式自由。涌现出民间文化人士开展的社会文化教育活动,个体知觉行为受到周围群众团体思想的影响,投身传播劳动文化、普及新宪法精神、产业文化等,开展讲座、设立社会学级制等。在民众觉醒运动中,外来文化、政府制度、外来指导、群众群体效应等都是个体知觉行为的主要因素,知觉意识觉醒,产生自由、积极进取的行为态度。这个时期的学习行为对个人自身产生跨时代的知觉冲击,提升自身知识素养,同时个体的发展,促进群体力量,提高整个社会成人教育水平,使社会得到快速发展。
(二)政府角色与民众参与意识不同
将政府与民众假设为一个独立体,他们之间形成的行为意识是直接推动社区成人教育发展的思想保障。在社区成人教育发展中,政府政策制度不断完善,民众的自觉意识越来越明显。
1.中国政策主导下的民众参与意识
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社区教育概念逐渐引入我国,围绕“社区教育”“成人教育”的政策文件,对教育内容、形式、机构设置、培育方式等越来越明确。通过文件通知的方式,自上而下对社区成人教育培训活动进行强烈的行政干预,由社区学院、街道等组织完成培训活动。
社区教育活动的行使权、执行权、管理权设置在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政府文件精神安排社区成人教育活动。社区民众对社区教育只有参与权,没有社区活动规划权与管理权,民众可向管理权提出想法与建议,但是行政管理机构需要依据教育政策,回复或者不回复。民众意愿没有直接体现在教育政策中。《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4〕16号)指出,“党政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以政府管理、发布任务为主,民众享有参与权。
2.日本政策配合中的民众民主化思潮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政府社会教育政策不断出台,民众自由、民主性不断加强,一些民间团体自觉组织社会教育活动,开展讲座,举办民众大学,向大众普及宣传科学及文化。以公民馆为主要教育设施聚点,在教育政策中,民众的自觉行为超出政策制度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自发组织青年团共同学习运动,被政府认可并法治化,法治化的青年团共同学习失去了自发性,民众提倡自由的、自发的共同学习。在教育法、安保法修改案中,强调了教师考核、警官强制执法等政策,引起民众强烈反对,使政策法案未能顺利执行。
伴随经济高速发展,《宪法》《教育基本法》内容的空洞,教育政策与民众学习热潮出现矛盾,农村被虚弱化,人们涌入城市生活,出现城市、农村教育设施等环境问题,民众对公共教育设施批判情绪高涨。民间的自主性学习活动实践,奠定了社会教育活动的基础,在民众自我社会教育活动实践中,制定了相关教育政策,社会教育的保障权越来越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深化。政府关注民间社会教育各项活动,不断提升社会教育保障权、学习权政策等。民众在政策指导下,提高了社会教育权的自觉性、公共性。
六、结语
对中日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与民众的行为意向、规范意识等进行理论比较,可以看出,在非个人意志行为意向、成人教育概念发起行为、社会变化中个体求知欲增强等方面,呈现出的民众反映、政府政策背景是相同的,随着社会不断变化,对技术技能要求提高,民众的求知欲增加,自主意识变强。在教育载体、教育活动主体、教育辐射方式、教育对象、政府角色等方面不同。中日政府意愿、民众意向以及社会控制条件的不同,有不同的行为结果,形成两国各自不同的社区成人教育形式。
中国社区成人教育政策制定后,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完成民众的生活、文化需求。政府从现有资源、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确定培训内容和形式。宣传途径和力度有限,不能有效调动社区成人全员对培训项目的认知,往往形成参加活动只是协助政府完成任务而已,活动的民众实效性不强,如何获取民众行为意愿、符合市场对民众的有效需求、协调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进而形成政府计划为民众、民众参与为个人、个人成长为社会的循环机制,是我国未来的探索路径。
日本社会教育发展相对成熟,社会教育设施齐全,以民间组织、政府配合和调整的方式为主,强调学习的自由性,提高社区社会教育价值的创造性。随着日本新生人口的减少,老龄化的扩大,社会教育范围与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老年人的教育活动以适应社会需求、老年职场就业为主,社会教育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任重而道远。
通过比较可知,中日社区成人教育的发展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发展历程、政策支持、教育模式、社区参与、民众意识等方面。在智能化时代,互联网技术不断提高,AI技术不断替代,中国社区成人教育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社区成人教育活动还没有全面渗透到民众。社区居民对社区成人教育的参与度相对较低,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育发展历程中,社会团体组织、民众参与意识、政府执行中扮演的角色和支持方式与力度对社区成人教育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中国政府主导性强,终身教育理念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1]薛滩,房为厦.社区成人教育的逻辑定位[J]. 成人教育,2008(8):40-41.
[2]张汉龙.社区发展与成人教育互动机制的形成[J].山西成人教育,1998(1):4-5.
[3]王杏改.我国成人教育与社区教育的协同发展策略研究[J].时代教育,2015(13):90.
[4]郑丽.成人教育与社区教育的协同发展策略分析[J].文学教育(下),2018(8):90-91.
[5]吕慧.反思与前瞻:国内日本社会教育研究35年——基于1985-2019年文献的可视化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20(4):28-35.
[6]罗雪琳.日本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现状综述[J].成人教育,2012(7):119-120.
[7]笹川孝一. 社会教育学の視点からESDを問い直す-「社会教育としてのESD」プロジェクトの研究成果から-[R].日本环境教育学会,2015.
[8]欧阳珺茜.社区成人教育的发展模式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1.
[9]厉以贤.社区教育的理念[J].教育研究,1999(3):20-24.
A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
Li Yanhua Deng Xiangning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Wuxi Profess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xi 214111, China)
Abstract:By comparing the embryonic perio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policy, adult learning willingness and government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The changes in government control, public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control conditions in China and Japan have produced different educational behavior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forms of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behavioral demands of the public are the same. With the change of society, the individuals’ desire for knowledge is enhanced, and the initiation behavior of adult education concept is the same.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changes in educational carriers, educational objects and government roles can reveal the factor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education resources.
Key words:Community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Government policy; Public awarenes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