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记录“我”
2024-09-25闫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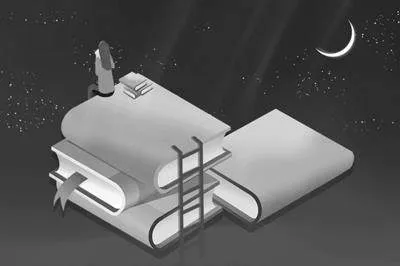
阅读是脱离“我”,写作是回归“我”。可以说,在短暂的阅读中,我可以成为任何的“我”,再以本我记录“我”。
上学期临近放假时,“阅读”找上了我。那种感觉如同馋虫,莫名想看看书,很迫切、很紧急。这种感觉在之前已消失良久,这次我实在是想要抓住,便赶忙去县里的书店买了两本书,又在网上下单了好几本。其中有往日心动却搁浅未读的,也有网络畅销的。
沉浸在故事中,去过另外一种人生。
刚拿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便匆读前十几页,但对比过厚度后,想着先“解决”薄点儿的《窄门》,结果被自己粗浅的“打量”所欺骗。“窄门”难跃,其中的情感纷繁,实在难以畅读,磨掉了好几天的闲暇时间才得以从“窄门”中顺利逃脱。没想到“两情相悦”也能如此纠结。
再捧起《额尔古纳河右岸》,虽是初次接触陌生的民族文化,但进入阅读之后,便在一气呵成的故事情节中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质感。后续进入蔡崇达所著的《命运》,认识了九十多岁的阿太,这让我想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认识”的口述人也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者——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从北到南,从鄂温克族到闽南渔业小镇,两位老者如同风雨百年的年轮,讲述着各自视角下人世间的变迁,回忆人生的相聚与分离。捧着书,像是捧着两位老人的一生。
不同于《窄门》中的情感纠葛,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命运》里,“死亡”紧密缠绕在两位老人周围。
死亡,是一直笼罩在纸页间的阴云。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风里来风里去。自希楞柱(鄂温克人住的圆锥形的帐篷)的风声中“生”,最后尘埃落定于“风葬”。生虽相同,死却各有各的“轻易”:在采摘野果的路上、在跳舞的过程中、在洗画笔的河流旁……鄂温克人的死亡大多是原始而意外的,鲜少因病痛或衰老离世。若不是无尽的死亡,这本书本该是一种轻快的基调:自然原始的生活、空灵清澈的山水、充满灵气的驯鹿,但死亡的不断出现给这个氏族蒙上了一层黑纱。
鄂温克人相信生死轮回,认为生命与自然是相互转化的过程,死亡并非终结,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开始。
《命运》中阿太的人生观:没有生离也没有死别,不过是天上的人来了,天上的人又回去了。
阿太自六七十岁就开始为死亡做准备了,她和邻里姐妹组成“死亡观摩团”,谁家有老人要离开,“观摩团”就去谁家“研习”。后来,“观摩团”的成员一个个都“毕业”了,唯独阿太始终没有等到自己的死亡,以至于后来她总是念叨:“哎呀,它怎么还不来?”对待死亡,阿太没有畏惧,没有悲伤,而是期待,这是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
阿太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从小没了父亲,16岁刚结婚母亲就扔下她跳海自尽。她没有孩子,先后失去了婆婆、丈夫、妹妹。
经过岁月的洗礼,阿太的内心逐渐归于平静,过去与未来都无法再惊扰到她,此时的阿太已与岁月共存,与命运和解。
不管是相信生命的转换,抑或是回到本该回到的地方,我们活着的目的本就不是改变我们最终要面对的结局。在人生这段旅途中,尽量圆满每一种关系,看遍能去到的每一处风景,勇敢地成就自己便好。
最后,我想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一则摘录结尾:“但我想生命就是这样,有出生就有死亡,有忧愁就有喜悦,有葬礼也要有婚礼,不该有那么多的忌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