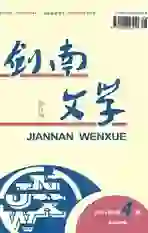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
2024-08-22曾蒙
一见钟情
■辛波斯卡
他们两人都相信
是一股突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
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
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
既然从未见过面,所以他们确定
彼此并无任何瓜葛。
但是听听自街道、楼梯、走廊传出的话语──
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
我想问他们
是否记不得了──
在旋转门
面对面那一刻?
或者在人群中喃喃说出的“对不起”?
或者在听筒截获的唐突的“打错了”?
然而我早知他们的答案。
是的,他们记不得了。
他们会感到诧异,倘若得知
缘分已玩弄他们
多年。
尚未完全做好,
成为他们命运的准备,
缘分将他们推近,驱离,
憋住笑声
阻挡他们的去路,
然后闪到一边。
有一些迹象和信号存在,
即使他们尚无法解读。
也许在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个星期二
有某片叶子飘舞于
肩与肩之间?
有某个东西掉了又捡了起来?
天晓得,也许是那个
消失于童年灌木丛中的球?
还有事前已被触摸
层层覆盖的
门把和门铃。
检查完毕后并排放置的手提箱。
有一晚,也许同样的梦,
到了早晨变得模糊。
每个开始
毕竟都只是续篇,
而充满情节的书本
总是从一半开始看起。
(陈黎 张芬龄 译)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出生于波兰小镇布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波兰女作家,同时也是位杰出的翻译家,将许多优秀的法国诗歌翻译成波兰语,其作品因“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从而获得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她是文学史上继1945年智利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1966年德国的奈莉·萨克斯之后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同时也是第四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辛波斯卡是波兰最受欢迎的诗人,被公认为当代最迷人的诗人之一,享有“诗界莫扎特”的美誉。2001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名誉会员——这是美国授予杰出艺术家的最高荣誉。
据统计,辛波斯卡先后出版诗集《存活的理由》《自问集》《呼唤雪人》《盐》《一百个笑声》《可能》《巨大的数目》等十二部,散文集两部。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延续至2012年。《巨大的数目》在1976年出版时,1万册书在1周内就售罄。
辛波斯卡擅长以戏谑、幽默、调侃、反讽、诗意的口吻表达严肃主题和日常生活、万事万物。她涉及的题材广泛:生死、冥想、日常、荒谬、爱情、哲思,往住在不经易中突显出诗意,温暖而不尖锐。因之,读她的诗如读友人来信,仿佛久别重逢的欢喜与自在。自由不拘谨,敞开不紧张,有时从容机智,洞察人间;有时节奏舒缓,吐气若兰,奉身如玉,相当沉稳如一。八岁起,辛波斯卡随父母迁居到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并在这里居住了大半个世纪,直至逝世。她一生无欲无求,淡淡地写诗,写书评,翻译作品,平静地如同墙角的棉鞋,一生书写着自己周围的事物与身体,她的窗外有一株白杨可以与其对视一生,窗外与窗内,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坚持着语言的要素,并抵制语言,这样的诗人自信而圆满。
胡桑在其《碎语、奇迹市场或希望》里说,我们可以想象,她每天走到窗口凝视树木时的静默神情:
生前栽于屋旁花园中的树
仍在为他生长。
辛波斯卡在中国大陆有着戏剧性的经历,其中国内最早翻译时她的名字叫希姆博尔斯卡,就是林洪亮翻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呼唤雪人》。2012年8月陈黎、张芬龄合译的《万物静默如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据说销售达10万册之多,刷新诗歌书籍销售之最。2014年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胡桑译《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经过10多年的跋涉,希姆博尔斯卡在中国变成了耳熟能详的辛波斯卡。
或许国内读者广泛知道《一见钟情》这首诗歌的,可能是根据台湾绘本画家幾米漫画改编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电影中引用了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这一首情诗,讲述了一段有关相遇与错过的爱情。
“红蓝白三部曲”的波兰著名导演基耶洛夫斯基回忆,一次在书摊上购买了辛波斯卡一本诗集,因为他的朋友罗曼·格伦最喜欢诗人辛波斯卡,他决定买一本送给罗曼。“就在胡乱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红》这部电影十分相近。于是我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他自己留下了这本诗集,并由此拍出了电影《红》。
基耶洛夫斯基所说的这部诗集,就是辛波斯卡的《开始与结束》。让基耶洛夫斯基“一见钟情”的那首诗,跟著名的电影《红》一样,它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又隽永,扑朔迷离,是是非非既是命运,又是无常: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偶然相遇,一见钟情,仿佛此前从无瓜葛,没有任何联系。或许事实上,在此之前或者之后,他们可能早已相遇,又错失多次。某个街口、某段楼梯、某个走廊、某个红绿灯的斑马线前、童年灌木丛中,或者一个打错了的电话之间,匆匆而过,面容模糊,又似曾相识。
“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纸页上才刚写下最后一个句点,便开始犹豫,开始体悟到眼前这个答复是绝对不完满而可被摒弃的纯代用品。于是诗人继续尝试,他们这份对自我的不满所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成果,迟早会被文学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放在一起,命名为他们的‘作品全集’。”(辛波斯卡《诗人与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辞 陈黎 张芬龄 译)
有论者认为,辛波斯卡的诗歌大部分是沉思,但也谈到死亡、酷刑、战争,也因其凝练、清澈、悠游从容的风格而被誉为“诗坛莫扎特”。抛开早期与政治的关联,辛波斯卡从1957年出版的《呼唤雪人》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题材触及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爱情的关系,以及她对生命的认知。从《呼唤雪人》开始,辛波斯卡找到了自己诗歌的声音,重新定位想象、诗思的跨越,难能可贵。但是我读胡桑译本《我曾这样寂寞生活》,非常感动:用句简单洁净,意象也不复杂,睿智冷静,日常而亲切。辛波斯卡让我改变了对诗歌的看法,并深刻影响了我的创作。诗人的想象力可以不离开自己半步,可以在周遭的事物中展开,可以与平常情感结下硕果。万物静默如初,万物粘连住诗意,诗人的专利由此舒展开来。
辛波斯卡在《种种可能》中写道: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在《无需标题》中她写道:
当看见这些,我不再确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为重要。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语言的无限,而是语言和交往的内在困境,如她在《巴别塔》中表达的。即使在少数几首关于写作的诗中,她也并未蜕变为形式主义者……“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必须是时代的孩子。也许我在某些方面属于十九世纪,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属于二十一世纪。我之所以属于下一个世纪,是因为我并不喜欢本世纪的所有事情。”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如是说。对她而言,可能性并非预示乌托邦性质的专制性未来,并不代表对待世界的相对主义态度,而是在人类认清了自己的必然束缚之后仍不懈求索而得到的自由,是召唤希望的入口。她相信个体的、日常而微弱的、对雄辩具有天然体抗力的声音,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隐秘小径,尽管它曲折而漫长。她在文茨卜的访谈中说过:“我觉得我只能拯救这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部分。当然还有别的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拯救这么一个很小的部分。”(参见胡桑《碎语、奇迹市场或希望》,《我曾这样寂寞生活》,2014年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这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诗句,用来总结他的好友、另一位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一生恰如其分。
诺贝尔文学奖给予辛波斯卡授奖辞说:“通过精确的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由这样的观点出发,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
《纽约时报》评价说:“她的诗可能拯救不了世界,但世界将因她的作品而变得不再一样。”
每个开始
毕竟都只是续篇,
而充满情节的书本
总是从一半开始看起。
2012年2月1日深夜,辛波斯卡因病逝世于克拉科夫那所她居住近半个世纪的屋子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沉睡中写满了她88年沉重而又轻盈的一生,平静地画上了一个圆润的“逗点”,正如她在《墓志铭》(陈黎 张芬龄译)所写的那样:
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
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作者简介】
曾蒙,本名冉超,四川达县渡市人,70后诗人,毕业于西南大学,现供职于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写作逾三十载。 16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被收入多种选本。2005年创办中国艺术批评网,2012年创办中国南方艺术网。著有诗集《故国》《世界突然安静》《无尽藏》等五部,部分作品在马来西亚、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