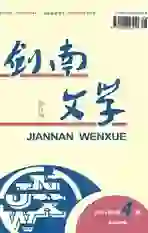夺补河畔的白羽毛
2024-08-22王琴
王琴,四川平武人,有作品发表于《散文》《莽原》《广西文学》《剑南文学》等刊物。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夺补河养育了神秘的白马藏族。
夺补河是涪江左岸最大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平武县西北的原始森林——色润坪大窝凼。源头处海拔4233米,流域面积1490平方公里,河长119公里,河道陡峻,流经平武白马、木座、木皮等藏区,在距离平武县城十公里处的铁笼堡汇入涪江。
这是地理意义上的夺补河。
在夺补河两岸有十八个藏族寨子,光是寨名就带有远古原始的气息:稿史脑、伊瓦岱惹、亚者造祖、厄里、扒昔加……这些寨子的木板房沿河而建,头戴插有白羽毛的白色毡帽、身穿色彩艳丽的藏袍的白马人生活在这里。
这是我第一次去白马时留在记忆中的信息,这是我想要记录下来的人文意义上的夺补河。
几年前的夏天,我陪同外地的朋友乘坐一辆当地人的包车去王朗保护区,在厄里寨停留了一天。那时还没有修建高速公路,寨子外是一条土路,车子一过,烟尘四起。路的右侧是一栋栋藏式民居,三层木板楼,明亮的褐黄色墙体,屋顶上站着一只昂首挺胸的白色公鸡。路的左侧就是夺补河,水面不宽,但水流很急。几个藏族姑娘背着背篼在河边走过,一身色彩艳丽的藏袍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很是耀眼,白色毡帽上的那一根根长长的白羽毛随着步伐的移动轻轻飘摇。
朋友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举起相机开始连续地“咔嚓”,他说,根本不用找景点,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美景图。
我们住在厄里一户杨姓的藏民家,这是一户最早接待外来游客的民宿。朋友来自山外的都市,对藏区的一切都充满了小孩一样的好奇。他说,走过很多藏区,就没有看过帽子上插白羽毛的藏民。
美丽的杨青青是民宿的老板娘,她的藏名叫索门早,肤色略黑,爱笑,表情丰富,戴了一对绿松石耳环。她在有火炉的屋子里给我们烙饼,朋友追着她问,关于他们身上的服饰,关于屋顶上的白色公鸡,还有他以为有的漫山遍野的牛羊。
青青笑着说,每来一个客人,都要问同样的问题。她半弯着腰,翻动着放在火炉铁皮上的面饼、土豆,手烫到了,赶紧放到嘴边吹一下,又去翻动。一边干活一边开始介绍他们这个民族古老的故事和一些风俗习惯。
白马藏族在历史上是白马番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已经消失了的神秘氐族。传说,他们原本生活在平坝,就是江油的“蛮婆渡”一带,三国时,受了诸葛亮的欺骗,才全族搬迁到这远离平原大坝的深山中。屋顶上大白公鸡是他们的保护神,在一次遭受外来入侵者的夜袭时,多亏了一只白色的公鸡跳到最高的屋顶上引颈鸣叫,惊醒了梦中的白马人,他们才躲过了灭族的灾难。从此以后,公鸡就是白马人心中的神,在屋顶上供着。男女老少头顶的毡帽上插着的白羽毛也成了这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
至于牛羊,青青抿嘴一笑,说,那就去牧羊场吧,自从王朗成了保护区,就不允许在山里散放牛羊了,要保护山里的植被。
朋友听了青青的介绍,竖起大拇指夸赞她有知识,懂得多说得也清楚。当他再问起有哪些风俗时,青青卖了个关子,说多来几次就知道了。
在白马吃饭,有着无关礼仪的豪迈。寨子里的白马姑娘端着酒碗唱起了祝酒歌,是白马本地的语言,虽然听不懂歌词,但那高亢嘹亮的嗓音就像要掀翻屋顶飞上云霄一样,令人惊叹。歌声中,三碗蜂蜜酒下肚了,是温过的蜂蜜酒,从唇边到肠胃一路下去,没有白酒的辛辣,只有适度的熨帖。食物摆放在长而宽的板凳上:剁成一指长的腊排骨,切成一寸厚的腊肉,荞面皮,烤熟的土豆。虽然放了筷子,但是没有人用筷子,手就是筷子,拿起来就啃。朋友手里拿着一块排骨,顾不得擦去嘴边的油渍,哈哈笑道,吃得真是酣畅淋漓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人生最畅快的事也不过如此。
白马姑娘一旦说起本民族的语言,她们就在瞬间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语速快而热烈,脸上的笑是自家人才有的松弛的会意的笑。白马人的语言只有本民族才能听懂,这是上天留给白马族最后一点独属于他们自己的秘密。
白马人是没有s2hnykmuraR2rF1t/V1m/w==文字的,只有口口相传的语言。在口耳相授时,这个民族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大,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朝代的更替中,历经艰难也要一步步走下去,从远古一直走到现在。
杨青青家有一间小陈列室,摆放着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物件,挂在墙上的几张色彩丰富的面具吸引了我和朋友。面具是整块木头雕刻的黑熊、老虎这些林中猛兽的面孔,浓黑的眉毛,圆睁的大眼,露出獠牙的血盆大口,额头上盘绕的两条蛇,整个面部表情凶狠狰狞。青青说,面具在白马语言中叫“曹盖”,每一年的春节,寨子里的祭祀活动中,“跳曹盖”是最重要的活动。在青青的描述中,我仿佛看到了白雪皑皑的冬季,在夜晚的篝火边,一群人拿着大刀,穿着白色的羊皮袄,头顶上披着牦牛尾,脸上戴上凶猛可怖的曹盖,在激昂的锣鼓声中,迈着粗犷的步子,跳起了再现祖先为了生存激战厮杀的场景的舞蹈。这是白马人对祖先的敬畏和怀念,也是对新年的驱灾与祈福。这是他们的信仰。一个民族有了信仰,才不会迷失自我,才会走得更远。
我记起来刚刚进入白马境内的大门口时看到的一座山,同车的师傅说,那是白马人的神山,叫“白马老爷”。看到眼前的曹盖,也回忆起了看到的一段资料:白马人崇拜自然,日月水火、山石草木,都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崇拜就是敬畏,这又契合了现在的观点,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才是长久的自然之道。想到这里,我对这个民族又多了一份敬意,他们骨子里的一些品质最原始,也最美好。
牧羊场不远,走走就到了。那是夺补河边用栅栏围起来的一片草地。果然,有一群摇着尾巴只顾埋头吃草的牛羊。白色的山羊,黑色的牦牛,在静谧的山中悠然自得。我们在草地边坐下来,有一只小山羊抬头看了我们一眼,轻轻地“咩”了一声就跑走了。夺补河的水就在抬眼之外,潺潺的流水声如轻音乐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我们在厄里寨子晃晃荡荡地随意走走停停,不知不觉中,天色就暗了下来。山里比山外黑得早,气温也低了很多。阳光隐去了,山风起来了,夺补河周围的群山成了寨子青黛色的幕布,一场篝火晚会就要开始了。
寨里的人不多,一家来了客人,就是一个寨子的客人。杨青青家的院坝里已经点燃了一堆篝火,篝火旁聚集了二十多个白马男女,他们围着篝火排起一个圆圈。看见我们,几个女孩嘻嘻哈哈地跑过来,拉着我们的手就加入了圆圈。音乐响起来了,非常欢快的曲调,是我听过的白马歌曲《白羽毛飘起来》:
寨子里的姑娘出嫁了,出嫁了
哎呀呀呀哎呀呀
白羽毛飘起来
哎呀呀呀哎呀呀
飘起来,飘起来
随着音乐声,圆圆舞跳起来了,气氛热烈,篝火越烧越旺,噼啪作响。火光照亮了白马姑娘红扑扑的脸蛋,精灵一般。
我们随着圆圈不停地移动脚步,沉浸在这歌中舞中,浑然忘了身在何方。
圆圈舞后,是敬酒歌。一个姑娘唱完,另一个姑娘又唱,她们站在篝火边,举起酒杯,唱山唱水唱自己,一曲罢了,酒也就喝下去了。歌声悠扬,在白马山寨晴朗的夜空中传播,远处的山在听,近处的水也在听。
不知道这篝火什么时候熄灭的,不知道喝了多少杯酒,只记得我们是在歌声中进入了梦乡,一觉天亮。
第二天,我和朋友吃过早饭,准备出发去王朗了。杨青青穿戴好民族服饰,站在路边挥手送行。晨风中,白色毡帽上的白羽毛轻轻地摇摆,夺补河的水安静地流淌。
(节选自征文《沿河而下,水里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