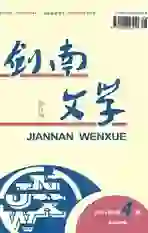干涸的河
2024-08-22张玉博
张玉博,1996年生,河南开封人,文学硕士,现居四川绵阳。2022年开始创作,首篇短篇小说发表于《广西文学》。
一
亚男,我累了,你已千百次将我送上这条路,又在最后关头把我喊回去。白日里,你也常走这条路。路两边长满你讨厌的锯锯草,夏天时它们的小刺须会在你的胳膊腿上留下划痕。它们于我,无碍。可我不想徒劳地徘徊于此。
你第一次看到我时,我在哭。是你要哭。你为什么要哭,是因为闻到了醪糟红糖鸡蛋甜甜的味道吗?我在这样的味道里走进墙角。你让我替你哭,替你蹲在墙角哭。那里叠摞着两口木箱子,乌漆麻黑中只有铜锁扣泛出一丝亮儿。充当箱子架的是个方桌,下面织满蛛网,拦截了不少灰絮。我的脸上黯淡无光,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遇到墙角陈年的泥灰时发出“噗噗”的气泡声。这些被驱逐出的霉味最后又融进木箱。我抬头看上逸的气时,脸上反光的泪痕照亮了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我们长得一模一样。我在哭,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哭。你看到我哭,短暂惊讶后满意地咧了下嘴,睡了过去。
在你入睡之后,在我回去之前,我知道了你为什么哭。那天快中午时,你拎着装了不少泥鳅的桶回到家,发现爸爸妈妈和新的小弟弟回来了。他很新,连名字都没有,爷爷奶奶叫他“小乖乖”“大孙子”。所有人都围着他,爸爸和爷爷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忽高是习惯性地大着嗓门说话,忽低是立刻想到莫吓到小弟弟。你刚察觉时感到好笑,一边试图挤过大人的腿到妈妈床边仔细看弟弟,一边怪腔怪调地模仿。爸爸发现你泥猴似的样子和怪模怪样的学舌后,一下子火了起来,骂你没大没小,骂你腌臜。
奶奶把你从人堆里解救了出去。你委屈地蹲在院门口的河塘边,任由奶奶絮絮叨叨着给你洗手洗脚。这时她才看到你手里拎着的装满泥鳅的小桶,惊呼数量之多。你高兴了起来,甩着俩长长的麻花小辫给奶奶讲抓泥鳅的趣事。
那天的阳光很柔和,散发着多彩的光晕。你与邻居巧姐姐一同去村头抽干了水的河塘捉泥鳅。你们不敢走进河塘中央,只在边缘圈了一片区域,裤腿高高挽起,弯腰认真地翻着稀泥。河塘里挖泥鳅的人很多,“哇哇哇”“好大一条”“诶诶诶”的声音此起彼伏。冰冰凉的泥土把你的脚连同小腿都包裹了起来,重心不稳的你紧张地把十个脚趾张得开开的,仿佛这样能生根般把地面抓紧。你的运气很好,不大会就捉到一条小泥鳅,灰褐色的背,银白的肚皮,身量不长却肥肥的。你高兴地捧在手里举给巧姐姐看,结果小泥鳅一个打挺就掉进了塘泥里,你们四只手赶紧去捉,抓来抓去,好不容易才又把它逮住放进了小水桶。巧姐姐不仅捉了许多小泥鳅,还捉了几条黄鳝。
你炫耀似的举着小桶给奶奶看,看到里面浑浊的水,突发奇想地要把小桶放进河塘里换水,被奶奶拦了下来。河塘水深,会给小泥鳅们逃跑的机会。奶奶的话很密,平日里你懒得听,可今天她是家里最疼你的人,你愿意听她的,回家用水缸里的清水给泥鳅换水。你想养几条泥鳅玩,它们软软的身体看起来很好玩。小弟弟看起来也软软糯糯。他闭着眼,嘴巴嘟囔着吐泡泡,因太黑而显得湿漉漉的头发支棱着,偶尔粉嫩的小手小脚不老实地踢弹两下。妈妈躺在床上,侧着头看弟弟,脸上洋溢着幸福。你也想进入这个幸福的光圈里,于是你问:“妈妈,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呀?我也像弟弟一样总是吐泡泡吗?”“你?忘了,大概一样。”妈妈温柔地掖着弟弟的襁褓。“怎么会忘记呢?”这话你没问出口。你和爸爸妈妈并不相熟,两个月前,他们才从打工的地方回来,在此之前,你没见过他们几次。
你离开小弟弟,到院子里找泥鳅玩,可一条都没了。浓郁的鲜香味从厨房飘出来,你听到奶奶说:“这可全是亚男的功劳,小丫头一早就去河塘里捉泥鳅了。”巧姐姐的黄鳝被单独养在一个搪瓷盆里,几条黄鳝游在团簇的荷花和两只鸳鸯上。阳光下水里的黄鳝浑身流动着金沙,排列整齐的斑点仿佛威严的盔甲。你在想象里变成黄鳝,在浅溪中自在地游动,太阳出来后,爬上露出水面的青礁石,美美地晒一场阳光浴。阳光把全身晒得暖洋洋时,巧姐姐把搪瓷盆端进了阴凉处。“为什么端进去啊?那里冷,让黄鳝晒晒太阳吧。”“傻瓜,黄鳝和泥鳅都喜欢阴冷潮湿的地方,放太阳下会被晒死的。”“怎么可能有动物不喜欢晒太阳呐!”你觉得巧姐姐单纯是不想让你看了。
那天,你捉了一小桶泥鳅,可你一条都没有吃到。那夜,奶奶没有搂着你睡,她在照顾妈妈和小弟弟。于是,你唤醒了我,看我在墙角哭泣。可流着泪的我,分明在你的梦里看到你拥有水中黄鳝的自由和七彩的莲瓣,你内心的快乐营造了它们。我无以为食,只好重新陷入沉睡。
二
亚男,入睡的日子里,我睡得并不安稳,你那低却密的呼唤像是额前的碎发,若有若无地干扰着我的睡意。奶奶不再总搂着你睡觉,爷爷天天把“乖孙子”挂嘴边,这些微不足道的痛苦,已无法把我唤醒。更何况,爷爷带你去田里捡宝贝时,你的快乐先于痛苦到来。或许你并不十分清楚,但那时的我终于能安稳沉睡,直到快乐的后果出现。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清晨或傍晚,这些行人寥寥的时刻,视野朦胧。起初,你穿过熟悉的田埂路时,衣裳收获了锯锯草的碎屑和新鲜的露水,锯锯草的刺挠让人烦恼,露珠的凉意又让人快乐。爷爷双手背在身后,随意地打量着四周,欣赏风景似地站定,漫不经心地说,这田里不仅能长东西,也能藏东西。这些你当然知道,田里长庄稼,能养鱼虾、泥鳅和黄鳝,还藏有数不清的蜗牛、青蛙、蛤蟆和蛇,所以你也只是站定打量。爷爷却催促着让你进田,可露水混合着泥土早已把你的腿脚裹成泥塑,你僵直着腿挪不动一步。快去,一会儿人该多了,好好找,别踩住了。爷爷催促着,推搡着。你走进了田里,挥动着随手折的小棍,低头看着裤腿上的泥,裂纹随着脚步张开又闭合,像是在呼吸。低头好好找,别踩碎蛋了!田埂上传来充满怒气的低沉声,吓得你打了个激灵。
离开田埂回家时,你和爷爷肥大的口袋里总装着几个蛋。你小小的手紧张地固定着鸡蛋或鸭蛋,防止它们撞碎。往家走时,腿上的泥被吹干,开合的裂纹逐渐剥离、掉落,泥塑露出真身,皱巴的八分裤。你低着头,厚厚的刘海遮住视线,穿过街道,回到家,把口袋里的蛋放进厨房小竹篮里。至此,别家散养的家禽下的蛋成了你家的。小弟弟每早都能吃到香喷喷的鸡蛋羹。鸡蛋羹出锅时,奶奶会滴上几滴香油,用勺子轻轻划开,舀一小勺抿进弟弟的嘴里。像奶奶用舌头舔香油瓶嘴那样,等在旁边的你,会把碗里弟弟吃剩的鸡蛋羹刮个干净。通常这些时候,你很快乐。爸爸妈妈离开后,你也爱上了小弟弟,他让你抱,还会牵你的手。晚上,你闻着奶奶和小弟弟的味道入睡,会感到幸福。
我颤抖着醒来,心脏被一株急速生根的藤蔓撑满,它不停地不停地抽发,细密的根须沿着血管生长,堵在咽喉缠作一团。我栽倒在学校的水池旁,脚下是横流的冷水,你看到我了吗?我想你没有看到,你在恶狠狠地洗手洗脸洗胳膊,厚厚的刘海湿溻溻地糊在脑门上,褪色的衣衫上沾满泥污、油渍。同学们在操场中间玩,你水淋淋地站在操场边的篮球架下,等待太阳把你烤干。操场中央的小学生们在玩游戏,里面有你曾经要好的朋友。你干裂的嘴唇将自己出卖,你曾经的好朋友也没做到“保证不告诉别人”,你“捡”鸡蛋的事情就这样在低语里传播。
“小偷”“叫花子”“臭水沟味”……你不想一次次听背后密密麻麻传来的夹杂着嬉笑的声音。你将我推了出来,挡在你的身前,丝毫不顾我苍白的嘴唇和干涸的眼眶。曾经飞扬的麻花辫被芝麻粒大小的虱子吞噬,我顶着参差的短发从街上走过,佝偻的背一截截塌陷,直至扑倒在地。你踏着我回到家中,抱着弟弟试图汲取家庭的温暖。可我知道你的痛苦来了,它们如潮汐般席卷我,填满我。墙上的相片框里卡着爸爸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弟弟的百天照还有他和妈妈的合照,爷爷奶奶为自己准备的遗照也夹在里面。里面唯独没有你。
亚男,你沉默着将枕头浸湿,黑暗中你脸上的泪水泛着光亮。黄鳝不喜欢晒太阳,因为太阳会将它冰冷的盔甲腐蚀。你不再大笑,也不喜欢听别人大笑,震耳的笑声会损坏渐硬的心。在这样的夜晚里,你成长了,你看到了我,你知道了我,你以我为矛为盾,去攻击去防御。当我把双手捂在操场大笑的人嘴上时,站在篮球架下的你笑了。你在想象中完成复仇,乐此不疲。
三
当你指挥我像操控一个木偶,供自己取乐时,我虚弱不堪,你的快乐不是我的补给品。你似乎适应了一切,独自一人上学,和爷爷去田里,和奶奶弟弟一起入睡。简单,反复。冬天来临时,冷风白雪将你的味道掩盖,你瑟缩却快乐地走进教室,把头埋在书后,看窗外的飘雪,得出人生不过如此的结论。亚男,你的人生如果能一直如此平静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成为那条路上的徭役,不停地往返。
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回来了,相片框里的一家人高高兴兴。玩具、零食、新衣服,你沾光吃到一些零食。那晚弟弟没有和你一起睡,你把牙咬得嘎嘣嘎嘣响,我得以恢复。你恨的是谁,又是谁让你难过?墙角的哭泣早已停止,我打开房门,站在院子里,看家里还亮着灯的屋子。年轻的夫妇逗弄着孩子,弟弟笑个不停,明明白天他还不愿被爸爸抱。你再一次感受到背叛,这个70厘米高的小人儿就这么轻易被收买了。现在的你比他刚出生时更讨厌他。
你没有讨厌他太久,毕竟你的人生没被眷顾,连如何恨都不想教会你。我再次被唤醒,看到你睡在一张小床上,不是奶奶那个屋子。从你的床边到院门口的河塘边,我穿过了两道门,一道是木门,一道是铁门。我止步于河边。没学会稳稳当当走,就开始踉踉跄跄跑的弟弟,没来得及在河边停下。当时你和爷爷在院门口的土堆儿里擦蛋壳上粘的屎粪,你担心被同学看到,低头干得飞快。都装进篮子后,又抢着把篮子送去厨房。爷爷进院子里找铁锹,准备把土堆儿铲得规整一些。弟弟乖乖地蹲在那里玩土。乱哄哄的狗叫声响起时,你刚放下鸡蛋篮,在厨房里寻摸吃食。你下意识想起弟弟在院门口,怕狗咬到他,你又飞快地往院外跑去。流窜的群狗没有咬弟弟,但吓坏了他,他摇晃着往前跑,边跑边哭,直到掉进表面漂着一层碎草枯枝的河塘里。前后脚出门的爷爷和你眼睁睁看着弟弟栽进去。爷爷跑着跳进河塘,你捡起有着长柄的铁锹,想递给爷爷用它捞弟弟。
爷爷抱着弟弟满身脏污地从河塘里爬出,斜斜歪歪地往村诊所跑。后来,救护车拉走了爷爷奶奶和弟弟,还有在家的大伯。吃晚饭时婶婶一遍又一遍地问你当时的情况,你重复着回答,直到她将这出悲剧归咎于爷爷奶奶偏心,给小儿子带孩子,才停止索问,转为细数她家因不得偏爱而失去的种种财物。你不懂这些,你只是懊恼。如果你牵着弟弟的手一起把篮子送回家,如果你陪弟弟在院门口玩,等爷爷出来再去送,如果奶奶洗衣服时愿意让弟弟玩水,如果爷爷再跑快点……可惜,你独自一人睡在黑夜里,“如果”只存在于假想中。
害怕,后悔,侥幸,大胆设想。弟弟还在医院,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会给他治疗。不久前吃年夜饭时,爸爸妈妈说以后要接弟弟去城里上学。尽管他们弄哭过弟弟,但也会哄他。总之,无论如何他们的爱没给过你。你身上的气味,乱糟糟的头发,实在不能让人心生爱意,尽管这不能构成父母不爱子女的理由。
我绕着河塘走到天亮,你睡不安稳,各种怪象在你梦里出现,你抽搐得和医院里的弟弟一样。几天后他们都回来了,包括刚走没几天的爸爸妈妈,爷爷灰黑着脸、塌着腰走在后面,大伯搀着奶奶。弟弟,你再没见过。你设想的“如果”,有一项成了真。你捡起的铁锹,被爸爸拿起,敲碎了几个狗脑壳,它们的主人不敢阻拦。
爷爷花大价钱请来算命先生。算命先生从车上下来,并不进院子,而是观察四周后点了点门口的河塘。河塘正对大门,以河水流向论,院落位于河左,为凶;因日益堵塞难以流动而变浑浊的河水,亦凶,阻运势妨体健。进了院子,算命先生看看这看看那,不停地掐算着手指,最后说幼辈子女里有六亲缘薄之人,当尽心爱护以免去运增煞。听到这话,奶奶抹着泪搂住了你。爷爷重重地叹了口气,对一家人来说,弟弟可不就是这个六亲缘薄之人,早夭就是因为没得到尽心爱护。算命先生走后,爸爸不知从哪找来抽水机,堵上河塘本就狭细的两个端口,一下午把里面的水抽干了。没人敢阻拦。没必要为一个早已发臭的垃圾河发声。
自那日起,你被搬进堆放粮食和农具的偏厦。因为你一个女娃家能吃能干,可老天偏偏不收,奶奶看到你就会抹眼泪,爷爷看到你就忍不住发火。爸爸妈妈的屋子,他们没想过让你住进去。也是从那夜起,我开始游荡在这条路上。
四
住进偏厦的你,像被抽干水的河塘,被太阳暴晒过的黄鳝,干枯无色。暗夜里,犁、锄、耙的冷色诱惑着你,你躺在小床上,看我挨个拿它们往身上划。你学会了在想象里伤害自己。你羡慕我的勇敢吗?可惜你在学会勇敢之前,先学会了为他人着想。
爷爷,奶奶,他们失去了心爱的孙子后,又失去了偏爱的小儿子与儿媳。爸爸妈妈整日吵架,爷爷不敢劝阻,他是罪人,奶奶也不敢,她也是罪人。你更不敢。你去喊他们吃晚饭时,看到爸爸正侧身在床头的凳子上卷烟。点燃后粗糙的烟卷在爸爸妈妈之间轮转,不成形的烟雾模糊了他们的面容。你拘谨且低弱的声音,还未传出就弥散进烟雾。那根短短的烟并不经抽,最后一口的归属引起了争执,妈妈没有交出去的意思,久没接到的爸爸挣扎着起身去抢。撕扯,谩骂,打乱了黄昏的步调。爷爷奶奶进来劝阻,发现了异样。很久没抬过头的爷爷,拿起门口的扫帚开始打爸爸。朦胧的房间像是一场电影,你是观看者。
第二天爸爸妈妈走了,你以为他们是去打工。在后来漫长的时间里,你没接到过他们的电话,他们再没寄过钱,你才反应过来这不叫走,这叫消失。他们抛弃了你们。你和爷爷奶奶回到了弟弟没出生之前的日子。可到底不一样了,你们都驼着背,沉默不语。
爷爷再次叫你去田里捡蛋补贴家用时,你去了“婴儿沟”。那条长满锯锯草的道路尽头有个老桥洞,你以前听倚着槐树讲故事的老头说过,老桥洞下的那条河沟其实叫“婴儿沟”,里面有早夭的婴孩,也有被遗弃的多余女婴,深夜常有啼哭从那里传遍田野,与地面闪着幽光的坟包呼应。眼前的老桥洞和周围的田地一样坑洼不平,干涸地发不出一声嚎叫,你突然理解了音讯全无的意思。弟弟。爸爸。妈妈。音讯全无。六亲缘薄当尽心爱护。沉默的你把这条路也走沉默了,虫鸣鸟叫不在,色彩缤纷皆无。你在这条路上走进初潮,走进16岁,走进了不再需要我的时空。
亚男,你想清楚了吗?彻底放开我,让我去陪弟弟,让我替你回到你本该在的地方,在道路尽头?你也要离开吗?当个流水线女工,结婚,生子,过日子。
亚男,16岁的你没有得到爱,没有学会恨,用你那迟钝的心去争取普通生活吧。周身流彩的我竟被你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