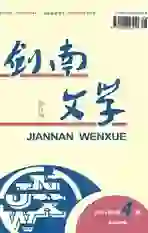春见
2024-08-22朱斌
朱斌,笔名龚旭,青海果洛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现居常州。2010年开始在《莲池》《骏马》《椰城》《火花》《大地》《地火》《牡丹》《短篇小说》《延安文学》《北方文学》《四川文学》《中国铁路文艺》等文学期刊发表短篇小说。
一
小赵是老爷子请的护工。
在省二医院泌尿外科病房里一见到小赵,我叫了她声“阿姨”。论年龄,我是不该这么叫的。但是在我工作生活的江南,对她这类人普遍都是这么称呼的。可是,生于青海长于青海的小赵却不受用,她大大方方地要和我兄妹相称。在问过我属相后,小赵振振有词:“你属猴我属牛,你比我大五岁呢,再不要叫我阿姨了。你若不嫌弃,就叫我妹妹吧。”
我一愣,多少感到有点尴尬。她一口一个“爷爷”地叫着我那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却要和我兄妹相称?但是,此时此刻,正当用人之际,我又怎敢嫌弃她呢。
元旦那天,我和老爷子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有小赵照顾着,一切都好,尿出的尿也不那么红了,有时甚至不见血色,估计再有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我听着不放心,追问他尿血的原因找到了没有,他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是炎症在作祟。我算了算,至此,他已住院五天了,每天挂几大袋子的盐水把膀胱中的血块往外冲。前两天,他还可以自己外出吃饭,并没有请护工。到了第三天,就只能成日躺在病床上,不得不请护工了。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做好了随时赶过去的思想准备。果然,元旦过后,我刚上了半天班,正在单位食堂吃午饭时,老爷子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尿不出尿了,难受得很,他的主治医生让我立马赶过去签字做手术。我不得不连夜乘飞机往西宁赶,第二天上午九点前赶到了省二医院泌尿外科病区。术前谈话把我的心紧紧地揪了起来,我一听“膀胱占位”几个字,大脑中就一片白茫茫,只听得清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谁知在等着做手术的节骨眼上,小赵和我们玩起了心眼儿。她对我家老爷子说:“爷爷,哥哥已经来了,你把这几天的钱算给我,我要走了。”
听得老爷子着急起来,带着恳求的语气对她说:“他刚来,啥都不熟悉。我就要进手术室了,你现在可不能走啊。你得等我做完手术,能下床了再说走的话啊。”
小赵把头转过来看着我说:“哥哥,你是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大女儿来过了,给我送了感冒药和八宝粥,还帮着我把爷爷换下来的衣服给洗了。我女儿说:妈妈,你在这儿都不能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感冒都这么多天了还不好,不要做了,回家吧。我老公也打电话来劝我回家,说一天才二百块钱,别干了,回家来吧。现在哥哥你来了,就让我走吧。”
我听明白了,这个老妹儿是在坐地起价呢。我问老爷子:“你一天给妹妹多少?”
“讲好的,我每天给她二百二,出院时结算。”
“妹妹,你看这样好不好?从今儿开始,一天给你增加二十元,二百四一天行不行?”
小赵没有马上回答我行还是不行。她并不理会我和老爷子急切的眼神,两颗黑眼球就像两个黑色的算盘珠子左右摆动了几个来回后,点开手机,小声地对着手机说道:“哥哥来了,爷爷不用我了。我这就把五天的钱结了,我再不做了。”
她怎么这么说?她这是在和谁说呢?不及多问,我和老爷子赶紧交流了一下眼神,急切地央求她:“过几天老爷子出院后可能还要请保姆。你再辛苦几天,把他照料好了,就请你到家去做保姆,不比你在医院里做护工强?”
我到省二医院时就注意到了,好多护工就睡在病房外的地上。到了夜里,小赵在地上铺块毡子,蜷缩着睡在老爷子的病床跟前,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还有那些找不到活儿干的人,天知道他们夜里住哪儿。要知道,三九隆冬的,在青藏高原上过夜,不要说露宿街头,就是住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也是能把人冻死的。
可能是要请她做保姆的话打动了她,小赵端起褐色的塑料暖瓶盖头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后对我说:“哥哥,不是我故意要涨价。讲好的,爷爷一天给我二百二,我还要每天给上家二十。”
“给上家二十?上家是谁?”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护工这次没空,是她把小赵介绍来的。她就是小赵的上家。她按日从小赵的工钱里抽二十,这是她们间的规矩。”老爷子给我解释道。
“哥哥,你看,我刚才把这六天的一百二十块已经转给她了。如果还想我再做下去,我想请哥哥帮个忙。”
她一边说一边把手机点开来递到我面前让我看。
“什么忙?你说。”
“我刚刚给她讲了,哥哥来了,爷爷再不用我了。她要是打电话来问,你们也这个样子说给她听。”
嘿,这小赵虽说是个文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脑子还挺鸡贼。原来她这是想把此后每天的二十元抽头给省下来。成人之美,何乐而不为。但我没有立刻答应她,而是把目光投向老爷子,希望他来答应她。谁知老爷子叹口气,摇摇头,没有作声。正当我要开口应承下来时,老爷子的手机响了。我看见小赵的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两眼巴巴地望着老爷子。老爷子拿起手机接听了一会儿后说道:“对,我儿子赶过来了。小赵今天完了就不做了。”
我和小赵会心地笑了起来。
本以为一切都搞定了,不料这些护工的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我正和老爷子说着话,猛然进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劈头问我们:“护工呢?”
“在外面。”我毫无防备脱口而出。
男子听后转身就向病房外走去。我突然反应过来,赶紧跟了出去。
小赵正在泌尿外科病房外阴暗的长廊上百无聊赖地来回走着,那男子上前一把扯住她问我:“她是不是你们的护工?”
“你干什么?”我警觉地问道。
那人并不回答我,手上加力把小赵推了一个趔趄,凶狠地压低声音吼道:“走走走,赶紧走。”
我赶忙上前把那又矮又瘦又猥琐的男子拽住,问他:“你要干什么?”
“不要她在这儿干了。”
至此,我心里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似笑非笑地对男子说:“我家老爷子今天就要手术了,你把她赶走,谁来帮我照顾老爷子。”
“给你换个护工,马上就可以来。”说着,猥琐男挣开我的手,又去推搡小赵:“你走你走,还不快走!”
面色煞白的小赵被猥琐男一推一个趔趄,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火了,上前用身子隔开小赵,伸出两手按住猥琐男的双肩,盯着他的眼睛说:“你搞清楚,是我请护工。我爱请谁就请谁。现在,我就请她了,你想怎样?”
猥琐男恶狠狠地回盯着我的双眼,用力扭了几下肩膀,但没挣脱。他不知今日遇上的我是一个练家子。我双膝微弯,两手按在他膀子上,看似普通的一按,实则使的是形意拳中的虎扑。正所谓打人不露形,露形非为能,我要是发力,能把他提起来给扔出去。但老爷子就要做手术了,在这当儿我不想把事儿弄大,只想稍事惩戒让他知难而退,所以我两手稍一用力,把他摁得两腿打弯半跪了下去,然后就松开手看着他说:“还不快给我滚!”
猥琐男灰溜溜地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回过头来冲小赵发狠:“你给我等着。”
我和小赵回到病房。
在病房里把门外发生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的老爷子对小赵说:“你看你,弄巧成拙,把事情做下了吧。今天要不是我儿子在,你就被他弄到医院外打了。”
“光天化日的,不至于吧。”我以为老爷子在吓唬小赵。
“你是不知道,这儿的人野蛮着呢。今天你要是不在这儿的话,她肯定要落一顿打的。”
“他打我,我就报警。”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他们要整你有的是办法和机会。唉……”老爷子长叹了一口气,一边点开手机翻查着,一边嘟囔道,“你看你,我这都要进手术室了,你给我整了这么一出。喂,我给你说,我后来想了想,小赵我还得留下用几天。你不要和她计较,一天二十块钱,到时我直接给你。我,你还不相信么?说好了就一分都不会少你的。你们再不要找小赵麻烦,听懂了么?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啊,我这都要进手术室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对不对?那你给小赵说几句,说开了,今后还要见面,是不是?”
说着,老爷子把手机朝向小赵,只听一个得意的女声清晰地传了出来:“刚才是我让我弟弟特意赶过去看看的。我就说了嘛,你果然在耍我。本来是要给你点颜色,教训教训你的,现在既然爷爷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老爷子收起手机后,又不放心地叮嘱小赵:“这两天你要是出去,一定要让他陪着你。我本来还想让你去把你俩的午饭打来,现在他走不开,我又怎么敢让你一个人去。你看你把事儿闹的!唉,这样吧,等我进了手术室,你在门外等着,让他去吧。”
老爷子转头望着我说:“等我进了手术室,你和麻醉师谈过话签了字后,就去吃午饭。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吃完后给她带一个干拌就行了。”
小赵听后不满地嘟囔道:“又是干拌。”
这时,护士拉着平推车进来喊道:
“六十床,手术啦!记着把假牙拿下来。”
老爷子慌忙把手机交给我,然后脱下假牙拿了出来。小赵赶忙用餐巾纸把假牙包好,正要放起来时,老爷子却又把假牙要了回去,转手交给了我。
二
老爷子的这台是急诊手术,插进去做的。从十一点推到十二点左右,然后一直拖到了下午近两点钟,手术室才空出来。此时,我已经很饿了。我只在早上七点来钟从机场开往省二医院的出租车上吃了两块面包,喝了几口矿泉水。等老爷子被推进手术室,麻醉师和我谈过话后,我的心里一团乱麻。无论是主治医生还是麻醉师,都讲了考虑到老爷子身体耐受力等因素,决定采取腰部以下麻醉,手术时间为两小时。我想索性再忍一忍,等手术做完了再去吃饭。成语有度日如年。我在手术室外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难捱。一会儿担心老爷子的那个膀胱占位若是恶性肿瘤该怎么办?一会儿担心如果出现了医生们在谈话中提及的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意外中的一种,我又该怎样应对?譬如一次手术解决不了问题,还需要第二次手术;他再也起不了床等等。就算这些都没发生,手术很顺利,可是术后呢?我只能请这么几天假,后头谁来照顾老爷子?直想得我在手术室外坐立不安。
十多年前,我家老爷子做过一次前列腺增生电切手术。那时我母亲还在,是她陪着他到山东的一个县级医院去做的。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我小姨的儿子、我父母的养子在那儿做外科医生。对于这个跟老爷子姓并且落进我们家户口本的养子,我父母投入了太多。他们不仅把他从农村带到青海,养着他从初中一直念到了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去他亲生父母生活的那个乡村所属的县医院做医生,可谓恩重如山了吧。就这样,他的亲妈我的小姨在得知我家老爷子要到她那儿去做这么个不大的手术并顺便探亲时,竟然给我打了个不该打的电话。这个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在电话中是这么说的:“知道不?你爸尿不出尿来了。”
“知道啊,我妈不是打算陪着他到您那儿去找俺弟做手术么?”
她在电话中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又说道:“姨是这么想的,你,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你爸妈,让他们……别来我这儿了。”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下定决心回答她:“我是这么想的,他们,决定去找俺弟,一定有他们的理由。我是不会打电话横加干涉的,我遵从他们的意愿。”
我心里想说的话是:他们帮你养了十多年儿子,用一下又怎么了?!
那次手术,老爷子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都是我母亲照料的。现在母亲不在了,我该怎么办?光是切个前列腺增生组织,就让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天知道这次要躺多少天!我穿着三条裤子,外面是加绒的牛仔裤,中间是厚毛裤,里面是棉毛裤,就这样坐在手术室外的红色塑料椅上还犹如坐在冰面上。我打了一个寒战,不禁想:亲人间尚且推三阻四,非亲非故、鬼点子又多的小赵能心甘情愿地侍候我家老爷子么?刚才又闹了那么一出,天晓得今后还会发生什么!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为了钱,她还有啥豁不出去的!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小赵的揣度完全是偏见的。小赵趁着老爷子做手术的空档儿,把他的病床彻底整理了一番后,来到手术室外陪我。她穿着草绿色的羽绒服,绿意浓浓地坐在我身边,很有经验地告诉我:“哥哥,你不要担心。爷爷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吧?他们没有再喊你,就是一切正常。做手术,最怕中间被喊进去。我有一次照料一个病人,说好半天的手术,早上八点不到就被推进了手术室,结果做了不到一小时,家属就被喊了进去,我们在外面等呀等,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钟才被推出来。后来那人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还是走了。我看爷爷不要紧的,你不用担心,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好好地出来的。”
小赵的话只让我把心放下了一小会儿,很快又提了起来。她的话提醒了我,要是在这个时候喊我,不是更可怕么!我紧张地不能自已,一个劲儿在心里默念着:千万别喊,千万别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为了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我刻意转移话题问小赵:“妹妹家是哪儿的?”
“我家就在机场旁边的一个乡里。”
“那儿不吵吗?”
她不解地望着我。
“我是说,靠着飞机场住,飞机起落的噪音很吵人的。”
“哥哥原来是担心这个。不吵不吵,我们家离机场有一二十里路远呢。”
这回轮到我不解了:离一二十里,还叫靠着?
她见我面带疑惑,赶忙解释道:“哥哥可能不知道:我们一个乡的地盘儿大得很,人家都说有你们江南一个小县那么大呢。”
我吃了一惊,问她:“你去过江南么?”
“去过。小时候,阿大告诉过我们,我们祖上是从南京竹子巷迁过来的。但我没去过南京,我去过泰州。我的一个姐姐嫁在那儿。前年她嫁女儿,把我们都叫了过去,住了好几天。”
“哦,妹妹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阿大阿妈养了六个女儿,就是都没上过学,不认识字。”
我一愣,还想再问她点什么,却见她点开手机看了看,对我说:“呀,爷爷这都进去两个多小时了,该出来了。”
说着话,她就起身往手术室门口走去,我也随即跟了过去。
我和她在手术室门口甫一站定,门就开了。开门的护士看了我们一眼,仍然按规矩喊了一声:“六十床家属。”
“在这儿。”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赶过去,俯下身在老爷子脸上找答案。由于是半麻,药力只有两个多小时,老爷子此时是完全清醒的。他抿着一张瘪嘴满面含笑,看了我和小赵一眼后,伸出两只手把两个大拇指都竖了起来。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我们回到病房后不久,主治医生就来了,向我们详细说明了手术情况:“恭喜恭喜,手术十分成功。现在可以排除肿瘤可能性了,占位是前列腺增生组织进入膀胱造成的。探找出血点花了点时间,找到后进行了电凝止血。接着清理积在里面的血块又花了些时间。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尽全力清除增生组织,清除了有百分之九十多吧。可惜没时间了,麻醉师已经在催我了。”
“就是就是,那时,我都有感觉了。”老爷子忍不住插嘴,“真的很感激您,没想到您的技术这么好!”
此时我才注意到,躺着的老爷子和站着的小赵都是两手合十在胸口听医生说话,我赶忙也照他们的样子把两只手合十在胸前。
“老爷子,您先别急着谢我。现在您还不能多说话,话说多了,明天伤口会疼的。”
说到这儿,主治医生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老爷子,您以前是不是做过前列腺增生电切手术?”
老爷子点了点头。
“怪不得呢。左右两侧和上面的增生组织都切除了,下面的没有切,长着长着长进膀胱了,发生了占位,虚惊一场。”
听了主治医生的这番话,我和老爷子当着人家的面没说什么。后来和他谈起来的时候,我对他的那个养子颇有微词。老爷子说:“算喽,今后可能都不会见面了,还怪个啥嘞。”老爷子这一说让我想起,我母亲的葬礼,她的养子没有到场。
看得出,手术十分成功,主治医生也很激动,他在病房里和我们说了好一会儿的话,临走时还详细叮嘱小赵:“记着两小时给他翻下身,按摩按摩他的下肢。晚上六点,吃一片降压药,水尽量少喝,明天才可以放开喝。若是饿的话,可以给他喂点粥……”
主治医生交待完就走了。老爷子想了想,在手机上打了几个字给我看:
她在这儿,你去吃饭。
这时已近五点了,好在医院旁的一条小巷子里各色饭店鳞次栉比,大都全天不打烊。我没有按照老爷子事先交代的那样,自己先在饭店吃好,然后给小赵带一份干拌回去,而是要了两个大份干拌。在等面的时候,我又挑了八十多块钱的一大块牛肉,特意关照店里的师傅说:“切好加到两份干拌里,一定要加得一样多。”
我拎着两份加肉干拌赶回病房,先拿了一份给小赵。她望着袋子里的另一份说:“哥哥,你还没吃?”
“没有,咱们一块吃。外面冷得很,不晓得面还热乎不,赶紧吃吧。”
她打开饭盒后,两眼一亮:“还有这么多肉!”
她望着我的饭盒问我:“哥哥,你够不够?我把肉拨给你一些吧?”
“不用,一斤出头的牛肉呢,咱俩平分,快吃吧。”
老爷子干咳了两声,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着我,我没反应过来,也顾不上反应,因为肚子实在饿极了。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后,发现小赵只吃了一半面和三分之一左右的牛肉,就问她:“不喜欢吃这个?明天哥带你吃别的。”
“不是,剩下的等晚上饿了再吃。就不吃晚饭了。”
“吃了吧,晚饭我再去买。”
“真的不用了。我们晚饭一直是这样的,把中午剩下的热一热就行了。”
“行了,老儿子,晚饭你自己吃去,爱吃啥吃啥去,不用管她了。”老爷子迫不及待地插了进来。
“你咋又说话了,医生不是说了吗,今天你还不能多说话么。”
我想夜里就在医院里陪着老爷子了,小赵说:“哥哥,你回去吧。我在这儿,用不着你的,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有她在,确实用不到我。倒尿盆、找护士换药、洗洗弄弄什么的活儿,小赵一人全都料理了,完全不需要我插手。一点儿经验都没有的我也插不上手,譬如老爷子撅撅屁股用手指指那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小赵立马明白了,马上给他屁股底下垫上了纸……我在这儿,也就是站在一旁看着,又不能和老爷子说话,大眼瞪小眼的,在这儿也无益,真不如回去好好睡一觉。
说起来,我小时候也在青海生活过七八年,可是大学一毕业,就到了江南。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身体已不适应高原环境了。此次回来,我明显体会到了缺氧,不到一天时间,两手的手指甲的色泽就变暗发灰了。连夜长途乘机转机,加之提心吊胆,真的是身心交瘁,急需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调整调整。可是我又转念一想,若是我离开了,一口一个“哥哥”地叫着我的这个女人会不会在夜里再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老爷子看出了我的犹疑,他在手机上打了几句话让我看:你回家去好好睡一觉,明天也不用急着来。我感觉挺好的,赶紧回吧。记着明天吃了早饭来。早饭,不用管我们。还有,你不用给她买那么好的饭菜,我给她的不少了。
三
我决定要想方设法让小赵把老爷子当成一条大鱼,让她放长线钓大鱼,然后,我就可以拽住长线留住她。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来之前,老爷子每天早上一碗小米粥一个鸡蛋,中午让小赵从医院食堂打一份不到二十块钱的饭菜,他先吃,吃剩下的给小赵吃。晚上要么喝点粥,要么什么也不吃。其实,我家老爷子不差钱,正科级公务员退休,每月都能拿到一万多元,他一个人怎么都够花了。但他是个苦过来的人,改不了抠门的习惯。我曾在他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起床整理床铺时,竟发现褥子底下垫了厚厚的一层百元大钞,看得我目瞪口呆哭笑不得。我忽然想起他曾在微信里让我家里要备些现金,我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谁知他在家备了这么多现金。
不去理老爷子的账,我决定从带小赵吃好午饭入手,笼络住她。升米恩,斗米仇,笼络升斗小民也要讲究技巧。
等我在兴海路上一家羊杂馆花二十六元喝了一碗精品羊杂汤,吃了一个手工大饼赶回医院时,出乎我意料,我家那位高大胖的老爷子已经像座肉山般地坐在病床上把小赵差使得滴溜溜地忙个不停了。他一见到我,就用右手指着我说:“你来了,等下你去办件事儿。到时叫小赵带你去,去买六份砂糖橘,每份五斤,装在红色塑料袋子里,给护士们送一份,四份给主治医生和他的助手,一份我们自己吃。”
“为什么要这样买?砂糖橘吃起来虽然甜,但看起来那么小,还装在塑料袋子里去送给人家,小气吧啦的,不太好吧?”
“你小孩子家的不懂,这样子最实惠。”说完,他自觉失言,缓和一下口气说:“真是的,你也是奔六的人了,还把你当小孩子。那你说怎么办?”
“不如我去买六箱春见,又好看又好吃。”
“春见是什么?”
“春见就是耙耙柑,现在可时兴了。”小赵插嘴道。
老爷子显然没吃过春见,不过他从来都很能想当然,他把我们的话过了过脑子后说:“再别提什么柑不柑的。那天我让小赵买了砂糖橘给护士们送去,正好撞上主治医生也在那儿,我赶忙又让小赵去买了沃柑,谁知那沃柑竟然……那当上得!啧啧,看得见摸得着的尚且如此,装在箱子里的,哼,天知道。你还是按我说的去做吧。”
“不要一棍子都打死嘛。你让小赵说,送人水果是装在箱子里的好呢,还是装在袋子里的好?”
“当然是装在箱子里的好啦。”
“你懂什么!”老爷子粗鲁地抢白小赵,气得小赵噘着嘴不言语了。
“真的,照你说的去买,我都不好意思去送。”我又劝道。
“你不好意思去送,我还不要你去买了。”他竟然火了。
“不买就不买。”
“不买就不买。”
他声气儿比我大,我暗自一乐。看来他恢复得又好又快,也许明天就可以下床了!到底是省医院,自有回春妙手,岂是区区县医院能比的!
就在我和他杠上了谁也不理谁各耍各的手机时,管床护士走了进来甜甜地叫道:“老爷子,量血压啦。”
我赶忙冲她客气道:“真是麻烦你们了。我家老爷子年纪大了,反应慢,多担待一些哈。”
“谁说的?你家老爷子啊,脑子比我都好使,还要他多担待我一些呢。”
管床护士的话说得我和小赵,还有邻床的病友都笑了起来,老爷子讪讪地说:“我和你们说不着。”
“说不着,我们还不和你说了。走,妹妹,我们先去吃饭。”
我穿好外衣后问老爷子:“说吧,午饭你想吃什么?我好给你买回来。”
“我想吃羊肉饺子。若是没有羊肉饺子,牛肉的也行。”老爷子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盯着小赵说:“你少吃点,当心吃坏肚子。”
小赵笑眯眯地回他:“放心吧,爷爷,我肚子好着呢,吃不坏的。”
我忍着笑带小赵出了门。
医院旁五六百米长的一条巷子,我和小赵从这头找到那头,又从那头找到这头,大大小小十多家饭店,只有一家有牛肉萝卜馅的饺子供应。等饺子的时候,我让小赵挑一块牛肉。她跟我客气了一番后,挑了一大块牛腩,店里的厨师把它切好摆在一个大白瓷盘里,盘里头还有一大朵用紫晶色的洋葱雕成的雪莲花。我又从柜台上拿了一盘凉拌海带,和小赵在冷冷清清的大堂坐了下来。下筷吃之前,小赵用手机把两盘菜逐一拍下来发了出去。小赵对着手机是这么说的:“你看,哥哥请我吃这么多肉和菜,还有牛肉饺子。饺子还没来,你再不用担心。哥哥来了,对我好着呢。”
“发给谁了?”
“发给我大丫头了。”
“哦,她也在城里?”
“在呢,原来在城西区的一家厂子里上班,去年厂子倒了,在家里歇了好几个月。下个月开始,她就要到高铁上当乘务员了。”
“哦,那很好呀。你有几个孩子?”
“三个,两个丫头一个儿子。另一个丫头在城里卖水果。我的儿子不争气,小时候不肯好好念书,被他阿大打,打了也没用,高中都考不上,到海西的一个电厂上班去了,苦得很,一个月还挣不到三千块钱。两个姐姐娃娃都有了,他还找不着对象。”
“那你老公呢?他是干什么的?”
“在家里,一个人要种十多亩地。”
“这么多!收入不错吧。”
“哥哥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地多是多,但种不出东西来,根本挣不到钱。明年开春,准备改种药材试试看……”说着说着,小赵忽然问我:“哥哥和嫂子一年能挣多少钱?”
“不多,五十多万吧。”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她。
“这么多的钱,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小赵惊呼道。她接着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你给爷爷说,等他出院了,就把我带到家里去做保姆。我一定好好做,把他侍候得好好的。”
“晚点我会和他说的。来,妹妹,多吃点。你辛苦了。”
我和小赵一边嚼着牛肉一边聊着天。小赵挑的这块牛腩很耐嚼,越嚼越香,就着店里沏的砖茶,更是别有一番风味。等了二十多分钟后,两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水饺就端上来了。我问服务员:“还有一份呢?”
“还有一份你们是要带走的吧?”
“是的呀。”
“那你们先吃着。要带走的那一份,我们给做的是蒸饺,估摸着你们吃完了,就蒸好了,能趁热带回去,好吃。”
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吃饺子时,我才发现,饺子底下还铺着粉条和油麦菜。汤,我尝着是牛骨汤,也喝得一滴不剩。
小赵又问店里要了一个塑料饭盒,把剩下的牛肉和海带拨拉了进去。她拿起店里准备好带给老爷子的蒸饺,高兴地说:“这么多,爷爷肯定吃不了。”
“吃不了,你晚上再热热吃,再打点粥。”
“美咂了美咂了。”
看得出,小赵是一个机灵勤快的女人。别的不说,她侍候老爷子这么多天,把他弄得清清爽爽,浑身上下一点异味都没有,病房里的卫生间也被她搞得比老爷子家里的还干净,连同房病友对她也是客气有加。但是这顿饭,我虽然和小赵聊了许多,心里却产生了一种不是那么好的感觉。因为聊天的时候,我在仔细观察她,无意看见她左手背上有五个深青色的圆点。我不清楚那代表着什么,可又不便多问。但在我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纹身的多半不是好人,尤其是女人。再联想到老爷子手术前她闹的那一出,我不由得给她的人品打上了一个问号。但是,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即便是权宜之计,我也要笼络好她。
我让小赵拿着饺子先回医院去。我要去转一转,看哪里有春见卖。我之所以坚持要买春见,不光是这种水果适合送礼,更因为这个名字。我真心希望和每个人都能在爱的阳春里相见相识。
四
我叫那人送了两箱春见到老爷子的病房。他的春见新鲜,他这人厚道。第一次让他送来六箱春见,他放下货就走,我忙不迭地追出去喊住他。他回过身来笑着问我:“咋啦?”
“我还没付钱呢。”
“哦。”他掏出手机,让我扫了一下码就走了。我望着他高大的背影,愣了好一会儿,才点开手机付了三百元钱。
他的春见一箱五十块,每箱不多不少两层二十四个。我开箱后,先拿了一个带着两片绿叶的给小赵,然后拿了两个给临床的病友和他老婆,再拿了一个给老爷子。他们聊得正欢。老爷子接了我给的春见后回过身来拿眼睛瞟着小赵说:“你先把剩下的吃了再吃新鲜的。”
小赵赶忙回答:“我吃的就是剩下的。”
我瞄了一眼,那个大大的带着两片绿油油叶子的春见正稳稳地坐在茶几上,憨憨的模样和小赵有的一比。我不由自主又去看她的手背,我不清楚老爷子有没有注意到那几个点点,我清楚的是他对小赵渐渐地好起来了。
小赵没事的时候会往那个暖瓶的塑料盖头里倒上些开水,笑眯眯地坐下来听我们拉家常。老爷子显然也注意到了她把暖瓶盖头当水杯用,他和我连着视频,让我从家里的百宝箱里把他存钱时银行送的一个看上去很不错的保温杯给找了出来,第二天带去给小赵。
我带着保温杯一进病房,未及拿出来,小赵就兴奋地抢先告诉我:“哥哥,爷爷说了,他出院那天要送我一箱春见让我拎回去呢。”
“真的?”我望着老爷子问道。
“一箱春见算个啥。”老爷子满面笑容。是啊,他已经可以下地,由小赵扶着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走走了,心情一天比一天好。我悄悄问过老爷子的主治大夫:“我家老爷子今后生活还能自理吗?”
“这你不用担心。”主治医生信心满满。
“他是不是今后一直要拎着个尿袋?”我小心翼翼地又问道。
“不会的。后天就可以拔管恢复正常了。然后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这次手术,我家老爷子恢复得又好又快,大大出乎我预料。就是这样,我也不能再陪他了,我的假用完了。
我要走的那天中午,我带着小赵走进了医院旁那条巷子里看上去最豪华的一家酒店。小赵一进门就用手机拍个不停,她一边拍一边发语音:“看,今天哥哥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
也许我们来得早了些,大堂里空荡荡的。我领着小赵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后,就有穿着一身正装的服务员抱着菜谱走了过来。我本想让小赵来点菜,但忽然想起老爷子告诉过我,小赵不识字,是个文盲,我就接过来一页页浏览着装帧精美的菜谱。老实说,这两天牛肉羊肉的轮着吃,吃得我火气都上来了。在江南生活了三十多年,难得回来,生活习惯彻底改变了,连我爱人都说我已变成了一匹浑身长满鳞的北方的狼,我迫不及待地想吃点水产类的菜。我指着标价不菲的臭鳜鱼征求小赵意见:“今天中午吃这个好不好?”
小赵盯着照片上那条通体黄绿的鳜鱼看了半天,尴尬地笑着对我说:“哥哥要是喜欢吃就吃。”
“什么话?我请你,当然要点你喜欢吃的菜啦。”
“我们平常都是吃面蔬菜,有时蔬菜也没有,撒点辣椒面就行。平常难得吃肉,鱼的话再莫吃着。”
明白了,我改点了一份麻辣腰花、一份炕锅羊排、一份清炒上海青、一份长豇豆烧茄子、三份麦仁饭。
等菜的时候,小赵又一次对我说:“哥哥,你和爷爷说过没?等爷爷出院后,就叫我做保姆侍候他。天气暖和的时候,我把他接到乡下的家里。乡下空气好,新鲜的蔬菜吃给、家里养的猪杀了肉吃给。等爷爷百年的时候,我们披麻戴孝来哭给。”
我正想打断她的话,菜来了。小赵赶忙又点开手机,一一拍了起来。她一边拍一边发语音:“没见过这么好的菜吧。你看,这么多这么好的腰花,你养了那么多的猪,还没吃过猪腰子吧。看青菜这么碧绿,茄子烧得和玛瑙一个样了。还有这么多的羊排,里面还有玉米、粉条、青椒、洋葱,这么多的羊排没吃过吧?看这麦仁饭,像不像珍珠做的?”
发完,小赵拿过我要来的一次性饭盒,开始给老爷子搛菜,一边搛一边继续说:“把爷爷交给我们侍候,哥哥尽管放心……”
这时,我又清清楚楚看到了她手背上的那五个点点,就像是五个洗不掉的污点。我想是时候了,该问问了。否则,我怎么能够放心地离去?我叹口气,对她说:“妹妹,你知道不?若是在我们江南,可能都没有人敢请你做保姆或是护工呢。”
“为什么呀?”她抬起头,瞪大眼吃惊地看着我。
“因为,”我犹豫了一下,努力缓和语气,尽量装得像是在开玩笑,“因为,人家会觉得你不像是个好人。”
“怎么会呢?”她大吃一惊,停住手,让那五个点点横在我眼前。
我朝她那只手背努了努嘴:“在我们江南,好人不纹身的,尤其是女的。”
小赵像被烫着了似的猛地抽回那只手,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搓着五个点点说道:“原来是它们让哥哥误会我了。”
停了停,她一边合上饭盒一边给我解释:“这些点点是我小时候刺着玩刺上去的,长大了想弄弄不掉了。”
“小时候刺着玩刺上去的?”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哥哥,你不知道,在我们那儿,人人都在身上刺字的。”
“人人都在身上刺字?”
“你看这儿。”小赵一边说一边撸起袖管儿。我抬眼看过去,看到她白皙的右小臂上刺着深青色的“赵义梅”三个字,不禁脱口问她:“这是你的名字?”
“是的。”
“为什么要把名字刺在手臂上?”
“还不是因为我们不识字。出来挣钱,我们就怕别人问:你的名字怎么写?我们不会写,就给人家看这个。我们那里的老头老太都走不丢,找不着家了,人家一看手臂上的名字,就能给送回村里。我们每个村都有每个村的字样儿,都不一样的。有一年,我们村上一个尕娃找不到了,到处找,找了好多天。后来,在人家乡里的一个河滩上给发现了,整个人都被水泡得变形了,头有这么大,跟眺社火时候戴的大头娃娃面具一样,认不出来。还是警察看到了手臂上的名字,才知道就是那个尕娃。”
小赵说得若无其事,可能她说的次数多了,麻木了。可我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多把名字刺在手臂上出来讨生活的人!嫌弃化作苍凉,我的心隐隐作痛。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机械地劝她:“妹妹,多吃点。吃啊,你吃啊,别跟哥哥客气。”
“哥哥,我不跟你客气。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就放心走吧,没事的。爷爷能着呢,我保证把他侍候得美美的。”
“嗯!”
下午的时候,我正和老爷子依依不舍地说着话儿,小赵插进来问我:“哥哥晚上几点的飞机?”
“十点十分的,我准备七点半从这儿打车去机场。”
小赵听完,拿着手机出去了十多分钟后回来对我说:“哥哥,你可不可以乘滴滴到机场去?我二女婿就是开滴滴的。到时候,他到楼下来接你,我把你送上车,好不好?”
“那太好了!”我违心地说道,其实我心里对滴滴没有什么好印象。
小赵迟疑了一下,又问我:“他说要一百块,哥哥说贵不贵?”
“不贵不贵。”我记得来的时候从机场打的到省二医院是一百一十六元。但我暗自担心她女婿的车况不行,可是事已至此,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出乎我预料的是,这是一辆崭新的车。我坐进去后问他:“刚买的?”
“上周才买的么,贷款买的。”
“开滴滴几年了?”
“也才开。”
“哦,那你熟悉去机场的路么?”
“熟,我家就在机场旁边。”
“你丈母娘家也在机场那块儿?”
“我们就是一个乡的么。”
“哦,你开滴滴前干点什么?”
“开卡车运渣土。城管管得狠,只敢夜里偷着运么,抓住了,就狠狠罚,累死累活挣不到钱。”
“那你不好干点别的?”
“没考上大学,没技术,没办法,只好出来开滴滴。”他两眼直视着前方,脸色和语气都很平静。
“哦,听你丈母娘讲,你有两个孩子?”
“就是的,大的是个丫头,小的是个尕娃,在家里我阿妈给带着。尕娃两岁多,丫头上小学了,我阿大接送。家里老人也只是帮着看顾接送,都不识字,一点也辅导不了。课外班,贵得很,上不起,肯定又是输在起跑线上了。我们这一代一代的吃没文化的亏,不知要吃到啥时候。”
说着话儿,车子已开出了城区,两道灯光雪亮地刺进漆黑的夜色中,探照着前方的路途。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前方有一团灯光,我猜这灯光是机场航站楼的,我趁机切换低沉的话题道:“守着机场,滴滴生意应该不错的。等挣了钱,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里去读书。”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说道:“你到机场就知道了,机场里冷清得很,外面更是萧条。到了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能好些,可青海的夏天短得很。”
“很快会改观的,疫情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只好说说此类大话。
下车的时候,我悄悄地从包里摸出两个春见,放在座位上。我愿他吃了我的春见能够窥见春,他不在我置身的光明中,他在我看得见的无尽黑暗里。我想和每个人在人生的春天里相见,可这么多的人还挣扎在冬天里。
我目送他驾车离去,仿佛看见那方有无数只刺着姓名的手臂伸向苍天,苍天可认得这些名字?我记住了其中的一个:赵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