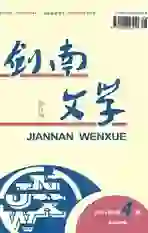历史在这里拐弯
2024-08-22张锐强
张锐强,央视讲武堂栏目“名将传奇”“书生点兵”系列讲座主讲,山东省作协一、二批签约作家。197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988年考入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三十岁退役后开始文学创作,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三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杜鹃握手》《时间缝隙》,小说集《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痛哭》、非虚构作品《名将之死》《诗剑风流——杜牧传》等十余部。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以及年度小说选本转载。曾获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全煤系统乌金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山花》双年奖等。
千里涪江奇山佳水,风光迤逦,地灵人杰,两千年来涌现出无数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与物,但真正直接影响到世界历史走向的,只有钓鱼城。蒙古大军横扫欧亚无敌手,唯独在此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其可汗蒙哥都丧命于此。
钓鱼城之后,涪江再无踪迹。它并没有消亡,只是跟嘉陵江完成了聚合。仿佛它这一路都在积蓄力量,都在小试身手,直到跟嘉陵江实现聚变,在钓鱼城点燃持续三十六年的绚烂光焰,然后定格。
一
历史往往存在着宿命一般的循环。两宋败亡的诱因高度相似,都在用悲哀的声调喃喃重复一个成语:唇亡齿寒。
北宋源于联金灭辽,南宋则始于联蒙灭金,而辽金本为两宋屏障。不同的是,宋辽和平维持百年,北宋突然毁约,然后又多次违背与金国达成的协议,导致覆灭,而南宋跟金战和不定,此前金军又曾大举南侵,仗一打就是七年。
绍定五年(1232年),一支人马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发,水陆兼程直奔大都(今北京),以敲定联合灭金的细节。这其中有个江西鄱阳口音的书状官,每天安顿下来,便不顾劳累,借着昏黄的烛火奋笔疾书,最终写成关于蒙古开创史的珍贵资料《黑鞑事略》。灭金次年(1235年),蒙古就开始攻宋,以汉中为基地的蜀口防线相继告破。嘉熙三年(1239年),那个奋笔疾书的书状官彭大雅摇身一变,以制置副使的身份入川主持大计。那时四川的军政中心已被迫后退至重庆,彭大雅搭眼一瞧夯土城墙,便断定不足为凭。因为他深知蒙军西征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攻城器具尤其精良,于是力排众议,改筑砖石城墙,并扩大范围,于是就有了今天看到的“古代重庆城”,延伸到通远门、临江门一带。
要保卫重庆,还需要外围屏障。百里开外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也入了彭大雅的法眼,这就是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东十里、嘉陵江接纳渠江与涪江处的钓鱼山。他派甘闰在山上构筑堡寨,作为重庆的前沿阵地。
八百年后,一个战史研究写作者从曾经就读四年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出发,出重庆溯江北上,抵达钓鱼山。一路上他满腹怀疑,同时又满怀好奇与景仰。那一簇熊熊燃烧三十六年的绚烂烟花穿越八百年的寂灭而璀璨于眼前,如梦似幻,颇有些失真。
川渝两地给他的感觉历来如同江南一般柔媚湿润,不,是比江南更加柔媚湿润。除了风景美食,他的印象便是麻将茶馆龙门阵。故而虽曾在重庆读书,却只知道合川肉片。浸淫战史凡三十年,钓鱼山的形象还没有完全将肉片覆盖。
二
母亲河总是那么的温柔细腻,不忍骤然流去。对于钓鱼山,她们更是格外多情。渠江绕了一个V字弯,护住它的北面,然后汇入嘉陵江;涪江本由西北而来,至此赶紧调整方向,径直向东,迫切地汇入嘉陵江,好像要给她一点力量;嘉陵江经过两次助力,越发精心,六次回头转身,牢牢护住它的西南两面。钓鱼山是幸运的,始终像被母亲拥抱在怀。
特别的发现需要特别的眼,这些当然不是肉眼视角,即便你能抢占制高点、登高环视,也还是身在此山。地图虽有所帮助,也还有欠直观,只能依靠无人机。拍摄画面逐渐拉近,突然发现所谓的山,其实就是一块巨石,近似长方形,山体几乎垂直上下,四壁峭立。正门前本来只是个坡,并没有路,当年在山体上搭建栈道以供交通。若有敌军来袭,栈道烧绝,他们只能望洋兴叹。不止正门,钓鱼城所有的城门都在险要处,前对悬崖峭壁,由栈道沟通。
青石路面平坦宽阔,“苔痕上阶绿”,颇有古意。江风吹来,空气中隐约有火锅的麻辣气息,而路边的芭蕉以及偶尔可见的红色土壤,都是强烈的青春记忆,合成出游子归乡的效果。毕竟当年他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了此生最美好最纯粹对未来也怀有最坚定向往的四年,不是故乡胜似故乡。虽则如此,他内心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遗憾,不为年华易逝物是人非,居然因为植被过于浓密。何也?一则裸露的红壤太少,对比不够强烈,二则大量的山体被遮蔽,普通人很难看出石壁峭立的险要,会本能地质疑那簇三十六年而不灭的抵抗火花。
那个瞬间,其实他也在质疑。尽管他确定无疑地知道此为南宋的最后一座城池,大汗蒙哥毙命于此。既然要踏勘古战场,那就不能任由纯粹游客的眼光随意飘荡,还是要有一点专业视角:从进攻者的角度,打量打量,窥探窥探。于是他抑制住内心青春回潮一般的急迫,没有直接进入景区,反倒掉头驱车从外围绕了一圈,也算渐入佳境。当年蒙古大军中这样的探子,应该派出过无数批次。
慢说在车上,即便步行,也难有发现。主要是树木丛生,视界不畅。周围只有巴山蜀水的田园风光,右侧的石墙不过若隐若现。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岔路处那块“蒙哥瞭望台”的牌子,不觉一阵欣喜,立即打转方向。
路越来越窄。停车下来,冲着右边的那组石砌台阶而去。台阶不过数步,末端是一户农家,炊烟在薄雾中升起,丰腴的少妇正低头洗菜,全无蒙哥痕迹。再一问,原来瞭望台在道路对面。
没有石砌台阶,也没有路,只有缓缓的荒坡通向一座土堆,很矮,目测相对高度不过十米,登临后并无视界拓宽的感觉。慢说钓鱼城,就连嘉陵江也多半被田野树木遮掩。难怪蒙古大军近在咫尺,也只是可望不可及。
转念再想,当时守军应当清理过射界,周边的树林必定被砍伐烧毁,情形与今日不同。
三
旅游攻略建议从北门进,乘观光车游览一周,出南门结束行程,但他决意直奔南门即护国门。无论攻防,第一目标都是制高点。既然城外的制高点无从查找,那就要首先掌握城内的制高点。若非传说中的钓鱼台,应当就是插旗山,当年的指挥台。由南向北,方向正好。
沿着宽大的条石路面,经外城的始关门朝景区正门亦即护国门而去。这是内城唯一的城门。全国各地,匾额石刻向以红色为主,所谓“书丹”,但这里不同,核心景观普遍使用蓝色,有别样的风致,充满蓝调音乐的抒情性。暗红色的山体巍峨高耸,是喀斯特地貌的特征,石砌的城墙发黑,形成明显的色差。这应当是余玠的政绩。在当年的历任四川主官中,此公政绩最为突出。“十六年间,四川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而余玠治蜀十一年,最终跻身宣抚制置大使,无论时间还是名位,都是政绩的旁证。直到今天,人们依旧记着他,城墙上飘扬着许许多多的“余”字黄旗。
余玠接手的是烂摊子,几乎无法收拾。四川的安危关键在于蜀口,即秦岭巴山中那些可以入川的山谷小道,诸葛亮北伐时走过的没走过的,其实是没有路的路。当时别说这些山谷小道,就连汉中都已沦陷,门户洞开。重新构筑防线迫在眉睫,但详细方案难以确定。最终余玠部分吸收播州土官杨文的意见,决定沿着水陆交通要道营建山城水寨,将各地败退下来的官军安置其中,形成扇形多节点防御纵深,彼此声援,于是钓鱼山上,以彭大雅下令营建的山寨为基础,形成了今天的钓鱼城。
筑城方案由冉琎、冉璞兄弟主持,要将整个钓鱼山建成固若金汤的堡垒。在耸立的石壁上垒砌巨型条石,延续一周,内外两道。城墙既高且厚,城外的滔滔大江正好是天然的护城河。城北城南,江边均有水军码头,沿江筑墙保护,并用一字城墙连接外城,平常水军驻扎其中,随时可以截江作战,就像张飞截江救阿斗。
四
沿途皆是景致,但他步履匆匆,甚至不敢回头。主帅必须保持最佳状态登上制高点,才能以最缜密的思维、最清醒的判断和最磅礴的勇气,衡量战局、做出决策。而慢说徘徊于古老的城墙,甚至略一回头,江水便会形成巨大的牵引,令他只想停下脚步,对此盘桓再三。
时令已是初冬,但此地还是一派青葱,毫无萧瑟之感,而薄雾之下的江水更加多情。身在合川,他突然想起一个字眼:江油。是的,这个地名给了他无法磨灭的印象,而且还跟李白无关。童年时看电影《巴山夜雨》,主角自报籍贯是江油。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他已经淡忘,但那种潮湿的缠绵气息,却像油一般不断滋养着记忆,让它从未生锈。那时的他无法理解,江与油怎么能联系到一起,直到此时,看见绿油油的江水。
翠竹从两边围拢过来,形成通道。就是苏轼词中、文同画里的竹子吧,不知是慈竹还是楠竹。自从姜尚直钩垂钓渭水,钓鱼便成了经典的政治姿态,这里的钓鱼台也未能免俗,历代吟咏无不由此破题,已味同嚼蜡,当还原其本意。闲暇时节,独自一人或结伴二三,就在这绿油油的江边垂钓片刻,那时何等的惬意。收获大鱼固然可喜,收获放松、收获内视或者反思的机缘,难道不是更为丰硕的获得?
果然还是一块巨石。古榕的枝杈掩映,前面崖壁上的三行蓝色大字格外醒目。无量寿佛、释迦文佛、弥勒尊佛。楷书线刻,笔力健劲,出自北宋的石曼卿。其下便是独一无二的悬空卧佛,长达十一米,下面刀削一般平整,旁有蓝色摩崖“一卧千古”。这两处石刻外加“钓鱼城”三字,被誉为摩崖三绝。
原来蓝色是为了强调。
护国寺、千佛崖……兵戈之地却有那么多的佛教痕迹,看似脱离尘嚣,其实增添了烟火气。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也少不了佛道儒。这应当是钓鱼城三十六年不倒的重要附注:它不单是堡垒要塞,还是可以供人正常生活的城市,而人总需要精神力量。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城市而来,希望休憩身心。他们纷纷慨叹沉重的肉身,渴望像鸟那样飞翔,但是作为文明象征的城市本身却又是暴力的产物,是隔绝与封闭的象征。
“城者,所以自守也。”
所谓暴力的产物,确切地说是为了隔绝暴力。但这种隔绝未必就如同我们的想象。比方长城,并非总是懦弱无力的被动防守,因为秦、赵、燕国的长城,都远离传统的农耕地带而深入戎狄的游牧区域,开疆拓土或曰侵略的姿态再明显不过。所以起初长城其实是攻击得手后暂时的防御,是攻击的间歇,是对新拓疆土确权的努力。
难道,余玠当时也有这样宏大的构思?
五
军营遗址位于中部平缓的山坡上。目测也有可能是全城制高点,但视野不良,无法在此瞭望。既然是遗址,那就不会有多少具体的建筑遗存,石头地面空空荡荡,已被风雨染成沧桑的黑色,强烈地隐喻着当年拼杀的鲜血。
香樟、黄葛、松柏,桂花、蜡梅、枇杷,绿意莹莹,但突然感觉阴气森森。这所谓的“阴”并非人们印象中单纯的负面信息,无关于三十六年流血征战和无数的死亡,也无关于完全被水封闭的环境,而是因为军事即为“阴事”,军用文书即为“阴书”,军营牌符即为“阴符”,军事谋略一向被称为“阴谋”。斗争双方都需要保密,因而见不得阳光。
蜀口的关键在于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县中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和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合称三关。三关之外,还有阶州(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西)、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天水军,合称“三关五州”。前沿位置更有“外三关”,即大散关、黄牛堡(今陕西凤县东北黄牛铺)、皀郊堡(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守卫这三道防线的职责,由川峡四路中利州路下属的四个军分区承担,即四都统司: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沔州(今陕西略阳)、金州(今陕西安康)和利州(今四川广元),合称蜀口四戎司。驻守钓鱼城的正规军便是兴元都统司所部,主将王坚以兴元都统的身份兼知合州。从兴元到钓鱼城,后退千里不说,部队还大量减员。兴元戎司的编制规模本有2.7万,而栖身于这片军营中的不过4600多人。局面之窘迫危急,可见一斑。
合州知州还保持兴元番号,就像唐末的平卢节度使侯希逸退到大海南边的青州还称平卢淄青节度使,虽有讽刺意味,但能给人意在收复的假象,聊可遮羞。而滔滔嘉陵江对于这数千军人既像护送,更像督促与追赶。
但凡胸有热血,谁能忘记嘉陵江西源在凤州、东源在天水?
早在百年之前,大将吴玠吴璘兄弟镇蜀时,考虑到关外四州(天水军后从成州析出,故而有时也称关外四州)尚无城垣,便创设了四处家计寨。选择地形险要且能容纳军民生活的地方修筑山寨,等金兵来犯,军民便退入寨内长期抗战。从吴玠到余玠,执行的是同样的战略。只是吴玠依山,余玠靠水。钓鱼城这样的城池,余玠八年来陆续建成二十余处,其中四处最具战略意义,被称为“四舆”:“巴蜀要津”“蜀口形胜之地”钓鱼城、“保蜀之根本”重庆城、“镇西之根本”嘉定城(今四川乐山)、“蔽吴之根本”白帝城。另外还有“八柱”。
计划虽然宏大,但并没有收复失地的进取姿态。并非因为余玠缺乏胆略,恰恰相反,因为他有足够的清醒。
六
插旗山果然是制高点,正对着北门出奇门,门外的一字城墙直通北码头。八百年前,一条粗壮的汉子曾经在此咚咚擂鼓。无法得知他的样貌,但却可以确定其性格无比坚毅,坚毅得简直是死心眼。这人便是王坚。
在他的印象中,王坚一副岳飞的模样。没有别的原因,只为童年时期小人书刻下了对宋代大将的全部记忆,再无空隙。
钓鱼城动工十一年后的宝佑二年(1254年),王坚奉命进驻合州。他征发“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齐集钓鱼城,进一步完善城郭,城中百姓“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收成够吃三年即为“丰”,够吃九年即为“登”。随便碰个五谷丰登的年份,存粮就足以支撑数年。与此同时,他还大量配备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火枪火炮。那时火器已从最初的燃烧装置升级为爆炸装置,炸弹与地雷的雏形均已出现。九口锅遗址就是当时的兵工厂,用于制造硝石火药。
又过了五年,蒙哥率领蒙古大军一路南下,直奔钓鱼城而来。先礼后兵,降将晋国宝奉命入城劝降,但王坚丝毫没跟蒙哥客气,直接将晋国宝的脑袋挂上了城头。
降将的血点燃了蒙哥内心的男儿豪情与血腥杀气。他是见过世面的大将,因而不怒不嗔,不慌不忙,调兵遣将:占领合州旧城,切断跟渠江沿岸其余宋军山寨的联系,阻击重庆方向的援军,派遣水军主力猛攻外围,劫掠钓鱼城南岸码头上的粮船四百多艘。
一句话,彻底孤立钓鱼城,等待瓜熟蒂落。
蒙哥直接统率的部队四万,加上其余各路人马,至少有十万之众。而王坚手下的正规军外加五县土兵以及少量山寨兵,撑死不过两万。敌众我寡,遥见城外旌旗蔽日,战马嘶鸣和咚咚战鼓又如同声声恐吓,城内军民不由腿肚子发软,但主将王坚心如石坚,副将张珏意志决绝。鉴于城北城西一带江岸地形平坦、难以防守,王坚果断放弃,集中兵力重点防御东城、南外城和西北外城。
钓鱼城三面环水,蒙哥只能从东边接近。从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初三开始,元军先后攻打一字墙、镇西门、东新门和奇胜门,但均被击退。强攻不成,改成突袭,又受挫于护国门。四月二十三日夜,元军好不容易攻破出奇门到江边的一字墙,最终攻入外城。
外城即是郭。“城以盛民,郭以守民。”外城就像内城的盔甲,一旦丢失,就意味着只能以肉体承接兵刃。危急关头,王坚和张珏督率部众,从暗道中杀出奇袭,再度逆转。
七
哲人云,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在军事攻防或曰杀戮这件事儿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
冷兵器时代,杀戮需要特殊技能,至少体格,需要武功箭术甚至所谓的骑士风范,但火药枪炮在大大降低杀戮门槛的同时,大幅提高了杀戮的效率。
元明清三代,为了统治安全,朝廷禁止民间研究新式武器,甚至故意雪藏已经成熟的武器与技术。但宋代完全不同,很多人因为进献新式武器而获得封赏,因而王坚军中有大量的火器,且射程与杀伤半径越来越远。蒙古骑兵的杀戮方式虽然相对粗糙,但他们实行拿来主义,从金,从中亚与欧洲各国拿。就在上年(1258年),蒙古骑兵刚刚使用金人的炸弹震天雷亦即宋人口中的铁火炮,一举攻陷巴格达。因此这不只是勇气的对决,更是新式武器的较量。
显然,辈分上属于徒孙的蒙古骑兵终究未能占据上风。钓鱼城的位置固然不高,但总比城外的蒙古人高出一头。
仗打到这个份上,蒙哥才意识到眼前的是硬骨头,而不是肥羊腿。此时有人建议将钓鱼城弃置身后,大军顺流直下,跟忽必烈的主力会合,直接挺进南宋的政治心脏。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这是个高明的主意,类似麦克阿瑟反攻太平洋时的跳岛战术,然而众多元军将领早已杀红眼,也缺乏足够的智慧,一定要在钓鱼城见个高低。
夏日的合州天气酷热,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汉子难以适应,况且大军久屯坚城之下本来就犯了兵家大忌。如果说此前的行动全都中规中矩,那么蒙哥此时的不够坚决或曰过分坚决,便是最终的败笔。他败亡的命运,至此已是板上钉钉。这个决策,好像是他中暑后的决策,脑子晕晕沉沉。
八
军事家孙膑将城池分为雌雄二类。居于低处比方两山之间、或者背临谷地水草不旺的为雌城,难以防守;居于高处或者背靠山岭又有良好水源的为雄城,难以攻克。从这个标准出发,钓鱼城这个海拔不足五百米的台地城池就是标准的雄城:城内不但水源丰富,有大小池塘13座、井92口,还有大片耕地,城外打得再凶也不耽误耕种。必须下马仰攻的蒙古骑兵如果知道这些内情,一定满怀沮丧吧。
由于地形狭窄,大军不易展开,作战正面有限,元军的兵力优势并不如数字对比那样直观。因而尽管不止一次攻破外城,终究无法立足。七月初五,元军前锋元帅汪德臣乘夜突破外城的马军寨,双方再度展开血战,彼此伤亡都极其惨重。天明之后下了雨,元军的云梯全被守军砸断,后援不继,再度败退。
汪德臣本是金国降将,归降之后颇受重用,已跟王坚在四川拼杀多年,彼此棋逢对手。虽然刚刚战败,但宋军的伤亡也很是惨重。作为带兵多年的将领,他深知此时的军心动向,于是单骑来到城下,再度劝降。
史书上找不到汪德臣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他那些话入情入理,很能打动人。毕竟王坚已经尽力,并非望风披靡。只是汪德臣没有想到,这番话虽然入情入理,但起点和终点都是利益,而世间或曰钓鱼城头还闪亮着两个大字:忠义,就像余王二字旗。
一阵砲石雨点般砸下,汪德臣瞬间毙命。
蒙哥的耐心终于抵达极限。他下令在城东脑顶坪筑瞭望台,台上树桅杆,瞭望城内到底有多少三头六臂。元军干得迅速,守军看得清楚,抛石机早已备好。人刚爬到桅杆末端,砲石已经飞将过来,将他“远掷”,“身陨百步之外”。
由于万历版《合州志》语焉不详,我们无法确知是桅杆倒地、将爬杆者抛出,还是砲石直接将他砸了出去,更不知道爬杆的是不是蒙哥本人,也有说法是蒙哥当时正在擂鼓。但无论如何,他身负重伤,最终殒命。
蒙哥一定想象不到,这方圆不足三平方公里、城墙周回不过十二里的小城,会成为自己的葬身之地。全世界都想象不到。接到消息,正准备渡江南下攻打鄂州的忽必烈立即掉头回师,以便争夺大位;兀良合台的大军由云南经广西北上,已经打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也匆匆北渡长江。从此以后,蒙古高层忙于内斗,对南宋的攻势不得不暂停,宋理宗终于喘了口气,否则也许他的头盖骨被做成酒器的时间会大大提前。
钓鱼只是传说,是失意文人或者底层官僚的牢骚用语,但最终居然真的钓到了一条大鱼。“独钓中原”的石牌坊下,不知多少游客拍照打卡,但它其实不够贴切。因为它钓到的不止中原,还有世界。忽必烈要回去抢位,他另一个兄弟、在中东攻势凌厉的旭烈兀自然也要抢位。旭烈兀东归之后,留下的将领与部队实力不足,在叙利亚惨败,最终未能攻入非洲,全球扩张的步伐戛然而止。蒙古骑兵的扫荡被欧洲历史学家视为“上帝的惩罚之鞭”,不意一个中国人,将上帝之鞭顺手折断。
这些说法都很贴切,只是说得太多,至今已不觉新鲜。他的感觉是,涪江、渠江和嘉陵江在此拐弯,历史也在这里拐了个弯。或者说,历史轻轻摘下帽子,对钓鱼城鞠了个躬。
想到这里,在忠义祠,他,退役陆军上尉立正敬礼。不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或者制作小视频,而是后来者对先贤真诚的顶礼膜拜,是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叹服。
他突然意识到,此行不仅仅是研究战史踏勘战场,也是为了凭吊。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