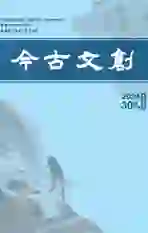电影改编《楢山节考》研究
2024-08-20肖汶佳
【摘要】导演今村昌平于1983年戛纳电影节荣获金棕榈奖的电影《楢山节考》,改编自深泽七郎的同名小说。电影文本继承了原小说文本对于贫苦山村以及日本东北地区自古以来流传的民俗传说,同时也根据时代语境进行了取舍和改写。电影文本并未将原文本从宏观角度对共同体的解构搬迁至银幕,而是通过聚焦到在食物匮乏的条件下努力挣扎以谋生存的小人物,放大了原作对于生命的思考,挖掘集体无意识中的丑恶引起受众的深思。并且这种注释性的改写又会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引发受众与小说、受众与受众之间新一轮的狂欢化的互文,给原小说文本带来更多释义的可能。
【关键词】《楢山节考》;文学与电影;改编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0-0088-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0.026
日本战后派作家深泽七郎写于1956年的处女作《楢山节考》对当时的日本文坛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小说以日本东北地区信州的某一小山村为舞台展开叙述,同时结合了民间传承的弃老传说等题材,描绘了深山寒村食物匮乏、难以过冬,不得已遵循部落风俗将自己的母亲遗弃在楢山的故事。这样原始而又残忍的风俗,在村子里被美化成“上山朝拜”,上了年纪的阿林婆主动将朝拜的日期提前,因对母亲的依恋但还是极不情愿地将母亲抛弃的儿子辰平,两人对于家庭的热爱使得残酷的现实更添一抹悲惨。该作品一经投出,即获得了日本《中央公论》杂志首届新人奖,受到当时评委伊藤整等人的盛赞。
从表层来看,小说展现了极限状态下人类为了自我的存活和家族的延续所做出的种种选择;然而追溯到更深层次则是村子里的所有人都被村里的“规矩”所束缚的现实,不论是违反还是遵守,留给这些村民的都只有破灭一条结局。小说对于以上现实的无声揭露,使得日本人不得不开始反思并怀疑迄今为止一直生活在其中,并赋予其无条件信任的共同体,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究竟是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电影《楢山节考》则是通过影像叙事,拉近了读者与他们自己建构的食物短缺、难以生存的想象能指。然而在电影文本中,不无改编者本人的创作,这既是对小说文本的视觉符号式的再生产,同时也是一次跨媒介的对话。本文将借助文学与电影相关理论,探讨电影改编文本对于小说文本的再次阐释,以及其作为另一种媒介为原文本的传播所带来的意义。
一、对共同体的重新阐释
电影《楢山节考》与小说文本相并行之处一目了然,即电影将小说的主舞台—— “食物匮乏的小山村”这一大背景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荧屏上,并以此为素材来进行创作性阐释。但在如何构建小山村这一点上,电影文本则与小说文本产生了分歧。小说的叙述主要围绕阿林婆展开,并通过多声部式的描写推进情节。开篇即借阿林婆之视角道出了小山村最重要的习俗——凡是年纪到了七十岁的老人就必须要“上楢山”,同时,作者还交代了在这之前阿林婆还有两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为自己的儿子辰平续弦,好让自己上山后还有人来照顾留下的几个孙子;另一件事则是自己完好无缺的牙齿,在这个食物匮乏的村子里,上了年纪后还有一副好使的牙口被认为是一件极为羞耻的事,阿林婆也因此受了不少冷嘲热讽。于是阿林婆试图用打火石敲碎自己的牙齿,并最终狠下心来往石磨上一撞,成功撞断了两颗门牙。但她不仅没有满足,甚至还将不停出血的嘴巴展示给村民们看,试图改变大家的成见并能够认可她的行为。可惜事与愿违,不但大伙看到那副鲜血淋漓的模样立马四散而开,还传出一个“鬼婆婆”的称呼。
除去阿林婆之外,小说还通过对其他几个人物的速写展现了村里的惯习。阿林婆的孙子袈裟吉之所以能够在家中为所欲为,只是因为他身为家中重要的青年劳动力,是家庭能够继续存续下去的依仗;阿林婆讨来的新儿媳阿玉则是刚成了寡妇,便匆匆忙忙地从对面山头的村里赶来,好让她原先的夫家能够尽快卸下负担;雨屋一家因为犯了村里的大忌,偷别家的粮食而惨遭灭门之灾;邻家的阿又不愿“上楢山”,并试图挣脱束缚逃跑,结果不仅被阿林婆训斥,还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踢下悬崖。从整体上来看,即便存在阿林婆在不久之后上山参拜这条情节,也不能说小说遵循着一条严格的时间线进行叙述,甚至还没有明显的空间转换。通过蒙太奇式的叙述手法,小山村里沿袭下来的规矩得以一一拼凑起来。
得益于原文本类似于剪辑的叙述,电影对于小山村这一共同体的描写,以及大体情节上并未也不需要做出过多调整。然而改编并不是原文本的镜子,它总是原文本的折射。①电影文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小说当中的人物、地点以及时间等一五一十地搬运来,而对于作为中短篇小说的原文本,改编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增添情节与人物甚至是很有必要的。电影开头的长镜头便将村民们贫苦的生活现状展现在观众眼前,盘坐在茅草屋里的阿林婆一直在编织着什么,到了“上楢山”之时这个伏笔才揭晓:原来她是在亲手制作送自己走向死亡的担架。而这个时候阿林婆用牙咬断茅草来编担架,却遭到孙子袈裟吉的笑话,无疑在小说文本赋予阿林婆毅然赴死以神圣化意味之上添了一抹讽刺。阿林婆自知自己的牙口给家里带来了负担,便积极操办自己的参拜仪式,而袈裟吉之所以看在眼里还出声嘲笑,是因为将生存的权利让渡给家里的年轻人这件事对于阿林婆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但在孙子眼里抢占了自己应有的食物这一事实仍旧存在。仁作老伯家的阿金婆卧病不起,老伯便开始跟利助商量让利助与辰平兄弟俩制作棺材一事。棺材早早做成,三人提着棺材来到老伯家门口,准备将阿金婆下葬之时,却看到阿金婆一脸痊愈的模样从家中走出。这一镜头充满了幽默的趣味,但却是在食物匮乏的状态下运作的共同体的一隅。
利助这一人物形象完完全全出自电影文本对于小说的读解,可以说是与小说文本对话的产物。身为辰平的弟弟,利助却没能够独立出来组成自己的家庭,反倒是蜗居于辰平家的阁楼上。暂且不论其兄长辰平,村里人都觉得利助身上散发着恶臭,一见到利助就摆出一副嫌恶的模样。甚至是听从丈夫遗言,为了赎罪而不得不和村里的男性轮流发生关系的阿艳,在利助认为按顺序应当轮到自己时毫不犹豫地跳过了他。在“性”这件事上,利助与袈裟吉不同,袈裟吉很容易就能找到对象,但利助只能偷窥他人,在整个共同体当中属于最低层级。当真只是因为利助浑身散发恶臭吗?从袈裟吉与阿松,以及后来跟从袈裟吉的女孩的关系可以得知,跟从作为下任家主的袈裟吉可以在他家住下、吃到他家的饭,如此一来生活就能得到保障。利助与袈裟吉发生口角时,阿林婆劝说利助做出让步,给出的理由也是“袈裟吉是辰平之后的继任当家”。而利助非但没有这一立场,对于辰平一家来说,他只是一个干活的帮手,甚至还会招来村民的非议。
小说对于共同体的刻画的确只停留在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而关于性的描述却有淡化的趋势。食、色皆为人性,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文本突破了加在改编上所谓的“忠实性”之束缚。电影文本对于原文本的注释性改编,其意义在于补充甚至是使构建小山村这一共同体的目的实现属于电影文本的历史语境的转向。需要指出的是,电影所提供的“逼真”的影像给了观众真实的印象,而这只是一种相对的真实。影片没有表现,或是未能表现的部分同样重要。电影文本言说的是性权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在小山村当中地位的高低,而无声地披露这一事实又扩展了原文本的含义:所有人都在为“物”奔波的社会现状下,性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如此未言说的部分就成了电影文本与原文本一同对文本外暗藏于泡沫经济之华丽面纱下丑陋现实的巨大冲击。
二、人物形象的变容
从上节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电影《楢山节考》并没有局限在小说中所提及的几位人物,而是承接起原文本的语境,构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共同体。与此同时,电影也赋予了几位主人公不同于原作的要素。这或许是出于小说的篇幅有限,以及影像符码所携带的信息相较于文字更加丰富等原因。但不论如何,比较分析这些人物形象可以加深对小说文本和电影叙事互文性的理解。
小说在阿林婆这样一个形象的塑造上是带有明显意图的。阿林婆自登场以来就一直为自己的儿孙着想,在为辰平续弦一事上,体现的是她对家庭的牵挂与担当。帮自己的儿子找到媳妇,这既表达了对儿子的爱,同时也是在为自己“上楢山”后空缺出的家里女主人的位置寻找继承人,为家族的延续尽到属于自己的责任。在同对面村里来传信的人商量好后,阿林婆因成功替儿子找好后妻一事喜形于色,立马便给辰平报喜,不仅如此,还在全家人面前骄傲地宣布,“明天你们的妈妈也许就从对面的村子过来了哦” ②。之后虽然遭到了袈裟吉的反对,但对孙子不满的态度,反倒是责怪起自己没有注意到孙子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关心。而在“上楢山”一事上,阿林婆早有打算不久之后便上山去。这样做既是在遵守村里的惯习,更是因为不能再给家里添加负担。拥有一口好牙因而被大家笑话,阿林婆是心知肚明的,这种观念同样深深扎根在阿林婆的认知中,撞掉自己的门牙是出于此,早早就开始筹备上山的仪式也是出于此。在发现孙媳妇阿松怀有身孕后,她立马提前了参拜的日程,为的同样是在曾孙出生后食物能有所保障。在树立起这样一个为家庭操碎了心的母亲形象之后,这位母亲却又不得不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此巨大的张力之下,阿林婆的“上楢山”就显得带有一些悲壮的色彩。小说的最后,在漫天飞雪中,一心念佛的阿林婆“前发、胸脯和膝盖上已经积了雪,像一只白狐似的两眼注视着前方的某一点” ③,又被赋予了一层神圣的意味。
而在电影中,阿林婆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渺小却也更加现实起来。面对袈裟吉的抗议,电影并没有采用旁白或独白的形式表现此时阿林婆的心理活动,甚至全片下来几乎都没有旁白的出现。另外,与小说形成极大反差的是,电影借助添加的新情节强化了阿林婆的女主人这一侧面。在阿松成为自己的孙媳妇后,阿林婆发现她丝毫没有可以为家庭做贡献的能力,反倒是因为吃得多给家庭带来了负担。电影文本在此与原文本走向了分歧,电影叙述到这里时,和原文本中体现共同体惯习的另一重要情节产生了联动:阿松在电影中成了雨屋一家的人。雨屋一族在先代就曾偷过他人的粮食,阿松也曾因为偷拿食物送回娘家被辰平发现过而受到教训,其结果就是这样的违规行为暴露后雨屋家受到了村民们的审判,藏在家里的粮食都被搜刮一空。这时阿林婆主动给了阿松一些吃的,叫她带给家人一起吃。阿松并未察觉这是阿林婆的计谋,老老实实拿着食物回到娘家,结果被村民们一网打尽,最终与家人一同被活埋。阿松的死,根本原因在于身无长物的她不能成为家中的劳动力,而在这连吃都是问题的小山村,没有人家有这种余力养活一个闲人。虽说如此,阿林婆设计杀害阿松这一事实也不能事出有因就改变性质。的确,这是阿林婆出于对家庭存续的考量而做出的选择。但这与小说中一心遵守村规,对山神有着虔诚信仰和崇拜的阿林婆的形象是有相违之处的。在电影当中,阿林婆的形象仿佛褪去了身上那层光辉,被还原成了面对生活无能为力,只能苟且活命的小人物,其内在的利己主义通过陷害阿松一事展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的辰平是一个不完整的存在,他不愿送自己的母亲“上楢山”,在听到村民们对母亲的嘲笑后,大动肝火和对方吵起架来,对于早已内化为大家的行动纲领的惯习,辰平所表现出的是抵触心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作为这个小山村的一员,他是不合格的,他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员。所以雨屋偷窃一事暴露、村民们抄家之后谈论如何处置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辰平,甚至还没有声称要挖个大洞把雨屋一家人活埋的儿子袈裟吉果断。临近阿林婆“上楢山”的日子,辰平仍旧是一副不太积极的样子,在听到母亲将日期提前后更是如此,但转折点也是在此出现,他由不能接受母亲必须上山参拜这一事实转为了被动接受。出于阿林婆自己的考量,她不得不催促辰平加入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程序中来,她命令儿子的声音“拥有一种让辰平绝对服从的强大的力量” ④。正是母亲的命令让辰平第一次直面村里人人墨守惯习的沉重,从而开起了他真正融入小山村的过程。在将母亲送上楢山后,他还曾在做最后的纠结,不知如何向自己的孩子们解释母亲已不在的事实。但看到孩子们哼唱“螃蟹歌”,得知他们都已经知晓后,辰平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成了共同体的一员。
电影的走向与小说恰好相反,辰平在一开始就认同“上楢山”的惯习。多年前辰平与父亲一同出去打猎,在得知父亲对于“上楢山”极为抗拒后,竟用猎枪将父亲打死后埋在了路边的树下。与小说的前半部分截然不同,这里辰平所扮演的是村规的保护者的角色。弑父的仪式从一开始就完成了,辰平早已被山村接纳。不仅如此,小说中讨论关于如何处置雨屋一家的情节,以及本该有所抵触的辰平在电影中却并未得到体现。面对难以跨越的严冬,辰平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粮食为赌注,同其他三人抓阄,结果把自己带来的那点东西全都输光。通过这一场景既能管窥村子的运行逻辑,同时也能看到辰平对于这些规矩的态度是积极的,若非如此,辰平也不会参与进来。其实也正好应了其父亲的遗言,包括“上楢山”,对于这些规矩,辰平其实并未理解,只是一味地遵从,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来说肯定是合格的。为了保证利助能继续为家里帮忙,他甚至还试图劝说刚刚讨来的后妻跟利助发生关系以满足其性的需求,全然不见自己的思考,抑或说是他思考后的结论。这种情况在临近阿林婆“上楢山”之时发生了改变,这或许是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做的妥协:在此之前,对惯习深信不疑的辰平甚至能对自己的父亲痛下杀手,而轮到自己送母亲上山后,他才出现了异样。上山时,他背着母亲走走停停,还是阿林婆再三催促他才肯舍得迈开步伐。当他母亲放下去接水喝,转身发现母亲不见了踪影时,认为母亲自己逃下山去,于是长舒一口气,像是放下心来。但这只是他的幻想,随后母亲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当他反应过来后所表现的落差感,就是心中对迄今为止一直默默遵循着的生存之道的怀疑的最好证明。电影的最后是对于原文本末尾的模仿,同时又能看到电影文本对细节所做的重新安排。但他看到袈裟吉又找了一个女孩带回家,以及母亲的遗物被其二人瓜分,想到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为了家庭终日操劳的结局竟是如此,眼中的迷茫和心中的苦楚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了的。
上述的两位主人公在电影和小说中的形象,的确是有所差异。在小说文本中,深泽七郎特意赋予阿林婆以慷慨赴死的赞许,并给出辰平最终与惯习妥协、真正成为村里一员的结局,看似二者都是正向的叙述。但身为战后派作家,他的写作意图没有仅停留在表层。生活在共同体中,违反规矩的雨屋和阿又暂且不论,一直小心翼翼、从不触犯他人利益的阿林婆和辰平二人都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事物,这样的共同体对于人们来说真的是能够仰仗的吗?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又能得知,让阿林婆的“上楢山”带有神圣意义,其意在揭露和讽刺战时日本政府对国民大肆宣扬忠君爱国的无耻行径。电影改编作为一种流动文本,不仅是小说中故事语境的回应,同时也是对小说写作时代,更是对改变时代的回应。⑤作为制作团队成员的一员,在今村昌平导演看来,攻击或是暗讽企图洗脑国民的政府也许不再是他的首要目的。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阴影处,趋于扁平化、无力化的日常生活,反而成了在经济高速增长过后的日本亟须拯救的对象。影视化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并不代表着需要将其情节乃至精神内核都忠实地搬上荧幕。虽然对于辰平的改动同样能引发人们对于共同体的思考,但改编者也有其自己的侧重:削弱添加在阿林婆身上的神圣色彩,同时将辰平的心路历程倒转,意在展现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努力求生的姿态,将人性中最为丑恶的部分挖出来让观众们重新体会生命的意义。
三、电影文本的创造力
如前所述,从小说到电影《楢山节考》,改编者使用了不同于原作的叙述手法,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文本进行了再生产,但镜头语言的生命力并不局限于此。在叙事时,插入几个貌似与叙述对象无关的特写,这样的手法在电影中多次出现。
例如在介绍辰平家的情况时,插入一个老鼠正在撕咬蛇的镜头,辰平家的生活窘境便一目了然;利助在干活时因为身上的臭味儿被袈裟吉赶走到一旁,随意游荡时突然折下路边的树枝,三下两下便将躲在树枝里过冬的幼虫抓出来吃下;阿林婆上了年纪也要帮忙干农活,此时阿林婆无意识中瞥见田里不远处有一条蛇正抓住一只老鼠大快朵颐;雨屋家偷粮食的事情败露,村民们前往他家兴师问罪时,又插入一个黄鼠狼偷摸进鸡窝的镜头等等。
短镜头能够在无声之中表现电影文本,今村昌平导演适时安排插入一些发生在山村里极其自然的事项,为的就是利用短镜头的这种特性将食物匮乏的现状、村民们面临的生存压力快速展现给荧屏前的观众们看。同时,有关蛇的特写在电影中多次出现。蛇的形象拥有比较丰富的内涵,有圣经故事中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的一面、有希腊神话中拥有永生的一面、有《古事记》和《今昔物语集》中展现出的拥有很深执念的一面,而在《风土记》以及《古今著闻集》的逸闻中,还能看到蛇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⑥
回到电影当中,除去已经提到的两处外,在辰平与阿玉交合时,辰平注意到房梁上有一条蛇探头探脑,辰平说是主人(台词中使用的是ぬし一词,在日语中有对神明或是妖怪使用这一词的习惯)来跟阿玉打招呼了,从侧面反映出在这个小山村存有对山神虔诚的信仰,为电影文本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而在袈裟吉与阿松寻乐时,插入一条小蛇刚刚出生的镜头,意在暗示阿松已经怀有身孕。袈裟吉认为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则要将其遗弃,其对于后代的爱甚至都比不上一旁努力养育后代的蛇。原文本的叙述仅涉及,袈裟吉即便面临吃不饱穿不暖的窘迫也要执意寻欢,产下“老鼠的孩子”(在原文本中即是对早生多生的讽刺)也无所谓的态度。而电影加入带有生命隐喻的蛇的特写,在观者心中形成瞬时的鲜明的反差。这种创造性的改编可以说是原文本隐喻的隐喻,暗讽麻木的现代社会追求享乐的人们,其所包含的生命力远远比不上毫无智识的动物。
长镜头也是电影叙事的手段之一,相较于从侧面使得电影文本更加立体的短镜头,长镜头的特点则在于从正面展开叙事的同时,还能保证足够多的细节使得故事更加丰满。例如在听到阿林婆决定明晚就上山时,辰平仿佛是突然间失去了力气似的躺了下来,并随手拿了块布遮住自己的整张脸。阿林婆立马将布扯开,可是即便如此辰平依旧没有开口说话,眼睛也不睁开就别过脸去。母亲所做出的决定让辰平感觉背负老人“上楢山”的责任就像是命运般地,从已逝去的父亲轮回到了自己这里。他终于明白当时父亲不愿履行职责的原因,因而自己也变得和父亲一样产生了抗拒,变得不愿去直面明晚母亲就要离开的事实。阿林婆试图让儿子正视自己肩上的责任,便扯去了他脸上的布,但没想到的是辰平还是别过头去。不论先前有多想否定父亲,认为从不愿承担身为共同体一员的责任的父亲是多么令人羞耻,此刻他总算是对村里的惯习产生了抗拒。
另外一处长镜头也很精彩,在听到村里有人说发现辰平的父亲利平出现后,阿林婆急忙赶到目击地点,结果错把先到的辰平认成了自己的丈夫。当他回头的瞬间,狂风大作,画面忽然褪色,背景音乐也随之一变。辰平将父亲消失的原委徐徐道来,阿林婆这才得知是自己的儿子在与丈夫起争执时将其杀害。他说父亲的灵魂便存于树下,因而先前几次目击到神似辰平或是利平之类的报告,说不定就是村民们看见了利平的亡魂。亡魂久久未能安息,时不时在现世飘摇,暗示着辰平心中一直都对杀害父亲一直心存芥蒂。阿林婆则试图开导儿子,安慰儿子杀害利平的不是他,而是山神大人。的确,此前辰平毫不怀疑地信奉山神,将背负家中老人“上楢山”看成一种义务时,倒是可以认为阿林婆所言属实。但如今辰平已经亲身体验过这种义务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已经产生犹豫的他再听到母亲这番话内心究竟作何想法就不得而知了。但阿林婆却是真心认为利平应当担起责任,背着自己的婆婆去参拜山神。这是出于对村里惯习,以及对山神的畏惧,还是拐着弯地想要瓜分食物,又或是两种缘由皆有,也都难以分辨。
总而言之,小说文本中未能引发的讨论,通过这样一个长镜头的刻画得以登上台前,出现在受众们的视野当中。把小说文本作为原始的素材,进行上述的独创、带有自由地发挥,使得电影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又独立于原文本,而不仅仅是在媒介上有所不同的新质文本。同时,在部分已经拥有原文本知识的观者眼中,两部文本又实现了互文,促使新的读解形成:在无法保证生存的大前提下,不论是最后受尽良知煎熬的辰平,或是自始至终盲目遵循村里惯习行事的阿林婆等,对于情节的重新设置,体现出了改编者的取向和电影的主题——即对底层小人物实存的关心。
四、结语
电影《楢山节考》既不是原作小说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仅仅顶着与小说相同的标题而内容毫无相干的凭空想象,而是与小说文本深度对话后的产物。在对整体环境以及情节的叙述上,电影文本戏仿了小说的结构与设计,同时也利用了影像叙事的特点,建构了一个更加立体、贴近现实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受到村里惯习凝视的不只是村民们和食物相关的各种活动,从食衍生出来、与性相关的制度,同样是对失格者(雨屋一家、利助等人)的无情镇压。同时电影文本对小说人物的重新塑造,以及对于原文本细节的重新编排可以看出改编者的取向。电影《楢山节考》于1983年上映,为何选择在这个时期选择改编深泽七郎的同名小说?其理由便在于改编者希望完善,或是弥补当代文化当中的缺省。改编者看到了原文本对于极限条件下依靠生存本能挣扎着的村民们的刻画,并通过合作、重写等改编策略,将其在文本诸多侧面中选择的这一侧面展现在观影者的面前,就是要在出现扁平化趋势的日本社会揭开习以为常之的生活表层,以野蛮、丑陋冲击人们的感性,以使人们重新思考人性与生命的内涵。
同时,无论是电影文本还是原文本,其本质都是符码的组合,关键的一步在于接受者的解码。改编者作为接受者其中之一,自然承担了解码的任务。电影《楢山节考》通过选择并放大原文本中的某一侧面,建立了自己的想法,并向其他接受者即观影者传递了改编者的解读,与他们形成了互文。阅读过小说文本的观影者在观影的过程中做了重读,对电影做出评论实际上对于原文本也进行了评论;而未曾了解过原文本的观影者可以快速把握其主题之一,参与到文本游戏当中,从而形成了文本的狂欢。
注释:
①⑤庞红梅:《论文学与电影》,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第67页。
②③④于荣胜:《日本现代文学选读(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第123页,第113页。
⑥近藤良树:「昔话·神话にみる蛇の役柄-知恵·生命·异性の象征となる蛇-」,『HABITUS』(西日本応用伦理学研究会·広岛大学伦理学研究室) 2003年第16期,第1-9页。
参考文献:
[1]于荣胜.日本现代文学选读(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庞红梅.论文学与电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3](美)玛里琳·艾维.消逝的话语——现代性、幻象、日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罗伯特·斯塔姆.电影改编:理论与实践[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2).
[5]张腾玮.书写蛆虫,至死方休——电影《楢山节考》[J].名作欣赏,2018,(32).
[6]刘惠子.楢山信仰包裹下的村落共同体与个人身份的建构——论深泽七郎《楢山节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1,(01).
[7]赵立.今村昌平的影像世界——以《楢山节考》《鳗鱼》为中心[J].日本学论坛,2006,(04).
[8]近藤良樹.昔話·神話にみる蛇の役柄-知恵·生命·異性の象徴となる蛇-[J].HABITUS(西日本応用倫理学研究会·広島大学倫理学研究室),20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