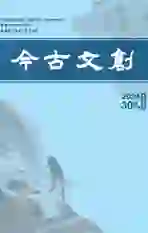王船山《礼记》诠释之章句体例及方法辨析
2024-08-20付兵高政飞
【摘要】王船山《礼记》以章句注疏体例不仅为汉宋之风流行的学术界注入了一股清流,在学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立足于王船山《礼记》章句注疏体例,通过文献研究、归纳比较以及统计分析等方法,辨析《礼记》章句的诠释特点。
【关键词】序文;题解;章旨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0-008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0.024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中国德性伦理:传统资源的阐释与现代传承”(项目编号:18GZGX17)。
“船山先生《礼记章句》,因《大学》《中庸》有朱子《章句》而作也。”[1]船山采用章句体例完全是沿用朱熹对《大学》和《中庸》的诠释,儒学重视道统心传的讲习与承前启后,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诠释,而阐发义理必须有文字训诂的基础,而此基础便是汉儒的章句之学。他融贯义理与考据,兼采汉宋诠释路向,加之“章句”诠释体例的特点——分章断句、字词训诂、判定辞义、串讲经文,因此注重训诂的章句体便成了该书最基本的诠释形式。
一、撰序文,点明要旨
王船山的《礼记章句》,是对儒家经典《礼记》逐篇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诠释之前,船山注重贯通辞气,阐明全书要旨,作全书总序《礼记章句序》,在对每篇进行诠释之前又撰写单篇序文进行题解,旨在“引导读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去阅读和理解文本,在‘意’与‘志’的融合中领悟和阐释经典文本的深层意蕴。”[2]
首先,于序文中交代《礼记章句》的写作背景:“夫之生际晦暝,遘闵幽怨,悼大礼制已斩,惧人道之不立,欲乘未死之暇,上溯三礼,下迄汉、五季、唐、宋以及昭代之典礼,折衷得失,立之定断,以存先王之精意,征诸实用,远俟後哲,而见闻交绌,年力不遑,姑取戴氏所记,先为章句,疏其滞塞。”
《礼记章句》作于船山晚年人生晦冥昏暗之际。据刘毓崧《王船山学谱》记载,《礼记章句》成书于1873年,于1877年(康熙十六年)修订完成,此时船山已经59岁,明朝已灭,清朝当权,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寄希望通过复兴古礼以实现移风正俗的目的。
其次,于序文中阐述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和作用,主张仁礼互为体用,高度彰显礼对于人禽、夷夏、君子小人的独特价值。“缘仁制礼,则仁体也,礼用也;仁以行礼,则礼体也,仁用也”,船山用体用范畴来阐释仁和礼的内在联系,认为仁礼互为体用。一方面就礼的生成而言,礼以内在的仁为基础,仁是本体,礼是仁外在的表现形式,因此,仁体礼用;另一方面,从发用的角度来看,礼是仁得以展开的基础,仁的发用必须依靠礼才能实现,所以礼体仁用。
最后,船山于序文中提出了礼的修养价值。“天下万世之为君子,修己治人,皆以是为藏身之固,而非是则仁道不显。”
除总序外,船山于46篇各有分序,以明篇章主旨。因《曲礼》《檀弓》《杂记》有上下篇之分,因此《曲礼下》《檀弓下》和《杂记下》无序言。纵观各篇序文,皆通过“此篇”“是篇”等形式先概括全文要旨,点明题意,帮助读者领会全篇的内容。
二、作题解,提示读者
于《礼记》单篇诠释中通过注释篇题来提示读者,点出读者采取恰当的阅读方法,指出读者容易误解及忽略之处,通过提示引导读者直达文章义理深处,实现“言”与“意”的内在统一,从而更好地把握全文主旨。
在提示阅读方法上,如《檀弓上》:“诚体验而慎思之”“诚学者择善之切图”;《王制》:“读者达其意而阙之,不亦可乎!”即对于《王制》篇中周制、夏殷之礼由于文献不足所截取的内容真伪难以区分,读者只需达意,不必穷究;《曾子问》:“学者不可以是而疑之也。”类似的读者提示还散见《文王世子》《乐记》《经解》《明堂位》等篇。
船山在篇序中提示读者惯用“读者”“学者”等语,旨在通过提示,确保读者阅读经文时采用恰当的方式,不至于咬文嚼字而忽略大意。同时,船山于序文中还指出篇章易误解及忽略之处,如《内则》:“学者勿以此篇为事迹之末,慎思明辨而笃行之,则经正而庶民兴,邪说之作,尚其有惩乎!”即学者不要因为《内则》记载的是细枝末节之礼仪而忽视,而应该坚持以此来慎独自勉,若此便可以制止邪说横行;《学记》:“此之不讲,乃有凌躐鲁莽以谈性命而诡于佛、老者,为正学之大蠧,固君子所深惧也已。”诸如此类提示还散于《礼运》《坊记》《乐记》《明堂位》《中庸》等篇目序言。船山通过序文指出全文易误解及忽视之处,旨在倡导读者不应该有前见,而应该注重文本内容,统观总体,兼具本末体用,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全文主旨。
三、分章释意,概括章旨
古人著书,不为章句。“在章句这一解释体式里,以分篇章、断句读为先导,训释词语、讲解句意以相互证法,阐释意蕴,是整个经典解释过程的中心部分、关键部分。”[3]船山以汉学为起点,通过分章释意,串讲经文,更好地实现文本解释与心理解释的内在融通,在阐释文本原意的同时更好地进行义理发明,概括章旨,显示意向。
首先,划分篇章。《礼记》文本驳杂,内容形式多样,为更好地阐释礼学内涵,船山首先对《礼记》文本划分章节,断定句读。即通过分章断句的形式来解析文本的内在结构,更好的阐释句意,抒发章旨。在《曲礼》中,船山指出“先儒因简策繁多,分为两篇。上篇凡六十三章。旧未分章,诸说多所割裂,今寻绎文义,为之节次如左。”传统文本简策繁多,由于未分章节,致使许多文本原意遭到割裂,不利于总体把握篇章要旨,而面对明清更迭,“大礼已斩”,为求文本原意,船山坚持章句的注经模式。
在给《礼记》49篇划分章节时,船山先在序言中指出全文章节总数,采用“凡……章”的模式。如《曲礼上》:“上篇凡六十三章”、《曲礼下》:“凡三十章”、《檀弓上》:“上篇凡百二十五章” ……此类共有45篇;将全文统作一章的有《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三年问》《深衣》《投壶》《丧服四制》6篇;没有分章的有《明堂位》《儒行》《大学》《冠义》4篇,针对此4篇,船山指出了原因:《大学》篇沿用朱熹之划分;《明堂位》记载的多是“吕不韦、蔡邕之邪说,不待辨而知其诬也”。《儒行》“词旨怪诞,略与东方朔、扬雄俳谐之言相似”,《冠义》篇一方面是与《士冠礼》相对应的,同时又强调了冠礼的重要性,未分章节是想“以词义通之”。
其次,注音释义。船山采用传统训诂之法,对文中关键且难懂的字词进行注音释义。在注音方面,船山采用“反切法”和直音法。如:《曲礼上》“敖不可长”中注“敖”为“敖,五报反”。除“反切法”外,对于文中某些难认的字,船山也采用直音的方式,用“读若”“读如”进行注音。如:在《曲礼上》“其尘不及长者,以箕自乡而扱之”一句注“扱”为“扱,读若‘吸’”。对于重复出现的字,船山仅注一处,并以“下同”“篇内并同”的形式进行标明,避免赘述。如在《曲礼上》“谋于长者,必操几仗以从之”,注“长”为“长,丁丈反。下同”。在释词上,船山首先释义篇题,如《曲礼》之“曲”、《礼运》之“运”、《大传》之“大”等,通过解释篇题避免读者误解。其次,通过借鉴传统训诂术语,采用同类释义法,充分利用“也、者、曰、为、谓之、犹”等传统训诂术语进行释义。如:“‘道’,顺也”、“在野曰‘兽’,见获曰‘禽’”。
最后,概括章旨。船山在释字词的基础上对文章进行串讲句意,概括章旨,显示意向,以此对词语训释和句意进行小结,并与题解相照应。如《曲礼下》各章章旨:
右第一章。此章所记操奉授受之容,与上篇第三十八、九章相类。特上篇所记乃少贱之事,而此所记者,为宗庙朝廷之礼。故不以类相属而系于此。
右第二章至右第七章无章旨。
右第八章。此上八章皆记士、大夫之礼。此下三章则杂诸侯以下之礼而记之。
右第九章至右十二章无章旨。
右十三章。右第十三章。自此章以下至于篇末,皆记天子、诸侯、大夫、士庶尊卑隆杀之节,而先详其名称之别。右第十四无章旨。
右第十五章。此章记容之殊,盖名正而分定,心安其分而著于容也。
右第十六、十七、十八无章旨。
右第十九章。右第十九章。自十三章以下记天子、诸侯、大夫等杀名称之别,君臣之名正而分定矣。至第十八章言君不虚贵之道,以见尊者之必有以尊。此章则言忠臣资敬事君之节,以见臣之尊君不徒以其名而实必践之,记者之意深矣。此下十一章则以補前章之所为备人杂记之焉。
右二十至右三十无章旨。
如上,船山在概括章旨时并不是对每章都逐一概括,而是于义理凸显处进行总结,概括前文内容,于义理微末章只划分篇章而不彰显章旨。同时于恰当章节给出提纲挈领性的章旨,既总结上述章节内容,又统领下面章节内容。如:在第一章章旨中,船山便解释了将《曲礼》划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原因,即上篇记载的是“少贱之事”,而下篇所记载的为“宗庙朝廷之礼”,因此所记载的是不同的礼仪,故而分之。在这里,第一章章旨便是起着总结性的作用,点出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体,而第二至第七章完全是第一章“体”的发用,因此只需划分章节无须概括章旨。而第八章则是提纲挈领性的章旨,“此上八章皆记士、大夫之礼。此下三章则杂诸侯以下之礼而记之。”它既是对以上八章的归纳总结,同时又引出第九至十二章的内容。同样,第九至十二章是对第八章“体”的发用,因此也只划分章节而无章旨。第十三章又是统摄性的章旨,“自此章以下至于篇末,皆记……”即第十九章章旨如同第十三章,它涵盖余下章节全部的内容,因而余下章节亦无章旨。可见,船山在划分章句时,极其注重诠释技巧,善用体用范畴,既意思明了又详略得当。
四、互相参引以求礼
“以经典相互作为解释和说明的依据,也才是最为可靠和最具有权威性的。” ①船山治经,注重群经会通,充分发挥经典文本内在义理。在《礼记章句》中,船山充分吸收传统典籍,除充分征引传统礼书材料外,还大量引用其他文献来进行参证,以经证经,以经解经,从而实现“《礼记》这部内容庞杂、语句晦涩的典籍,豁然贯通,宗旨明晰” ②。
首先,以《礼记》单篇互参。《礼记·檀弓上》:“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船山注曰:“‘缩’,直也。‘古’,谓始有冠时也。一副之布不周于首。古冠辟积少,以一幅布稍益之,直裁而缝合之,足矣,《杂记》所谓‘条属’也。” ③引《杂记》而证,在《杂记》中,船山释“条属”为“条属者,斩衰以绳,齐衰以下以布,即为武之一条而垂其余为缨,吉冠则武缨异材也。” ④“条属”所代表的是一种首服之冠的材料,丧服不同,条属自然也不相同,也就是说,吉服之冠的冠带和冠卷是采用不同的材料制作的,而丧服之冠的冠带和冠卷则是用一根布条折叠而成,即屈折一绳为冠卷,然后垂下为冠缨。⑤《礼记·檀弓上》:“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船山注曰:“皆谓在远闻讣而哭也。若同国中,则就哭之。按此与《杂记》及《奔丧》不同,传者异也。以情理推酌,此为得之”。⑥而针对远闻死讯而哭丧,《杂记》记载为“闻兄弟之丧,大功以上,见丧者之乡而哭”船山注曰:“《奔丧》篇云:‘大功望门而哭’于此异。卢氏谓是降服大功者,未知是否” ⑦,即针对奔丧的对象、亲疏远近、关系位阶不同,哭丧的位置也不同,因此,船山强调哭丧应该根据人情事理来进行审定,不能越位失礼。
其次,以《周礼》《仪礼》参证。船山尤其注重“三礼”之间的互为体用的辩证关系,因此,在《礼记章句》中,他时常援引《周礼》和《仪礼》中的文本来佐证与引申《礼记》,从而实现《礼记》诠释“参互考校,借彼证此,乃得贯通” ⑧的效果。如:《礼记·曲礼上》:“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间,愿有复也’,则左右屏而待。”船山注曰:“‘间’,空暇也。‘复’,如《周礼》之‘复逆’之‘复’,下告上之辞。” ⑨“复逆”出自《周礼·天官·宰夫》:“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关于此句,郑司农注曰:“复,请也。逆,迎受王命者。” ⑩郑玄谓:“复之言报也。” ⑪此处的“复”阐释的是下级对上级之礼,船山于此解释“复”字,利用《周礼》予以佐证,从而严明上下等级关系。《礼记·曲礼上》:“故日月以告君,齐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船山注曰:“‘日月’,谓所生年、月、日也。《周礼·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书成登于朝,是‘告君’也。” ⑫郑玄注:“《周礼》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书之以告君,谓此也。《昏礼》凡受女之礼皆于庙,为神席以告鬼神,谓此也。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会宾客也。” ⑬船山于此引用《周礼·媒氏》来介绍娶妻之礼制,旨在彰显礼之别之义,凸显礼的独特价值。
最后,以“五经”互通互证。船山认为“六经”最后的宗旨都重归于礼。他说:“《六经》之教,化民成俗之大,而归之于《礼》。” ⑭因此,在《礼记章句》中,船山大量引用“五经”中的材料来解释《礼记》中的文本内容,从而为“以经解经”寻找可以互证的文本依据。《礼记·檀弓上》:“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台鲐始也。”船山注曰:“台,本‘壶’字之误,户吴反。去纚而露其紒曰‘髽’。‘台鲐’,《春秋传》作狐骀。” ⑮郑玄注曰:“台,当为‘壶’字之误也,《春秋传》作“狐骀”。⑯而在《郡国志》和《孔子家语》中都写作“狐骀”,船山于此遵循郑玄的观点,并引用《春秋传》来进行校勘,旨在尊重史料,凸显兵为祸始,不可轻试。《礼记·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船山注曰:“此与《尚书》及《周礼·职方》事不合,记者传闻之异,约略计之尔。” ⑰据《尚书·夏书·禹贡》记载:“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⑱这是早期的“五服制”,即以国都为中心,把依次向外延申五百里的区域称为“一服”,根据距离远近依次便有“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孙希旦解释为:“《禹贡》据一面而言之,故曰‘五百里’,此据两面言之,故曰‘千里’”。⑲船山认为此处的“甸”“采”和“流”与《尚书》等记载不符,应该是传闻的差异,希望通过多重文献来参证早期的疆域概念,凸显其博闻强识的思想特质。
五、辩证诸篇以求礼
第一,以体用诠释篇章联系。关于“体用”范畴,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辞典》中解释说:“‘体’指形质,即本体或实体,‘用’指形质的妙用、功用和作用”。⑳“体”“用”概念起源于先秦,到了魏晋时期,“体”“用”才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如船山认为文中《礼运》与《礼器》、《坊记》与《表记》、《孔子闲居》与《仲尼燕居》、《学记》与《大学》之间都是体用本末关系。
在《礼记》和《礼运》篇中,船山用形而上与形而下、道和器、表和里等哲学范畴来诠释两者内在的体用关系。他认为“体用相函者也……体以致用,用以备体”。㉑即是说:“‘体以致用’,言‘体’用来求得功用,或者说,‘体’包含者‘用’。‘用以备体’,言‘用’一定有它的实体,‘用’就是‘体’的作用”。㉒一方面从“体”而言,礼作为二气五行三才之德,必须依赖于礼节情去私的功用,才能使天下万物自然运行各得其所,而另一方面,要使礼能充分发挥节情去私以合天理的功用必须依赖于作为二气五行三才之德的礼。正如船山所言:“凡言体用,初非二致,有是体则必有是用,有是用则必固有是体,是言体而用固在,言用而体固存矣。” ㉓因此,体用相摄,“天下无无用之体,无无体之用” ㉔,二者不可分割,密切统一。
第二,注重经传相分。“‘经’一般是指孔子以前就已存在的文献资料,在经过孔子之手删削和整理之后存留下来的文本”。㉕“所谓‘传’者,既有传递、转达的沟通之意,也有展开、解说的阐发蕴含,恰如所谓‘hermeneutics’的意思可相对照”。㉖经传相分本是“朱子经学解释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㉗而船山在《礼记章句》中也强调经传相分。他说:“此章释第三章分地建国之制而以算法详之者也。自第三十章以上皆王制之正文,此章以下至末,则因前文名例之未悉者而为释之。古之著书者具有此体,前为经而后为传也。” ㉘在《礼记章句·王制》中,船山将《王制》全篇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按照他的划分,此篇共35章,第一章至第三十章为正文,是经,主要讲述的是各朝的典章制度,而第三十一章至文末(第三十五章)则为传,主要解释前面正文部分的复杂制度。船山之所以沿用此种经典解释方法大概是因为此篇是汉文帝令儒生根据记忆编辑而成,“其间参差不齐,异同互出,盖不纯乎一代之制,又不专乎一家之言,则时有出入” ㉙,因此要求读者“达其意而阙之” ㉚。
除在同一篇目采用经传相分之外,船山还采取跨文本的方式来实现经传相分,即以《周礼》《仪礼》为经,而《礼记》为传,船山说:“《周礼》《仪礼》,古之礼经也。戴氏述其所传,不敢自附于经,而为之记,若《仪礼》之记,列于经后以发明之焉。” ㉛《礼记》是对《周礼》和《仪礼》的引申和发挥。如:船山认为《内则》是《周礼》师氏用德行教化民众具体仪节的记载,他说:“周礼师氏以德行教国子,曰‘孝德’,曰‘孝行’,曰‘友行’,曰‘顺行’,其节目之详,着于此篇。” ㉜同时,他认为《礼记》中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和《聘义》六篇都是用来解释“《仪礼》当篇之义” ㉝,船山于这六篇序言中皆有发明。也就是说,《仪礼》当篇为经,而对应的《礼记》当篇之义则为传。船山注重经传相分的解释模式,旨在克服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只讲传注而不注重经义,从而出现脱离经文以探求义理的偏向,也从侧面凸显出了船山黜虚崇实的学术精神。
注释:
①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②梅显憋:《融通六艺,博而守约——郑玄〈礼记注〉特色一瞥》,《历史文献研究(第29辑)》,第54页。
③④⑥⑦⑨⑫⑭⑮⑰㉑㉘㉙㉚㉛㉜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38页,第977页,第160页,第975页,第41页,第46页,第1171页,第150页,第307页,第631页,第366页,第299页,第299页,第11页,第669页。
⑤丁鼎:《〈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⑧冉觑祖:《礼记详说序》,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9页。
⑩⑪郑玄注:《四库家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0页。
⑬⑯⑲㉝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页,第179页,第319页,第1468页。
⑱张居正:《尚书直解》,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⑳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㉒吴乃恭:《船山理论范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㉓㉔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62页,第328页。
㉕㉖景海峰:《论“以传解经”与“以经解经”——现代诠释学视域下的儒家解经方法》,《学术月刊》2016年第6期。
㉗杨浩:《孔门传授心法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30页。
参考文献:
[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作者简介:
付兵,第一作者,男,湖北荆门人,新疆理工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儒家哲学。
高政飞,通讯作者,男,新疆理工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