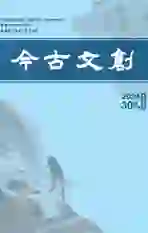曹丕散文略论
2024-08-20魏昭青忆
【摘要】曹丕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为我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诗、赋作品外,他在散文方面的创作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典论·论文》基本包括了曹丕的文学批评主张,是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开山之作,其书信体散文一改两汉时期只讲应用不讲审美的风格,文学价值极高。本文分别分析曹丕的《典论·论文》及书信体散文,并通过对其作品的了解,探索曹丕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0-003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0.011
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曹丕的研究一直不为学界所重视。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好转,曹丕的“文气说”“文体论”等文学理论观点成了学者们探讨的热点,其诗歌,散文辞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与探索。曹丕散文是其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包含着他的政治态度及人生观与价值观,从实用角度可以分为公文、书信和《典论》三部分。其中,《典论·论文》集中了曹丕的文论观,撰于曹丕太子时期,曹丕以其自身深厚的文学修养以及作为邺下文人中心这一特殊身份对当时文坛上的批评现象以及文体论做出了系统的阐述与评论,为后世文学批评的完善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典论·论文》
曹丕作为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在建安文坛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作《典论》原有22篇,后大都亡佚,只存《自叙》《论文》《论方术》三篇,《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视为中国文学自觉开始最早的标志。曹丕在其中首次提出“文气说”“四体八科”等文体观点,为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文学批评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在《典论·论文》的开篇就对文坛自古以来的陋习做了总结。“文人相轻”这一现象在文学史上从未断绝,刘勰更是在《文心雕龙·知音》一篇中,以韩非、司马相如、班固、傅毅等人为例,列举了大量“文人相轻”的实例。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我国古代的尊儒思想有关,儒学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据强势地位,因此“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一直根植于每位学子文人的心中,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下极易导致“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局面。而对“文人相轻”这一现象的评价,学术界历来也是褒贬不一的。褒者认为这一现象可以形成竞争的局面,促进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发展;贬者认为它有违“道德观”,在文学评论方面有失公允。从《典论·论文》的内容来看,曹丕显然属于后者。究其原因,或许是因曹丕自幼学习儒学,而“文人相轻”从功德上来讲,与儒家思想讲求的中和与仁义是相违背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了两种错误的批评态度,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二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新语·术事》中写道“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在历朝历代的文学批评作品中,每每提及“文人相轻”,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引入“贵远贱近”的现象来进行论证。”刘勰也在《文心雕龙·知音》说:“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贵远贱近”现象的产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古人不会参与到今人激烈的竞争中,因此今人对他们的评价,往往能够摆脱现实因素导致的主观色彩,更加公平公正。对古人的作品,后人大多挖掘作品中的现实意义以及审美内涵,对其长处欣赏夸赞或者学习借鉴。而对“今人”的作品,文人大多“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将文学评说的重心放在“挑错”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今人对“古人”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滤镜,这种滤镜是由我国自古以来的“尊古”心理造成的。《庄子·外物》说:“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先祖迷信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以及日常生活,更是深度渗透进文化思想中,以《诗经》和《楚辞》为例,作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的作品,其意义以远超于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更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伫立在后世文人士子的心中。针对“文人相轻”现象,曹丕认为应“审己以度人”,从自身角度出发,审查自己,衡量别人。在文学批评方面,应持有公正的态度,对自身的短处要有清醒认知,对他人的长处也应心怀敬佩。这一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而曹丕对文学创作的这种清醒认知,与其作为邺下文人集团核心这一特殊身份有关,也与其自身胸怀气度有关。除此之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凭借着自身的文学素养以及对“建安七子”及其作品的充分了解,通过分析“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和艺术特点,较为全面地对他们的作品做出了总结,为后世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建安七子”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文值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典论·论文》作于曹丕身处太子之位时,他不仅是一位创作者,更深处权力的中心位置,《典论·论文》一篇看似只为批评文学,实则也暗藏着曹丕争位的私心,也可看作其为稳固地位所作。当时的曹丕虽然已经取得了立嗣之争的胜利,身居太子之位,但心中仍惴惴不安。才高八斗的曹植不仅仍然深受曹操的偏爱,其本人也有建功立业之心,曹丕将文章的价值提到“经国大业”的高度,除为了自己的政治功绩以外,一方面也是希望曹植能专心创作,效仿徐干淡薄政治。然而曹植的功业之心甚烈,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则认为:“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曹植这种对政治抱负的渴望给曹丕造成极大的压力,因此兄弟间的竞争即使在曹丕处于太子时期,也从未停止过。曹丕的《典论·论文》很大原因是出于政治功用所作,一方面他深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其父曹操,因此选择在文学方面下功夫,其得意之作《典论·论文》不仅是文学批评文章,更是他治国理政的代表。另一方面,建安文学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和《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文学作品紧密联系现实,文章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曹丕的“文章经国”思想不仅是为了提高文章的地位,更是为了加强文章的现实功用性。
(三)文体论
“文气说”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又一重要观点。《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最早出现的“以气论文”观点,曹丕受其影响,提出了“文气说”,然而二者又有区别,孟子认为:“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气”要靠后天养成。曹丕所说之“气”更偏向“元气”,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他首次将自然之气引入“文”的范畴提出了“文气论”,而关于“文气”究竟指“人之气”还是“文之气”,学术界向来众说纷纭。纵观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发展史,曹丕所说“文以气为主”应当为“人之气”。曹丕认为这种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因此每个人都拥有独特之气。《典论·论文》中“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清”“浊”之论源于道家“阴阳之说”。《黄帝内经》:“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而“为气所主”之“文”,亦属于天地万物。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体性》中写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刘勰亦认为作家的先天之气影响作品的创作。
除此之外,曹丕认为,唯有“齐气”,才能众体皆备。刘勰在《养气》一篇中提出,作家唯有“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才能“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只有心静气顺,才能写出好文章,作家以气养文,气之好坏,影响文之优劣,气齐而顺,则营养均衡,文杆粗壮,文体枝繁叶茂。而不同作家之气养出的“文之树”也各有千秋,或擅辞赋,或擅章、表,或风姿俊逸,骨气清奇,或气缓文舒,文采优美。
除“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外,曹丕还在《典论·论文》
中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分类观点,并用“雅”“理”“实”
“丽”来描述八种文体风格,开启了我国文体学观念,后世《文赋》《文心雕龙》中关于文体论的观点,都是在曹丕四科八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书与信中的生命意识
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战争时时刻刻危及人们的生命。朝不保夕,生命苦短,因此魏晋文人大都对生命有着特殊的感怀,在整个大环境的熏陶下,他们逐渐开始变得对死亡释怀,转而探索在有限的光阴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死观的转变,纵观三曹的作品,可窥一 二。《秋胡行·其二》:“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曹操认为担心生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唯有“爱时进趣”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价值。《龟虽寿》亦可以看出曹操的生命态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哪怕年岁已老,也要在暮年的光阴中迸发出别样的力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曹植作《薤露行》:“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表达在有限的人生中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亦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期望以著书立说扬名后世。
(一)文章不朽观
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写道:“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可见曹氏父子三人,在面对时间焦虑时,都是积极进取的心态,但与其父兄相比,曹丕似乎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别样的自我实现道路。曹操与曹植都希望通过实现政治抱负,来使短暂的人生意义非凡,而曹丕想得更为长远,他不仅立足当下考虑,而且将眼光放在千百年之后,唯有“著书扬名于后世”,才能永垂不朽。如果说“文章经国”思想是曹丕作为魏国太子的政治手段,那“文章不朽”观则是他摆脱政治身份后,个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体现。与“文章经国”相比,曹丕的“文章不朽”观是曹丕站在一个文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论的。曹丕自幼习得儒家经典,虽“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却“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留下大量文学作品的帝王。事实上,他也真正做到了“文章之不朽”。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视为中国文学自觉开始最早的标志。他不仅推动了建安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在创作层面上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七言体《燕歌行》被誉为“七言之祖”。杂言体《大墙上蒿行》句式参差,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具有开创意义。
(二)及时行乐,乐往哀来
曹丕的“文章不朽”观与其独特的生命意识密不可分。他生于乱世,虽自幼就习惯了战乱对人们生命的迫害,但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疫,却再一次改变了他的生命观,突发的疫情使建安七子中的五人陨落,昔日“行则连舆,止则接席”的好友在这场浩劫中顷刻的丧命,这场变故刺激曹丕开始重新对生命的思考。他在《与吴质书》中回忆昔日的南皮之游:“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游猎宴饮,好不快活,但却在万籁俱寂时忽然伤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极致的快乐会带来突如其来的悲伤,当事情发生时已经到达兴致的巅峰,往后的每一秒都在失去,因此极致的欢欣背后是心中的怅然若失之感。故事的结局是昔日南皮之游的好友阴阳相隔,建安七子众星陨落,邺下文人集团人才凋零。后来,当曹丕终于踏上九五至尊之位,阶下众臣同贺,却唯独少了年少时期陪在自己身边谈天说地的友人。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因此,当及时行乐,曹丕在生前沉迷奢华的狩猎宴饮,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夜饮”与“夜宴”的描写。然而这并非曹丕独创,《古诗十九首》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面对岁月匆匆,建安诗人以及时行乐相抗,他们在诗歌中所抒发的,并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惜时之感,而是一种对人生的绝望与幻灭之感。曹丕《与吴质书》亦感叹:“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人生苦短,哪怕点燃蜡烛,也能争取片刻的欢愉。“烛”在古代是珍贵之物,曹丕却常常举办奢侈的夜宴,然而作为帝王,曹丕在死后选择了薄葬,他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在历史上大多追求长生的帝王中,显得格格不入,正如他在《与王朗书》中所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这种生死观,在当时极具先进性。曹丕虽不追求肉体的“永生”,但他却极力追求精神上的“不朽”,他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
三、结语
魏晋的文学自觉促进了文学各方面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诗赋创作的发展,写作的高度发达加上文人间密集的交流与思考同时也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生。曹丕散文的创作艺术成就颇高,其《典论·论文》虽是出于政治目的所作,但却在文学批评领域价值极高。
除《典论·论文》外,曹丕的书信体散文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文选》于曹丕文章,所选除《典论·论文》外,其余三篇全为书信,它们反映了邺下文人集团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是曹丕生命意识的书写。与古诗十九首的诗人不同,面对时间焦虑,曹丕虽也有及时行乐的心态,但其“秉烛夜游”是为了惜时,在飞逝的时光中,尽可能地享受欢愉,感受人生,而非精神幻灭后的自暴自弃。面对生命的无常,曹丕虽然也时常感伤,但总体而言还是积极进取的,《典论·论方术》:“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他将生死看淡,只有摆脱恐惧,才能更好地看待当下。
自古众多评论家认为曹丕的文学成就不高,不及其父兄,但这种说法恐有失偏颇,《文心雕龙》:“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援,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选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可见,曹丕无论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做出的贡献都是非同一般的。
参考文献:
[1]王淑洁.魏晋书信文研究[D].华侨大学,2011.
[2]朱丽卉.浅谈曹丕散文中的死亡意识与庄子的道家哲学——以“伤秋” “悲风”为意象进行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05):22-26.
[3]杨天平.魏晋书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2.
[4]杨士卿.曹丕散文研究[D].扬州大学,2007.
[5]赵立新.集大成与开风气——试论杜甫的诗学思想[J].杜甫研究学刊,2001,(03):16-22.
[6]谷维佳.从“正变”到“真伪”:论盛唐李、杜诗论中的“真伪之辨” [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129-138.
[7]张岳林,杨洋.“文章”经国与“作者”自觉—— 《典论·论文》原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J].文艺理论研究,2019,(01):138-145.
[8]张东星.试论曹丕“文本同而末异”之“本同”[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02):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