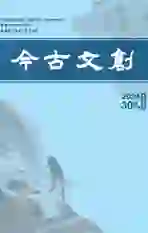解构主义视角下的《恋爱中的女人》
2024-08-20田园
【摘要】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采用解构主义的视角,对当时盛行的男性中心主义及其对性别角色和家庭结构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小说以伯金为中心,重塑男性形象,瓦解性别二元论刻板印象,展示了他情感上的细腻和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劳伦斯通过伯金与厄秀拉的关系,描绘了一种基于平等、理解的新型男女关系,超越传统性别动力结构。这种关系模式不仅在文学上具有意义,也为当代探索平衡的性别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解构主义;性别角色;男性中心主义;性别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0-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0.002
一、引言
《恋爱中的女人》由劳伦斯创作于20世纪早期,此时社会观念和文化正经历转型,但男性中心主义在社会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该时期男性在各领域占主导地位,展现坚强理性的形象,而细腻的情感被视为女性特质。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旨在揭示文本内在矛盾,挑战传统文学中的二元对立观念,如理性/感性、男性/女性。德里达认为文学作品是开放、多重解读的空间,意义随读者背景变化而变。作家的文本常在解构某种逻各斯秩序或“暴力的等级秩序”的同时展现生命力。[1]本文通过解构主义视角分析《恋爱中的女人》,以角色伯金为核心,探究劳伦斯如何重塑男性形象,打破性别二元论,理解小说文学价值及当前社会文化意义。
二、伯金的形象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
(一)柔弱病态的外形
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基础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即男性支配女性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模式。这种二元逻辑结构是建立在男性和女性不平等的预设上,其实质是默认男性优于女性进行的等级划分,确立压迫与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一错误的逻辑在男权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也破坏了男人和女人的和睦。[2]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通过伯金和杰拉德两个角色的对比,巧妙地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下的传统男性形象,揭示了性别角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解构主义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解构结构的存在。[3]杰拉德的体貌特征符合传统的男性美学标准,他身体健壮,浑身蕴藏着未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4]“杰拉德本来肤色白净,但让太阳晒黑了。”[4]他的身材强壮、皮肤白皙却晒得健康的肤色,金色的头发,这些外貌特征都符合西方文化中经典的男性魅力,暗示着他与自然界的密切联系和户外活动的热爱,进一步强调了他的阳刚之气。杰拉德的这些特征符合男性中心主义下的理想男性形象,即强壮、自信、有领导能力的男性。
与杰拉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金,他的外貌和性格特征与男性中心主义下的理想男性形象大相径庭。“伯金像克里奇先生一样瘦削,苍白的脸上露出些许病容。”[4]伯金的身型和神态都显露出他与传统男性气质的不符,而病后的伯金的形象则是更为糟糕。“他很瘦削,两腮下凹,一脸的可怕表情”[4],毫无生机与活力,更加背离了男性中心主义框架下的理想男性形象。伯金的外在形象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成为了解构男性中心主义下传统男性形象的重要元素。通过与杰拉德的对比,伯金的形象突显了男性角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挑战了传统男性形象的单一性和刻板印象。
(二)敏感不安的情绪
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社会对于男性角色的期待是体现坚强、勇敢以及理性的属性。而恐惧和悲伤等通常被贬低为软弱的情绪,需被压抑以维护男性的强势和独立形象。在内在世界和情感表达方面,伯金同样与理想男性形象有显著的偏离。他高度重视内心体验,坦然面对自身的脆弱和不确定性。
伯金从不避讳表达自己内心的脆弱。“整个观念已经死了。人类本身已经枯萎腐烂。他们看上去很像样儿,很漂亮,是一群健康的男女。可他们都是所多玛之果,是死海之果,是树上的虫瘿。”[4]伯金将内心敏感恐慌的情绪尽数倾出,表达了他对现代人类和社会的深刻不满和失望。他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极端批判和对人类本质的根本怀疑,揭示了他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所多玛之果”和“死海之果”暗喻了他对现代人类的深刻不满。所多玛和死海在圣经中代表着罪恶和毁灭,伯金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现代人,显露了他对人类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的看法。劳伦斯并不是男性沙文主义者[5],伯金时常表达内心动荡不安的状态,从不刻意伪装强大的男性形象,是对中心的偏离,也是为女性的让位。伯金直白地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不安,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和对现代文明的根本性怀疑。这些观点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这种对个人情感和心理状态的深度关注以及对社会价值观的根本性质疑,揭示了伯金对自己内心和情绪变化的敏感不安。
(三)反理性的行为
伯金的反理性行为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背离了理想男性的形象。首先,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于赞美理性、自制和坚强的男性形象。然而,伯金的行为却完全背离了这种传统的男性角色设定。在与赫麦妮的争执后,他的情感失控,采取了一种极端的、非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冲突。他知道他无法恢复理智,他是在黑暗中游动着。他脱光衣服,赤身坐在樱草花中。[4]伯金的这种行为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男性坚强形象的反叛。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框架下,男性被期望掩藏自己的脆弱和恐惧,但伯金却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展现他的情感和内心世界。通过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融合,伯金试图在自然界中寻找安慰和自由,这表明他对传统社会规范的抵制以及对更纯粹、自由生活方式的渴望。
其次,伯金对旧的道德、人和人类感到厌倦“但他对旧的道德、人和人类干到厌倦了。他爱的是这温柔、细腻的草木,那么清爽、美妙。他对旧的惆怅不屑一顾,摒弃旧的道德,在新的环境中获得自由。”[4]这反映了他对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深刻质疑。他在自然中寻求自由,这种行为揭示了他对现代社会构造和人际关系的深层次不满。劳伦斯热衷于生活在一个神秘的宇宙中的想法,超出了理性或合理化解释的还原能力的范围。[6]劳伦斯借伯金这一人物,拒绝遵循旧的道德和社会规范,展现了一种对个人自由和自我表达的强烈追求,这与男性中心主义倡导的自我牺牲和社会责任的男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伯金对人类社会的恐惧和逃避反映了他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空间的极端珍视。“他是多么惧怕别人、惧怕人类啊!这惧怕几乎变成了一种恐怖,一种噩梦——他怕别人看到自己。如果像亚历山大·塞尔科克·一样独自一人在孤岛上与动物和树林为伴,他就会既自由又快活,绝不会有这种沉重与担心。”[4]这种对个人空间的珍视和对社会评价的恐惧,显著背离了男性中心主义中男性应有的自信和权威形象,也揭示了他对人类社会的深刻不满和对自然世界的向往。伯金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期望,为理解男性角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伯金理想亲密关系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
(一)新型两性关系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
德里达指出:“人们总希望保持一个中心,因为它可以使人的存在呈现出来,或保证人作为一种存在的地位。”[7]男性中心主义将女性排挤到他者的边缘地位上,而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与厄秀拉之间的亲密关系深刻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展现了一种基于平等、互相尊重和自我独立的新型恋爱关系。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婚姻往往被视为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关系,其中男性拥有支配地位。“你可以在婚姻中找到永久的平衡,同时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两者不会混淆。”[4]伯金坚持在婚姻中保持个人独立性,这不仅适用于女性,也适用于男性,显示了一种性别平等的理念。如果简单地“颠倒”等级秩序的两方,则不能脱离二元对立的“否定”逻辑。德里达认为重复二元对立的做法并不可取。[1]伯金对于婚姻的观点突破了男性中心主义下婚姻中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架构。他提倡的是一种双方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仍能维持平衡和和谐的关系。这种观点挑战了传统男性中心主义下的性别动力,强调了男女关系中的相互尊重和个体独立。
在伯金眼中,厄秀拉是无比高尚美丽的存在,是高于男性的生灵。他崇拜她,就像老人崇拜青年,他为她感到自豪,是因为他深信他同她一样年轻,他配得上她。与她的结合意味着他的复活和生命。[4]甚至认为要成为其附庸才能获得自身的完整。男人得先成为女人的附属才能获得真正的地位,获得自己的完整。[4]这一观点更是直接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权力结构。在男性中心主义中,男性通常是家庭和社会的中心和支配者。然而,伯金却认为男性的完整性实际上依赖于与女性的平等关系,而不是支配或控制女性。解构主义揭示了所有意识形态的象征性质,因此能够揭露性别等范畴中固有的人为构造。[8]因此借由解构主义,劳伦斯通过塑造伯金和厄秀拉的恋爱关系解构了以往传统婚姻中的二元性别对立。
德里达针对的结构是逻各斯中心的结构、压迫性的结构。解构的对象是这种结构,尤其是这种结构的逻各斯的逻辑。[1]而伯金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性别角色和社会构造的关系正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在这种理想的关系中,男性和女性作为两个独立且平等的存在,相互给予自由,形成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关系模式下的双方相互尊重、享受自由和保有个体完整性,而不是同以往男性中心主义主导下男性统治女性的僵化局面。“我知道我需要与你结成完美、完善的关系。我们几乎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确建立了这样的关系。”[4]可以说,伯金与厄秀拉的关系是对其理想亲密关系的切实实践,伯金在与厄秀拉的恋爱过程中获得了自身的完满。
(二)理想的亲密关系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
伯金提出的理想亲密关系构想不仅涵盖了男女间的情感联系,还包括了与男性的深厚友谊,即所谓的“血谊兄弟”。这一构想深刻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框架下的亲密关系模式,提出了一种超越性别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全新亲密关系模式。伯金想与杰拉德结为血谊兄弟,宣誓站在同一立场上,相互忠诚——彻底地、完全地相互奉献,永不再索回。“这是超越人性的联合,可以让人获得自由”[4]。在男性中心主义中,男性间的关系往往被看作是基于竞争、力量和支配的。《恋爱中的女人》是劳伦斯的同性恋看法和观点由激烈反对到宣扬的过渡阶段的作品,伯金和杰拉德的关系是界于兄弟情谊和同性爱之间的同性吸引和同性依恋。[9]伯金提出的这种基于深厚情感、相互支持和忠诚的男性友谊,展现了男性关系的另一面,即情感丰富、亲密和非竞争性的一面。
解构引起的不稳定的力量其实是引发变化的活力:它揭示逻各斯的自相矛盾,由此在体系内展开能指的自由游戏,创造开放的话语。[1]而伯金所描述的理想关系并非二人之间的封闭关系,而是包含了第三人或者更多人的多元开放结构,这其中的三人关系并非传统婚姻关系中的复制叠加,而是一种全新的关系结构。“去获得自由!在一个自由的地方,和少数几个人在一起,获得自由!这是一种你、我及他人之间完美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起自由。”[4]这突破了传统关系中的性别界限。这种关系模式不仅包含了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了男性间的深厚友谊,强调了人际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我的确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一种永恒的联盟。可一对男女之间永恒的关系并不是终极,当然不是的。我相信男人与男人间完美的关系可以成为婚姻的补充。”[4]伯金的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上把异性恋关系视为唯一合法和“正常”的关系模式。德里达在继承和发展海德格尔“拆解”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构”,既“破”又“立”,既“拆”又“建”。[10]伯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虽然重要,但不应被视为唯一或至高无上的关系形式。他提出,男性间的友谊也可以成为婚姻的补充,这一观点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关于性别和关系的界限,并重新构建了理想亲密关系的架构。解构者是写作的读者,阅读的作者,也是观察者和批判者。[1]劳伦斯通过伯金将男性中心主义解构,将男女两性置于平等地位,破除以往两性各处一极的解构,加入第三人“血谊兄弟”,是其对传统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的深刻批判。
四、总结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通过伯金这一角色深刻解构并重构了男性中心主义,展现性别角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伯金背离了传统男性典范,其身体的柔弱、情感的敏感、行为的反理性质疑了固有的性别设定。劳伦斯在伯金与厄秀拉的关系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平等和独立的新型亲密关系模式,挑战了男性中心主义下的性别动力结构。这不仅解构了传统男性形象,而且推动了对亲密关系理念的重构,强调男女关系的互相尊重和个体独立性,提倡将男性间的友谊视为婚姻的有益补充,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和关系界限,而且重新定义了亲密关系的理念。
参考文献:
[1]童明.西方文论关键词解构[J].外国文学,2012,(05):105.
[2]杜洪晴.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重读《紫色》 [J].文教资料,2008,(03):56.
[3]杜钦.从解构主义角度分析罗伯特·库弗的短篇小说[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4]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M].黑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5]Blanchard L.Love and Power:A Reconsideration of Sexual Politics in DH Lawrence[J].Modern Fiction Studies,1975,21(3):432.
[6]Stelzig E.Romantic Reinventions in DH Lawrence's“Women in Love” [J].The Wordsworth Circle,2013,44(2-3):93.
[7]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12.
[8]Poovey M.Feminism and deconstruction[J].Feminist studies,1988,14(1):58.
[9]吴群涛,罗婷.《恋爱中的女人》:劳伦斯笔下的“血谊兄弟”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1):134.
[10]彭梦岩.解构主义视角下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 [J].牡丹,2023,(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