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互联网视域下中国青年电影的诗性回溯与未来指涉
2024-08-19李艳丹裴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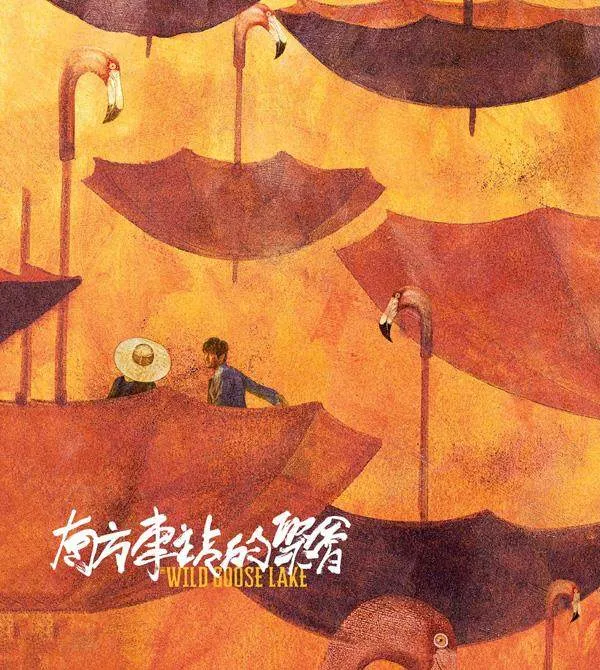

【摘 要】 后互联网存在时空断裂、语境断裂等问题,这让电影诗意塑造显得更为困难。然而,中国青年电影在面对后互联网时却表现出从容的姿态。他们凭借吸纳类型片架构、易变类型片内容的方式,实现电影诗性的延续和拓展。一方面,青年导演致力发掘类型片的拓展空间,依据本土电影理论,塑造出诗意影像的东方性格;另一方面,后互联网本身催生出的“梦核”“池核”“怪核”等实验影像也揭露诗性指涉未来的可能,给青年电影做出提示。现实发展似乎正如德国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所预言,当代银幕的诗性逻辑已经悄然改变。未来诗性必须借助更复杂的情动机制、更异化的劣质影像才得以实现。对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来说,后互联网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在后互联网的骇浪中,导演们既感到走向未来的阻力,又朦胧看到迎面的曙光。
【关键词】 后互联网; 中国青年电影; 诗性回溯; 未来指涉
后互联网视域下,人类的时空观受到冲击。一个典型的移变是:时空既呈现漂浮的碎片样态,又沦为供以消遣的压缩制品。“碎片化的特征使每个人都是不同个体,每个个体的时间都是不同的”[1],由此,无数个体的经验被切分,个体的消遣对象也不再具有一致性。某种意义而言,这意味着大众对媒介产品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电影作为后互联网时代媒介产品的重要一环,为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相应调整生产机制。在电影场域,纯粹的商业类型片已难再满足长尾市场。中国导演,尤其是青年导演纷纷构筑回溯式的电影诗学,以期开拓新的疆域。这里需要指出,学界对于青年电影的界定尚未明确,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青年导演创作的电影”[2]。青年导演的电影诗学既来自经典的诗意影像实践,也源于青年导演充分反思历史定位后所做的创新尝试。《白日焰火》(刁亦男,2014)、《路边野餐》(毕赣,2015)、《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2018)、《南方车站的聚会》(刁亦男,2019)等这些接踵而至的优秀作品是新一代导演创作野心的鸣唳。青年导演在“诗性回溯”的旅程中,充分表达了对诗意传统的敬重和赓续,与此同时,他们也依托后互联网亚文化,延拓出怀旧范式中的未来指涉。很显然,诗性回溯与未来指涉正是研究当代青年电影不可或缺的两个面向。从两个面向折射的绘景中,可以看到青年电影蓬勃生长的光明前程。
一、后互联网视域下的中国青年电影
时代影像的最精彩瞬间,通常由青年导演们构建。青年导演的审美趣味、个人经历以及文化感受,通过具象的手段,转换为精神的光影投射,呈现出同时代青年人对于世界的理解。由于中国青年导演的成长轨迹与互联网发展轨迹高度重合,其观念或多或少受到互联网形态的影响。现如今,随着英国学者哈维(David Harvey)预言的“时空压缩型”社会逐步来临,后互联网场域不断展开,资本与技术无限膨胀,异化为凶猛野兽,将人的精神世界挪为沙漠。时空压缩意味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3]。于是,在哈维的脉络下,后互联网向青年导演揭示了社会演进的两种面貌:其一,人的生存处境约略等同于互联网的发展处境,内卷化的生活对应互联网机制的效率目标。后互联网的大众基本具备数字劳工身份,他们在互联网的虚拟景观里游览、消遣与劳作,精神世界和他者相互隔离[4];其二,鉴于后互联网仍不断压缩时空,诗意的产生相对困难。缓慢是诗意萌生的土壤,如若弃用慢时空,诗意将在后互联网的无尽链接和闪切场景中逃逸。不妨说,后互联网在为青年导演们提供创作便捷性的同时,也留下棘手的“烂摊子”。中国青年导演既然存有回应时代的决心,就必须处理后互联网视域下技术与艺术相互影响的时代语境。
经过多年艰难探索,诗性回溯是青年导演们给出的共同答案。他们面对后互联网留下的精神沙漠,毅然决定以诗性对抗技术时代的种种异化。纵观青年导演所组构的星丛,可以发现,他们大多都背负精神原乡,昂首阔步迎接挑战。生于贵州凯里的导演毕赣在故土开掘失落的“南方”,在《路边野餐》(2015)、《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中探索文化地缘和主体情感的复杂关系。他的诗意源于中学时代阅读的佩索阿及痖弦;同样专注地缘描写,青年导演刁亦男视野则不在于自己的故土,而在于一种故土的意象。他对异陌领域充满“恋地情结”,在被遗忘的边陲小城,刁亦男借由《南方车站的聚会》(2019,以下简称《南方》)铺展对诗意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南方》中的“野鹅塘”,分别由武汉、孝昌、咸宁等地景观拼凑而成,在野鹅塘无序的情感地理空间的统驭下,诗意既充满美好,也弥漫阵痛。[5]无论毕赣、刁亦男,抑或其他青年导演,其诗性影像都携带厚重的超文本性。这种源于后互联网的经验给青年导演作品留下暗红的烙印,其探索不仅背负精神原乡,而且还指向互联网形式的深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外,一些青年影像实践也不容忽略。爬梳未命名的亚文化,可以看到,梦核、怪核、池核、后室等互联网景观逐步进入实验电影,亦裹挟诗性而来。青年导演的思考、反抗和迷茫在作品里一一浮现。这些青年导演摒弃通常意义上“更好走”的纯粹类型片道路,而向着诗意进发,个中缘由须要溯源至后互联网所孕育的特殊的危机意识。
二、诗性回溯:对诗意传统的敬重和赓续
对诗意传统的敬重和赓续,展现了青年导演修习技艺的谦逊的一面。这些青年导演“成长于差异性的影像经验中,喂养与浸泡他们的文化机制、媒介形态与他们后来面对的制片体制、市场样态同样都携带着历史自身的断裂与延绵”[6]。由于经验差异的不断扩大,新一代青年导演往往具有更加鲜明的危机意识。他们更愿意打开视野,向前辈导演学习,并从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
(一)青年导演的危机意识
中国电影历史进程的自陈,使青年导演对危机充满警惕。在青年导演们看来,危机无处不在。首先,一个显在的危机源于当代类型片本身的陈旧形式。这些广泛汲取异他性文化资源的青年导演通过敏锐洞察,发现纯类型片的颓势。现如今,类型电影已经走到转型的关键节点,亟须在其他要素的刺激下重现新生。尽管网生代群体对《九层妖塔》(陆川,2015)、《上海堡垒》(滕华涛,2019)的视觉奇观仍旧迷恋,但显然,这种迷恋不会一直持续。基于视觉奇观的迷恋,并非“迷影”(Cinephilia),而是对视觉中心主义、逻各斯主义的崇拜。一旦奇观电影中的异陌手段构成不断压榨内时间体验的机械,人们就会重忆电影“灵韵”(Aura),放弃奇观,而走向平常的审美。德国学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以“惊颤”(Chockwirkung)一词表达电影视觉奇观的冲击,“‘惊颤’正是电影等机械复制艺术诞生后与之相适应的感知方式,大众喜爱这种时时作用于感官的惊险刺激,喜欢群体共时性的接受方式”[7],然而,本雅明没有提到的是,惊颤体验无法始终奏效。尤其当后互联网场域惊颤过载时,大众对类型片的好感便会有所下降。
其次,危机还源于以往诗性经验与当下语境的脱节。以青年导演的视角看,影坛能够直接使用的诗性经验近乎无。一是第二代导演费穆、孙瑜的诗性影像因时代过于久远而难以模仿,只能从中习得表现技巧。第二代导演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电影诗意和当时文坛创作潮流相呼应,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二是第四代吴贻弓等人的作品虽然兼具个人经验和诗性描写,却没有涵括市场化的转型进程,缺乏对大众媒介的理解。《城南旧事》(吴贻弓,1983)、《百鸟朝凤》(吴天明,2013)多有民风、民俗记录,其诗意主要在于对真情的讴歌,而不在于对后现代性的诗意发掘;此外,第六代导演对西方经验的化用是较为成功的,然而,他们却在市场转型时期陷入相对尴尬的境地。举例来说,作品从《站台》(贾樟柯,2000)、《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2001)的抒写诗意的蓬勃决心,到《江湖儿女》(贾樟柯,2008)、《沃土》(王小帅,2024)却归于沉寂。第六代始终徘徊于文艺片、类型片两极,难以平衡二者关系,也鲜少留下诗性电影转型成功的范例。前辈导演诗性实践的不可复制性,引发青年导演的创作焦虑,促使其走上独立的发展路径。
(二)类型电影的诗意改造
为应对危机,青年导演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实践角度看,对类型电影进行诗意改造,即是青年导演自觉化解危机的办法之一。不同于以往的导演代际,新锐青年导演从小生长在大众传媒的熏陶下,对大众传媒的制式和话语都较为熟悉。他们未曾经历往代导演“拧巴”的转型,自然也就相对顺利地进入后互联网语境。某种程度而言,这些导演本能地了解当下受众的偏好,同时,还能在保持本土文化和诗性语言的基础上,对纯类型电影进行改造,使之兼具诗意特征和类型片特征。学者石敦敏曾准确指出青年导演在改造类型电影时的贡献。她认为,青年导演的诗意改造,既拓展了叙事文本的表意能力,又使“情绪叙事”成为本土类型片叙事的新路径。“中国的诗性修辞强调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即情感的外化和情绪的意象表达。因此,中国诗性电影的叙事往往是以‘情绪’而非单纯的‘情节’来结构影片。”[8]
在刁亦男的犯罪类型片《白日焰火》中,情绪正是剧情主要的推动来源。为了更好地制造悬疑效果,导演特地将叙事结构设置得较为复杂。此处如若影片没有情绪推动,观看体验将大幅下降。不妨说,《白日焰火》有了情绪,才得以形成复调的协奏。在电影一开始,死者出现,警察张自力和妻子离婚,张自力第一次见吴志贞,情绪低沉而压抑;尔后,张自力进行案件调查,发现吴志贞与多个死者的关联,情绪稍有回升;紧接着,张自力察觉自己已经爱上调查对象,他不可遏制地主动接近这个危险女人,情绪到达顶点;影片最后,女人在白日焰火的照映下,被抓捕。沉云和惨雾又将电影重新按回压抑的气氛。可以说,刁亦男对犯罪类型片的改造较为成功。他不仅在影片中拉扯出诗性的张力,更在情绪的波动过程里,完成悬疑叙事的动力构建。于此而言,其实人们也不难从导演董越、曾国祥的诗意影像中找到类似的机制。青年新锐导演在类型片改造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诗性经验,形成了不同于前辈导演的创作心得。
(三)诗意影像的东方性格
当然,仅通过上述办法化解危机是不够的。中国青年导演应广泛吸取前辈经验,走向东方文化,确立诗意影像的东方性格,才能具备应对危机、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近年来,以毕赣为代表的青年导演有意在电影中体现东方文化的异质特征。他们摒除好莱坞视角,“无论是视听表达还是时空观念,抑或是影片意蕴,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传统民族美学观念的影响和渗透来”[9]。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对自然山水、民俗的关注,对后现代情感的发掘,超越了对故事机制本身的执念。相比于前代导演,青年导演已经不再单纯希望只“讲好故事”,而是希望从故事中透露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他们着眼于乡村、边陲小城、废弃工厂等这些资本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界,试图通过长镜头等,完成对地缘空间的诗性刻画。除此之外,一些来自西方的巴洛克式的创作技法也被他们尽数吸收,化作游刃有余的本土表征。在青年导演看来,西方的创作技法、电影理论可用来开拓艺术视野和学习先锋探索的经验,“诗”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源头。新锐青年导演所热衷的山峦、迷雾、孤松、积雪,正是呈现东方美学意境的特殊词汇。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描摹意境并非青年导演的最终目的。他们对自然山水、民风民俗的关注,对后现代情感的发掘,实则归于超然的文化心态。源自《老子》《庄子》《诗经》《楚辞》的诗化句法,与源自孙瑜、吴贻弓、吴天明、贾樟柯的电影话语,汇聚到青年导演这里,变为凝视具体生活的“诗性眼睛”。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将这种诗性眼睛概括为一种“远式美学”:“以‘远’为方法,是中国电影艺术的美学思维与意境形塑的方式:它一方面源于我们感知世界的体验,且深受传统哲学,尤其是道禅观念的影响,源远流长;另一方面,从‘远’出发,是建构中国式电影理论的一条路径——它是中国电影美学兴味的关键所在,也是远式电影创作的理论补偿。”[10]进一步说,在以“远”为方法的加持下,经由“诗性眼睛”的遴选,封闭的生命经验就此拂去灰尘,散发光芒。青年导演借助秉持东方性格的诗性影像将人们的精神孤岛连成一片,同时,他们也巧妙利用细腻笔触发现当代生活中传统文化心态的积淀。
三、未来指涉:由怀旧范式所引发的创新
通过诗意怀旧范式进行指涉未来的艺术创新,展现了青年导演突破传统的一面。由于深受后互联网影响,青年导演对复杂诗性叙事、后现代电影理论的情动机制以及亚文化中的劣质影像偏爱有加。正因为此,他们的电影实践中,往往带有这三个创新的要素。
(一)复杂的诗性叙事
后互联网向青年导演展现出的超文本性,被青年导演挪用到作品的诗性叙事当中。以往代际的导演并不追求的复杂诗性,青年导演将其奉为圭臬。也就是说,青年导演在互联网语境中学习到的复杂性观念,在他们的电影中得到进一步表现。青年导演既不像前辈那样那种温暾的诗意抒情,一种歌颂生活的姿态,又摒弃了同时代类型片导演简化电影的做法。青年导演希望创造复杂性和诗性共存的影像,由此一来,可以尽力探索电影结构的极限,发掘后现代社会幽微的情感和文化。毫无疑问,这些导演理想中的叙事是指涉未来的,他们用文化地理和悬念创造出复杂的叙事结构,让观众一面陷入影像的迷宫,一面进行深刻的意义追问。就文化地理层面,青年导演有意让电影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三者相互融合,将叙事和文化地理的延展匹配起来。《刺杀小说家》(路阳,2021)中,导演路阳选择重庆山城作为故事开展的舞台,营造出扑朔迷离的电影质感。电影中的小说家空文生活在重庆,操着重庆方言,也有重庆人的犀利性格。导演常用镜头跟随空文的脚步,让镜头在重庆迷乱的石阶上游行。电影不时会描绘沿街老旧的居民楼,为画面镀上一层饱满的诗性油彩。《刺杀小说家》这部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电影,采用元叙述的手法,使得整个故事陷入眩惑的复杂的境地。[11]观众一开始不仅为电影的剧情迷惑,更为电影人物命运的走向而揪心。就悬念引信设计的角度而言,路阳在《刺杀小说家》中的伏笔可谓精彩。在超文本性的叙事结构的裂变中,电影划分为世界和小说世界。剧情推进过程中,两个不同的世界既相互影响,又有各自独立的发展。观众被悬念一直吸引到电影最后,当所有人物回到现实世界,电影才终于在诗意的唏嘘中走向结束。从上述例子可见,青年导演想要营造复杂的诗意,其中有探索叙事结构的决心,也有把控诗性流动的信心。他们在电影中雕刻出一个个诗意的微小景观,并用悬念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二)重设的情动机制
“情感的生成/流变,并非一种空洞的生成。它们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强度。”[12]学者汪民安在论述德勒兹的情动理论时,曾对情感生成机制做出如此判断。的确,如汪民安所言,情感的生成和流变是复杂的,情感既不会无缘无故来,也不会凭空过渡到另一端。生活中的情感必须沿着一定线索才能完成构建,电影中的情感何尝不是这样。在电影中,如若要表达诗意情感的流动,首先就要了解情感流动的机制。从以往的诗意影像实践中,可以看到,导演对情动的理解一直受到诗性形式的牵涉。例如《城南旧事》里英子对骆驼咀嚼草料的细节投向凝视,这一凝视的缓慢推动形成镜头的诗意迁移。然而,导演在电影中着重突显的诗意来源并不是电影剧情,而是电影的镜头语法。由于导演使用了含情脉脉的镜头来跟进拍摄对象,所以拍摄对象也都晕染了诗性的灵韵。相比之下,新生代的青年导演对情动机制产生了全然不同的理解。他们并不驻留于形式上的情动,而较为关注情动与电影剧情的相互配合。青年导演明白,在后互联网视域下,生活中的诗性近乎消磨殆尽。他们只有在电影画幅的狭窄空间内活动,才有可能将诗性重新注入影像。以李睿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为例,导演既以西北大漠的浩瀚和荒凉引发观众的情绪反应,又通过兄弟俩返乡游历的故事追溯中国北方的诗意。导演深知观众对慢节奏的难以适应,所以特地选择故事和描景的结合,用层层递进的手法将一种历史的记忆传递给观众。电影中干涸的井水和无人的村落,处处暗示历史在此已经是过去时态。诗性躲藏在每一次游历的步伐里,对黑暗中观影的人发起冲击。
由此可见,新锐青年导演实际已经掌握另一套情动机制,通过重设机制,他们平衡了观众对慢节奏的怨气,将观众重新带回诗的现场。事实上,从另一位青年导演徐磊的影片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动机制重设。他的代表作《平原上的夏洛克》(2019),以侦探故事的特殊情调,将电影拉回乡土,使乡土无缝地融合进先锋侦探叙事。影片中,超英和占义只要出发去探案,就会驾驶一辆落伍的农用三轮。尽管这样的场景与观众熟知的后互联网环境格格不入,还是创造出巨大的电影诗性空间,使观众短暂忘却外部世界,跟着电影剧情一同情动。观众内在情动的绵延,佐证了青年导演新的情动机制的显著效果。显然,青年导演在电影中放置的情动机制是面向未来的,无论人们生活怎样变化,都依旧受到此类机制的影响。
(三)刻意的劣质影像
在后互联网亚文化中,人们常可以看到“电子包浆”的数码梗图,即那些在互联网中被反复压缩、传播而形成的劣质影像。这些劣质影像表面是数码图像的降格,实际却融入当代艺术,成为青年人阐发情感的工具。“怪核”、“梦核”、“池核”,此类异陌的元素借助人们对早期电子数码产品的体认,在劣质影像中制造光怪陆离的精神迷梦。举例来说,怪核影像引用早期互联网技术的视觉界面,通过其中空旷无人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引发观者的怀旧和不安。劣质影像起到的作用是引起观者记忆,同时又拒绝观者欲望回到记忆当中。可见,劣质影像并不是单纯的Lo-Fi低质量摄影,其内里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意涵。学者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将“劣质影像”界定为“当代屏幕世界里的畸零儿,视听产品里的残渣,被冲上数字经济海岸的垃圾”[13]。她指出,劣质影像是影像中的无产者。在史德耶尔的论述中,劣质影像艺术具备两个鲜明特征:其一,平民性。现如今的后互联网场域,几乎人人都可以参与,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偏好,制作和传播劣质影像;其二,边缘性。劣质影像绑定一种“被边缘化”的情感。使用劣质影像作为艺术的青年人意识到自身被主流话语排斥的境遇,进而无奈地在这种境遇中追求个性释放。平民性和边缘性是劣质影像渲染诗意情绪的关键。不少青年导演都曾刻意援引劣质影像来抵达指涉未来的诗性。譬如,《宇宙探索编辑部》里唐志军接受采访的一段画面,孔大山以劣质影像和春晚背景乐的组合,突出电影的诗性和黑色幽默。劣质影像里漂浮、抖动的唐志军,一方面因向往外星文明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也因“被边缘化”的感受而陷入一种落寞的诗意气氛。此处劣质影像与其说是还原时代感的道具,不如说是绘制人物心绪的诗性笔法。它用平等的视角抹除了艺术世界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以一种温柔的诗意关照一些弱势群体的处境,发掘他们的闪现的温情。当然,除了院线上映的电影之外,后互联网场域也有许多未名的怪核、梦核短片,通过2000年左右对早期互联网的记忆印象,将剧烈情绪隐藏在颇为吊诡的氛围当中。经过长期的发展,怪核类艺术也具备了本土特征。一种名为“中式旧核”的影像艺术借助对中国新世纪初家具、交通工具、建筑等静物的描绘,为观者制造了如真似幻的原乡,给予观者不同于纯怪核艺术的精神抚慰。这些后互联网流传的劣质影像的艺术光谱,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青年电影的实践,为未来青年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先行的实验材料。
结语
通过爬梳后互联网视域下青年电影的发展,可以看到“诗性回溯”和“未来指涉”是青年导演诗性创作的一体两面。在诗性回溯中,青年导演不仅虚心模仿前辈纯熟的诗性创作技法,而且也学会如何化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他们对地缘空间、地缘情感的关注,展现了作品的人文关怀,让世界看到中国青年导演创造的全新气象;在未来指涉中,青年导演不断从后互联网场域话语中汲取营养,将后互联网的一些形式引入电影,开创出具有千禧年风格的诗性电影之路。后互联网所赋予青年导演的除了使命,还有方法论启迪。这些青年导演一方面受到后互联网环境的辖制,无法回到诗意电影的本真状态;另一方面却又在后互联网土壤中奇艳地绽放。
现如今,中国青年电影乘风破浪,在前行中成绩和隐忧同在。必须指出,中国青年电影发展趋势虽然日趋明朗,但仍然不可忽略未来可能出现的两大障碍。第一大障碍是主流体系对青年导演的收编改造。随着青年导演逐渐登台亮相,主流体系对他们的收编和改造已经在所难免。如何在主流体系中始终保持突破自我的决心,恐怕将成为青年导演下一个阶段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第二大障碍是后互联网场域的冗杂话语对青年导演创作的干涉。后互联网的形态在未来总是会发生一定改变。青年导演要么服膺于后互联网话语的影响,要么与后互联网话语保持距离,以意大利美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当代人视角感受“时代脊骨的断裂”[14]。很显然,第二种道路前途开阔,但路途艰难。青年导演须要保持对身边一切要素和话语的警惕,从荆棘中穿越,抵达最终目的地。无论如何,中国青年电影发展到现在,依旧只是打上一个逗号。接下来青年电影怎样书写,要靠整个中国电影体系的扶持,也要靠青年导演不断开拓视野,真正营造方法论独立的电影创作风气。
参考文献:
[1]蒋晓丽,赵唯阳.后互联网时代传媒时空观的嬗变与融合[ J ].社会科学战线,2016(11):154-160.
[2]黄阿美.青年电影——难以界定的电影类型[ J ].文教资料,2014(30):188-190.
[3]冯建辉.“时空压缩”语境下的后现代批判——对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的文本解读[ J ].理论与现代化,2010(05):12-17.
[4]朱健刚.内卷化、时空压缩、无组织化新技术时代青年工作意义贫困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J ].人民论坛,2021(25):32-35.
[5]杜梁.刁亦男电影中的“情感地理”图绘[ J ].当代电影,2020(09):47-52.
[6]王昕.用艺术抵达现实:当下青年导演的电影观[ J ].电影艺术,2017(01):35-40.
[7]邹赞,张艳.光与影的救赎——瓦尔特·本雅明论电影[ J ].文艺评论,2023(01):113-120.
[8]石敦敏.艺术·商业·主流:青年导演影像的诗意复归[ J ].当代电影,2022(02):136-138.
[9]王名成.从自然山水到精神原乡:青年导演的东方视角和时空观念[ J ].当代电影,2022(02):128-130.
[10]王海洲,丁明.以“远”为方法:中国电影的美学思维与意境形塑[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06):23-31.
[11]路阳,陈旭光,刘婉瑶.现实情怀、想象世界与工业美学——《刺杀小说家》导演路阳访谈[ J ].当代电影,2021(03):61-72.
[12]汪民安.何谓“情动”?[ J ].外国文学,2017(02):113-121.
[13][德]黑特·史德耶尔,滕腾,孙红云.论弱影像[ J ].世界电影,2018(06):111-117.
[14]汪民安.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06):10-17.
【作者简介】 李艳丹,女,河南南阳人,南阳理工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影视文学研究;裴蕾,女,江西新余人,广州体育学院体育传媒学院助教,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媒介文化、健康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电影语言的民族化路径研究”(编号:21YJA76004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