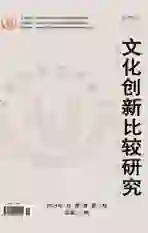哀伤之下的温暖底色
2024-08-06王晓婷

摘要:抒情诗《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1921)是叶赛宁精神危机初期的代表作,该文拟从音韵色彩、布局谋篇、抒情言志、文本间联系四个角度来分析诗歌的艺术特色,结合诗歌的创作背景及诗人的创作理念,发掘诗歌的艺术内涵。诗歌以抒情之“我”为话语主体,立足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维度,诠释了春天与秋天、青春与苍老(心灵苍老)、生与死的对立主题。全诗音韵和谐优美,主题鲜明突出,抒情之“我”经历了自我安慰、不满现状、追忆青春、妥协祝愿的心绪转变,在哀伤的基调下铺陈了温暖的底色,以真挚的情感引发读者共鸣。诗人的创作灵感源于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1842),所成之诗又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生活的故事》(1945—1963)、路遥《平凡的世界》(1986)中留有印记,足见诗歌隽永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叶赛宁;《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20世纪俄罗斯诗歌;诗歌艺术特色;叶赛宁精神危机;文本间联系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5(c)-0005-07
The Warmth Beneath the Sorrow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ergei Yesenin's Poem I don't pity, don't call, don't cry ...
WANG Xiaoting
(School of Russi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lyrical poem I don't pity, don't call, don't cry... (1921) is a masterpiece written by Sergei Yesenin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spiritual crisis.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m from following perspectives: rhyme, color, layout, emotions, thoughts and intertextual connections, and to explore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po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et's creative concept. Based o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poem takes lyrical "I" as the main subject of discourse to interpret the antagonistic themes of spring and autumn, youth and old, life and death. It is harmonious in sound and rhyme, clear and prominent in theme. The lyrical "I" undergoes a mood shift of self-comfort,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miniscence of youth, compromise and wish, which creates warmth beneath the sorrowful tone and resonates with a lot of readers by sincere emotion. This poem was inspired by Gogol's Dead Souls (1842), and later was quoted in Paustovsky's The Story of a Life (1945-1963) and Lu Yao's Ordinary World (1986), which is enough to prove the poem's wide artistic appeal.
Key words: Sergei Yesenin; I don't pity, don't call, don't cry ...; 20th century Russian poetry;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em; Yesenin's spiritual crises; Intertextual connection
叶赛宁(С.А. Есенин,1895—1925)出生于俄罗斯梁赞省的一个农民家庭,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抒情诗人,新农民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歌感情真挚,自然流畅,浓郁的抒情气息中弥漫着淡淡的忧愁,营造出无穷的意蕴。早期的叶赛宁诗风清丽明媚,将纯真的童趣与乡村田园风光融为一体,色调明朗温暖。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诗人一改以往诗风,以澎湃的热情欢迎革命的到来,诗作气势宏大、立意新奇。但不久后,由于战乱使乡村受到重创,革命后的现实世界与诗人理想中“庄稼汉的天堂”不符,诗人理想破灭,陷入精神危机,苦闷的情绪、暗淡的色调笼罩着这一时期的诗作。虽然自旅居美国、重返故国后,叶赛宁的观念有所转变,开始接受现代文明的到来,作品中再度出现瑰丽的亮色,但新旧思想的冲突依旧令他忧心思虑,精神危机依旧存在。最终,诗人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俄罗斯诗坛巨星陨落。
抒情诗《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Не жалею, не зову, не плачу...》)作于1921年,是叶赛宁精神危机初期的代表作品,原诗与译诗如下:
Не жалею, не зову, не плачу...
Не жалею, не зову, не плачу,
Все пройдёт, как с белых яблонь дым.
Увяданья золотом охваченный,
Я не буду больше молодым.
Ты теперь не так уж будешь биться,
Сердце, тронутое холодком,
И страна берёзового ситца
Не заманит шляться босиком.
Дух бродяжий! ты все реже, реже
Расшевеливаешь пламень уст.
О моя утраченная свежесть,
Буйство глаз и половодье чувств.
Я теперь скупее стал в желаньях,
Жизнь моя!иль ты приснилась мне?
Словно я весенней гулкой ранью
Проскакал на розовом коне.
Все мы, все мы в этом мире тленны,
Тихо льётся с клёнов листьев медь...
Будь же ты вовек благословенно,
Что пришло процвесть и умереть.
( С.А. Есенин )
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
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
如同苹果树花开花落,一切都会消逝,
我不会再有青春年华,
整个身心都充满金色的倦意。
心已被侵袭,经受过寒冷,
此时你已不再那么激越怦然,
印有白桦图案似的国家,
也不再吸引我赤脚游手好闲。
流浪汉神气!你越来越少地
煽动我倾吐炽烈激情,
啊,我那失却的青春朝气,
愤慨的眼神,情感潮涌!
就欲望来说,如今我很少希冀什么,
生活啊,莫非你真是我梦中的情景?
仿佛在那欣欣向荣的初春
我骑在红鬃烈马的背上驰骋。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家都会消失,
如枫树上悄然飘落叶片铜币……
但愿你永远幸福如意,
即使是风华正茂,抑或面临死期。
(叶赛宁作;顾蕴璞译)
全诗以哀伤为主基调,反映出诗人面对青春流逝、理想幻灭时的苦闷心境,诗中的大自然风光充满了凋零与逝去之感,就如同青春年华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色,不可逆转地奔向生命的尽头。但与此同时,哀伤的基调之中又显露出温暖的底色,最终化作叶赛宁给予世人的美好祝愿,祝愿每一个生命都能于向死而生的征程中幸福如意。在音韵色泽的变换、时光季节的流转、情态心绪的起伏中,青春与年老、生与死等对立主题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本文拟从音韵色彩、布局谋篇、抒情言志、文本间联系四个角度来分析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揭示其深邃的艺术内涵,发掘其丰厚的艺术魅力。
1 音韵色彩
叶赛宁的抒情诗音韵和谐,旋律优美,就连初至莫斯科、不懂俄语的美国舞蹈家邓肯,也能透过朗诵感受到叶赛宁诗歌乃至俄语的魅力。正是因为叶赛宁的诗歌富有音乐性,他的许多作品受到作曲家的青睐,比如,苏联作曲家波诺马连科(Г.Ф. Пономаренко)就将《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改编为歌曲,使之成为深受听众喜爱的浪漫曲,广为传唱。
全诗由5个诗节组成,每个诗节包括4个诗行,是一首五音步扬抑格诗。扬抑格(хорей)多用于民间文学创作,较抑扬格(ямб)相比情感更充沛,速度更快,侧重于抒情而非言志。由5个音步(стопа)构成的诗行较长,“节奏缓慢,适合表达诗人对往事的回忆与沉思”[1]。读者在朗读的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陷入一种忧郁哀伤的氛围,感受诗人复杂矛盾的心绪及对于已逝青春的追忆与思索。第一诗节第三诗行、第三诗节第一诗行各多出一个音步,超出读者预期,变缓的节奏既与第一诗节第三行中увяданье(枯萎;衰老)的状态形成呼应,也符合第三诗节第一诗行强化的语气(реже重复出现两次)。诗行中不规律地出现重音音节缺失的情况,以及诗节中偶然出现的打破交叉韵(перекрёстная рифмовка)的情况,使得诗歌的旋律节奏更加丰富多样,从而折射出抒情主人公起伏不定的心绪。
叶赛宁不仅注重诗歌的音韵,对于色彩的选择也十分考究。“文学作品中的色彩世界是由作家创造的”[2],其不单是为了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及自然界中的色彩,往往还凝结着作家的审美志趣与心绪情感。叶赛宁“非常善于运用颜色,这一点不仅在俄罗斯诗歌中罕见,甚至在世界诗歌中也极为突出”[3],《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就彰显了叶赛宁的这一才能。本着哀伤的总体基调,诗歌中的色彩世界通常是黯淡的、清冷的,但叶赛宁却选用了表示亮色的形容词及具有亮色指向性的隐喻词汇。
第一诗节第二诗行中率先出现了中性色白色,为全诗的色彩世界铺陈下纯净的底色。诗人以белый(白色的)来修饰яблоня(苹果树),可是在自然界中,真正为白色的不是苹果树,而是苹果树于春天绽放的花朵。原诗中虽未直接提到花朵、花瓣,但随之出现的дым(烟)无疑是对飘落花瓣的隐喻,这不仅与第三诗行中的увяданье(枯萎)相互呼应,更透露出隐约之美、朦胧之美。
Увяданье(枯萎)所修饰的中心词золото(金子)是落叶的隐喻,因为两者在颜色上具有共通之处,均为金色。在俄罗斯文化中,金色是鲜艳璀璨、高贵神圣的颜色,象征着神、太阳、富裕与荣耀;在俄语中,金色也大多用来形容美好的事物,如золотая осень(金秋)、золотые руки(巧手)等。可是在本诗中,明艳的金色与凋零的落叶、逝去的青春关联起来,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在情感上形成反差。金色属于黄色调的颜色,在叶赛宁的诗歌中,纯黄色鲜少出现,诗人通常借助隐喻来表现黄色系颜色之间的细微差别,如金色、金黄色、黄铜色等,因深浅度不同,这些颜色的伴随意义也有所区别。在本诗最后一节的第二诗行中就出现了медь(铜)一词,该词虽然同为落叶的隐喻,但其指向的黄铜色与金色相比明显黯淡了几分,可见抒情之“我”在经历了一番情绪波动后并未完全释然;相反,“我”的愁绪变得更加深沉凝重,只不过“我”选择将其藏于心底,以云淡风轻示人。
除了金色以外,第四诗节第四诗行中的розовый(玫瑰色的,绯红色的)也是鲜亮的暖色,并且比金色更加明艳热烈。诗人之所以使用该词,是因为此处描写的是欣欣向荣的初春自然美景,是朝气犹在的梦中生活情境,抒情之“我”骑着玫瑰色的烈马驰骋在原野之上,那份快意与畅然唯春天可以带来,唯青春可以拥有。玫瑰色既是烈马之色,也是青春之色,更是“我”炽热内心的颜色。只可惜青春已逝,炽热不再,万事万物终将化作尘埃。当幻梦中的热烈与激情褪去,“我”不得不接受现实、面对现实,心中的感伤愈发深重。
2 布局谋篇
诗歌一开篇,抒情之“我”就直抒胸臆,Не жалею, не зову, не плачу(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虽为全诗的第一诗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于已逝青春一直秉持这样的态度,这只是“我”的自我安慰。诗人在展示“我”的情绪波动前,率先亮明了“我”希望自己达到的情绪状态,与后文形成反差,为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我”以自然界中的落花来类比世间万物,表示没有什么可以永驻于世,一切都终将逝去,这一观点看似是助“我”平复心绪的关键,但其实忧思并未真正离“我”而去,而是在“我”的心底暗自翻涌,第一诗节剩余两行诗表现出来的衰颓之意就是有力的证明。
第二诗节中,诗人从内在、外在两个方面来展示抒情之“我”当下的状态。从内在来看,“我”的内心已不再如从前那般激越怦然,而是被寒冷侵蚀,逐渐失去对于周围事物的好奇及对于生活的希冀,“我”以第二人称“你”来指代自己的内心,从而营造出一种对话感;从外在来看,即便是“我”曾经热爱的自然风光、乡村美景,也无法吸引“我”像从前那样赤脚游逛。由此可见,内心的寒冷与漠然已蔓延至全身,外化为“我”的行为举止。
第三诗节中,“我”仍在同自己的心灵对话,只不过诗人在此处运用了换说(перифраза)的修辞手法,以дух бродяжий(流浪汉的魂魄)来代替上一诗节中的сердце(心),进一步增强了“我”的情绪感染力。虽然流浪汉的魂魄(即“我”的魂魄)尚在,可是它已被寒冷侵蚀,这份寒冷不仅辐射至“我”的行为,也投射在“我”的言语中,“我”越来越少像从前那样倾吐火热的言语,“我”的一言一行均因内心的寒冷而黯淡下来。可是“我”难以接受现在的自己,也不知为何会丢失过去的自己,因此主动发起对话,想要谴责一番这“流浪汉的魂魄”。但这“魂魄”本就与“我”一体,“我”谴责无果,只好发出一声长叹:“啊,我那失却的青春朝气,愤慨的眼神,情感潮涌!”
继第三诗节的长叹以后,“我”的情绪短暂回落,感慨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对生活充满希冀,但紧随其后的是新一波高潮。“我”不再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而是将矛头对准生活,向生活发起反问:“生活啊!莫非你真是我梦中的情景?”此处的生活从现在切换为过去的时间维度,在那里,有欣欣向荣的初春,有鲜衣怒马的快意少年,“我”自由自在地驰骋在乡间……这是“我”曾经的生活,真真切切,可如今却已成为回忆,如梦境一般朦胧模糊,如春天一般转瞬即逝。如此说来,весенняя гулкая рань(喧响的初春)是对молодость(青春)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四诗节中,诗人两次运用感叹号,一次运用问号,可见“我”的情绪在这两个诗节中抵达了高峰。
最后一节中,抒情之“我”又一次发出自我安慰,将此前外溢的情绪敛入心底,并试图开导与自己有着相似情绪的人们,世间万物都会消逝,自然界如此,人亦是如此。此刻,自然线索与人的线索合为一体,“我”不再局限于关注自身或者外部的自然风景,而是将世间万物囊括其中,视野更加开阔。最终,“我”以第二人称“你”来指称世界上的所有生命,祝愿其无论正值青春还是老之将至都能够幸福如意。可见,个人的忧伤在结尾处转变为对于世间万物的大爱。
全诗融合了人与自然两条线索,以抒情之“我”为话语主体,于过去、现在两个时间维度的交叠中抒发感情,呈现出春天与秋天、青春与苍老(心灵苍老)的对立主题。其中,第一个对立主题针对的是大自然,第二个则指向人类,二者紧密交织。如果将青春与苍老推向生命的两级,便得到了生与死的对立主题,这一主题既适用于大自然,也适用于人类,可将世间万物囊括其中(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现在维度的篇幅远远大于过去维度的篇幅,仅第四诗节第三、四诗行展示了过去的维度,其余内容均立足于现在维度。由此可见,美好的青春转瞬即逝,往昔的回忆只有在梦中才能短暂复现,抒情主人公多数时间里都沉浸在现实中,被愁苦、忧伤的心绪笼罩,这与诗歌的总体基调完全吻合。
3 抒情言志
在本诗中,抒情之“我”的苦闷一方面源自逝去的青春年华,另一方面源自理想志向的破灭。第二诗节第三诗行中的страна берёзового ситца(印有白桦图案似的国家)除了指代集所有美好于一身的乡村童年乐土,似乎还寄寓着诗人“农民天国”“木屋天堂”的理想。他将社会主义的前景与“木”这一元素紧紧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愿景中,“那里,耕田而没有赋税;那里,‘木屋是崭新的,是用柏木板盖的顶’”[4]。叶赛宁之所以如此看重“木”的元素,一方面,因为木可以用来搭建房屋,为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场所;另一方面因为木即树木,象征着自然与生命。先祖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用树叶擦拭身体,在树木的庇护下生活,希望能够像古树一样永葆生机,以德行润泽子孙后代。农民们会在床单、枕套、手巾上缝绣树木和花卉的图案,因为这是“对农民的生活意义的神圣化的礼赞”,以装饰图案祈愿生命之流生生不息。本诗中出现的缝绣图案为白桦,白桦既是俄罗斯的诗化象征,也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象征,可见,诗人理想中的农民天国应如白桦一般纯洁美丽、坚韧不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亲眼看见了残酷斗争及乡村的凋敝景象后,叶赛宁的理想彻底幻灭,这也是诗人于1920年春写下《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的原因。而在《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中,诗人将理想幻灭的苦闷匿于青春逝去的哀愁之后,以“印有白桦图案似的国家/也不再吸引我赤脚游逛”来实现一语双关的效果。
第三诗节第一诗行出现的дух бродяжий(流浪汉的魂魄)同样值得关注,抒情之“我”以“流浪汉”自称,而这个忧愁思虑、柔肠寸断的“流浪汉”形象“毋庸讳言,正是诗人心态的自画像”[5]。在叶赛宁的抒情世界中,“流浪”主题与“流浪汉”形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在诗人的早期诗作中,“流浪”主题多表现为在乡野间的漫游,抒情主人公也并非真正的流浪汉,只是具有流浪汉的心魄,沉浸在青春年华与大自然的美好中,感受精神与心灵上的无边“流浪”。然而,当诗人陷入精神危机后,他失去了自己理想中的“木屋天堂”,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过起了真正的流浪生活。这一点在诗人1922年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我要抛弃一切,蓄着须/做个流浪汉,把罗斯漫游”(《请不要谩骂。有什么奇怪……》),“我不过是个街头浪子,/对迎面的路人嘻笑盈盈。/我是莫斯科的流浪汉,/走遍整个特维尔市区,/街头巷尾的每一条狗/熟悉我的轻捷的步履”(《我不打算欺骗自己……》)等。此外,这个“流浪汉”整日混迹于莫斯科酒馆,狂饮闹事,放荡不羁,比如“我自己也是耷拉着脑袋,/用酒灌得两眼迷茫”(《这里又酗酒、殴打和哭泣……》),“人生是床单一条、床一张。/人生是接吻并跳入漩涡”(《唱吧,唱吧。伴着该死的吉他……》)。不过,这个“流浪汉”很快就从醉生梦死的荒唐生活中醒悟过来,是爱助他走出自暴自弃的困境:“我第一次歌唱爱情,/第一次远离打架斗殴的地方。/过去的我,全然如一座荒芜的花园,/痴迷女人,恋色而又贪杯,/如今我不喜欢暴饮和街舞,/不愿把自己的生命一味地浪费”(《无赖汉之恋》)[6]。这一时期的“流浪汉”形象虽有不少乖张胡闹之举,但并未全然丧失人性及对爱的渴望,他只是因为失去理想的庄稼汉天堂一时迷失了方向。《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作于叶赛宁精神危机初期,诗人虽已察觉自己的“流浪汉”心魄正在慢慢冷却,但尚未开启真正的“流浪汉”生活,处于人生际遇转折点的他,回望曾经那个朝气蓬勃的自己,回首那段热烈欢畅的青春年华,何其感伤,可是他最终选择收敛自己的痛苦,将祝福回馈给世间的每个生命,此为大爱的表现。也许理想的幻灭会使精神麻痹、心灵偏航,但本性中那份对万物生灵的爱不会消失。
1925 年叶赛宁自杀离世后,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批判叶赛宁习气(есенинщина)的运动,卢那察尔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作了一场名为《青年中的颓废情绪(叶赛宁习气)》的报告,布哈林也在真理报上撰文抨击叶赛宁习气的不良影响。“叶赛宁习气”指的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在部分青年中产生的不健康的颓废情绪,他们把这种情绪用叶赛宁的名字命名,就是认为叶赛宁及其诗歌是这种情绪的罪魁祸首”[7]。对于叶赛宁及其作品的这种评价有失偏颇。卢那察尔斯基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应将叶赛宁本人及其作品同“叶赛宁习气”分开,甚至公然表明,“叶赛宁本人就是叶赛宁习气最大的反对者之一”[8]。在《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中,抒情之“我”经历了自我安慰、不满现状、追忆青春、妥协祝愿的心绪转变,虽然字里行间散发着忧伤,甚至是有些颓废的气息,但是诗歌开篇的“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诗歌结尾对于世间万物的美好祝愿都是对于忧伤颓废情绪的反拨。即便青春逝去的苦涩没有完全脱离“我”,甚至可能深深地潜入“我”的心底,但“我”没有放弃与之抗争,自我掩饰也好,自我安慰也罢,表面释然也好,真诚祝愿也罢,“我”终归想要通过种种努力化解颓废的情绪,至于结果如何,这并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内。虽然抒情之“我”并非诗人本人,但“忧郁和真诚是叶赛宁最突出的个性特征”[9],“我”的每一次心绪起伏、每一次情思开合均映射出诗人的主观内心态度,诗人本人一直在同自己的负面情绪作斗争。
4 文本间联系
在《俄语修辞学》(《Русск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2006)中,俄苏语言学家、修辞学家戈尔什科夫(А.И. Горшков)提出了文本间联系(межтекстовые связи)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包含在某个具体文本中的、借助特定言语手段表现出来的对另一个(或另一些)具体文本的参阅”[10]。此外,他总结出引文(цитата)、卷首题词(эпиграф)、引用典故与引发联想(аллюзия и реминисценция)等文本间联系的表现方法,以及集锦诗(центон)、文本间动力(межтек-стовый импульс)、续篇(продолжение)等文本间联系的类型。诗歌《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就与其他作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本间联系。据叶赛宁的第三任妻子索尼娅·托尔斯塔娅回忆,这首诗“是在《死魂灵》中一段抒情插话的影响下写成的……有时,叶赛宁会笑称:‘人们夸我这首诗,殊不知夸的不应是我,而是果戈理。’” [11]。在《死魂灵》第六章的开头部分,果戈理没有直接推进对于乞乞科夫拜访普留什金的叙述,而是以抒情插话的形式呈现出乞乞科夫路遇陌生村庄时的所思所想:
现在,我是无动于衷地驶近任何一座不熟识的村子,无动于衷地望着它的平庸俗气的外貌;我的冷了下去的眼光觉得腻烦,我不再感到欢乐有趣,在以往的年代里会在我的脸上即刻激起反应、引起我欢笑和难以穷竭的言语的那些东西,现在都不留痕迹地闪滑过去,冷淡的沉默封锁住我一动也不动的嘴唇。哦,我的青春!哦,我的蓬勃的朝气![12]
通过比较发现,果戈理笔下的这段文字与本文研究的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果戈理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通过描写不同时期乞乞科夫路过陌生村庄时的不同反应,凸显了青春朝气的可贵,表达了对于逝去青春的留恋与惋惜。尽管这段感怀青春的文字只是《死魂灵》中的一段抒情插笔,与整部作品的主线情节、主旨思想并无紧密关系,可正是在这段文字的触动下,身处相似境遇的叶赛宁有感而发,写下了《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因此,这首诗与小说《死魂灵》之间构成的文本间联系类型为文本间动力,即其中一部作品为另一部作品提供创作动力,但二者在情节、主题等方面几乎没有联系。
美好的青春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苦涩心绪可能出自对于青春年华的怀念,也可能出自对于生活现状的不适,还有可能出自对于未卜前程的忧虑。这种心绪为人之常情,通过写作来抒发这种复杂心绪的作者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叶赛宁因受果戈理的启发写成了《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随后,这首诗又在后世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迹,构成了文本间联系。
比如:俄苏著名浪漫主义抒情大师帕乌斯托夫斯基(К.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生活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жизни》),就引用了这首诗中的个别诗句作为小说第一卷的卷首语。帕乌斯托夫斯基一生历尽风浪,人到中年,方才有底气执笔书写自己的故事。小说第一卷回溯遥远的年代,追忆童年遇见的人、事、景、情,孩童新奇的视角与中年成熟的视角相互交织,抒发了中年之“我”对于童年之“我”的珍视与怀念。将叶赛宁开启青春回忆的诗句“生活啊,莫非你真是我梦中的情景”用作卷首语,可谓恰如其分。
中国当代作家路遥在小说《平凡的世界》尾声部分同样引用了这首诗,当时的孙少平只有27岁,却因煤矿事故毁容入院,一时间心灰意冷,是金秀的鼓励与陪伴唤起了少平的生活的信念。在他决定重新走向生活、热爱生活之际,“猛然间想起了叶赛宁的几句诗: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13],虽然青春已经逝去,但未来还有很多日子值得期待、值得珍惜,应当以饱满的状态投入生活,活得不负自己,不负众爱。小说中这种积极向上的基调虽与原诗有所出入,但两个作品之间的文本间联系显而易见、毋庸置疑。
5 结束语
抒情诗《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是叶赛宁精神危机初期的代表作,音韵和谐,布局考究,虽然有着哀伤的总体基调,但却镶嵌了明亮的色彩。全诗以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维度为基础,诠释了春天与秋天、青春与苍老(心灵苍老)、生与死的对立主题,结合人与自然两条线索,将世间万物纳入关注视野。抒情之“我”经历了自我安慰、不满现状、追忆青春、妥协祝愿的心绪转变,虽然无法全然消解对于逝去青春的惋惜以及理想幻灭的苦闷,但仍旧选择及时收敛情绪,祝愿世间万物生生不息,不忘大爱本色。全诗不仅内涵丰富,与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同样丰富,诗人的灵感源于前人的作品,所成之作又在后人的作品中留有印记,如此多样的文本间联系更彰显出诗歌隽永的艺术特色。
青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它如春天一般瑰丽温暖、生机勃勃,却也好似流星,转瞬即逝。当青春逝去,世人大多伤怀叹惋,更何况是心思敏感的诗人?但叶赛宁传递给读者的并不全是哀伤,那声“我不叹惋,不呼唤,不哭泣”,那句真诚的祝愿,终究还是为读者带来了直面岁月的勇气,这也许就是诗歌蕴含的无穷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徐稚芳.俄罗斯诗歌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84.
[2] 刘恒.文艺创造心理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304.
[3] 龙飞,孔延庚. 叶赛宁传[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153.
[4] 叶赛宁.玛丽亚的钥匙[M].吴泽霖,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22.
[5] 张建华, 宗琥,吴泽霖.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理论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0-170.
[6] 叶赛宁.叶赛宁诗选[M].顾蕴璞,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101.
[7] 许贤绪. 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29.
[8]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татьи 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M].М.:Учпедгиз,1958:438.
[9] 朱凌.试论叶赛宁诗歌创作过程的个性特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116-118.
[10]ГОРШКОВ А И. Русск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M]. М.:АСТ:Аст-рель,2006:72.
[11]БЕЛОУСОВ В Г. Сергей Есени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хроника[M]. М.:Сов. Россия,1969-1970: 89.
[12]果戈理. 死魂灵[M]. 满涛,许庆道,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39.
[13]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