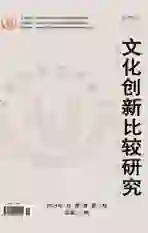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爱弥拉姑娘的爱情》
2024-08-06王敏
摘要: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由西方国家逐渐蔓延至全球。它倡导的是一种更加整体和相互关联的世界观,强调人类、自然及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王蒙的新疆题材小说既有着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汉文化思想的辐射,同时又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达成了某种默契。他的作品既关注女性的命运,同时又表现生命与自然的互动。该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爱弥拉姑娘的故事进行剖析,试图探讨王蒙在创作中流露出的平等和谐的生态女性主义观,以及生态环境、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和行为。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王蒙;《爱弥拉姑娘的爱情》;女性;自然;性别角色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5(c)-0001-05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Love of Lady Ai Mila
WANG Min1,2
(1.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gdong, 266100, China; 2.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2, China)
Abstract: Ecofeminism, born during the third wave of feminism, has gradually spread from Western countries to the global stage. It advocates for a more holistic and interconnected worldview, emphasizing the interplay and balance between humans, nature, and societal structures. Wang Meng's Xinjiang novels, rooted in the influence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radiating Han cultural thoughts, simultaneously resonate with Western ecofeminism. His works not only focus on women's fates but also portra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fe and nature. This paper, through the lens of ecofeminism, analyses the story of Ai Mila in The Love of Lady Ai Mila, seeking to explore the harmony and equality in ecofeminism as depicted by Wang Meng. It also examines how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ender ro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fluence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behavior.
Key words: Ecofeminism; Wang Meng; The Love of Lady Ai Mila; Women; Nature; Gender roles
生态女性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毁灭》中最先提出,90 年代以后逐渐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其目的是通过文学研究对文学创作,进而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改变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唤醒人们的生态整体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包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存在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1]。
“国内生态女性主义一方面与西方批评理论积极对接与融合,另一方面逐渐强化基于中国经验的自主反思与本土批判意识。”[2]王蒙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但他的小说中少见剧烈的性别冲突,也不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相反,他的作品超越了女性主义的界限,转而将关注点放在了广阔的自然世界上,将生命的关怀融入角色。这正是他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异曲同工之处,王蒙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和自然浑然一体的形象,通过对她们命运及其发展过程的考察和对她们生存境遇的观照,表现出了他对女性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重新审视。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是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中的一篇。主人公爱弥拉生活在一个传统的维吾尔族家庭中,她试图摆脱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寻找自己的身份和自由。在爱弥拉的成长过程中,她的原生家庭和社会环境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既是她的庇护所也是她遭受心灵伤害的源头:养母图尔拉罕的过度保护和对传统的坚持,以及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限制,都成为阻碍她自由的障碍。面对家庭和传统的压力,爱弥拉在情感和身份认同上经历了深刻的冲突和挣扎,她的故事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本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了爱弥拉在传统和家庭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同时通过对比爱弥拉与其他女性角色的不同反应和选择,探讨生态环境、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和行为。
1 纯粹本真的自然之子
在新疆生活过 16 年的王蒙怀着对自然美的由衷挚爱描摹了一帧帧绚丽而多情的自然世界:挺拔的白杨、清清的渠水、盛极而衰的紫丁香……,这些自然景物构成了小说的诗性意象。它们赋予作品独特的精神层面和艺术境界。“苹果树开花如雪,小鸟在枝头和茶棚上跳跃,牛、羊、驴、马、狗、猫、鸡都起劲地拉长了声音鸣叫,在春天,它们叫得比任何别的季节都更多情。”[3]这些诗意文字的背后蕴含着王蒙“博大的生态情怀”[4]。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被视为孕育万物的母亲,女性在社会中通常扮演着母亲和家庭的守护者角色。这种角色与自然的孕育特性存在着深刻的相通性。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性天生不是驾驭自然的存在,而是具备保护环境的潜质。爱弥拉姑娘,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展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听她说话的时候,你很可能想到山野里的一只羚羊,或者一只小鹿,或者山谷里的忽而跳跃、忽而分散的溪流。”她像大自然一样,既纯粹又美好,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在故事中,她在面对社会动荡时,展现了女性的坚韧和勇敢。尽管她的心理和外貌因为压力而发生了变化,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爱情选择,勇敢地追求个人幸福,这就像自然界中的生物在逆境中仍旧顽强生存一样。王蒙作品中自然美与女性美相互依存,女性不仅在性格上与自然的赋性相似,而且在外貌与气质上也具有天然美。
爱弥拉姑娘的生活深深植根于她所属的农村公社,这个公社与自然紧密相连,其生活方式、文化习俗都展现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点。爱弥拉和养母打造了一个朴素而精致的花园,其中包括不作为食物而仅作为观赏植物的黄花菜、温柔的马兰小紫花,这种关怀和培育是女性对自然和生命的深刻感悟。“金针是那样高傲而热情”“玫瑰花在窗前探头”,爱弥拉的成长、情感经历,以及她对未来的渴望,都在自然的怀抱中得到映射和反思。就像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自然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还承载着文化、情感和精神价值。在爱弥拉的生命历程中,自然充当了多重角色。它是她心灵的慰藉,是她美好生活憧憬的源泉,同时也是她面临的社会约束和文化传统的象征。自然在这里既是一个供她逃避现实束缚的避难所,也是一个不断提醒她家庭和社会期望的存在。通过这种复杂的互动,爱弥拉的故事反映了女性如何在自然环境中寻找自我认同,同时也展现了她们如何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寻求自我解放。
沃伦曾指出:“女性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可以为女性和自然治愈由父权社会带来的伤害提供一个场所。”[5]爱弥拉姑娘通过与自然的亲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力量。她的选择最终获得了家庭的理解和支持,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成长,也是社会对女性自主选择的渐进性接纳。在爱弥拉姑娘出嫁后,她的养母图尔拉罕和“我”的房东大娘阿依穆罕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她们不再咒骂或埋怨爱弥拉,而是接受了这一事实,并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体现出对家庭和生活的热爱,如一起品茶、制作食物等。这都描绘了自然与女性的密切联系,而且展示了自然和女性相互治愈、相互依赖,实现双向互动的过程。在王蒙的作品中,自然被描绘为能够抚慰女性情绪的力量,而女性则能够跨越文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鸿沟,找到心灵的归宿和安宁。
2 被禁锢的女性与自然
波伏娃在其女性主义代表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女人同所有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母系制度的特征在于,女人的确被大地所同化”[6] 。而这种同化在爱弥拉姑娘的生活中得到了体现,她的经历揭示了女性在传统父权社会中如何被视为与自然同等的被动和受制于人的对象。在当时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成长和发展的路径已经确定。爱弥拉姑娘的角色塑造不仅反映和拓展了她的自然本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的强制性影响。爱弥拉姑娘所在的毛拉圩孜公社深受传统观念的制约,家里女人负责“举案齐眉”端盘子,男人才有资格给客人递茶碗;女孩子要早早嫁出去,父母让嫁谁就嫁谁,万不能白白给人家,“做丈夫的吃饭时总是摆出一副等待伺候的老爷架子,而且当着外人的面,更是连正眼看都不看妻子一眼,说话也都是粗声粗气的”。可以看出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受到严格限制,社会伦理和父权制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建构十分明显。爱弥拉的养母图尔拉罕和其他亲戚已经为她物色了一位合适的人选——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一位大队干部。此外,社会和文化环境也对爱弥拉构成压力。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结婚,否则会引发问题。爱弥拉的家人亲戚都不支持她的恋情,甚至公社领导也介入,警告说如果她嫁到天山公社,将不得不退职成为农民。她非常痛苦,经常哭泣而不发一言。地狱般的煎熬让她“失去了往日的姣好的容颜和青春的光彩,失去了往日的令一切人满心喜悦的魅力,她变得憔悴、神经质、魂不守舍”。人们对女性的期望是服从和顺应,女性被期望扮演传统的角色,如照顾家庭、生育后代。无论是她的养母图尔拉罕的过度保护,还是众人反对她的恋爱选择,都反映了一种深植于文化中的女性角色观念。这种观念不仅限制了女性的个人选择和自由,也体现了一种对女性自然属性的固有理解,即女性像大地一样,是需要被保护和掌控的对象。这种观念中的“保护”实则是一种控制和压制,剥夺了女性的自主权和发展潜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即便是女性,也往往被这种强大而无处不在的男权意识内化[7]。女性常常被迫接受并传递父权文化的价值观,这不仅表现在母亲和女儿之间,也体现在女性之间的互动中。例如,养母图尔拉罕对爱弥拉的期望和行为受限于她自己对女性角色的理解和接受,这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弥拉的限制和控制。
公社其他人对爱弥拉的看法和评价也是基于传统性别角色的期望,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在无形中维护了父权制文化的规范,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父权专制的文化氛围。女性被期望遵守特定的行为规范,任何偏离这些规范的行为都会受到周遭的批评和排斥。爱弥拉的情感经历和她对未来的梦想,与人们对女性角色的严格界定相冲突,从而加深了她的困境和挣扎。此外,这种父权专制的文化氛围不仅影响了女性,也体现在对自然的态度上,自然被视为资源和工具[8],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小说中多处描述室内的布局和装饰,如雕花木窗扇、印花羊毛毡、库车地毯和丝织壁挂。这些元素一方面展示了人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和美化其居住空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或支配,这种对自然的利用与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是相互关联的,都源于一种不平等和支配的思想。小说表达了对深受父权制文化迫害的女性与自然群体的同情与关注,呼吁平等和谐的生态关系与两性关系,与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
3 和解与自由的实现
“当伊犁河谷落下第一次雪,当株株挺拔的杨树在一夜之间尽情地落光了自己的叶子,当远山戴上银冠,当农家幢幢土屋的烟囱冒出了无形无色却又折光折影的烟的时候”,爱弥拉最终还是决定追随自己的心意,嫁给了那位男教员,她那无法抑制的情感,就像大自然的蓬勃生命力一样。她抛下了母亲、亲人和方便的生活环境,以及每月四十多块钱的体面工作。她与坚守着当时传统观念的女性不同,内心深处不知在何时早已种下蔑视迂腐传统观念的种子。她对浪漫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有自己的定义,允许自己爱上一个需要自己放弃一切而远嫁他乡的男人,她不愿意再考虑这个世界,她要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不会为了迎合任何人而改变自己。当然爱弥拉姑娘的选择意味着与家庭的冲突和分离,给家庭带来了痛苦,但她的选择代表了一种从传统生态角色中解放出来的尝试,展现了个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发现和成长,反映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摆脱压迫和操纵的内在勇气和意志力。爱弥拉姑娘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与自然紧密相连的边疆农村。这种环境通常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如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的照顾者和维持者角色。爱弥拉姑娘的选择始于她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深刻认识。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梦想与她所在环境的期望不符。尽管她的养母图尔拉罕给予了她爱和关怀,但也限制了她的个人选择和自由。爱弥拉姑娘的觉醒是在遇到喀什河上游天山公社的男教员后加速的。她对这段感情的追求使她开始质疑和反思她的生活,她开始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由。面对家庭的反对和社会的压力,她选择遵循自己的心声。
爱弥拉的选择不仅是个人层面的偶然事件,而是在个人需求、社会文化变迁、女性地位提升及传统观念挑战背景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在传统和现代观念冲突的情况下,爱弥拉的选择也可以被视为对传统家庭和社会期望的必然反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觉醒,追求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需要女性持续审视自我,清晰地追索生命意义,找到激活主体意识的内在动机和人生目标。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女性增强主体意识,实现自我重塑的主要途径。”[9]“她最爱读各种书了,我们家里的灯油,都被她读书时用去了”,“我看的那些书多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 像《青春之歌》呀,《红岩》呀”“我的女儿最喜欢看电影了,小时候,她常常想当一个电影演员”。受教育的过程激发了她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向往,也影响了她对传统生活的看法,促使她寻求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而文中“花盆里的四棵石榴好像具有挑战意味,谁说生活不应该更加鲜明耀眼呢”,似乎也暗含对传统性别角色和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挑战。在传统文化中,女性通常与柔和、内敛的特质联系在一起,而石榴的鲜艳和生命力则挑战了这种刻板印象。石榴在这里代表了女性的力量和活力,暗示女性不只是被动的、温顺的,而是充满能量和生命力的。女性生态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特殊联系。在这句话中,石榴的生长和它们的鲜明耀眼象征着女性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以及女性在维护和关怀自然中的重要作用。
婚后,虽然她的家人最初反应激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平静下来,开始含笑地议论远嫁的爱弥拉姑娘,充满了惦念之情。婚前两腮凹陷的爱弥拉变得丰满了,她带着高大英俊的丈夫回娘家住了五天。“阿依穆罕大娘看到谢米什丁这样照顾和服侍妻子,她的惊奇大概与第一次看到半导体收音机所差无几”,“穆敏老爹含笑微微点着头”首肯了这门婚事,“图尔拉罕则是一种喜不自胜的样子”,可见,社会和文化是动态变化的,爱弥拉的婚姻获得家庭认可,正是文化和社会结构能够适应个体需求和现代价值观的表现。爱弥拉所实现的和解和自由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胜利,也是对传统社会期望和角色的一种挑战和重塑。爱弥拉姑娘的故事是一段关于个人觉醒、鼓起勇气和抗争的旅程。她通过对传统家庭和社会期望的反抗,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独立,最终实现了和解和自由,尽管这个过程伴随着痛苦和牺牲。她的这一决定体现了对自身幸福和自由的坚定追求,实际上更是对这种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在生态女性主义观念中,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争取,也是对生态和社会结构的挑战。
生命之网中的任何一条线受损都会损害自己。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的休戚相关、互蕴共荣的生态系统整体性意识[10]在王蒙的《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得到充分体现。王蒙的这部作品更加贴近自然,更加注重生命本真,更加追求人性之美,可以深切地展现他对于自然的敬重和热爱,都与生态女性主义达成了某种默契。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够体会到边疆少数民族乡镇真实的风土人情及老百姓淳朴坚韧的性格特征。同时,他在作品中将女性自然化,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独立人格和丰富个性的女性形象,使得女性和自然相互融合,彼此救赎,并通过书写女性对于传统观念的反抗建构了有情有义、万物生命同一的生态共同体。在这个生态共同体中,既有男性对女性的尊重,又有女性对男性的感念,呈现了一种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关系,以形象化的方式折射了王蒙尊重女性、尊重自然的精神 ,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相契合。他以一种不同于女性主义作家的温和姿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怀让人们看到了男女相互扶持、平等关爱的和谐性别生态;用自然的智慧缝合着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心灵伤口。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家园的构建使他的作品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自然维度和性别维度,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4 结束语
王蒙通过《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不仅创造了一部文学作品,更倡导了一种生活哲学和价值观。在他笔下,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共生不再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而是通过具体的故事和形象展现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性。这也无疑为我们当代社会提供了反思与启示,指引我们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环境共生。
参考文献
[1] 陈茂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述[J].齐鲁学刊,2006(4):108-111.
[2] 纪秀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回溯、中国经验和叙事启示[J].山东社会科学,2023(2):69-77.
[3] 王蒙.爱弥拉姑娘的爱情[M]//王蒙.你好,新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 张岚.论迟子建作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蕴[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34(5):56-62.
[5] TRISH G.Karen Warren's Eco-feminism[J].Ethics&the Environment,2002,7(2):12-26.
[6]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7]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D].成都:四川大学,2003.
[8] 张轶,孙晓安.《呼啸山庄》中艾米莉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宿州学院学报,2021,36(2):46-50.
[9] 陶琳.觉醒·超越·共生:电影《绿山墙的安妮》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美与时代(下),2023(2):147-149.
[10]戴桂玉.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2005(2):105-11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