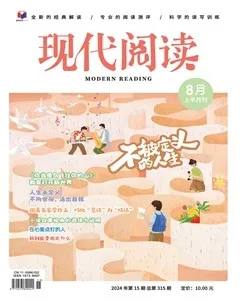山水能否 为精神解围
2024-08-02梁开喜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其散文形式多样,独树一帜,在传记、寓言、游记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永州八记》虽是短章一束,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其中的《小石潭记》更是如明珠般璀璨夺目。
《小石潭记》的无穷魅力到底表现在哪里?一般认为,它超出了一般山水游记的写景状物,将个人际遇安放于自然风景之中,是那样的气韵中贯,又是那样的不着痕迹,无不在写景,同时又无不在写心。
明代文学家茅坤曾评价道:“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所谓“善记”,自然包括以少胜多、意在言外的语言艺术。的确,除去末段对同行者的介绍,这篇游记只有不到170字,然而,在这有限的文字中,作者不仅将游历过程叙写得井然有序,而且将内心情绪表现得凝敛深婉。毫不夸张地说,《小石潭记》既是游记散文的典范,也是语言学习的绝佳样本。
美不胜收的景物描写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作者发现小石潭的经过,同时对小石潭的特点及其所处环境进行了富于情致和十分精妙的描写。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且是“如鸣珮环”的清心醒耳之声,让人想一探究竟。于是,“伐竹取道”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世间的美好往往如此,唯有探骊方能得珠。“水尤清冽”是作者对小石潭的第一印象,也是整体印象。“全石以为底”看似平淡,实则写出了潭的小和水的清:以整块石头为底,足见潭之小;整块石头竟然一目了然,足见水之清。接下来的“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则是大词小用,通过描绘山石的不同形态将小石潭表现得气象峥嵘。对“青树翠蔓”,作者用“蒙络摇缀,参差披拂”这八个字来形容,笔墨俭省却意蕴丰厚,没有写风,但总让人感觉有风掠过。此段在“心乐之”之后,由潭而水,由水而石,由石而树,视角的不断转换带来了景物的不断变化,使读者自然地产生了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感。
文章第二段是最令人津津乐道、赞赏不已的部分。其主要理由是,作者在鱼、水、光的自然互动中将虚实之妙和动静之趣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从而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浑然忘机的意境。“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看似写鱼,实则写水,或者说,在写鱼的同时写水,曲折而婉转地道出了潭水澄澈无比、一览无遗的情景。“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不说鱼而用“影”,可见日光的明亮无碍;而一个“布”字,则生动描绘出鱼长时间静止不动时的样子。“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特别容易唤起读者的生活经验,鱼的轻灵迅疾,似乎就在眼前。“似与游者相乐”,并不直接写人之乐,而是从鱼的角度写人,心随景动,曲尽其妙,从而达成了物我的高度契合。
点到即止的忧郁情感
如果说,文章前两段的情感基调是“乐”(柳宗元两次写到了“乐”),后两段的情感基调则是“清”(“清冷”与“凄清”)。“潭西南而望”是个转折点。作者先前的身体姿态是“游”或“行”,心是向外打开的,而此时停下来“望”,是省视内心。于是,好奇心和惊喜感悄然遁去,人境重新侵入物境,理性重新统领感性,“无我”重新被“有我”所替代、所左右。溪流的蜿蜒曲折(“斗折蛇行”)和时隐时现(“明灭可见”),以及岸势的犬牙交错和水源的不知其源,似乎象征着作者大起大落的经历和不可预知的前途,但可以肯定的是,静止的状态(“坐潭上”)让作者一度打开的心门重又关上,封闭(“四面竹树环合”)而荒僻(“寂寥无人”)的环境激发了作者的身世之慨和命运之忧,是完全符合人的心理演进逻辑的。当然,作者此时仍然写得非常克制,“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那种终究逃无可逃的抑郁与落寞点到为止,并没有酝酿成一泻而下、不可遏制的情感的洪涛。
若教学只是停留在分析“石之怪”和“水之清”,并在简单机械的知人论世后为这篇文章贴上惆怅、感伤、凄凉、悲怆等标签;而对于文字与心情是如何缠绕在一起的,文字本身隐藏着怎样的心理密码和情感脉络等分析,却总是浅尝辄止、语焉不详,将必然导致“言”“文”分离、“景”“情”分离,让言语和思想变成两条平行线。这一点,在对第四段的解读中尤为突出。
为此,我们不应该对作者的内心变化视而不见,但也不能对“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折射出的微妙心理作无限放大。
精神方面的“围城”
我们将作者被贬谪当成他无法走出精神“围城”的唯一理据时,对“寂寥”的探究势必成为重点和难点。于是,“永贞革新”的失败成为解读作者和作品的重要的知识背景,从这一事件对作者的深刻影响而言,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在柳宗元的性格特质中去寻找另外的解释呢?
与其散文成就相比,柳宗元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似乎要逊色一些。但他创作的五言绝句《江雪》却足以冠绝群伦,写出了孤独的绝高境界。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天地辽阔,万籁无声,“千”“万”之中,唯剩“孤”“独”,还有谁能把那种孤傲和清高写得如此不容侵犯而又令人神往,写得如此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呢?不得不说,相比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作为哲学家的柳宗元的孤独感和压抑感更为强烈,这种气质也自然而然投射到他的作品中。当竹树如聚,寒气来袭,或许对他人而言,这种寒气只是迎面扑来;而对柳宗元而言,这种寒气却是深入骨髓的。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同年进士,也是一世的挚友,但两人的性格却迥然不同。尤其是被贬之后,柳宗元的心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因“永贞革新”被贬的刘禹锡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柳宗元会说“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刘禹锡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柳宗元会说“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刘禹锡说“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柳宗元会说“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如果说勇猛精进始终是刘禹锡的生命底色,那么,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的沉郁压抑便成了柳宗元的情感标签,这对他们各自的创作态度与创作风格都有着决定性影响。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水对柳宗元的情感慰藉只是暂时的,心灵的孤寂与哀痛则是无法磨灭的。长期以来的郁郁寡欢被眼下的一方胜景暂时推开,然而,好风光终究冲淡不了旧忧伤,生机盎然的山水,也终究无法为柳宗元的精神解围。
(同步链接: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