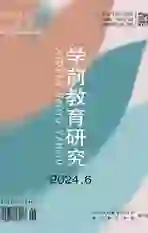“可爱”神话的读解与祛蔽
2024-07-31袭祥荣杜传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童年观念史”(项目编号:19BZW147)
**通信作者:袭祥荣,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博士
[摘 要] 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旨在利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探讨日常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从神话修辞术视角来看,“可爱”作为当代社会言说儿童的方式,含蓄意指儿童“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和孩子气”的特质,与现代儿童观的兴起不无关联。其具体成因包括:现代家庭对儿童局限的情感化接纳、大众传媒的娱乐化言说以及现代教育学的标准化定名。“可爱”神话存在压抑儿童发展能动性、成人童年价值理性和本土儿童教育理念的风险。通过践行参与式教育、规范隐性教育、发展本土教育,创设儿童自我建构的空间、管制童年资本化的生产理路、推动传统儿童教育理念与可爱文化优势互补是破解“可爱”神话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可爱;儿童;神话;现代儿童观
“可爱”在当代社会俨然有进化成赞誉儿童的万能标签之势,如在日常生活中,评价孩子最为常用且不会让家长们感到冒犯的词汇便是“可爱”。与之相对,“聪明”“漂亮”等词汇固然会让家长和孩子们感到高兴,但同时意味着对其他孩子的贬低:有聪明就有愚笨,有漂亮就有丑陋,而没有人喜欢愚笨、丑陋……可爱具有无气味的文化属性,[1]适用于所有儿童,能够为所有人接纳。日常生活中对儿童无差别的“可爱”称赞使其成为一个被滥用的空洞化词语。
凭借无气味的属性,可爱也悄然渗透至教育场域,对教育者行动产生影响。笔者在一项调查中发现,教师表达对儿童的积极情感时,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便是“可爱”,①一项国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相关研究显示,在家庭生活中,母亲对相貌“可爱”的子女会投入更多关注。[3]而在社会场域,外形和举止可爱的儿童更容易被陌生人施以援手。生物学将其原因解释为:“可爱”代表的“婴儿模式”能够激发成人的保护欲,提高个体的生存概率。[4]按照这一逻辑,“可爱”的儿童更有可能享受金色童年。但事实并非如此,“儿童网红”等童年资本化乱象的兴起、儿童伤害事件的屡禁不止提醒我们:可爱反而为儿童招致了更多生存风险。校园霸凌、熊孩子等问题也隐隐指向这一事实:可爱或许并非儿童真实且唯一的面目。四方田犬彦直接指出:“可爱”就是横亘在当今社会的巨大神话。[5]可爱神话隐藏的美丽风险引发我们思考:当我们在言说儿童“可爱”时,本质是在说什么?“可爱”缘何从儿童的护身符转变为达摩克利斯之剑?“可爱”神话引发了哪些后果?面对“可爱”神话,教育能够有何作为?
一、“可爱”神话的读解
(一)作为当代社会言说儿童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说儿童很“可爱”时,我们都能理解其意味,但进一步思量,又难以确定“可爱”何谓,罗兰·巴特甚至讽刺“可爱”是一个说不清的呆板词语。在罗兰·巴特看来,由于法律不禁止谈论任何事务,因此,世上万物无论是否合乎情理,均能从封闭缄默的存在转变为适合社会利用的自由状态,从而演变为神话。恰恰因为神话形成过程灵活随机,故而神话也具有历史性,某一事物在一定阶段可以被称为神话,而在其他阶段,不一定同等成立。
儿童之“可爱”亦不外如是。在我国,儿童与“可爱”的结盟较为晚近,虽然多数人面对儿童时会自然而然产生喜爱之情,但受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祖先崇拜、儒学思想等旧式家庭伦理的影响,“有用”才是衡量古代儿童价值的核心尺度——或凭借家务、耕种等体力劳动为家庭产生经济效益,或通过勤勉读书等脑力劳动振兴家族。故而,“俨若成人”的儿童形象备受推崇,幼童虽值得怜爱,但不被尊重。从南北朝至隋唐,“弱不好弄”的儿童形象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宋代延续古风,推崇聪颖、好学、稳重、至孝的模范儿童;[6]明清之际,在科考入仕价值观的驱动下,“生而凝重、少不嬉戏”的儿童形象更为成人称许,[7]虽诗文中散见关于“稚子”“童心”等偏重儿童之可爱的论述,但绝非言说儿童的主流方式。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将儿童当作成年预备期的童年观念被批驳,儿童之“可爱”才为成人发现。[8]新中国成立初期,儿童在社会结构中被定位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该认识使“可爱”再次进入休眠期。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教育理念唤醒了成人对儿童之可爱的关注:可爱虽无法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但具备情感慰藉价值。至此,“可爱”的缄默状态得以解除。由是观之,“可爱”仅是当代社会言说儿童的方式,既不永恒,也不权威。
(二)“可爱”神话的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
神话是由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共同建构的层级套叠的双重符号系统,直接意指表示符号在语言系统中直接明示的意义,含蓄意指表示符号在神话系统中隐匿的特殊意义。读解“可爱”神话的关键在于明确其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以“钻石代表爱情”为例,“钻石”直接意指碳元素构成的矿物质,而含蓄意指为“爱情”,是“钻石”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指称。当人们在提及“钻石”只能联想到“爱情”时,“钻石”的丰富意义便被掏空,成为一个“神话”。这一层层剥离的过程,便是神话的形成机制。
1. “可爱”神话的直接意指:可爱的多元内涵及相关行动。
“可爱”在语言学符号系统中直接意指其字面意思,即可爱的多元内涵及与可爱有关的行动。在日常用语中,可爱即“令人喜爱、值得爱”,意味着事物在被看的过程中能够凭借自身的某些物理特性引起观看者的喜爱之情。而成人之所以觉得儿童“可爱”,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儿童的某些表现给成人带来了审美愉悦感。从学理层面来说,可爱文化起源于日本,最早可追溯至《枕草子》中“可爱的事物,张开嘴准备吃甜瓜的孩子的脸”,是贵族阶级表示积极情感的词汇。在下层阶级的俗语中,“可爱”直接意指“凄惨、可怜”等消极意义,直至中世纪以后,其消极意义才被逐步削弱,并凝练为一门独特美学。扩展到世界各国文化,“可爱”的直接意指更为丰富,在汉语中,“可爱”最早见于《诗·大禹记》,有“令人敬爱”之意;在英语中,“可爱”有“机敏伶俐”之意;在意大利语中,“可爱”则意指“昂贵、高级”……“可爱”如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图腾一般,承载着丰富多彩的神话。
2. “可爱”神话的含蓄意指: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孩子气。
“可爱”神话在我国发轫于改革开放后海外文化的输入,其直接意指逐步为日本可爱文化取代。根据四方田犬彦的考察,“可爱”在当代社会意指“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孩子气”,[9]与我国当前文化语境中的“可爱”内涵如出一辙。具体来说,幼小是“可爱”的外形特征,指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不成熟,暗示儿童脆弱且需要受到保护。因此,他们无需特别行动,便能得到成人的怜爱。怀旧是“可爱”的情感基调。康德认为,怀旧源于个人内心的缺失感,是一种美化过去的热情。童年世界作为脱离现实的美好世界,其纯粹性和神圣感不因时间的流逝变质。[10]当成人疲于应对复杂现实生活时,儿童幼态化言语、纯真精神等可爱元素能够为成人提供情感慰藉,唤醒成人的怀旧情感。孩子气是“可爱”的行动特点,是儿童无意识表露出来的神态、动作、语言和行为,其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儿童对成人的某些秘密领域保持无知。儿童只有无知甚至偶尔犯错才会可爱,过于懂事的孩子则因循规蹈矩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童真感。“可爱”神话的含蓄意指建构了日常生活中人们评判儿童可爱与否的标准。
(三)现代儿童观:“可爱”神话的形成理据
罗兰·巴特认为,语言符号之所以成为神话,缘于人们在运用这一符号时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以致其含蓄意指挖空并遮蔽了直接意指,从而让受众顺从这种强加的意识形态。[11]对于“可爱”神话来说,虽然儿童是多元社会角色的集合体,但在现代儿童观的笼罩下,“可爱”对儿童的占有在当代社会达到最大值,以自身的永恒性和典型性取代了其他性情品质。
“可爱”神话代表的“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孩子气”等特质与现代儿童观内涵有所重叠。一方面,“可爱”神话蕴含的积极力量与现代儿童观的“生成”话语不谋而合。四方田犬彦指出,可爱文化推崇未成熟之美,因为未成熟意味着希望,正因未成熟,成人才会“怀着将来会开花的期待”。[12]现代儿童观也欣赏儿童的未成熟性,认为儿童的未成熟状态指向一种积极的势力或能力,在适宜条件支持下能够按照自身节奏实现自我创生。[13]另一方面,可爱神话对儿童的单一认识和不成熟性定义又在现代儿童观的本质论立场和二元论短板上有所投射。本质论立场认为儿童在本质上不存在差异,将特定文化视野中的童年样态,比如“可爱”,绝对化为永恒的、普遍的童年本质,而忽略了社会文化背景、家庭现实处境对儿童的多元形塑。二元论假设认为儿童和成人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儿童是未发育完善的成人。对于“可爱”神话来说,无论是幼小、引发怀旧情感还是孩子气,都是以成人为评判标准的,只有相对于成人才成立。现代儿童观对儿童形象的勾勒坐实了四方田犬彦归纳的“可爱”神话的含蓄意指,而其相应的丰富的直接意指被切除,丧失了历史真实。
二、“可爱”神话的成因
罗兰·巴特指出,通过让那些不言而喻的“现实”重新历史化可以洞悉意识形态之骗局,揭发神话背后的权力作用机制。[14]“可爱”神话滥觞于20世纪末期,以现代儿童观为理据,借由现代家庭的“种痘”、大众传媒的同语反复和现代教育学的事实确认等得以形成。
(一)“种痘”:现代家庭对儿童可爱局限的情感化接纳
“种痘”是神话修辞术之一,指通过“坦诚制度偶然之恶来更好地掩盖其根本之恶”,抵御自身被全面颠覆的风险,看似对事物进行了补偿,实质上消除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撤空了事物的真实。[15]现代家庭将儿童可爱的局限合理化为成人的情感寄托,便是典型的“种痘”手法。在“旧家庭”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日常生活不稳定,多数孩子早早便操作家事,少数世家孩童则自幼面对家族斗争和严苛规矩。[16]由于大龄儿童能够创造出更高价值,故而成人倾向于采取对他们更有利的生存策略,“可爱”象征的幼小、怀旧、孩子气等特质则因其经济上的无用性被排斥。进入“现代家庭”时代后,生产力发展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父母不仅无需子女参与经济劳动,还通过主动控制生育、降低儿童死亡率着力提高子女生存质量。[17]在经济收入提升和子女数量减少的双重加持下,成人意识到可爱代表的“经济无用”这一欠缺特质内隐的情感价值,对此如同“种痘”一样产生了集体免疫。
这与“可爱”神话在我国勃兴的关键节点相契合。20世纪末,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相继出台。一方面,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充盈了家庭收入,成人对儿童参与体力劳动的需求锐减,相应也不再以“有用”为标准衡量儿童价值高低,而是以浪漫的眼光将可爱的局限性合理化为充满积极力量、在某些方面超越成人的童年精神。“可爱”象征的幼稚变成了天真纯洁,非理性变成了浪漫随性,容易闯祸变成了充满勇气,能力欠缺变成了充满成长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儿童数量和质量的控制保证了成人的情感投入。实际上,童年的发现与儿童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成人情感投入密切相关。[18]如19世纪以前,西方儿童受疾病、经济条件、照护条件、杀婴传统等因素限制,死亡率居高不下。[19]儿童微弱的成活率意味着父母情感投入和金钱投入极易打水漂,故而成人吝于向子女倾注太多情感,甚至连教育家蒙田都直言:我已经失去了两三个尚处哺乳期的孩子,并非没有遗憾,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快。[20]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新生儿出生率的同时,儿童医疗的发展有效降低了儿童死亡率。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自1990年到2013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24.9‰降到7.7‰,继而呈持续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成人早期教育投入能稳定获得回报,成人可以放心向儿童投入更多情感。
(二)同语反复:大众传媒对儿童之可爱的娱乐化言说
文化传播需要借助助推力,这一助推力在现代社会便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兴起使其取代思想价值成为受众需要考虑的文化传播的首要因素。尼尔·波兹曼在电视时代便意识到影响人们对事物接受度的是图像。[21]罗兰·巴特进一步指出,各种娱乐手段将幻象符号渗入人们的意识,导致人们沉迷于“似真”的意识形态之中,实则是一种新型社会控制技术。[22]符号渗入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刺点”,即在平淡无奇的整体形象中存在一个不为外人注意却唯独触动到某个观看者的小细节。这个小细节本身并无异常,却在这个观者眼中如芒刺般跃然而出,把观者的思绪引至无边无际的回忆中。[23]
“可爱”神话的“怀旧”特质构成了成人的“刺点”。如前所述,怀旧源于内心的缺失感,其讨论的并非真正发生的过去,而是被赋予了特定含义的理想化的过去事物。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抓住这一“刺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有综艺以展现儿童个性、增进亲子关系为名打造系列节目,通过兜售儿童私生活、加工儿童形象将“可爱”打造成媒体空间资本生产的重要符号。当儿童做出笨拙、懵懂等的行为时,大众传媒会不失时机地在荧幕上配上“可爱”二字加以解说,即便暂无可爱的样态,也会通过后期人为剪辑和动画特效制造“可爱”意象,如在脸颊上加上明显的羞涩红晕、反映内心情绪的动画形象等。近年来,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也不失时机地掀起“晒娃”风气,通过短视频、表情包等资本化手段渲染儿童的欠缺特质,儿童相对于成人的缺陷反而为自身赢得了流量空间。同时,动画片等电子传媒也着力强化儿童之可爱。如《大耳朵图图》《喜羊羊与灰太狼》纷纷热衷于打造不谙世事、淘气且纯真善良的儿童形象。当儿童与成人在日常生活中频频接触这些媒介时,同语反复开始发挥作用——经过无休止的重复,把意义牢牢嵌入听众的头脑中。大众传媒巧妙塑造了成人对儿童之“可爱”在视觉层面上的审美判断,切断了其他可能意义。
(三)事实确认:现代教育学对儿童之可爱的标准化定名
大众传媒言说儿童之“可爱”的致命缺陷在于仅反复以同样的词语来界定某一事物,这种空洞的表达形式缺乏理论说服力,必须以权威为挡箭牌。因此,可爱神话需借助事实确认,即将某一意识形态以真理为名确定秩序,以合理化自身存在。[24]教育学科学化的转型为可爱神话提供了权威理据。
教育学的科学化滥觞于赫尔巴特将心理学引入教育学。在启蒙运动之前,成人对儿童的认识带有宗教论和经验论色彩,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十分模糊。直至18世纪,教育学开始依托医学和心理学研究,凭借年龄、是否换牙等标准划定“童年期”。[25]19世纪以降,教徒和慈善人士开始创建儿童学校,尝试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安排专门建筑和设施、选用专门的教学方法、编写专门的儿童读物、择取专门的教学用具等,成功建立起儿童与成人的区隔。20世纪以降,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发展学派通过实验法,更为科学地印证了低龄儿童语言发展不完善、认知思维粗浅、情感外露多变等特质,这些特征恰与“可爱”意指的幼小、孩子气契合。
“可爱”神话在我国落地较为晚近,直到改革开放,受欧美儿童教育理论的冲击,现代儿童观才生根发芽。国Dn6FRZy7hdFUZYG+TDDnrQ==家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对儿童的年龄特点、发展标准等予以制度化规定。在宏观政策牵引下,幼儿园课程倾向选用“循序渐进”模式,借鉴诸如目标导向的泰勒课程原则、评量为重的布鲁姆课程理论与布鲁纳的认知心理学,形成了一套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育理论体系,以推动儿童的阶段性发展。与此同时,其埋下了剥夺儿童潜在发展可能性的陷阱,儿童任何偏离年龄特征的表现均有可能被打上“特殊”“超常”的标签,这反过来又印证了现代心理学的合理性。“可爱”神话也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成为常理。
三、“可爱”神话的后果
神话是虚构的产物,在面对适应对象群时,会掩饰自身的行为意图,营造政治无意义的假象,有愚弄和欺骗个体的嫌疑。在现代儿童观支配下,可爱神话存在压抑儿童发展能动性、扭曲成人童年价值理性以及遮蔽本土教育理念的风险。
(一)情感化童年对儿童发展能动性的压抑
现代家庭将儿童从工业劳动和死神手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对儿童情感价值的过度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儿童发展的能动性。以新童年社会学为代表的儿童观冲击了现代儿童观设想的纯真童年,认为儿童是活跃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行动者。情感化童年虽合理化了儿童可爱的局限性,但是存在将儿童隔离于真实世界之虞,遮蔽了儿童勇敢、聪颖等其他多元品质。
具体来说,第一,以保护为名挤压了儿童自由发展的限度。自由发展指人自主的、独特的和富有个性的发展。可爱之所以能唤起成人的怜爱,很大程度上源于可爱意指的幼小、孩子气反证了成人教化的合理性。这虽然使儿童免于被戕害的命运,但对成人—儿童二元对立鸿沟的强调致使日常教育实践走向了另一极端——以保护儿童天性之名强化成人支配地位。因此,儿童只有“乖顺”才会被视为“可爱”。即便违规,违规行为也仅限于偷吃糖果、吵吵闹闹等符合成人审美趣味的无伤大雅的小错误。[26]成人对儿童可爱的规范化裁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儿童的生存空间,但也否定了儿童的行动自主性,将儿童从真实世界中排挤出去,成为规训儿童的隐性手段,压抑了儿童自由发展的空间。
第二,逗趣心理的理性僭越抑制了儿童自我建构的可能。儿童较之成人的幼小、孩子气特点会激发成人“逗趣”心理,成人热衷于逗弄儿童做出成人化举动,人为地将儿童的天然稚拙赋予成熟色彩,打造充斥“美与怪诞”趣味的儿童形象——一种是装可爱的小大人,即儿童虽然心智成熟,但为获得可爱红利,依旧刻意表现出不谙世事的天真形象。如有童星在成年后依旧表现出“可爱”的言行举止,产生极大的违和感。另一种是装大人的小可爱,即儿童穿着成人化服饰、做出成人化动作、言说成人化语言。如有成人将低龄儿童装扮为妆容成熟的成人形象,更有甚者,故意让低幼儿童摆出抽烟、喝酒等成人化举止,并视这一怪诞行动为可爱。如此一来,儿童或主动或被动地按照成人的设想表现自己,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选择能力被抑制。
(二)资本化童年对成人童年价值理性的扭曲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对,不同于工具理性对行为结果的重视,价值理性具有非功利性特点,追求事物之于主体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事物本身带来的预期。[27]可爱本是儿童情感价值的体现,寄托着成人怀旧情感和慈幼情怀。但在娱乐至死时代,大众传媒将可爱建构为娱乐化的消费符号,以榨取其经济价值。为迎合市场需求,部分儿童的监护者热衷于将自己的孩子打造成童星、网红,收割可爱红利。至此,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工具理性超越了呵护童年精神的价值理性。
成人童年价值理性的扭曲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牺牲儿童健康为代价谋取经济利益。在童年资本化的裹挟下,“可爱”儿童被笼罩在“楚门的世界”下,成为短视频等大众传媒兑换丰厚经济资本的法宝。这致使儿童“本质上是怎样的”已无足轻重,关键是“看上去是怎样的”。但是,丰厚的资本是以压榨儿童的生长空间为代价的。为尽可能延长儿童的“事业期”,一些成人罔顾儿童的身体发展需求,通过饮食控制儿童生长,以维持儿童的可爱形象。[28]如有新闻爆出3岁网红“佩琪”因吃相可爱受到欢迎,为维持热度,父母强迫孩子暴饮暴食,以致“佩琪”健康受损。二是以功利化榜样误导儿童价值选择。心理学研究早已多番指出,学前儿童行动受榜样影响。如若父母反复向儿童灌输“成名”的价值,或者大众传媒反复推送童模、网红等资本化的可爱形象,就会在无形中为儿童树立功利化榜样。相应的,儿童会在成人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开始关注自身是否足够可爱,以“获取金钱、名望”等功利化取向支配其价值选择。如儿童美妆博主直言希望自己未来当网红,表现出金钱至上的价值观。[29]
(三)标准化童年对中国本土儿童教育理念的遮蔽
现代教育学以年龄为依据,拟定了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在语言、情感、动作等方面“理应”达到的标准,走向了“生物—心理学”式儿童观。该儿童观的一大缺陷是将儿童视为剥离于文化经验的存在,关注的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类儿童”。大卫·帕金翰曾指出,童年是建构的产物,并不存在一个本质永恒的童年等待被发现。然而,神话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其功能在于使主流思想的支配力永久延续。[30]以“可爱”言说儿童,实则无意间让他者文化做了中国儿童发展的脚本。
第一,以借鉴为名遮蔽了本土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改革开放后,为取代新中国儿童“接班人”“革命者”的形象,我国开始借鉴国外教育理念拟定教育政策和改革教学活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等无不渗透着现代儿童观的理念。宏观政策变动进一步影响着教育实践活动,瑞吉欧教育、蒙氏教育、高瞻课程等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进和自下而上的行动逻辑共同筑就了美好的儿童发展愿景——珍视儿童的可爱便是践行现代儿童观,便能弥补我国传统儿童文化的缺陷。但因缺乏文化适宜性考量,现代教育理念在落地中存在水土不服、矫枉过正的问题。儿童中心被理解为去除教师支架的儿童自由玩耍、消解教师权威的儿童盲目探索、肢解知识传授的儿童任意成长;科学话语被异化为对儿童进行分类、筛选的手段,人为制造出问题儿童与正常儿童、绩优生与差生之别……不加反思的教育借鉴致使我国本土教育理念发展迟滞。
第二,以科学为名遮蔽了多元化传统儿童形象。可爱经现代教育学的权威化定名,在我国影响力见长。但是,现代教育学主要针对欧洲、北美中产群体,是关于“某些儿童”的研究,无法回答“教育如何对不同天赋、不同阶层的人都一视同仁”的问题。不同于现代“可爱”神话,我国传统社会推崇的儿童形象极具个体能动性,如临危不惧的司马光、扶弱救贫的马良,与幼小、孩子气的可爱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在“可爱”神话的攻击下,现代教育学被异化为适用于一般人群的力量,其结论也表述为“儿童如何”而非“某些儿童如何”。[31]当成人习惯性用“可爱”作为称赞儿童的话语时,往往忘记了儿童仅是因为具备某些品质才可爱,而非每时每刻都是可爱的。同时,儿童具备除可爱之外的诸多品质。换言之,可爱本是儿童一瞬间的无意识行为,正因其短暂才弥足珍贵,但被“可爱”神话扩展为持续性行为,走向了本质论的陷阱。“可爱”神话解除儿童身上的历史、习俗、文化传统等藩篱的同时,又在科学语境中不断强化对儿童的新迷信。
四、“可爱”神话的祛蔽之道
在现代儿童观的驱动下,“可爱”神话弥散在大众意识形态中,遮蔽了儿童的真实、多元样态,并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消极影响。罗兰·巴特提出,合理的破解神话路径是通过劫掠神话本体将神话神话化,即将原神话的意指充当此神话的能指,bee97b26e29155c3cffb1ff16ab6df51进而恢复话语的直接意指。[32]基于“可爱”神话的成因,可从践行参与式教育、规范隐性教育和发展本土教育入手,超越现代儿童观的局限,以破解“可爱”神话。
(一)践行参与式教育,创设儿童自我建构的空间
“可爱”神话放大了儿童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和孩子气等特质,肯定了儿童身体内蛰伏着积极潜能。但出于保护儿童可爱天性的考量,成人发展儿童潜能的方式是将其放置于人为创设的、简化、平衡的教育场域中,如幼儿园、游乐场、博物馆,在温室花园内小心翼翼地向儿童展示世界的真善美,企图在儿童和真实世界之间设立缓冲带。现实矛盾在于,世界是多维的,美好与邪恶交织,成功与挫折并存,真实与虚伪共舞。当儿童一旦接触到真实世界,巨大的反差会造成儿童的适应困难甚至心理障碍。因此,成人有必要向儿童展示世界的多维向度:我们不能让儿童接触杀戮,但可以允许儿童认识战争;我们不能让儿童接触饿殍,但可以允许儿童认识苦难;我们不能让儿童接触阴谋,但可以允许儿童深度思考。具体到教育实践,成人可以带领儿童从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制度化场所走向超市、田野等真实生活场域;与儿童欣赏美丽童话的同时,也尝试讨论政治社会、职业启蒙、自然灾害等话题,打破儿童经验的单调、偏颇和虚假。[33]
在参与真实世界时,教师要尊重儿童的多元存在样态,为儿童创设自我建构的空间。新童年社会学指出,儿童是多元化的存在,会随着社会结构、文化要素的变化被不断建构。这种建构既意指儿童被成人所建构,也意指儿童具有自我建构的能力,而后者在教育实践中往往被忽视。[34]在现实生活中,既有洋溢着乖顺、淘气等可爱感的儿童,也有怯懦、蛮横的不那么可爱的儿童。即便同一个孩子,可能在某一阶段十分讨人喜欢,在另一阶段则令人崩溃。教育者要有教无类,坚决抵制将“可爱”作为教育行动的指导准则,应给予所有儿童同等关照,尤其关注贫困儿童、弱势儿童。[35]同时,教育者应接纳并尊重儿童的想法、志趣等,在与儿童的对话中理解儿童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将选择权留给儿童,为儿童实现自我建构提供契机。
(二)规范隐性教育,管制童年资本化的生产理路
大众传媒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形式本无可厚非,糟糕之处在于它作为一种隐性教育资源,为儿童设下了“可爱”神话的圈套。改变神话的社会背景可有效圈定神话的作用范围,[36]因此,管制童年资本化生产理路是破解“可爱”神话的有效途径。
第一,将儿童影像消费正式纳入儿童保护法律法规,防范可爱商业化。儿童影像消费是视像媒介在商业的驱动下将儿童变成观赏性文化景观的过程,真人秀、广告、综艺节目中的儿童都是“可爱”神话制造的娱乐消费符号。国家虽曾多次颁布“限童令”“禁童令”等,但上述法规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力,而专门针对学前儿童的《学前教育法》关注的是幼儿园等制度化场域中的儿童处境。《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虽具有法律效力,但因儿童权益受监护人影响较大,因而在执行中不可避免存在策略空间。如《劳动法》提出文艺单位招用未成年人要保障其义务教育,而作为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儿童,是否能得到保障依旧存疑。因此,亟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弥补这一空白。第二,相关部门应严格审查儿童节目与儿童短视频,禁止可爱工具化。具体包括:建立新媒体空间生产法律法规的执行检验机制,将检查要求具体落实到童年影像消费的生产运营者、参与者和监督者身上;严禁过度宣传儿童的高额薪酬,坚决禁止消费儿童牟利的行动策略,强化对短视频创作者的素质把关,强化对儿童节目和短视频的内容把关。第三,展示多元儿童群体生存样态,避免可爱娱乐化。当前电视、短视频等大众传媒为避免引发受众的不适体验,博取流量,倾向将佩戴着健康、纯真标签的童年身体影像推向前台,同时把贫困儿童、战争儿童等处境不利儿童隐藏在后台。这种做法实际上窄化了儿童的真实样态,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国家应鼓励以关怀、公平为出发点设计儿童节目,从多维度展示不同阶层儿童群体的优势和缺憾,激发社会对弱势群体儿童的关怀。
(三)发展本土教育,推动传统儿童教育理念与可爱文化优势互补
我国传统文化由儒家主导,主张的“儿童是小大人”的儿童观与可爱神话相悖,致使教育在两个端点摇摆不定。实际上,我国另一理论流派道家的儿童观,与“可爱”神话存在相通之处。同时,我国部分经典儿童形象也充盈着可爱的底色。与其一破一立,不如着力实现融通平衡,归纳出具有文化适宜性的本土教育理念。
第一,融通道家等儿童教育思想与可爱文化的关联,匡正可爱神话的教育偏颇。道家秉持“道法自然”的儿童观,认为儿童乃天赋自然之人,其天性不仅体现为身体柔弱,而且体现为天赋的生命力及思虑无邪和机敏聪慧的心灵。该观点与“可爱”神话的含蓄意指如出一辙,即均认可儿童的幼小、孩子气的积极意义。同时,道家儿童观超越了“可爱”神话的二元论短板,认为成人与儿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交替的关系,[37]儿童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效仿成人“为学日益”,反倒是成人应该通过“涤除玄览”“为道日损”,接近或复归于“含德之厚”的“赤子”。该观点打破了“可爱”神话对儿童需要被成人保护的认识局限,肯定了儿童反哺成人、为成人提供精神滋养的可能性。因此,可将道家等本土儿童教育思想与可爱文化进行互补,为改进当前教育实践提供观念指导。
第二,挖掘本土经典儿童形象的可爱意味,发挥“可爱”神话的积极力量。受传统儒家儿童观念影响,中国传统经典儿童形象带有强烈的教化色彩。无论是传说中的儿童形象(如神笔马良),还是神话中的儿童化身(如孙悟空),抑或历史中的真实儿童(如司马光),在既往教育中,成人倾向于从政治立场或道德教化入手,解读他们不畏强权、勇敢睿智等品质。实际上,他们身上也充盈着孩子气的一面,如爱憎分明(如马良同情弱者厌恶权贵)、随心所欲(如孙悟空大闹天宫)、乐于游戏(如司马光砸缸发生于“群儿戏于庭”时)。如果在教育实践中,成人仅仅出于道德教化目的将上述人物树立为行动榜样,儿童可能会表示尊重,但无法产生亲切之感。但若能挖掘经典儿童形象孩子气的一面,再将其与教育内容相结合,则更有可能引发儿童的情感共鸣,推动儿童道德情感认同的实现。
五、余论
“可爱”本无罪,但其以神话的形式渗透进成人意识形态,太过于隐蔽以至于掩盖了其对儿童权利、成人价值理性和本土教育价值的劫掠。福柯认为,语言是将个人意愿抛在一侧,强加于个人身上的。由于语言本身是不完善的知识,因而会导致谬误,在混乱的秩序中产生虚假观念。布尔迪厄继而提出,“一个研究者的贡献在更多情况下是提醒人们关注某个问题,关注某样因为太明显、太清晰反而没人注意的事情”。[38]在日常教育实践中,诸多成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亦值得神话修辞术的解码。
注释:
①笔者以“提到儿童,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您在表扬班里孩子时,最常使用的词汇是什么?请举例说明。”为题,通过问卷星向幼儿园教师征集答案。对于第一道题目,有六成的教师明确回答是“可爱”,还有三成的教师使用了“纯真”“天真”“单纯”“无邪”“好玩”等近似词汇。对于第二道题目,有四成教师明确回答是“可爱”,如“你衣服上的蝴蝶结真可爱”“××小朋友的表情也太可爱了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幼儿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幼儿”而非“少年”“青年”“成人”,所以多会选用符合幼儿身心特征的词汇。幼儿的身心特征,概而言之,就是“幼小”“孩子气”“引发成人怀旧情感”等,而“可爱”符合这样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1][5][9][10][12]四方田犬彦.论可爱[M].孙萌萌,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160,58, 136,104,105,99-100.
[2]BURDELSKI M, MITSUHASHI K. “She thinks you’re kawaii”: socializing affect, gender, and relationships in a Japanese preschool[J]. Language in Society,2010,39(1):65-93.
[3]哈里斯.教养的迷思[M].张庆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4.
[4]SHERMAN G D, HAIDT J, COAN J A. Viewing cute images increases behavioral carefulness[J].Emotion,2009(09):282-286.
[6]周扬波.宋人的儿童观——兼论“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2(5):147-155.
[7][16][37]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3-124,69-70,176.
[8]李玮.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J].鲁迅研究月刊,2018(11):39-46.
[11][14][15][24][30][32][36]巴特.神话修辞术[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57, 176,147,184,26,166,175.
[1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49-52.
[17][19]贝奇.西方儿童史:上卷[M].申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317.
[18][25]贝奇,朱利亚.西方儿童史:下卷[M].卞晓平,申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04, 334.
[20]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M].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7.
[21]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5.
[22]汪静波.反虚构、解神话与政治化——重读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J].中国图书评论,2016(08):36-42.
[23]巴特.明室[M].赵克非,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41.
[25]杜明城.儿童文学的边陲、版图与疆界:社会学与大众文化观点的探究[M].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7:132.
[26]杜传坤.爱与规训:图画书中的儿童教育省察[J].当代教育科学,2016(18):3-7.
[27]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阎克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28]何勇海.首个童模保护机制具有破冰意义[J].人民法治,2019(11):67.
[29]王若辰.5岁女童直播教化妆?“少儿美妆博主”跑太偏![N].新华每日电讯,2021-09-15(007).
[31]丁道勇.儿童观与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15,35(2):26-32.
[33]康永久.作为知识与意向状态的童年[J].教育研究,2019(05):1-11.
[34]郑素华.从“旧”童年社会学到“新”童年社会学——发展与争议[J].学前教育研究,2023(11):1-17.
[35]李长伟.沟通自然与自由的桥梁:康德儿童教育思想概说[J].学前教育研究,2023(10):26-38.
[38]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0.
Interpretation and Decoding of “Kawaii” Myth
—Based on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cal Rhetoric
XI Xiangrong, DU Chuankun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cal rhetoric aims to use structuralist semiotics to explore the ideology behind daily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ological rhetoric, “Kawaii”, a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refers to children as “young, triggering nostalgia and childishnes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modern view of children. The causes include: the modern family’s emotional acceptance of children’s limitations,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mass media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pedagogy. “Kawaii” myth has the risk of suppressing the initiative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adult childhood and the concept of local children’s education. It is possible to crack the “Kawaii” myth by practicing participatory education, standardizing recess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ing local education, stimulating children’s potential of self?鄄construction, regulating the production path of childhood cap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education concept and cuteness culture.
Key words: Kawaii; children; myth; modern view of children
(责任编辑:刘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