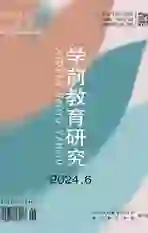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立法与实践的双重审视
2024-07-31王兴华谭欣歌邱月李晓巍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培优项目“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普惠性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编号:YLXKPY-XSDW202209)
**通信作者:李晓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
[摘 要]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幼有优育”的必由之路,而立法则是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为根本立场,旨在解决学前教育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草案》强调以公益普惠为基本方向,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参与权;推进科学保教,遵循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规定家园社三方协同育人责任,优化学前儿童的成长环境。尽管《草案》在许多方面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对学前儿童权益的高度重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条款,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 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学前教育法;公益普惠;科学保教;协同育人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终身学习的开端,对个体发展、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具有关键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构建幼有优育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当前,学前教育虽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推进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仍任重道远。从宏观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城乡、区域、不同群体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仍有较大差距,弱势儿童接受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权利尚未得到充分保障。[1]从微观的教育过程来看,儿童参与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生活的机会仍有限,[2]幼儿园重教轻保、未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以幼儿园为主导的家园社协同育人模式面临瓶颈。这些问题凸显了在保障儿童权利、维护儿童利益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六条提出“对学前儿童的教育应当坚持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是我国有关儿童事务立法的进步,也是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亮点。如何在教育实践中最大程度地落实该原则,是实现“幼有优育”的着力点,也是实现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促进学前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和提升全民族素质具有深远意义。
一、“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指导学前教育立法的合理性
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是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对儿童权益的关怀,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学前教育法律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深入剖析该原则的历史渊源、内涵及优势,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其作为学前教育立法指导原则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的历史渊源与我国法律实践
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可以追溯至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儿童权利保护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法律适用标准最早出现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离婚、监护、收养等案件中。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法院处理涉及儿童案件时应该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判决的首要考虑因素。[3]此后,各国积极践行该原则,通过立法和政策制定,不断强化对儿童权利的保护。
在我国,传统的家族和家长本位观念曾导致儿童的个人利益被置于社会和家庭利益之下。但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儿童的个人权益逐渐被提至重要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的保护责任,以及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同时禁止任何形式的虐待儿童行为。我国自1991年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后,结合本国国情与文化传统,陆续制定和修订了多部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收养法》《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等,均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进一步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首次直接提出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强调在处理与儿童相关的具体事务时,必须确保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看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准则,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国对该原则的践行,展现了从传统的家族和家长本位观念向儿童中心价值观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法律文化,也深刻影响了我国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构建和政策导向,标志着我国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持续进步。
(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困境
尽管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理念上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面临诸多挑战,其适用性存在一定困境。其一,该原则是一个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概念。《儿童权利公约》尚未对其内涵、外延和价值进行明确界定,该原则作为直接移植使用的国际术语,在我国的相关政策、法律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界定和解释,导致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不确定性、不平衡性甚至过度使用等问题。[4]基于适用的困难性和争论性,我国的许多政策法规将“儿童优先”作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具体化使用。例如,2006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的优先保护原则;其二,何为“儿童最大利益”的判断标准不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一项法律原则,而非一项能提供判断标准的法律规则。尽管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需要根据每个儿童或儿童群体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最大利益,如儿童的年龄、性别、经验、特殊状况(如残疾)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等,[5]但在不同时间和情境下,具体的判断标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判断何为“最大利益”以及哪些决策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在实际操作中仍是一个挑战;其三,儿童最大利益的判断主体存疑。理想情况下,判断主体应是儿童本身,这符合儿童能动自治论的观点。[6]然而,由于儿童的年龄较小,他们可能无法充分理解何为自身的最大利益,尤其是学前儿童,他们表达个人意见和做出决定的能力更为有限。因此,《儿童权利公约》只赋予儿童相对有限的决定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机关、儿童监护人等成为判断儿童最大利益的主要主体,导致实践中较难以儿童的利益为主,本应优先考虑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适用方法论上仍可能成为较为靠后的考虑因素,[7]这明显与该原则的初衷相违背。
(三)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的内涵和优势
基于上述困境,《草案》(2023)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代替202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中的儿童优先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以更全面、深刻地反映该部法律的各项具体制度,更好地指导各制度的实施。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委员会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内涵的三层面阐释,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是指,在涉及学前儿童的各项事务中,应始终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发展为首要考虑因素,确保学前儿童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和尊重。这一原则不仅是一项实质性权利,即学前儿童有权要求决策者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措施时优先考虑他们的利益;同时,它也是基本的解释性法律原则,可以指导法律专业人士在涉及学前儿童的法律事务中,始终从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角度进行考虑和判断;此外,它还是一种行事规则,要求在处理与学前儿童相关的各类事务时,始终坚持以最有利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草案》将“坚持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置于总则部分,意在将这一原则贯穿学前教育法的全部内容,确保无论在教育决策、资源分配,还是在日常的教育实践中都能优先贯彻该原则。
相较儿童优先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具备以下优势。首先,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紧密结合了国内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在国内法律环境中展现出更强的适用性。随着国内法律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出台,“最有利于”的提法已经逐渐在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例如,《民法典》中的第三十五条、第一千零四十四条、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均明确提到,监护人和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或“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不仅是对国际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国内法表达,更是一种法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种对应关系不仅体现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衔接,也展示了国内法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的积极进步和创新,使得法律的实施更加贴近国情。
其次,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为各方参与者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和明确的决策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无需过多纠结如何判断“最大化”,而是可以直接依据“最有利于”这一标准来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操作难度,提高了原则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再次,该原则内涵更加丰富。在总则第六条中对如何坚持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进行了细化,围绕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人格尊严、参与权、表达权、平等性、全面发展等展开,是对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内涵的本土拓展。
此外,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更加强调儿童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儿童不仅是家庭成员,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讨论儿童利益时,应考虑到儿童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发展,避免片面追求儿童利益最大化。相较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更注重平衡与协调。该原则并非简单地追求儿童最大利益,而是强调在保障儿童基本权益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倡导儿童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共进。
最后,该原则更符合儿童本位论。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从利益的角度抽离出来,摒弃了功利性教育的色彩,聚焦于学前儿童的主体成长体验。这有助于围绕学前儿童的兴趣、需求和发展特点设计和实施教育活动,使得儿童能够在愉快的氛围中自主学习、自由发展,从而实现其潜能的最大化。该原则以学前儿童为中心,让学前教育真正回归其本质——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不仅符合儿童本位论的要求,也为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上所述,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到“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的调整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学前教育实践困境的深度反思,顺应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趋势和儿童权利保护的主流方向。该原则是我国儿童保护领域的首要原则,反映的是以学前儿童为主体和中心,将儿童置于所有决策和行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既体现了对儿童权利与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也与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和加强儿童权利保护的趋势相一致。《草案》的制定,正是基于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整合了学前儿童的各项权利,充分考虑学前儿童身心发展需求、特点和规律,鼓励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协同配合,为学前儿童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谐的教育环境,让每个儿童获得充分的关怀与支持,从而激发其潜能,实现全面发展。
二、“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在学前教育实践中的落实仍面临挑战
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与参与权是儿童的四项基本权利。其中,生存权和受保护权是基础,一直以来受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的关注,并被赋予了全面而详尽的法律规范,为儿童的生存与安全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石。随着学前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追求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成为共识,改革和发展的重点转向儿童的全面发展。鉴于国内现有的法律体系和学前教育发展现状,《草案》更加聚焦于学前儿童的发展权和参与权,对这两项权利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述,旨在为儿童营造一个更高质量、更加适宜的教育环境。然而,在教育实践工作中落实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保障学前儿童的发展权和参与权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学前儿童的基本权利保障仍需持续加强
1. 弱势学前儿童受教育权保障有待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学前教育公平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8]适龄儿童依法享有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党和国家在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强调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属性,持续加大投入,新建、改建、扩建一批幼儿园,积极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尽管过去十多年来学前教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仍存在挑战。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归根到底是由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而这一矛盾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间都有所体现。[9]从学前教育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城乡、区域、不同群体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仍存在差距,弱势儿童接受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权利尚未得到充分保障。[10]在学前教育城乡发展方面,县镇幼儿园的结构性质量指标优于农村幼儿园,城乡学前儿童在认知发展、非认知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等各领域也存在一定差异。[11]在学前教育区域发展方面,东部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由于起点最低且增长乏力,存在着“中部塌陷”的问题。[12]最后,从残疾儿童群体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来看,学前融合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学前残疾儿童的入园率较低,普通幼儿园接纳残疾儿童的数量有限,且面向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教学资源仍较为匮乏。[13]
2. 学前儿童参与权保障需加大推进力度。
参与权是《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提出的儿童的基本权利之一,旨在“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看待”。成人根据学前儿童的能力水平,为儿童创造更加多元的机会,使其能够自由、平等、广泛而理性地参与不同领域的活动,真正实现教育公正,构建民主的生活。[14]我国在保障学前儿童参与权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例如,通过《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政策文件明确了儿童参与权的内涵,并鼓励和支持儿童参与家庭、学校和社会事务,畅通其参与和表达渠道。再如,《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明确指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问题”“尊重并回应幼儿的想法与问题”等。
然而,学前儿童参与社会事务决策的机会仍然有限,很多学前儿童缺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15]儿童虽然在家庭的琐碎事务中相较以往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仍然较少参与到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中。在幼儿园中,教师对儿童的观点缺乏足够的重视,儿童深入参与环境创设与课程决策的机会仍有限。[16]在社会事务的决策上,学前儿童相对拥有更少的话语权。成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往往将儿童看作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使得儿童的参与权在文化观念层面难以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关注。[17]学前儿童在许多实际问题上仍然不能独立地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制定。
(二)科学保教水平有待提高
1. 保教分离、重教轻保的问题仍然存在。
学前阶段是儿童身体生长和发育的关键时期。高质量的保育和照料能够为学前儿童提供良好的营养、充足的睡眠、适当的锻炼和优质的卫生保健,促进学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学前儿童的学习方式不同于其他年龄段的儿童,他们日常行为习惯的培养和各方面的发展是在生活和游戏的全过程中进行的。[18]保教分离既不符合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也错失了许多教育契机。[19]为推进幼儿园科学保教,党和国家制定并颁布了多项文件,如《保教质量评估指南》《幼儿园督导评估办法》等,为幼儿园科学保教提供了明确指导,为提升保教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然而,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中还存在着保教分离、重教轻保的倾向。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教师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教学和游戏活动中为幼儿提供教育指导,较少承担保育任务。部分教师即使承担保育工作,也误将保育等同于身体照料,可能忽视一日生活中蕴含的教育价值。[20]在家庭和社会层面,成人在不同教育理念与行动的相互博弈中缺乏对儿童立场的考虑,在全局性的教育焦虑中迷失了方向,而幼儿园的保育、教育以及管理功能也在这一焦虑的背景下发生异化,[21]使得学前教育有时偏离了保教结合的规律,坠入“学前教育小学化”的陷阱之中。
2.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尚未全面落实。
学前儿童学习和发展的特点要求学前教育必须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游戏不仅是学前儿童的一种活动方式,更是其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22]游戏是学前儿童的自然天性,能帮助学前儿童体验周遭的生活世界,鼓励学前儿童的自我表达和创造。同时,学前儿童的学习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材料,还需要与周围的人和物发生互动,通过获得直接经验和积极的情感体验促进学习的发生,[23]因而学前儿童需要游戏为其提供直接、丰富、综合的经验。随着成人对儿童和童年理解的加深,游戏作为学前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活动得到广泛认同和重视。
然而,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观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挑战。部分幼儿园一日活动的安排不尽合理,学前儿童自主游戏的时间不充裕;[24]区角投放的游戏材料结构化程度较高,且许多材料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此外,由于班额大、室内活动面积相对不足,学前儿童的游戏空间也容易受到挤压。在家庭教育中,仍有部分家长持有传统的“唯学习论”观念,片面重视知识学习,忽视了游戏对学前儿童发展的价值。[25]
(三)家园社协同育人面临困境
1. 幼儿园未有效发挥协同育人主阵地作用。
幼儿园是对学前儿童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承担着学前儿童的保教责任,是学前教育的主阵地。一方面,学前儿童在幼儿园度过大多数时间,与教师、同伴、园所环境密切接触,受到幼儿园全面的教育影响。另一方面,幼儿园在家庭、社区之间架起沟通桥梁,为学前儿童创设了从家庭、幼儿园到社会的系统性教育环境,并在其中给家庭和社区育人提供有力支持,是发挥教育整体功能的重要纽带和关键主体。根据交叠影响域理论,作为学前儿童生活的三个主要场域,幼儿园、家庭、社区的协作伙伴关系可以增加学前儿童的社会资本,产生最佳教育效果,[26]若三方不能有效地沟通合作,学前儿童全面发展的机会将会受到限制。
目前,幼儿园愈发重视与家庭和社区的合作,积极探索有效的协同育人模式。但目前幼儿园协同育人状况并不乐观。幼儿园在多数情况下处于主导地位,因其专业性定位在合作中起着支配作用,与其他主体的合作表现出单向性,主体关系尚未从合作走向协同。[27]尽管家园合作已成为较为主流的共育模式,但家园共育目标尚不精准,家园共育内容较为单一。[28]幼儿园协同社区的共育意识不强,社区教育资源未能充分融入幼儿园教育。此外,家园社三方未能有效解决主体分工问题,存在责任边界模糊,角色缺位、越位或错位等问题。[29]上述问题反映出幼儿园尚未有效发挥主阵地作用,协同共育意识不足、深度不够、质量有待提升。
2. 家庭未有效履责行权。
家长教养子女的责任和权利具有天然性和基础性。一方面,基于父母生养子女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父母和子女有直系血亲关系,抚养、保护、教育子女是家长的至高责任;[30]另一方面,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儿童的第一个课堂,家庭的影响自儿童出生以来就已存在,且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其他教育无法比拟的,也是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即便家长将儿童送入幼儿园接受教育,仍无法取代家庭教育的基础地位,家长仍需积极行使教育权利。
但在教育实践中,由于家长教育理念存在偏差、教育主体意识薄弱,以及受到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家长未有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充分行使家庭教育权。一方面,部分家长教育理念相对落后,重智轻德或担心教育投入不足,导致出现超负荷教育现象;[31]另一方面,部分家长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主观上免除自身教养之责,将儿童托付给幼儿园,未积极参与儿童成长全过程,更多时候在家园合作中扮演倾听者和服从者角色,家园合作处于单向支配关系,且在社区教育中参与度也相对较低。此外,家庭在教育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如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竞争加剧、社会对成功标准的单一化追求等,导致家长感到无奈和挫败,降低了他们的教育自我效能感。上述主客观因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教育效果,不利于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的实现,反映到学前儿童成长中往往会造成诸多问题,比如身心健康受损、全面发展机会受限等。
3. 社区未充分开发和利用资源和环境。
随着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建立,幼儿园不再是学前阶段唯一的教育权威主体,社区教育、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平等存在,社区作为大环境系统,持续影响着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社区的积极参与是进一步改善幼儿园和家庭教育效果,促进学前儿童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外在保障。具体而言,社区的协同对于统一幼儿园、家庭、社区的教育步调、形成教育合力,为学前儿童早期发展施以一致的价值观、教育观、实践观影响,促进学前儿童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32]
在学前阶段,教育的偶发性相较于其他学段更强。而且学前儿童主要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来探索周围世界,对他们而言,“自然即课程、生活即课程”,[33]学前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的接触中不断内化生活经验。然而,目前社区的资源和环境建设、活动组织和服务内容等并没有充分考虑所在地儿童的需求,社区大多提供的是行政性服务,因此较难参与进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34]此外,尽管部分社区建有儿童活动中心、少年宫、图书馆等场馆,但仍未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协同育人作用,资源利用率较低,甚至演变为教培地点,导致教育资源和空间的浪费。可见,社区尚未能为学前儿童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环境,尚未有效发挥协同育人的物质和空间载体作用。
三、在立法与实践中有效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
基于上述实践挑战,《草案》提出学前教育应坚持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回应社会问题,为构建更加公平、科学、优质的学前教育体系提供法律支撑。为了确保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在教育实践中的有效实施,仍需进一步审视和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
(一)权利为本:保障学前儿童基本权利
1. 加大弱势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力度。
在政府主导下开办普惠性幼儿园,坚持贯彻公益普惠这一基本前提,是我国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草案》第八条明确指出:“国家推进普及学前教育,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深入贯彻了党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战略部署,并针对学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且质量参差不齐的核心问题,回应了社会公众对学前教育普惠、高质量发展的切实需要。学前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是其正当权益,而《草案》则在法律层面上对尊重和保障学前儿童这一程序性权利做出了规定,确保学前儿童在受教育问题上的平等正义。[35]
坚持公益普惠的基本方向,贯彻落实学前教育公平,必然要求资源的合理配置,缩小个体、城乡、区域之间学前教育发展的差距。学前教育的补偿性公平要求在教育机会公平的基础上给予处境不利者资源上的倾斜,而差异性公平则要求基于受教育者自身条件的区别提供差异化的资源配给。[36]针对前者,《草案》第八条突出强调在相应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向几个重点区域和重点群体倾斜,为学前教育实现普惠、均衡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而针对学前教育的差异性公平,一方面应通过立法保障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另一方面,也应进一步明确幼儿园教师在承担融合教育任务上的主体责任,并就幼儿园如何在环境创设中保障融合教育的开展、如何建设融合教育师资队伍以及如何对融合教育过程进行评估与监督等关键问题建立合理的评价和监督机制,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
2. 厘清保障学前儿童参与权的主体责任。
在国内的成文法中,儿童的参与权已经得到了确认,《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参与权与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共同列为未成年人的法定权利,实现了儿童的参与权从应有权利到实有权利的转化。[37]同时,《草案》明确提出:“鼓励学前儿童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生活,重视学前儿童的意见。”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保障儿童参与权的要求,承认了学前儿童是整全、独特、具有独立意义且能自由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主体,有助于在立法层面鼓励儿童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建构之中,自主表达意见,提升权利意识。
尽管《草案》从立法层面强调了学前儿童参与权的重要性,自上而下引导社会各主体在观念和行动上做出相应的转变,但是要保障学前儿童的参与权,仍需要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各主体厘清各自的角色和责任,进一步明确儿童参与权的范围、形式和程序。政府应配合《草案》出台相应的儿童参与权保障的实施细则,建立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的协作机制,保证各方主体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二)发展为旨:遵循学前儿童发展规律
1. 完善落实保教结合原则的培训与考核体系。
保教结合不仅对于保教实践和园所管理有所助益,更是学前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的突出体现。虽然早在1979年颁布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出“幼儿园必须贯彻保教结合的原则”,其后颁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等也在政策层面突出了保教结合的价值。但是,囿于相关政策的立法层级低、权威性弱等问题,其能够发挥的效力有限。[38]为了应对保教实践中的问题,优化教师和保育员的角色定位,《草案》与学前教育领域的政策一脉相承,从更高的立法层级明确提出“幼儿园应当坚持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为保教结合理念向实践转化提供了立法保障。
要落实《草案》提出的保教结合原则,一方面,应加强全面系统的培训,切实帮助保育员和教师树立科学的保教观念、提高认识,提升保教能力。另一方面,要健全管理机制,完善评价体系。首先,应细化、规范不同岗位的工作行为、职责任务、考核指标体系,体现保教结合原则。其次,要优化考核制度,鼓励幼儿园建立内部自我评估机制。最后,可以健全激励机制,调动教师参与保育工作的积极性,有效贯彻保教结合原则。
2. 贯彻游戏权为学前儿童的基本权利。
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是学前教育相较于其他阶段教育的关键区别,这一区别不能仅停留在教育的理念层面,更应该在法律中加以强调。《草案》中明确提出,“幼儿园应当以学前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强调了游戏对于学前儿童发展的价值,明确了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基本定位。
《儿童权利公约》中已明确提出,“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游戏权已经被视为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游戏权的存在以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区分为前提,承认儿童的游戏权正是承认儿童作为独立的认识主体的体现。[39]只有将游戏权视为学前儿童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体现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的价值。因此,应在立法层面明确规定保障学前儿童的游戏权,引导社会各界充分重视游戏对于学前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并保障学前儿童游戏的时间、空间、条件等。
(三)协同为要:优化学前儿童成长环境
1. 坚持幼儿园主导,强化家庭教育指导责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校社三方互动关系提出法律要求后,《草案》再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学前教育阶段协同育人的重要性,对幼儿园开展协同育人提出了基本要求,如“幼儿园应当充分利用家庭、社区的教育资源,拓展学前儿童生活和学习空间”。这一规定与《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精神相一致,即幼儿园在协同育人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且,《草案》着重提及家庭教育指导,提出“幼儿园应当主动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交流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状况,指导家庭科学育儿”,为幼儿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做出基本规范。该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内容相呼应,实现了两部法律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有机衔接。
当前,家庭教育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家长在科学育儿上存在各种困惑,幼儿园与幼儿园教师熟知幼儿在园表现,是指导家庭科学育儿的主力军。然而,实践中很多幼儿园对家庭教育指导这一工作落实力度尚不足。[40]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中将其明确提升到“责任”层面,参考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中“学校要把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重要职责,纳入学校工作计划”,明确规定幼儿园应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其工作职责。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幼儿园责任具有更强的实践引领力,有助于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施效果,优化学前儿童的家庭养育环境。
2. 保障家庭主体,扩展家长教育权并完善支持体系。
家园社协同育人中,家长不只有责任,也拥有权利,权利的赋予使家长具备更强的协同育人意愿和积极性。我国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民法通则》等对家长教育权的描述多指向责任与义务,忽视赋予家长权利,[41]从而影响了家长教育子女的主体意识和参与学校教育的热情。而OECD的《强势开端Ⅲ:幼儿教育与保育》报告表明,很多国家都将参与早期教育与保育活动作为家长的基本权利。[42]为弥补我国对家长教育权重视的不足,《草案》将对家长教育权的关注提高到法律层面,指出“家长委员会可以对幼儿园重大事项决策和关系学前儿童切身利益的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和日常管理进行监督”。即强调家长应当享有对幼儿园教育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并且有权监督幼儿园教育的实施。家长拥有上述权力是改善家园合作、提高幼儿园教育有效性的现实之需,也是进一步保障学前儿童权益、实现最优发展的重要手段。《草案》中对家长教育权的强调,对于改善家园协作的效果、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合力促进学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效果是值得期待的。与此同时,《草案》也对家长的家庭教育责任做出要求,提出父母应“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创造良好家庭环境,为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必要条件”,“积极配合、支持幼儿园开展保育和教育”。即家长应根据孩子身心发展特点实施家庭教育,同时应加强和幼儿园、社区的交流合作,为学前儿童发展提供多样化资源。这是对家长“怠于履责”的预防要求。
为了实现儿童的最优身心发展,当家长无法负担起儿童的所有教育时,会选择将其部分教育权利让渡给学校教育。[43]因此,家长有责任对学校教育进行监督,享有对幼儿园教育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类似的,家长也会将其部分教育权让渡给社会教育,家长在社会教育层面的权利也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家庭责任章节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密切配合,积极参加其提供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该条例对家长的社会教育参与权做出规定。因此有必要做好《学前教育法》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衔接,在法律层面补充社会教育中的家长教育权。此外,许多家长感受到自身教育能力不足,教育效能低下,进而产生教育焦虑的心理体验。这实际上反映出深层次的制度机制问题。为此,应更加重视家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与《草案》的配套衔接,不断完善家庭教育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家庭教育支持,为家长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指导,从而缓解他们的教育焦虑和压力,提升教育效能,为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促进全社会参与,提供优质育人资源。
继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对社区支持和全面育人提出要求后,《草案》的颁布进一步为社区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律保障,要求“全社会应当为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在这种综合性教育的过程中,学前儿童将得到来自幼儿园、家庭和社区三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从而为其创造一个更加完整、健康、丰富的成长环境。丰富的资源和环境是学前儿童学习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协同育人顺利开展的重要物质和空间载体,因此《草案》提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当提供适合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公益性教育服务,并按照有关规定对学前儿童免费或者优惠开放”。该条例将社区空间环境利用从成人视角转向儿童视角,明确了社区场馆资源服务于学前儿童的公益属性,也规定了场馆资源的开放性和可获得性,保护了学前儿童享有社区资源的权益。
社会作为各个家庭单元的集合,在教育资源的多元性与实践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对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有益补充。随着《社区教育服务规范》《社区教育工作者岗位基本要求》等文件的出台,社区育人正朝着规范化和高质量方向发展。[44]如果在立法层面对社区面向幼儿园和家庭开发并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提出要求,将有助于建立完整和谐的育人生态,进一步提高协同育人质量,实现幼儿园、家庭、社区间的资源共享和互动共赢,为学前儿童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在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的教育目标。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坚持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是学前教育立法的根本,是保障学前儿童利益,促进学前儿童全面发展的现实之需,也是实现“幼有优育”美好愿景,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呼唤。《草案》基于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为维护学前儿童受教育权和参与权,实施保教并重、游戏为主的教育教学活动,优化学前儿童的家园社成长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在立法层面与学前教育实践中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可以保障学前儿童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为其创造更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助力学前儿童的全面均衡发展。与此同时,这一原则应贯穿并融入其他相关法律体系,如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等,共同构筑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综合性法律支持体系,还需关注该原则在儿童成长各阶段的持续应用,确保儿童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得到最有利于其发展的关怀和支持。
参考文献:
[1][10]姜勇,郑楚楚,赵颖,等.中国特色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7(02):1-12.
[2]洪秀敏,朱文婷,钟秉林.不同办园体制普惠性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差异比较——兼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质量效益[J].中国教育学刊,2019(08):39-44.
[3]UNITED NATIONS CHILD’S FUND(ED.).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for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 Geneva:UNICEF,2007:37-38.
[4][7]黄振威.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基于19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J].法律适用,2019(24):58-69.
[5]CHILD RIGHTS INTERNATIONAL NETWORK. UN CRC general comment no.14(2013)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have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s taken as primary consideration[EB/OL].(2013-07-26)[2023-01-25]. https://archive.crin.org/en/library/publications/un-crc-general-comment-no-14-2013-right-child-have-his-or-her-best-interests.html#:~:text=General%20Comment%2014%20issued%20by%20the%20Committee%20on,her%20%28in%20both%20the%20public%20and%20private%20spheres%29.
[6]PHILIP A.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reconciling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4:28.
[8]李天顺.准确定位《学前教育法》立法宗旨[J].幼儿教育,2020(31):55.
[9]滕锐.论我国学前教育的立法优化与体系建构[J].理论月刊,2019(11):149-160.
[11]宋映泉,康乐,张晓,等.城乡儿童发展与幼儿园质量差距:以华北某县为例[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18(3):32-59+187-188.
[12]蔡迎旗,张春艳.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J].教育与经济,2023,39(6):11-20+30.
[13]梁梦君,宋国语,陈夏尧,等.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J].残疾人研究,2020(02):12-22.
[14]胡金木.儿童参与式民主生活的建构:必要与可能[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06):120-127.
[15]贺颖清.中国儿童参与权状况及其法律保障[J].政法论坛,2006(01):151-159.
[16]蒋路易,郭力平,吕雪.CLASS视角下师幼互动研究的元分析——基于中国14省市892名教师的师幼互动质量评估结果[J].学前教育研究,2019(04):32-44.
[17]王玮,王喆.参与式幼儿园空间营造设计框架与实践——基于儿童权利、能力和发展的视角[J].学前教育研究,2016(01):9-18.
[18]闫静,褚宏祥.增强角色意识,树立现代保教理念[J].现代教育科学,2009(10):27-28+15.
[19]赵玲.幼儿园生活常规活动的价值与开展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17(03):64-66.
[20]姚丽娟.“保教结合”再审思[J].早期教育(教育教学),2019(10):34-35.
[21][29]贾周芳,张学强,马以念.一切为了孩子: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经验的当代价值[J].学前教育研究,2022(10):18-28.
[22]丁海东.论儿童的游戏精神[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78-81.
[23]马健生,陈元龙.学前教育小学化:困惑与澄清——基于“儿童发展中心”的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5-14.
[24]程秀兰.多学科视野中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透视[J].教育研究,2014,35(9):69-76.
[25]谢高明.儿童游戏权利的教育价值及其保障策略[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34(05):41-45.
[26]WALKER S A. Exploration of ELL parent involvement measured by Epstein’s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D]. Chicago: Chicago State University,2016:14-15.
[27]黄瑾,王双,陈清莲,等.幼小衔接中的多主体协同:现状调查与路径建议[J].学前教育研究,2024(03):1-11.
[28]张韵.幼儿园家园合作现状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幼儿园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2009:40-41.
[30]王丽萍,郎芳.《民法典》视域下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23(02):131-137.
[31]段升阳,刘丙元.从个人私利到社会责任:家庭教育社会职能的实现[J].中国教育学刊,2018(09):39-44.
[32]徐东,彭晶,程轻霞.交叠影响阈理论对我国幼儿园家园社协同育人的经验与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35(3):53-59.
[33]李雪艳,马琳琳.生态式幼儿园课程的内涵与构筑[J].学前教育研究,2017(08):67-69.
[34]高闰青,田道敏.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意义、现实问题及机制建设[J].中国教育科学,2023,6(5):136-148.
[35]申素平,周航.学前教育立法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J].中国教育学刊,2019(04):44-47+72.
[36]张曙光.规范性、公平性与教育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体现的三重价值及其完善[J].当代教育论坛,2021(04):43-48.
[37]邓芸,杨可.浅议儿童参与权[J].社会科学家,2007(S1):43-44.
[38]刘莉,李祥.幼儿园儿童游戏权保障的政策困境及其破解路径[J].教育评论,2021(07):64-73.
[39]刘智成.儿童游戏权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35.
[40]谭欣歌,刘辰,李晓巍.基于供需适配性理论的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现状分析及优化路径[J].幼儿教育,2023(33):31-36.
[41]刘彬.论我国家长教育权的缺失与保护[J].教学与管理,2009(05):23-24.
[42]OECD. Starting Strong II: a quality toolbox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B/OL]. (2011-11-16)[2023-10-13].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23564-en.
[43]王秋霞.家、园、社区协同教育的现状、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J].学前教育研究,2014(05):64-66.
[44]邵晓枫,郑少飞.新形势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特点、价值与机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5):82-90.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Revisiting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WANG Xinghua, TAN Xinge, QIU Yue, LI Xiaowei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o achiev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new proposi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enactment of legislation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raft) takes “the best interes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legislation, aiming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the practi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t emphasize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public welfare and universality to guarantee preschool children’s right to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t establishes principles of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care and education, and play as the basic activity, following the rule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it stipulat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amily, the kindergarten and the community to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lthough the draft law provides legal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the practi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urther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provisions and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measures is needed.
Key Words: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c welfare; scientific care and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责任编辑:熊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