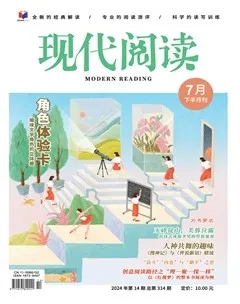人神共舞的趣味
2024-07-22凌士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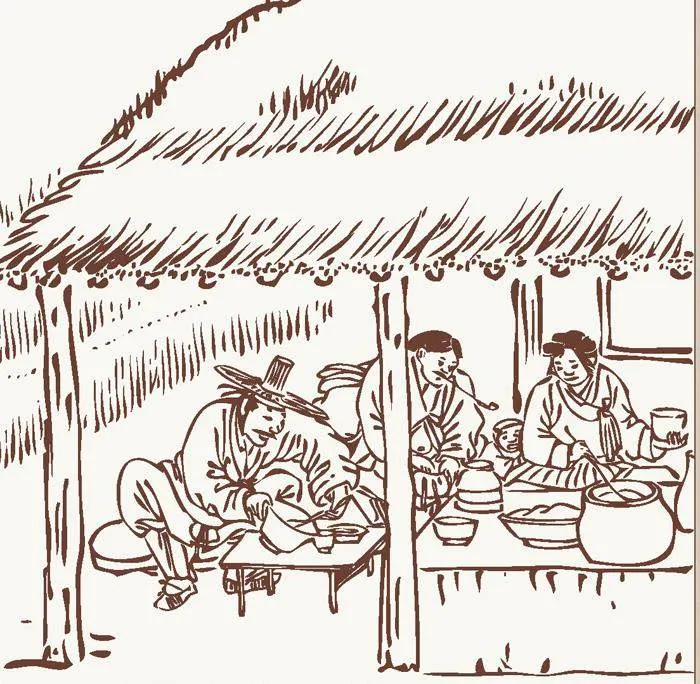
特约名师:凌士彬
名师简介:安徽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合肥市高层次人才。先后获得“安徽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称号、“江淮好学科名师”提名奖。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教学论文等六十余万字。
教育宣言:课大于天,行胜于言。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搜神记》和《世说新语》是两部标志性作品。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以“神魔”传世,南朝宋刘义庆组织文人编写的《世说新语》以“世情”示人,这两部作品中的故事都情节简单、篇幅精简,有的虽只有三言两语,但是语言、动作、场景等细节刻画十分精彩和传神。《搜神记》能让人感受到人情百态的力量,有如身处烟火人间,趣味十足;《世说新语》能让人领略到风姿通脱、言语峭拔的“魏晋风度”。两部作品联读,前者的味道在于情思互通,人神共舞,神有人趣;后者的味道在于思想深邃,行为出世,人有神趣。这种“趣味”就是跨文本联读的核心“大概念”。
大概念是指居于核心地位,能够统摄多文本,具有迁移和生长功能的重要概念。就文学作品来说,鉴赏“趣味”就是立足于“风格倾向”,理解和品鉴文学形象的共性特征和个性价值,能够高屋建瓴地看清、读透不同文本间既互相融通又呈现变化的趣味,从而培养阅读文学文本尤其是早期小说的核心素养,逐步生成鉴赏和评价新文本的能力。
一神有人趣
先说《搜神记》写神之人趣。今传的二十卷本《搜神记》主要记载奇闻异事和一部分民间传说,其中很多人物历史可考,但情节诡异,细节离奇。东晋大臣、清谈家刘惔看了《搜神记》后,评论干宝道:“卿可谓鬼之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晋国史官,以敢于秉笔实录著称于世。刘惔此话意为干宝的“搜神”是从“搜人”开始的,记载神异故事从不避名人尊者讳,有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史家风范。干宝不管是写“妖祥梦卜”、灵异怪闻,还是写神仙方士、地方神邸,都把神事当作人事如实记载,人事是由头,神事是过程和结局。干宝认为,神事的内核是“气”,他曾说,“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皆可得域而论矣”(出自卷六)。“得域而论”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加以讨论议定,因此读《搜神记》要用“人”的眼光,从“情”“理”“度”“法”的视角寻求理解上的突破。“度”主要指的是“人”与“神”的视角转换要自然适恰,“法”指的是向读者传递价值观的规则。
再看《搜神记》中的人情之趣。
(华)佗尝行道,见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声,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虀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搜神记·卷三》)
神医华佗表面上看的是病情,其实看的是人心—体察人情,妙手回春。再神的医生,都离不开“望闻问切”;再神的药,都离不开天地万物。药食同源,用大蒜捣成末,兑上酸醋,取三升喝下即可治好咽炎,且还熏出一条蛇,这里的“蛇一枚”为故事增添了神话色彩。
体味人情就是理解人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比如王祥的“卧冰求鲤”(出自卷十一,下同)、王延的“叩凌而哭”,都是“孝感天地”的人间正道。神异的故事之外,有着作者对人情世态的感悟。
再思《搜神记》中的人理之趣。这种人理之趣往往与人伦天理密切相关。
吴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顷,复起,犬又衔衣。恪令从者逐之。及入,果被杀。其妻在室,语使婢曰:“尔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瞻视,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搜神记·卷九》)
这段是取材于三国时期吴国辅臣诸葛恪被嗣主孙亮和武卫将军孙峻谋杀于殿堂的历史故事。该故事的神奇之处在于诸葛恪遭遇意外前后有三个征兆:一是朝见君主前夜,诸葛恪心神不宁;二是出门之前,家犬两次咬其衣服拉住他;三是妻子闻到了婢女身上的血腥味。诸葛恪本人、家犬、妻子和婢女表现出的奇特灵异的感觉,充满玄幻色彩。这一情节写出了狗的忠诚、妻的情分和婢的义愤,把反差悬殊的君王与臣子、人类与动物、主人与奴仆融合到一起,蕴藏着率真天趣、和谐物趣和恩义人趣。其中,“家犬爱主”之两度“衔衣”,其实是一次又一次对家主安危的提醒;而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的夸张动作,传达出知晓主人被害后忠诚家奴的切齿之恨和切肤之痛。惜护主人的狗与婢,充满人理之趣—作者从不易为人觉察的视角,描写人物际遇和命运,通过家常生活细节表达人伦主题。
干宝用史家笔法写作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得益于他本身也是史学家出身。东晋初年,朝政草创,经开国元勋王导举荐,干宝领修过国史,著有《晋纪》二十卷。由于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为后世史学家所推崇。干宝在《搜神记》序言里说这些故事的来历是“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他有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史相仿的经历和风范,以记史的标准和对事件的领悟来整理创作,“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故所写之神事,饱含人世情理趣味。因此,《搜神记》与《世说新语》联读,能够读出“亦真亦幻”的感觉和意味。
二人有神趣
先说《世说新语》写人之神趣。这里的“神”有神逸、玄妙之意,书中人物有仙风道骨、与世无争的风范。《世说新语》是包含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小说,人物有着“非虚构”的真实感,但细节又带着几分夸张,刻画手段惟妙惟肖,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它描写的是“当时当事”的实情实景,语言超凡脱俗、简洁传神,展现出人物丰富的精神面貌。
神趣首先表现在人物的语言上。《世说新语》非常注重记言,这可能源于魏晋的清谈之风。魏晋文士受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喜爱清谈玄理,涉及很多对人物、时事的品评。鲁迅曾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那时文人们喜欢聚会,王羲之《兰亭集序》里的“修禊事”,即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清谈盛会,清谈的收获大多是诗歌文集,而记录清谈过程的就是散文或笔记体小说。
比如清谈中的神侃之趣。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世说新语·德行》)
周子居认为黄叔度这样情操高尚的朋友有涤荡心扉、澄澈品行的作用,真乃超拔常人的见识。这是以近写远、虚实相衬的手法—反省说话者“复生”的“鄙吝之心”,令人想起黄叔度“大方”“大度”“大道”的品格及其影响。史载东汉官员周乘(字子居)“天资聪朗,高峙岳立”,是个志行高洁的人,十分注重对标朋友,时常自我反省。古人讲“益者三友”,笔者在这里再加一友,子居即为“趣友”。
神侃的更高境界是神喻。
(郭林宗)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住两夜)。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世说新语·德行》)
神喻之趣,意味深长。识人如识物,其理相通,一个人器量之深广,如万顷湖泊,外力想把它搅浑了都不行,真是器识深广,高德难测。黄叔度没有出场,但以上两则妙语嘉言,已经生动地刻画出他品行高洁、令众人敬仰的人物形象。
小说语言的最高境界是“个性化”。笔记小说时代,大多数作者不会有意识地追求“个性化”,但要写出人物特点、如实记载,在客观上也就“个性化”了。《世说新语》的语言里朴素的“个性化”特点,不仅表现在说话者本人,还表现在说话对象身上。通过这些俏皮、神妙的语言,可以解读人物的精神面貌,探究其内心世界。
神趣还表现在人物的行为上。一般认为,魏晋时期部分有远见的文人学士开始有意识地保持思想独立性,不拘泥于传统礼数教条,他们崇尚自然,行为洒脱,行事率真,不拘小节,所以常常“任诞”,乃至“忿狷”。《世说新语》中有很多看似令人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描写,实则更能彰显人物的真性情。
比如率性之趣。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世说新语·任诞》)
“竹林七贤”之阮咸,人称“小阮”,是个旷达而不拘礼节的人,懂音律。有艺术气质的人多豪放,他以瓮代杯,与大家相向大酌。他与同族人甚至不嫌猪的腌臜,把群猪饮过的浮在上面的酒舀去,接着“共饮之”。他们认为,生灵没有贵贱,万物均是齐等,与猪同饮又何妨?
这种率性之为,因可笑而显得可爱。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世说新语·忿狷》)
东晋蓝田侯王述不仅性急,还很天真。《晋书·王述传》记载他的朋友谢奕“极言骂之”,王述不知如何应对,只是“面壁而已”,过了半晌,谢奕骂累了走了,他才坐了下来,如犯错的孩子接受老师的批评一样,十分可爱。此时的他吃鸡蛋,扎不着,掷于地,用木屐踩,又拾起放入口中,用牙齿咬,咬破即吐,也是孩童秉性,可爱可贵。类似这样的奇异行为,与《搜神记》的奇异情节进行联读,可谓呼应成趣,相得益彰。
三人神共趣
《搜神记》与《世说新语》两部作品,都是由一个个小故事组合而成的,结构比微型小说还简单,以“异闻”“奇崛”见长而传世。作品中所有关于“神”的虚构与幻想,其实都是来自人—神是人情世故的幻构。神人穿梭,跨界袂行,需要的正是联想和想象。立足于人的情思,善于幻想与奇构,文学艺术才能散发出趣味和魅力。
《搜神记》与《世说新语》这两部笔记小说,都充满人神共舞的趣味。如果把两部作品根据中国小说体裁特点来品鉴,它们都具有小说发展前期“稚嫩”“简单”而又不失小说“元素”(如情节、人物、环境等,此时还不能被称为“要素”)的特点,是介于短散文与传奇之间的过渡性作品,展现出早期中国古典小说的“稚趣”;如果把两部作品置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去阅读和考查,它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兼具的风格已初步形成,双峰并峙,彼此融合,共同发展,演绎着神人互通的情趣和理趣,展现出小说风格变幻的“妙趣”;如果把两部作品放在自然文本的层面来阅读,就要认识文本的共同追求和独特价值,因为每个独立的文本都是作者独特的精神世界,是不同文人才情和识鉴的展现,它们在主题内容上百花齐放,在表现形式上都是短章载道和故事书情,展现出文本的“意趣”。
以“趣味”大概念贯穿跨文本联读的过程,开阔了我们的阅读视野,突破了文本孤岛,打破了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的情境壁垒,从哲理的高度提升了我们思考问题的层级,在高阶思维上培养了分析、综合、辨异、品评能力,乃至融会贯通、追求发展的创新能力。
课堂指引
最新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设置了“文学阅读和写作”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两个学习任务群,都提出了提升文学欣赏力和文化理解力的课程目标,因此我们可以用《搜神记》与《世说新语》两个古代优秀文本,设计出适合高中生的群文阅读课程。通过课堂学习,师生一起立足于历史,扎根于现实,读出两部作品“稗史传说”和“信史传真”的味道;立足于文本,着眼于故事,读出两部作品“情节传奇”和“细节传神”的味道;立足于人性,细究于主题,读出魏晋时期人们的“心灵神思”和“传世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