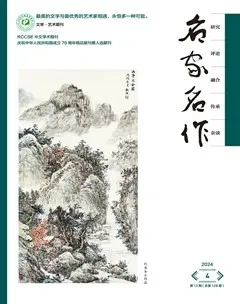从“气韵生动”谈任伯年写意画中的自然观
2024-07-07盖仁平
盖仁平
[摘 要] 中国“天人合一”及“道法自然”的哲学观,衍生出了在中国画中所呈现出来的自然观,即“中得心源”的绘画观念,并且形成一种独特的笔墨结构语言即“气韵生动”,体现了中国画是富于精神,而不是单纯进行摹画。从任伯年的绘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自然观念。任伯年作为海派的领军人物,其绘画风格师承前人并将其内化形成新的艺术风格。而任伯年的写意画不落俗套,标新立异,题材广泛,生趣盎然,画面“气韵生动”,正所谓“妙在通幅皆灵”。任伯年不仅绘画技法高超,更是在整幅画的画面效果以及构图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驾驭能力,因此,他的写意画都是气韵十足,整体给人以神韵生动之感。
[关 键 词] 任伯年;气韵生动;意境;自然观
一、任伯年与自然观
任颐(1840—1896),字伯年,清末著名画家,海派代表画家之一,与任熊、任熏合称为“海上三任”,又与吴昌硕、蒲华、虚谷并称为“清末海派四杰”。他天资聪慧,才华横溢,画技高超,对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走兽、翎毛等绘画题材都无所不能,其中花鸟画和人物画更是一绝。
任伯年作为海派代表画家,不仅将传统绘画的技艺发挥到极致,而且吸收了西方绘画的理念,因此,海上画派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绘画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方向。而同为绘画大师的徐悲鸿对任伯年的评价也很高,他在《任伯年评传》中这样评价道:“吾故定之为仇十州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殊非过言也。”
“天人合一”及“道法自然”等观点在中国绘画中处于重要地位。综观我国现存的书法绘画,都能体现出当时文人欣赏自然、感受自然、表达自然、融情自然等的情感,而这也是国画的自然观的内容。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指的是顺应自然,不应破坏自然规律,只有符合自然才是美。艺术创作的过程离不开自然,但是画家如果一味描摹自然,作品就会显得呆滞,毫无生气,“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光强调了向自然学习,以自然为师的重要性,而且强调由心出发,通过“师”走向造化。[1]《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意思是天地与我们都是道心之大用的妙用所生,万物与我们都是一个本体而没有人与万物之别,人和自然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体现出画家要将自己与自然连接起来,领略其中的奥义,并从中得到启发,才能达到“天人合一”,达到与宇宙同频的效果。而这积淀了中国千年来的美学精神,在人与自然的沟通与感应中,形成了万物之“道”与艺术之“法”,两者汇聚而成的“气韵生动”的思想也成为沟通自然后塑造形象的最佳标准。[2]
二、任伯年绘画作品中“气韵生动”的形成
(一)前人绘画对任伯年绘画的影响
任伯年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任鹤声(号淞云)是一名民间画家,也是任伯年绘画的启蒙老师。任伯年自幼受到父亲关于绘画方面的熏陶和指导,同时父亲对他价值观的形成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父亲早逝后,任伯年一直靠着卖画为生,而后跟随任熊、任熏兄弟学绘画,而这也使得任伯年对传统绘画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任氏兄弟师承陈老莲,画面色彩艳丽,没骨、写意、双勾皆通,构图巧妙,颇具生活气息。[3]任伯年的画风也受此影响,学习了大量双勾技法,间接继承了陈老莲的绘画技艺。《上海县志》中记载道:“仿宋人法,纯以焦墨勾骨,赋色肥厚,近老莲派”。同时他的写意画又受徐渭、八大山人的影响,任伯年对这些大师的笔法进行了仔细的揣摩和研习,并运用到写意画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二)海上画派对任伯年绘画的影响
任伯年远赴上海时期,海上画派当时的领军人物胡公寿推荐他为驻店画师,因此他十分感谢。胡公寿本人善画山水兰竹,而任伯年的山水经胡公寿指点后,有所领悟及创新。任伯年与海上画派的画家联系非常紧密,如吴昌硕、虚谷等,经常一起交流与相互学习,因此,任伯年在此期间绘画技能进一步提升。任伯年也会与其他画师交流心得,这也使得他的绘画手法更加丰富,绘画技能更加深厚,同时个人风格逐渐突出,渐渐成为海派的领军人物。任伯年对海上画派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任伯年与众多海派画家一起,砥志研思,推陈致新,精益求精,直接推动了传统中国画向现代转变的进程。[4]
(三)民间艺术对任伯年绘画的影响
任伯年自幼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其父亲任淞云是一名民间画家,擅长人像写真,并将他的写真技法传授给任伯年,由此奠定了任伯年的摹写能力及造型能力。在父亲去世后,任伯年当时为了生计在街头摆摊,这使得他深入百姓的生活中,感受百姓的喜怒哀乐,体验百姓的所见所闻,并感同身受,并且摆摊的日子里也锻炼了他的写实技法,同时也让他之后的画面内容及风格,适于民间的审美习惯,反映了大众的审美需求,所以任伯年的画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任伯年的绘画能巧妙画出对方的神与形,尤其是他的花鸟画题材的作品往往很受人们的欢迎,因为太美的东西往往给人不真实的感受,人物和花鸟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同时任伯年还经常以日常生活中的瓜果蔬菜为题材来作画,正因为如此,他的画面内容大多通俗易懂,十分贴近人们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也颇受百姓的喜爱。
三、任伯年绘画作品中“气韵生动”的具体表现
“气韵生动”是国画的核心精神,南北朝时期的画家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论”中就提出“气韵生动”这一概念,而且还是六法之首,可见其重要性。画面要做到有气韵才能生动,可以将“气”比作阳,“韵”比作阴,而这就好比阴阳相生,缺一不可。“气”是中国美学的核心,可以理解为是作品的灵魂以及生命。“韵”是指画面的意境、味道和给人的感觉等,“气韵生动”是指画面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韵味、气质,带有生气的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美感的呈现。这一形式一直被传承并且沿用至今。
(一)画中笔墨的运用
任伯年的写意画具有很高的造诣,笔墨气韵皆有独到之处,能做到胸有成竹、气韵生动、一气呵成。墨分为焦、浓、重、淡、清五大色,而这五大色又会形成不同的变化效果,因此,笔墨是表达意境及“气韵生动”的手段,笔墨的虚实、线条长短、笔力的驾驭技法等,都是对整幅作品气韵的表达和体现。
1.《岛佛驴背敲诗》
《岛佛驴背敲诗》是任伯年于1887年所作的写意画。画面描画的是一位诗人骑着一头驴,行走在寒林萧索的山间小路之中。树枝好似干枯,因此用墨密且重,同时枝干也较短,让画面氛围更加凄凉,画面左侧的两组树枝丛,上面的较下面的颜色要浅,是想通过墨的浓淡程度来表达前后远近的关系,画面中主体是人物和毛驴,因此轮廓线颜色较深,造型简洁概括,寥寥几笔就将诗人眉头紧锁、正在苦苦推敲诗句时的冥思苦想的表情刻画得惟妙惟肖。画面中马鞍用的是跳跃的蓝色,不与人物服饰颜色所融合,也不与黑色的毛驴相融,达到突出及吸引目光的作用,让观者看到这幅画时首先就被这抹蓝色吸引。而且毛驴刻画得十分生动,且并未将其体积画大而是表现出毛驴好似不能承受之重的样子,整个场景妙趣横生。整幅画人物以及树的线条截然不同,树木及石头以淡墨皴出纹理,树枝用干墨绘制以配合画面整体意境,另外衣纹的纤长硬朗,严谨且不失飘逸。整幅画线条整体灵活多变,用墨的浓淡干湿、用笔的抑扬顿挫都恰到好处。
2.《归田风趣图》
《归田风趣图》是任伯年于1893年所画的写意花鸟画。描绘一片繁茂的瓜豆藤旁一只母鸡在悠闲地啄食。整幅画墨、色并举,相得益彰,叶子是用墨色晕染并且用浓墨勾出叶脉经络,老母鸡形象生动写实,毛羽丰满。整幅画颜色明净淡雅,大片的留白、令人遐想,构图清新大胆,用笔简洁,落墨果敢,用色大胆,并且水分把握巧妙。整体未出现大面积晕染,但在浓墨树叶的衬托下,使得花叶清丽繁茂,相邻的两簇叶子也用不同颜色区分开来,两个瓜也用的是不同颜色,画面整体颜色不落俗套,同时还生动地表现出农村的景色和情趣,是任伯年田园花鸟画不可多得的精品。画面总体笔墨洒脱、意境生动、简逸放纵、风格欢快温馨,这都得益于他平日注重观察,所以他笔下的花鸟造型精准,田园景象真实可爱,充满生机。
(二)构图方面的“气韵生动”
构图,是中国画历来所重视的,南北朝时期的画家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论”中就提出“经营位置”,东晋顾恺之所说的“置陈布势”,张彦远所言的“画之总要”等,这些思想所讲的其实都是构图,可见构图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和它的不可替代性。构图是画者对所观自然景色的一种经过内心精神酝酿、加工所得的图式,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物质相符合、相协调的和谐之成。[5]画面的主次关系、合理的布局、整体的比例关系等都是为了突出画面的“气韵”,经营位置讲究程式法则,但程式法则是要与生活相联系,脱离了生活而只追求形式主义就容易一味地继承前人的笔墨形式而没有了主观的生活体验与理解,便没有了“气”。[6]整幅画的事物间的连接与转折,是使整幅画有所意境的关键。画面整体气韵相连,才能生动有灵气,才能体现出气韵生动。
1.《封侯图》
《封侯图》是任伯年于1887年所画的写意画。画面中一只猴子站在枝蔓上向下看,且呈现出嘴巴张开露出獠牙的表情。猴子处于画面中心,且猴子的右前臂呈弯曲状握在藤蔓上,这使得主体猴子与藤蔓间自然地连接在一起。整幅画中藤蔓是处于上升的走势,指引视线向上看,叶子和猴子在画面左侧,且树叶的尖所指向下,主体猴子的目光也是俯视,二者皆是向下走势,使得画面中心落回,并促使画面的整体视觉中心呈现出向下的趋势,同时整体场景是作向画外延伸状。画面中间的一组树叶不仅与左下角树叶做呼应,还为上面光秃秃的藤蔓“夺”回些目光,以达到视觉平衡、构图稳定的效果。并且画面中藤蔓的起点都处于黄金比例处,不会使得画面构图过于死板,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也让人们对画外的场景产生无限遐想。
2.《蟠桃绶带图》
《蟠桃绶带图》是任伯年于1890年所画的写意花鸟画。画面中有两只在茂密枝头嬉戏的鸟儿,一只作直立状似在眺望沉思,一只头呈倒立状似想吃掉下面枝头的桃子一般。画面中枝干的起承转合恰到好处,并且为了使画面层次丰富,用不同浓淡程度来表现枝干的前后关系和它的枝干走向。画面中叶子呈一簇一簇地存在,这样既丰富了枝头,同时也将枝干间联系起来,使得整幅画面中的大的“开合关系”更加完整。树叶所在的位置既能将画面的事物都联系起来,又不会让画面内容看起来过于琐碎,而桃子在视觉上从树叶间跳脱出来,使画面整体结构更加完善。右侧的石头则是将画面中心拉回下方,给人一种这桃子树长在泥土中,而不是漂浮于空中的实感。两只鸟的嘴巴冲向不同方位,一只向上与那根向上的枝干一起与题字相呼应,而另一只嘴巴向下的鸟,则是与下方的桃子及树叶产生连接,使得画面从上到下的整体视觉延伸更加流畅起来,更能凸显画面生机,更富“气韵”。
(三)留白对整幅画“气韵生动”的影响
留白是我国传统绘画的重要构成元素和表现手法,是我国美学的精髓。“留白”“计白当黑”都能体现出画面气韵。“清戴醇士《题画偶录》谓:‘笔墨在景象之外;气韵又在笔墨之外。然则境象笔墨之外 ,当别有画在。这都是以虚无见气韵。”[7]因此,在创作时,要做到有所取舍,有时候“空”反而比“满”更能凸显画面中的意境和气韵,更能呈现作者之所想,以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承载着情感,达到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学效果。
1.《荷花双鹭》
《荷花双鹭》是任伯年于1891年所画的写意花鸟画。画面中荷花占了大量篇幅,但在叶间留有空白,不仅仅是为了花而留出空白,还为画面留有“喘息”的空间。荷花是在水中生长的,但是画中并没按照常理绘制水纹或者涟漪,而是在这幅画下方进行大面积留白来让观者进行自我想象。因此,观者可以想象出下面是水的存在,也可以想象出是两只白鹭正在上岸的情景,不同观者可以对画面内容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同时留白也是讲究位置的,左侧上方的空白与右侧下的空白是相互呼应的,这使得画面总体结构平稳。右上方的荷叶墨色很重,如果没有留白,则整幅画是呈现向上走的趋势,但是有了下方的大面积空白,不仅与荷叶墨色形成对比,还将画面中心有所调整,使得画面更加完整,更富意境和气韵,正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境”。
2.《枇杷稚鸡》
《枇杷稚鸡》是任伯年于1886年所画的写意花鸟画。画中两只鸡站在枇杷树前面的石头上,一只作抬头挺胸仰头状,一只作伏地状,好似要奔跑。画面中事物种类很多,有石头、枇杷、叶子、枝干,还有两只鸡,因此,画面一定要做到疏密得当,作者只将几簇树叶和枇杷做了繁密的处理,其他部分都有部分留白。树叶间有留白是为了让枇杷有“透气”的感觉,枝干也并未都渲染上颜色,只做效果皴,是对树枝不做强调,从而突出树叶和枇杷以及鸡。两只鸡在构图上巧妙地将它们身体重叠在一起的,处理方式十分独特,可以增加空间感,作者并未用艳丽的颜色或者墨色将其全部上色,而是在鸡身部分进行了留白处理,使得鸡在旁边浓密的树叶间脱颖而出,而鸡本身的设色也形成了对比,鸡头以及腹部还有翅膀尖端使用浓烈的颜色进行上色,而鸡身和翅膀的部分进行了留白,鸡在自身色彩以及周围颜色的强烈对比下,在画面中脱颖而出。下方的石头也只作了少许皴法和点染,并未进行大面积上色,是为了不剥夺画面的视觉重心,起到辅助画面结构的完整性作用,同时也起到强调画面意境的作用。
四、结束语
任伯年的画讲究结构,用色巧妙,笔法精妙,所表达的意境让人十分舒服,这也是为人所追捧的。他的作品融古通今,又吸收各家之所长,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任伯年的作品不仅仅为海派的艺术发展指引新方向,他的艺术还开启了一代新风,引领了当时的中国画坛。任伯年的画作和他的艺术思想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天人合一”的和谐共存提供借鉴,对后世的艺术家的创作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他的艺术思想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毕继民.浅谈传统中国画的自然观[J].美术观察,2004(7):95.
[2]孙玉宝.在研究和实践中体悟中国画艺术[J].美术观察,2020(5):142-143.
[3]王跃迪.任伯年绘画中的意境与审美思想分析[J].艺术评鉴,2019(23):40-42.
[4]胡逸格,刘汉娥.任伯年绘画风格的形成探析[J].美术文献,2022(9):64-66.
[5]石思梦.古代自然观影响下中国山水画氤氲缭绕之意境探析[J].巢湖学院学报,2021,23(1):78-85.
[6] 吕子青.论气韵生动在传统中国画中的审美意义[J].景德镇学院学报,2018,33(5):117-120.
[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