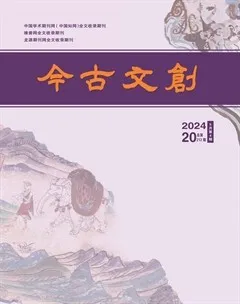论《温故一九四二》中的非虚构特征
2024-06-28刘芸竹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问世,因其文本结构的特殊性,很难界定其文本体裁。现如今非虚构写作浪潮在国内兴起,回望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就会发现这本书有着“跨文体”“介入性”“真实性”“反思性”等非虚构特征。刘震云走向历史,用在场的方式带领读者重返1942年哀鸿遍野的河南,通过史料还原真实历史,用底层视角审视这段苦难岁月。
【关键词】非虚构特征;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0-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0.005
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温故一九四二》是刘震云众多小说中的一个特殊文本。全文无主线,无明确人物,无明确立场,似为河南自然灾荒后裔在走访及查阅相关资料后所撰写的一段史料结合体。在小说文本中,对历史的爬梳和转述,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辨析,对历史人物的诘问和质疑,都给人一种开放性和复杂性相结合的直观感受。
一、作为“非虚构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的文体界定问题在文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有人将其视为河南史的纪实体小说,有人则将其视为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就连作者刘震云对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文体界别也一直游移不定。他曾先后用“纪实小说”“调查体小说”“唯一的非虚构作品”来界定这部作品,但他又对这几种说法表示质疑。在一次访谈中,刘震云曾坦言道:“说它是小说,它是一个非虚构类作品,说它是报告文学,但报告文学要么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要么就是有一个很波澜起伏的人生的人物。但《温故一九四二》都不是……没有合适的体裁能够装下它。”[1]
那《温故一九四二》这部作品的体裁文本究竟该如何界定呢?让我们先返回文本,在小说中刘震云曾为自己大量引用史料新闻表示抱歉,事实上,刘震云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是受朋友钱刚所托,写作1942年的河南旱灾,打算编入《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由此得知,刘震云写作《温故一九四二》的最初设想就是编写一部科普著作。但在调查的过程中,令刘震云感到惊讶的是,1942年那场大饥荒的目击者及其后人居然遗忘了这场灾难,这段历史就这样被人淡忘了。作者怀着惊愕与怀疑的心情,开始试图还原这一历史事件,并由此最终创作了这部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主要人物的“四不像作品”。直到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了“非虚构写作”的栏目后,非虚构写作受到重视,我们可以发现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温故一九四二》完全能够归入到“非虚构小说”的门类。广义的“非虚构小说”包括纪实小说、报告文学、新新闻报道、传记小说等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以非虚构为主要创作原则的小说类型。同时,学者沈闪曾明确表示非虚构写作是指作家与现实的直接接触,以一种鲜明的介入方式,直接面对现实,回溯到历史的深处,或者是追寻文化的踪迹。这种写作方式使得文本展现出无限接近真实、主体亲历性、反思性和跨文体的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创作风格[2],而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创作完全符合其“介入性”“历史现场”“真实”“反思性”“跨文体”等特征。
二、作者的在场:介入性写作姿态
“非虚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强调作者的在场。“在场”并非只要求作者如实记录,更要通过“介入”的手法,使人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振,从而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学者洪治纲曾提出非虚构是一种创作态度,它是作者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所采取的一种介入式的创作态度。[3]“非虚构写作”既没有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愿,也没有掩盖作者的现场情感和经验,就连对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材料的评判和选择,都是真实的。
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就存在两位“叙述者”,他们都是作者在场的分身。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就存在两位“叙述者”,他们都是作者在场的分身。“我”是一名受灾者后裔的调查员,同时也是一名忠实的历史纪录者,在与当事人的对话与史料的叙述中,“我”始终在对历史进行质询与思考。
在小说开头,首位“叙述者”就出现了,由吃食引入河南饥荒这一历史事件,“我”是河南受灾者的后代,受朋友嘱托来调查被人遗忘的一九四二。当“我”把时间倒回1942年,才发觉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河南大饥荒造成的300万人死亡,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小说从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叙述历史,使“我”在叙述与解读历史方面获得某种特权,从而在形式上为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提供保障[4]。“我”作为一名调查访问者,先后访问了姥娘、花爪舅舅、地主范克俭、郭有运、韩委员、姓蔡的老婆婆等,力图从亲身经历者的口中发掘隐藏在他们记忆中的真实。然而“我”所采访的历史亲历者却几乎忘却这一历史,得到的只是一些零碎的、不完全的片段。作者毫不避讳地写到“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5]、“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减叶”[5]。值得玩味的是,调查采访者“我”用真实的方式参与进来,他要面对“模棱两可,扑朔迷离”甚至有可能是虚构的故事,于是,作者应该怎样填补这个虚构与真实的巨大空隙?由此引发出小说中又一个“叙述者”的形象。
另一名“叙述者”所充当的角色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而刘震云则以大量报刊,杂志和新闻报道切实发挥着小说中忠实叙述者的作用。按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Scholes)的说法,这位叙述者希望为读者呈现一个事实的博物馆、永不停歇的研究者和分类者,以及一个头脑清晰且公正无私的法官。[6]新闻报道无疑比个人的历史回忆更具有真实性。在引用新闻报刊时,作者常常在场,“我”更像是一个超越历史的评说者,能够对报道内容发表看法。在这里的“我”似乎像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漠然地记载了一九四二年河南灾荒的情形。但实际上两位叙述者——无论是身为灾民的后裔的采访者,还是冷漠忠实的历史叙述者,都为作者在场的分身。这两者看似抵触的“叙述者”身份融为一体,让读者更能通过“介入”与作者产生共鸣,体会到作者隐藏在客观冷静叙述下的无奈的悲鸣。
三、史料的介入:重返历史现场
“非虚构”的另外一项重要特点就是它必须具备真实性,而真实性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要求。它至少得遵从事实,即故事并非无中生有。它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有些是以照片、录像、新闻、笔录、日记等形式呈现出来的,有些则是由作家自己亲自去发掘的“真实”,这些真实奠定了文本构建的基础。为了做到真实性,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引用了大量史料,他在小说中就明确表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象更真实一些”。刘震云参考并引用了《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河南民国日报》、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的书信、白修德的《探索历史》、张高峰的《大公报·豫灾实录》、南京国民政府在1943年的救灾材料、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的报告等史实材料。这些真实的史料,带领读者重返1942年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直面历史现场,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因亲历者的遗忘造成的历史记忆遮蔽。在《豫灾实录》中,读者们能够看到哀鸿遍野成千上万以树皮和野草为生的河南灾民,他们为了生存吃有毒的野草、难啃的干柴,卖儿卖女只为换一点粮食,在如此严峻的灾荒面前,县衙还要捉人逼捐,逼着灾民饿着肚子卖田纳粮。在《探索历史》中,读者们能够看到逃荒路上狗吃人、人吃人、卖孩子卖老婆、扒火车被轧死的各类惨状。在《看重庆,念中原》中,读者们能够看到河南灾荒如此之严重、河南人民如此之悲惨,而南京国民政府却无视河南灾情,强行征粮,反观重庆物价飞涨,阔人豪奢。在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报告中,读者们可以看到在灾荒中的灾民们还要承担不断加重的赋税,自己食不果腹还需要上交军粮……
事实上,史料原本只是处于一种原始的离散的状态,后来经过作者的发掘整理,重新编排组合,被作者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文本就有着“史料”加“评论”的组合体,既包含了作者想要传达的讯息,又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态度。根据白修德的《探索历史》和其他历史实录,刘震云还原了白修德历经波折见到蒋介石的场景,并在史实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推理和看法,对历史事实融入自己的阐释。然而究竟事实真相如何,人们不得而知。
另外,非虚构作品并非是历史资料的简单堆积,它是历史和文学的有限融合。美国当代作家诺曼·梅勒认为文本通过选择性的叙述视角和小说家独特的语言技巧,成功地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融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巨大飞跃,进一步消除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7]。在白修德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荒时,作者揣测蒋介石的心理:“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5]这段既是作者对蒋介石露出神情的揣测与解读,也是非虚构作品文学性的体现。在不破坏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消散了原始史料的无趣与呆板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可读性。
四、历史的重构与反思:被忽略的底层叙事
从叙事视角出发,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与报告文学追求的宏观叙事存在明显的差异。非虚构作品将叙述的焦点转向了底层的普通人和他们所经历的细微事件,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这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叙述视角。正如学者陈剑晖所言,非虚构强调从个人出发,以微观视角切入,关注人性和底层叙事,注重日常书写,不追求宏大的主旋律叙事[8]。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就关注到了被忽略的底层叙事。历史由谁书写?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值得被“载入史册”的历史似乎是1942年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类大事。但对于河南灾民而言,他们是灾难的承受者、历史前行的付出者,宏观的历史叙事却很少将焦点对准这些普通民众。作者刘震云以一种民间的方式展现了历史自身的无限丰富性,从而更贴近底层人民的真实命运。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抛弃了宏观的历史叙事,用戏谑自嘲的口吻来书写被遗忘的底层民众,试图重构属于底层人民的历史叙事。透过被采访者模糊不堪的记忆,人们走到了1942的那场灾荒面前。对于九十二岁高龄的姥娘来说,1942的灾荒在她九十二年的坎坷生命中无甚特别,只是多次饿死人的年头之一;当过村支书花爪舅舅回忆当年向山西逃荒的情景:一家人拉推着独轮车要饭,一路上吃树皮、吃杂草,为了活命要扒火车去陕西,在逃荒路中饿死、被火车轧死、家人失散的数不胜数。花爪舅舅逃荒到洛阳在施粥厂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才逃出。蔡婆婆在二十岁向西逃荒时,家中所有家当被盗,被父母卖掉进了窑子,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皮肉生涯,趁着战乱才逃回家乡。最悲惨的是老人郭有运一家,在逃荒路上家人们四散崩离:为治母亲的病,卖掉小女儿,但母亲依旧病死;大女儿得天花死了;儿子在扒火车时掉落被轧死;好不容易逃到陕西,老婆嫌他穷跟人贩子跑了,一家人出来逃荒,只剩郭有运一人活着回乡。底层人民面对灾祸的悲惨命运向读者展开,刘震云没有刻意强调这种悲惨,他用无奈戏谑的口吻平静地向读者呈现由底层人民构成的这段真实的灾荒历史。在小说附录中,作者发现了1942年刊登在《河南民国日报》上的两则离异声明,这说明在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大主题下,普通平凡老百姓的生活仍在继续,底层人民有着多样复杂的日常生活,这是不可忽略的。这给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整个灰暗的历史灾难回顾蒙上一丝日常化的温情色彩——在1942年饿殍满地的河南大饥荒中,还有普通人坚韧生活的足迹。
另外,“非虚构”还特别强调反思性。学者陈剑晖指出“它强调文学书写必须具有反思和质疑社会的品格,即知识人言说和阐释当下生活的能力”[8]。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处境的人面对1942年的河南灾荒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值得人们反思和探寻。
五、结语
总而言之,刘震云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比较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它具有了“真实性”“介入性”“主体性”“反思性”“跨文体”等非虚构特征,同时小说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作者对历史的诘问与反思。在小说中,刘震云以戏谑自嘲的口吻,带领读者走向河南这个灾难现场,通过史料再现历史场景,让1942年饿死三百万人的河南苦难历史能够被人铭记。历史总是大而化之的,但千千万万个底层普通人民构成了这段历史。底层的苦难不应该被遗忘,这应该也是作者温故一九四二的原因之一吧。
参考文献:
[1]许荻晔.喜欢小说的幽默,就是找到了它的魂[N].东方早报,2012-11-26(4).
[2]晏杰雄.双重文化视阈下的微观痛感叙述——丁燕非虚构写作论[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04): 180-192.
[3]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J].文学评论,2016,(03):62-71.
[4]周家玉.历史虚构的限度——《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历史叙事[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28(10):45-47.
[5]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9-89.
[6](美)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M].仲大军,周友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7]石雅芳.论诺曼·梅勒在虚构与非虚构中的穿越[J].浙江外国语学报,2012,(5).
[8]陈剑晖.“非虚构写作”概念之辨及相关问题[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5):20-27.
作者简介:
刘芸竹,女,山西吕梁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