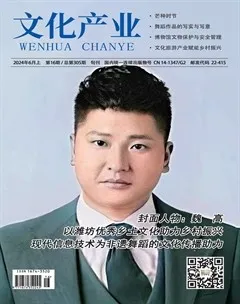学习越调《老子》唱腔音乐的感悟
2024-06-26王果
王果
在越调《老子》的声腔创作中,最大的特点是继“申派”声腔神韵固本求新。全剧的唱腔风格苍劲豪迈、清新优雅而又空灵飘逸。但却不失“申派”声腔的神韵,每段唱腔都彰显着申凤梅大师声腔的灵魂,尤其是“老子”的唱段无不显示着“申派”声腔的特质,这一点是我辈值得学习和传承的。
越调《老子》是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剧曾荣获河南省委宣传部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第十一届戏曲大赛“文华大奖”、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南北片)展演二等奖、河南省人民政府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艺术节获第十三届“文华大奖”、河南省第四节黄河戏剧奖“特别奖”,入选2010—2011年度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工程,2013年参加上海第15届国际艺术节获“优秀剧目奖”,同年被搬上荧幕。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而唱腔音乐是一出戏的根、一出戏的魂,是剧种的分野,想展现出一个剧种的风格及特色只有唱腔可以独占鳌头。《老子》的唱腔音乐着实不好写,因“老子”这一人物并非能用一般的“音乐形象”而塑造,还需有“道骨仙风”彰显其间;它要震撼、要深刻,也要含蓄、内敛;茫茫宇宙唏嘘感慨。作曲家深入领会剧情,深刻感悟“老子”,在剧种特色的统领下,以鲜明的时代感完成了“老子”的刻画与阐释。作为一名越调作曲者谈一谈我在学习越调《老子》唱腔音乐这一经典剧目中的一些感悟。
《老子》全剧的创腔牢固地建立在传统和“申派”声腔基础之上
《老子》全剧声腔是根据剧本要求,在“申派”和传统的声腔基础上创立的联套唱腔。“老子”第一次出场“驾青牛牧群鹿野趣无限”唱段,作曲家选择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散板”节奏“大起板”板式。“驾青牛”腔节音调古朴、舒缓,古琴奏出的过门空灵、典雅,透射出久远的历史感。第二腔节过门竹笛、拨弹乐的交替演奏,描绘成群结队的野鹿欢蹦乱跳的情景。尤其竹笛清脆明亮的音调,像似夹杂着“呦呦鹿鸣”的叫声。而后,随着“野趣无限”那长风般具有“申派”神韵的拖腔喷薄而出,穿过历史的时空,回响在空旷的大之野中。在古朴、悠扬主题音乐烘托下,“老子”驾青牛、肩抗铁锄,在群鹿簇拥下蹒跚而上。而后是飘逸、洒脱的“风场吹云长卷永恒再天”“二八”的演唱(“慢板”二腔)。就以上“大起板”“二八”两板式的演唱,道出了“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哲理,又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二八”之后,作曲家驰骋丰富的想象力,打破一般板式结构规律,借鉴歌剧音乐多声部创作手法,重复“驾青牛牧群鹿野趣无限”,来接续唱段,继而,男声、女声,女声、男声,舒展而愉悦的反复咏叹“风场吹云长卷永恒在天”,这节多声部与老子的演唱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与群鹿的舞蹈相得益彰,浑然天成,不自觉地把观众带入两千多年前老子故里,这片生机盎然、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景象。其唱腔在传统中见新意,增加了时代感和历史感,又不失剧种风格和“申派”神韵,多声部演唱形式的借鉴,既丰富越调音乐的声腔艺术创作技法,又满足受众对越调音乐的审美趣味。其后的“上善若水水性柔”唱段,是“老子”因事利导向众弟子诠释“水”的德行时所唱。该唱段分四个排比性段落,并在各段落最后都有学生“帮腔”。所以,音乐唱腔因词义的不同,而呈现的旋法、格调及色彩也不同。在板式的运用上,作曲家选用“二八”及变格“垛子”“碰板”联套而成。为使老子深情吟咏:“水乃生命,水育天下,水利万物而不争;上善懿行,莫若水也!”采用了“二八”完整过门音乐,在琵琶、古筝、二胡、循序渐进时,仿若溪水潺潺在石涧间自然流淌,紧接越胡率整个乐队奔涌而来,引出老子对“上善若水水性柔”的感叹之腔。接下来唱段在“垛子”的主架构(2/4拍),有多样的学生“帮腔”幕后女声伴唱。当“老子”唱“上善若水水性柔,人品当以水品修”这腔段时,作曲家以女生明丽悠扬,亲和、清纯,热情荡漾的变格模仿的伴唱,使“老子”对人性高贵品质的倡导得以充分地渲染。随后,为把唱段推向极致,在“我洗天下我成垢,我养社稷我无酬……”这节唱运用“碰板”的形态,腔体紧缩,层层递进,而在这里,男声(学生帮腔)女声(伴唱)错位进入,以“垛板”唱式将水的献身精神反复咏叹,使情感逐步浓烈升华。而后,将豪放、洒脱,激情四射并具申派“无怨忧”的甩腔一泻千里,把对“水”的赞美与张扬推向巅峰。“上善若水水性柔”唱段,在戏曲音乐传统形式,而又不拘泥于程式,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音乐元素与传统越调相结合,造就腔与词、词与曲融合体,进而表现特定的戏剧情境,使唱腔透射出古调新腔之感。作曲家与剧作家的相互融合,将深奥哲理融入戏曲审美领域,唱出“老子”贵“水”贵“柔”思想的丰富内涵和他所倡导的“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善行境界。运用传统板式架构、语汇创作既符合剧情又符合人物的新腔,是《老子》一剧唱腔出彩的特色。例如,第五场“河之图洛之书千年神鉴”紫葺唱段,用的是舒展、明快的“二八”板式,而在“洛之书”腔节落音,却一反常态地落在调式的属音(5),为唱腔增添传统中不曾具备的推动力,促使“千年神鉴”倍感灵动、活跃,“鉴”字的行腔更得以清流迭涌,舒展流畅,开拓性地唱出清新可人的“二八”“花腔”,使人心怡神往。接下来的“三年来出译文匹帛成卷,三年来写注释简片成山……三年来完成了洛书洪范”等排比句中,作曲家采用了“垛子”的架构,而却淡化传统的腔节感,并借鉴河南坠子音乐素材,使唱腔充满赞美与亲切感。当唱至“青牛叫,群鹿喊,云牵衣,风拽衫”腔段时给全曲高潮做了铺垫,欲扬先抑,轻盈吟唱而后,使“衫”字与“一片归心向青山”紧咬,力度猛增,激情四射,接着,“向青山”的甩腔一波三折似风逐浪叠的“花腔”模进上扬,以全段唱腔的最高音(),诚挚地歌唱出师徒二人对美好的向往,也把观众的审美情绪推向极致。
融会贯通,创立符合剧情、人物新板式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唱腔打破了越调长期以来男女同腔同调的习惯。在女生保持F调的同时,男生采用bE调,把男生音域从F调声嘶力竭中解脱出来,使音域、音色得到充分发挥,演唱起来游刃有余。对于塑造人物,刻画角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毕生放喉第一喊”是全剧的核心唱段,其板式由“导板”“慢板回龙”“慢花垛”“苦流水”“垛子”“紧续子”架构而成。该唱段在“道德经”被焚、青牛献牛黄、紫葺抢救“道德”残书相继身亡,“老子”的心灵深处忍受着一次次情感痛苦折磨的情势下,一字一音吟叹,在重复“第一喊”的“喊”字时,行腔上翻八度喷薄而出,并使拖腔落至调式属音(5),把对失去青牛、紫葺的满腔情怀倾吐在“喊”字上。通过击乐“帽子头”引出“惊醒了:千年的青松、万年的枯楝、沉睡的山岭、梦中的大涧——果然见紫葺东来漫天漂红烟”。这节唱的板式,是20世纪70年代借鉴京剧“回龙”与越调“慢板”腔节的融合嫁接“慢板回龙”板式的演唱,通过轻重强弱力度的对比与高低抑扬的旋律变化,使一个下韵句35字一气呵成,尤其“漫天漂红烟”的大甩腔,跌宕起伏、刚柔相济,以及节奏的控制和激情四射伴奏过门的烘托渲染,把“老子”呼唤紫葺的一片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一泻千里。接下来“见紫葺蒸腾起美美焕焕,见紫葺浮地走袅袅珊珊”抒发“老子”思念紫葺梦幻般情景的演唱,为了准确表达剧作家的深邃含义,以利于刻画人物,作曲家独出心裁地把“慢板”与“花垛子”融合嫁接而成。也就是把“慢板”(十字句)第二腔节之后删去过门接“花垛子”(十字句)第二腔节之后的重叠、倒置、再重叠词组,由于腔体的扩充,形成“见紫葺蒸腾起美美焕焕(重叠)焕焕美美(倒置)美美焕焕(再重叠)”十字句的变格形式。因为演唱节奏舒缓,曲调细腻委婉,为此,把这一新板式命名为“慢花垛”,这一板式的呈现极大地丰富了越调的声腔艺术和板式,形象地描绘出“老子”仿若看到紫葺靓丽的容颜,轻盈纤美的身影,以柔情步态浮地而起的情景。加之抑扬顿挫、唯美隽永的行腔,女声伴唱的烘托,表现“老子”触景生情,思念弟子紫葺的心境欲罢不能。在下面抒发“老子”情怀大段唱中,无论是板式运用和唱腔旋律的轻、重、缓、急与人物情感保持高度一致。尤其唱腔转入“紧续子”,节奏加快,当唱至“民是天民是地民是江山”戛然而止,为凸显“江山”,在重复演唱时突慢一倍,使“江山”二字腔体扩充,而申小梅(饰演老子)以申派典型音调那苍健激越,豪迈大气的甩腔结束整个唱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大爱无疆的高尚情操,使老子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以上述唱腔音乐的创作,有继承发展、又有创新,融会贯通是明显的个性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作曲家开阔的创作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主题音乐的运用
主题音乐贯穿是塑造人物音乐形象和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的一种有效手段。“一部音乐作品的主题,凝聚了其中最重要的素材,概括了最核心的本质,体现了作品最根本的构思。”(见《音乐分析基础教程》彭志敏著)。《老子》的主题音乐融入了越调典型音调的元素,其曲调简约、明晰、有着执着的个性。为此,在应用中无论是表现什么感情、描写什么环境,人物出场、下场都渗透主题音乐的因素。尤其是唱段的大甩腔和高潮处的渲染,都是利用主题音乐的展开、紧缩,速度的对比、节奏对比和变奏等手法,巧妙地转入传统过门接唱,能使人联想到主题音调所表现的人物的感情与形象,契合与当下追新求异的广大戏曲观众对戏曲音乐的审美需求。《老子》的主题音乐共13小节,具有性格鲜明,概括性强,可塑性大的特点。作曲家用它贯穿全剧,在剧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或层次上前继后续、循环往复、相互关联、衍展派生、或扩展,或紧缩,最后发展为“春秋一渡函谷关”的合唱主题。使全剧音乐既多姿多彩,又前后呼应,连贯而统一,准确、全面、整体把握了全剧的音乐风格,值得我们学习。根据剧情需要,《老子》的音乐在配器上使用了古琴、古筝、管子、箫、埙、编钟等古代民族乐器(或音色),为深入表现戏剧情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曲家利用乐器与乐曲的同构效应,恰当地表现了特定的环境、情状。孔子问礼中,古色古香、典雅曼妙的古琴、玉箫用于礼遇先贤圣哲,使整个舞台顿生庄严、辉煌气象,让人如身临先哲神圣的讲坛,肃穆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更加可贵的是,这些古代乐器与当代乐队的成功结合。戏的最后一场,与苦县百姓同哭的管子独奏,及哭紫葺的埙独奏,就不仅表现了哀痛、忧伤,而且隐现了先秦时空中先民的生存境况。该剧以古琴奏响全剧的第一声。它是一个重复的深沉、厚重的下行模进音型,犹如两击沉重的钟声,推开两千多年前历史时空的大门。继而,在渺远的弦乐背景下进入先贤的世界。而除去它准确的音乐描绘,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还有古琴等与越调、与该剧音乐主题的成功糅合,以崭新而独特的音乐风貌明示受众,一个叫做河南越调的剧种,演绎一个古代圣哲老子的故事。
传承与创新
以越调的传统声腔来表现道家鼻祖——老子,这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老子》的声腔创作中最大的特点是继“申腔”神韵固本求新。从戏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作为青年作曲者来说,不能着力追新猎奇,而是要着力塑造新的音乐形象,着力创造新的音乐语言,着力开拓新的音乐程式,要尊重传统、学习传统、继承传统,要把外剧种的音乐和多种形式的音乐融入越调音乐中,“化”为越调音乐,“创新”必须牢牢建立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之上。无论怎样发展,怎样变化都“万变不离其宗”最终必然回归到申腔越韵的母体之中。传统音乐是基础,即越调音乐的根本,所谓固本就是保留本剧种、本剧团固有的风格特点;求新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出新,绝对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另建一个空中楼阁,这是作曲者必须遵循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脱离这个原则就容易走偏。如果为了“创新”而我行我素地打乱传统板式严密的结构及板式运行的逻辑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哪一句腔弯好听就抄下来,将几句好听的唱腔拼凑一起构成一段唱腔,这种东拼西凑的做法,费尽心力写出来的唱腔失去越调音乐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又怎能不失去越调风味呢?又怎能保留流派特点呢?所以必须要尊重传统、学习传统、激活传统、继承传统,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守正创新、固本求新。
戏曲理论家汪人元先生说:“好的戏曲音乐作品应该有这样五个方面的特征,即像、准、美、新、高。”以此衡量《老子》这一剧的声腔音乐,无疑在“达标”“优秀”之列。原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主任、研究生导师朱维英先生曾在中国文化报发表文章盛赞:“《老子》这出戏的唱腔音乐在全剧中起到了很好的叙事作用和抒情作用,剧中主要人物的唱腔是在继承传统越调唱腔前提下再创造的,听起来‘既像新朋出现,又似旧友相逢,唱腔既有创新又不失本剧种音乐神韵……”音乐艺术的格调高低,与作曲家的才学、修养、品格,对美的敏感度、创作欲与创造力、审美取向等诸多综合内涵息息相关。它凭借着技巧与形式得以传达,但又绝对是远大于和高于技巧之外的综合素养所致。
通过认真学习《老子》唱腔音乐创作,使我受益匪浅,深深感悟到越调音乐的独特魅力。从而认识到,作为一名青年作曲者,只有沉下心来向传统学习、守正创新,坚持不懈地做全方位的修炼与提升,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时代优秀作品。
(作者单位: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