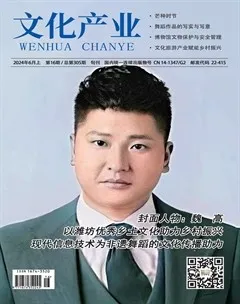新石器时代展览的讲解思路设计
2024-06-26邢楷
邢楷

在全国大部分历史类博物馆中,新石器时代部分的讲解都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过于久远的年代、匮乏的信史资料、灿若星斗的文化类型、不断更新的考古发掘成果等都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讲解工作带来了较高的难度。现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展陈特征对新石器时代展览的讲解方式展开探讨,意图寻找一种将文物、文化、文明融会贯通的讲解思路,力求向观众尽可能完整地展现我国新石器时代辉煌灿烂的文明史,阐明不同文化类型下主要文物的特征及其背后生产力发展的脉络,以期为博物馆新石器时代展览的讲解思路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概况
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在这一时期跨过了新旧石器时代,孕育出灿若星斗的文化类型,其中,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包括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
裴李岗文化是黄河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它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重要遗址包括舞阳贾湖遗址、临汝中山寨遗址、长葛石固遗址、新密莪沟北岗遗址等。裴李岗文化的代表性文物是用于谷物脱壳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该文物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中展出,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大地上农业革命的起源。
处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是从裴李岗文化演化而来。仰韶文化发现于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该遗址的发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著名的遗址包括仰韶村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河村遗址等。仰韶文化不仅展示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也蕴含着精彩的彩陶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文化类型。马家窑文化位于甘肃省中南部,主要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农业发展较快。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当时的居民主要种植粟和黍,主要经营原始的旱作农业。此外,马家窑文化与同样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的齐家文化一样,出土过早期的青铜器物,但对于马家窑文化是否属于青铜文化仍存在争议。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该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泰山地区为中心的山东中、南部以及江苏北部地区,晚期遗址分布较广。重要遗址包括大汶口遗址、西夏侯遗址、王因遗址、刘林遗址、大墩子遗址等。截至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大汶口遗址陶器上发现了30余个刻画符号,其象形元素主要包括日、月、山、树、钺、锛、王冠等。有些刻画符号与甲骨文类似,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应当是处于原始阶段的文字。
考古资料表明,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已经进入父系社会。而夯土建筑以及城墙、城堡遗迹的出现证明龙山文化时期极有可能已有了城市的雏形。
相较黄河流域而言,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有着更适合农业发展的条件。河姆渡文化因首次被发现于浙江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镇而得名,重要的遗址包括余姚市丈亭镇鲻山遗址、余姚市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宁波市江北区傅家山遗址等。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由于其堆积层位于水位线以下,与空气隔绝,刚出土时仍呈现金黄色。经鉴定,这批稻作遗存与野生稻差别明显,属于人工栽培稻。这不仅反映了河姆渡先民规模宏大的农业生产盛况,也表明资源的集中与分配制度的变化,反映了长江流域文明的演进。
除此之外,位于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被认为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这表明良渚文化极有可能已经有了明确的阶级制度甚至是统治阶层。
上文所述仅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比较典型的文化类型,这也说明,博物馆想要在一个单元甚至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内向观众系统阐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区的文明演进历程具有较高的难度。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新石器时代部分讲解要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新石器时代部分具有文化类型丰富、文物类型多、空间资源有限等特点,在进行展陈设计时难免会遇到取舍的问题。因此,如果观众在相关积累较少或未获得系统讲解的情况下,很难有效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辉煌文明。基于此,笔者将结合讲解过程中常用的展线顺序对展厅、展陈文物进行重新梳理,以探索更加高效的博物馆展览讲解方式。
重点文物的筛选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新石器时代部分展出文物达一百余件/套,涵盖多种文化类型,其中不乏鹰形陶鼎、人面鱼纹彩陶盆等国家一级文物。因此,在筛选该部分重点讲解文物的过程中,博物馆应关注文物、文化、文明等多个维度的标准。
第一,就文物层面而言,文物等级是筛选文物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等文件,不同等级的文物反映了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不同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代表性。第二,就文化层面而言,文物的筛选应尽量全面展现不同地区较为典型的文化类型,不仅要阐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基本脉络,还应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从而为观众展现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多元一体”的整体特征。第三,就文明层面而言,新石器时代是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时期,文明的形成包含了三个重要判定标志“文字”“冶金术”和“城市”在这一时期都开始萌芽,在讲解中阐明这三个标准及其演进过程将有助于观众理解中华文明产生的必然性。
因此,笔者认为反映农业生产已形成规模的河姆渡文化炭化稻谷,反映新石器时代信仰和艺术的贾湖骨笛、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反映礼仪制度雏形的仰韶文化鹰形陶鼎,反映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形式的仰韶文化蚌塑龙虎墓和姜寨遗址模型,反映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红山玉龙和良渚玉琮,反映中国早期城市出现及发展的龙山文化陶水管应在展览讲解的过程中作为重点呈现。
重点文物的讲解方向
根据观众的普遍反馈,整个“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讲解时间一般以3个小时为上限,如果按展览的部分平均分配时间,可用于整个远古时期部分的讲解时间不超过22分钟,应用于新石器时代部分的讲解时间应在10分钟左右为宜。这就意味着,站在文物前方详细介绍每件重点文物的传统讲解方式无法适应这一时间安排。而博物馆常见的解决方式包括延长整体讲解时间、减少讲解文物的数量或在整个展览的前半部分详细讲解,后半部分则采用快速串讲的形式,不论哪种解决方式都有其弊端,不利于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这一时期重点文物的讲解方向。
如前文所述,博物馆展览讲解应兼顾文物、文化与文明三个层面,但同时又受时间所限不能贪多求全。因此,在设计重点文物讲解方向时,应突出重点、有舍有留,实现基本科普、引起观众探究兴趣、培养观众正确史观的目的即可。针对同属一种文化类型的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可在简要介绍文物后,将该文化涉及的知识点如分布范围、历史年代、文化特征等分散在不同文物中进行介绍。如果该文物还具有反映文明进程的代表性意义,可将其文明角度的叙述放在该文物讲解内容之后,以此兼顾文物、文化和文明的系统化讲解。
以前述重点文物为例,新石器时代部分文物可供选择的讲解重点如下表所示。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新石器时代部分文物讲解顺序探究
博物馆展厅文物的摆放位置并非严格按照某一主线设计,这有其客观上的必然性,包括文化类型多、文物类型多、历史上不同地区各具特色且发展并不均衡等。这些因素都让新石器时代文物的讲解很难严格按照某一条主线进行。以下为笔者按不同逻辑进行的讲解展线设计及其优势、劣势对比。
以文化类型为主线的文物讲解顺序
如果以文化类型作为讲解主线,则新石器时代文物的讲解顺序为:河姆渡文化炭化稻谷—马家窑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鹰形陶鼎、人面鱼纹彩陶盆、蚌塑龙虎墓、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姜寨遗址—红山玉龙—良渚玉琮—陶水管,大部分相同文化类型的文物均可前后相接。但这一讲解主线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部分文物仍存在顺序倒置的问题,可用的解决办法为跳过其中一个或设计重叠路线。其二,由于玉龙与玉琮处在展厅正中且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类型,故部分文物在路线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顺畅性,尽管看起来只是走了一个反向螺旋,但在讲解实践中,由于该区域的观众数量较多,故环绕式讲解路线不具备可实操性。
以文明史演进为主线的文物讲解顺序
如果以文明史演进作为讲解主线,则需要对新石器时代文物的顺序进行重新梳理。其中,较为常见的标准包括距今年代的远近、社会组织形态的复杂程度、玉器加工技术水平等。在博物馆展厅中,由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距今年代相对久远,且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故将其放在首位;仰韶文化的文物尽管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且距今年代有一定差异,但在讲解实践中一般不具备详细阐明该文化不同类型的讲解时间,仍然将其作为一体说明;马家窑文化的距今年代相比仰韶文化要更近一些,故将其放在仰韶文化之后;其后是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由于良渚文化体现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且有“良渚古国”之称,故将其放在红山之后;龙山文化与夏相接,表现出明显且较成熟的城市特征,堪称王朝出现的“前夜”,故将其放在末尾。
如此安排讲解路线的优势在于可以借助文物较为清晰地向观众展示“文字”“冶金术”“城市”三个要素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的历程,能较为系统地展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文明的进程。但这一路线的劣势在于路线设计过于复杂,重叠路线较多,在讲解实践中的可实施性仍然较低。
文化类型与文明史的结合方式
文化类型与文明史的结合方式是以文化类型为主,兼顾文明史阐述的讲解方式。在该讲解方式中,文化类型所对应的时间顺序并非是文物排序的第一要素,同一种文化类型的文物也不一定要连续讲述,但需要在讲解过程中,考虑文物背后反映的文明史发展意义,特别是要对能体现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的文物着重进行说明。
在这一讲解方式下,河姆渡文化的炭化稻谷依然放在开端,其后介绍仰韶文化的鹰形陶鼎,此时可将重点放在陶鼎的功能、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对现代考古的意义上,其后引出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并沿途介绍舞蹈纹彩陶盆。其后,可分别介绍蚌塑龙虎墓、人面鱼纹彩陶盆,穿插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制玉水平介绍。在介绍良渚文化时,应重点说明文明的三个标志及其被称为“良渚古国”的原因,而后在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处简要回顾仰韶文化,最后在姜寨遗址和龙山文化陶水管处,通过两种居住形态的对比说明“聚落—城市—早期国家”的发展历程。
将文化类型与文明史相结合的讲解方式是本文探究得到的较为合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新石器时代部分文物的讲解方式,可以较好地实现统筹兼顾。但该方式仍面临一些难题。例如,如何向观众直观呈现不同文化类型在地理上的分布;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复杂逻辑的清晰传达;对于存在传承性的文化而言,如何借助文物本身及其他辅助资料直观展现其传承性;便携式多媒体设备是否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等。这些问题都有待博物馆在讲解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