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写照,正在阿堵
2024-06-20陆岩军
陆岩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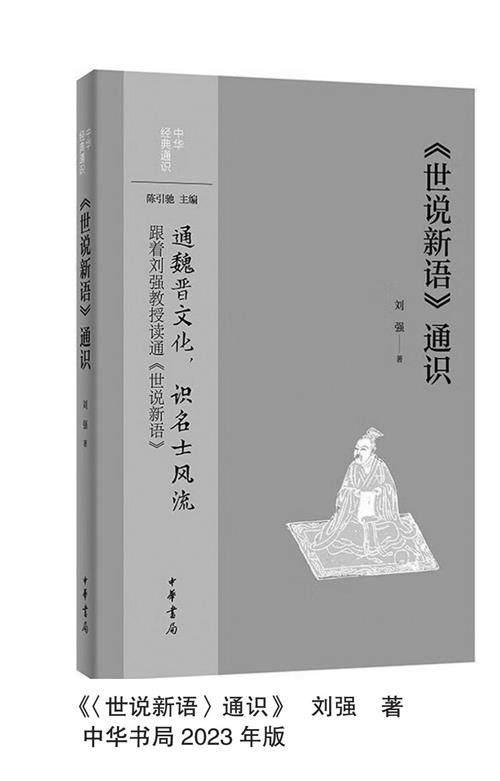
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更是魏晋风度与思想、魏晋名士言行的生动形象展示,被誉为“名士底教科书”(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古今唯一小说名著”(《诸子集成刊行旨趣》)、“风流宝鉴”(冯友兰:《论风流》),并以其续仿之多与评点之富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提及《世说新语》,自会想到洪应明《菜根谭》中的这句隽语,仿佛就是为《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而量身定做。《世说新语》“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宋高似孙语),其迷你型、微博体、段子式的传神表达及所蕴含的魏晋风度与美学思想历久弥新,神韵辞采,俱为一流。千载而下,其佳言佳行、流风余韵仍令人心驰神往。
自5世纪刊行迄今,《世说新语》一直受到读书人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注释、评点、续仿、研究、选编、翻译层出不穷,切实形成了“世说学”的研究格局。即从近一世纪来看,《世说新语》各类专著就有170余部,论文已近2000篇。其中,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世说学”研究在持续性、多样性、深刻性和普及性等方面,较为引人注目。自2000年发表论文《20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对历史真实的冲淡与对艺术真实的强化——论〈世说新语〉的叙事原则》起,二十余年来,刘强先后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世说新语文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世说学引论》,陆续出版《世说新语会评》(2007)、《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人物篇》(2009)、《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典故风俗篇》(2009)、《竹林七贤》(2010)、《世说学引论》(2012)、《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2013)、《魏晋风流十讲:〈世说新语〉中的奇风异俗》(2014)、《清世说新语校注》(2015)、《〈世说新语〉研究史论》(2019)、《世说新语资料汇编》(2020)、《世说新语新评》(2022)等十余部著作;又主编《世说新语鉴赏辞典》(2023),发起并召集五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或参编的四部会议论文集也已陆续出版。刘强在文献、评点、鉴赏、阐释、研究上多管齐下,既有文献基础的奠基与夯实,又有文本的深入解析与灵动阐释,更有学术史的擘肌分理与学科建构的奋力开拓。至此,刘强当初规划的“世说学工程”大体已备,取得了令人敬畏的成就,在“世说学”研究之路上留下了一长串无法绕过的足迹。
了解了刘强在《世说新语》研究上二十余年孜孜矻矻的持续开拓及不断获得的坚实学术成果后,再来看其新著《世说新语通识》,便会在惊叹之余,自然产生厚积薄发、炉火纯青之感。一言以蔽之,历史的眼光、现代的视角、当下的表形成了此书的独特风貌。
全书由导言和五大专题展开。导言从古今名人所提出的五大“美誉”(即古今绝唱、琐言第一、名士教科书、风流宝鉴、枕中秘宝)切入,牵涉古今中外,出入经史子集,准确传神地揭示了《世说新语》的特质和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颇具历史眼光。
接下来专题一深入讨论了《世说新语》的作者、命名及门类,为读者迅速厘清了“前文本”问题。关于作者,究竟是刘义庆独撰还是成于众手,自明代以来渐有分歧,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世说新语》“成于众手”渐成共识。而刘强对之前的观点有所修正,更明确地坚持“独撰”说,从写作动机、思想倾向、文学才华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极富情理的辨析,同时又持审慎态度,认为“尽管《世说新语》‘成于众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假说,但在找到确凿的证据前,刘义庆‘第一作者的身份,还是不容抹煞的”(第34页)。有细密入理之分析,而无偏执排他之独断,洵为通达之论。由此可见,好的通识著作给予读者的不仅是常识,更应是富有玄心洞见的高卓之识。关于书名,刘强亦从容与余嘉锡等名家商榷,又引申马森观点而立论,有驳有立,此正是其见功力、著精彩处。可以说,刘强此书并不回避难点,而是以充分之论断,为研读者梳理研究现状,带领其快速进入《世说新语》研究前沿,并以细密之新论引其深入思考,标示未来可思考、可挖掘之处,真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致。
专题二重点揭示《世说新语》的编撰艺术,颇富创见地指出,《世说新语》貌似无序排列,实则具有纲举目张的整体结构和相对一致的文体风格;更重要的是,其编撰意旨乃“以‘人的发现与探索、展示与描述、追问与反思、精神观照与哲学思辨为其根本旨归”,概言之,“《世说新语》就是一部以人为本的‘人之书”(第48页)。在对其编撰意旨有了准确明晰的把握后,再从孔子的“四科”“三品”、刘邵《人物志》“十二材”以及汉代的选官制度进行追本溯源,并巧妙引用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的名言“人是分类的动物”,自然而然地得出“《世说新语》自‘德行至‘仇隙的三十六个门类,可以看作是‘人的分类学”(第55页)的结论。当我们以为至此已无剩义时,作者又做了精彩的推论:
《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类,不仅具有“分类学”的价值,成为后世类书仿效的典范,而且还有“人才学”甚至“人类学”的价值,它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物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也浓缩了那个时代对于“人”或者说“人性”的全新审美认知和价值判断。《世说新语》的这一体例创变,在我国人物美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可说是划时代的,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理解的宽泛和深入。(第56页)
引申推导,启人良多,颇有往复论难、辩才无碍之风。
在谈及具体的编撰结构时,刘强将其概括为双结构(隐在结构+显在结构)、双维度(历史维度+文学维度)、一网(人物关系网)、故事链(同类故事前后相连,以达“形散而神不散”之效果)、大观视角(全景式鸟瞰+微观透视)、“留白”法。基于这些因素,刘强引导读者应从“浅表式”阅读进入“沉浸式”阅读,以得其三昧。本书的着力点正在于此,即引导读者由浅入深,给读者宏通、融通、通达之识,这对时下的大学通识教育课多善于传播“常识”而乏于传导“通识”之做法是一种纠正与示范。笔者身处大学,不乏听到教授们对时下通识课面面俱到而处处不深的忧虑之声。真正的通识课(包括面向社会大众的具有普及性的通识著作)理应超于常识之上,而能以深入研究之后所得之新识给人启发,这就需要著者既要有前沿问题意识,更要有真知灼见。
专题三深入揭示《世说新语》的思想内核,刘强以魏晋清谈为中心来剖析此内核。先从清议与清谈的“话术”转换来揭示时代背景的巨变与魏晋士人言说方式的调整之间的微妙联系。再从名教与自然的现实角力来勾勒清谈的三大发展阶段以及世道人心的幽微变化,精辟地指出:“‘名教出于自然是以道解儒,于调和中见紧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近道远儒,于偏激中显对立;‘名教同于自然则是弥合儒、道,于‘辨异中致‘玄同。”(第110页)从而得出“在‘名教与‘自然的思想博弈或者说儒、道两家的现实角力中,一直是此消彼长,相反相成的,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边倒的局面(至少在魏晋时是如此)”的结论(第111页),令人叹服。复从几场著名的清谈盛宴来展示清谈的话题及主客双方的风采,点评解析精妙,颇多画龙点睛之语,使何晏、王弼、乐广、王衍、王导、殷浩、支遁、许询、谢安、孙盛等人的清谈,传神写照,如在目前。行笔至此,几乎都是对清谈正面的解析与称赏。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对于盛行一时的“清谈误国”论,既指出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理路,又引谢安反诘王羲之的名言“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来剖析“清谈误国”论的简单化倾向,旗帜鲜明地指出:“清谈绝不是亡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能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腐败、国家沦陷的替罪羊。”(第134页)同时又引章太炎、刘师培、容肇祖、陈寅恪等学者的观点,以现代眼光来为魏晋清谈做了有力有理有据的学术辩护,并在总结中做了更全面的评价和更深刻的思考(参见第140—141页),直揭“清谈误国”论简单化倾向下的遮蔽之处: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以为清谈导致亡国甚至亡天下,不仅过分高估了清谈的破坏力,而且也容易避重就轻,转移焦点,以至于如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门阀政治的任人唯亲、国家决策的重大失误等这些更为重要的原因,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忽略了。(第141页)
如此思考和评价,有胆有识,揭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自然超越了以往的时代局限之论。读至此,真有惊心动魄之感。
专题四致力于阐释《世说新语》所包孕的精神气度,作者立足现代,从文化与人性的视角对魏晋风度做了深刻的审视与精彩的界定:
所谓魏晋风度,是指汉末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体说就是在道家学说和玄学清谈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种追求自然(与名教相对)、追求自我(与外物相对)、追求自由(与约束相对)的时代风气,以及由此在上层贵族阶层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风神与气度。(第143页)
限于篇幅,作者重点拈出魏晋风度的七个侧面(容止、服药、饮酒、任诞、雅量、隐逸、艺术)来具体解析其动人之处,其评析可谓“稳准狠”,“拳拳到肉”。如在容止之风中指出:“到了魏晋,随着人物品藻逐渐由重德行向重才性发展,人物天生的禀赋如容貌、音声、风神、气度、才情等更受重视,容止的要求则更偏重在‘容上了——这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潮是合拍的”,“毫不夸张地说,魏晋就是一个‘好色胜过‘好德的时代;尤其是,魏晋还是一个对男性美的欣赏超过女性美的时代。”(第145页)进而指出:“对人物容仪的欣赏在美学上必然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人的对象化和客观化;再往前一步,就是人的自然化”,“这种人的自然化对文学、艺术的赏鉴和审美影响深远。”(第152页)如在雅量之风中指出:“雅量的彰显,常常是在生死攸关的噩耗、猝不及防的危险和无从逃避的死亡到来之际——作为人生这部大戏的主角,事先你并不知道剧情,因而无从预演和彩排,更无法回放、修补和推倒重来。在对雅量的把握中,‘神气‘神色‘神意‘神宇是最重要的观察对象,而保持不变则是雅量的首要标准。雅量的完成过程,靠的是内在定力的坚韧和人格精神的稳定,任何外力的援助和观众的配合皆告无效,所以一出手就胜负立判,转瞬间便定案千古。”(第197页)再如,在隐逸之风中指出:“可以说,魏晋隐逸之风如果没有陶渊明出来‘收拾‘蹈厉一番,怕真要漫漶支离,‘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陶渊明《杂诗》其五)了。唐宋以后,‘儒隐之风日益流行,绝不是偶然的。正如饮酒和任诞一样,这又是陶渊明超越时代、‘高于晋宋人物的地方。”(第220页)复如,在艺术之风中指出:“魏晋之时,‘艺术的‘匠气似乎已被‘文气和‘灵气所取代,艺术家开始成为辨识度较高的一类人,从士大夫、文人、学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单独被欣赏、被推重的一种文化人了。”(第226页)以上引申、推论、研判,颇具只眼,真善于读书得间。这种提纲挈领、直指本质的解析是需要学养与识见支撑的。
专题五则从学术建构的角度,对“世说学”四大系统、四段分期、七个分支进行了要言不烦的简介与勾勒,并指出未来至少还可在版本研究与域外传播研究方面有所开拓,以突破研究进入“深水区”后的“瓶颈”挑战。因作者已有《世说学引论》《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三部论著的支撑,此部分颇有高屋建瓴、指点方向之势。
需要指出的是,刘强新著在吸收前辈学人解读意见的基础上,展开更深的思考,从容提出自己的体悟,竭力“再往深里看”,这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学术担当。如在解读王子猷雪夜访戴时,先引证骆玉明先生《世说新语精读》和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的相关观点,进而指出:“这固然不失为一种解读的角度,但如果再往深里看,此时的王子猷分明已从世俗的‘有待和‘我执中抽身出来,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逍遥游,其灵魂深处所经历的,是一种摆落‘意必固我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自由——这是一种长期沐浴遨游于审美人生和艺术精神中才能获得的高峰体验。因为处于这种精神的峰极上,对于此时此刻的王子猷来说,不仅过程和结果都已不再重要,甚至连‘吾本乘兴而行的‘兴,也如列子‘御风而行的‘风一样,成了大可弃之如敝屣的牵累!”(第188—189页)此处所论恰如本书前《编者的话》所言:“经典常读常新,一代有一代的思想,一代有一代的解读。”信然!
正如刘强在《一部伟大的书可以怎样读》中所体会的,《世说新语》是一部“灵性之书”“人性之书”“诗性之书”。因之,其解读之文也应是灵性之文、性情之文、诗意之文,如此庶几与之相配。记得十五年前,胡晓明先生曾为刘强《世说新语今读》写了这样一段推荐语:
写好《世说》,需有才、情、气。历来求解人不易。刘强君即是上佳的解人。他将《世说》看作灵性之书、人性之书、诗性之书,一路写来,逸气飞扬,无拘无束,得其灵性之精妙,大处用心,深切细微,更得其人性之美好,而满纸春意,又深得江南三月草长莺飞之诗意也。
以此衡之,十五年后,新著《世说新语通识》的文字更得灵性之精妙、人性之美好、诗性之雅致,兼得哲理之深刻,更加耐读。于刘强而言,学问之境,自是日进无疆。于读者而言,则是愉悦敬服的阅读体验。谓予不信,随意摘引几段以作例证:
我以为,这个故事(即“看杀卫玠”)的营造恰恰迎合了时代的审美需要:一个人因为美貌竟会被“看杀”,这种极端化的叙事本身也是极端化的抒情,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描述这一时代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狂热氛围。而这一切,又正好配合着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战乱和死亡如影随形的阴郁背景,就像废墟中开出的一朵鲜花,光彩夺目,尽态极妍,充满了凄婉烂漫的审美意蕴和感伤情调。(第155页)
在王子猷身上,最能体现晋人弥合分际、玄同彼我、超越一切的玄学人格。他对竹子的喜爱,不是对象化的,而是物我合一式的,“何可一日无此君”,正是长期与竹子厮守晤对,“相看两不厌”的审美境界的写照。(第184页)
不拘于礼,不滞于物,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这是何等襟怀洒脱、令人神往的审美人生!晋人的风流之美,浓缩于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常故事中,常常让拘囿于世俗矩矱之中的我们惊呼错愕,怅然若失。(第185页)
王子猷“造门不前而返”的那一刻,足可令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和文人墨客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至少在那一刻,王子猷达到了近乎“无待”的自由。当然,这一刻转瞬即逝,紧接着,凌空飞升的他便不得不收摄身心,拾阶而下,乘舟而返,回到那亘古不变的庸常里去了。(第189页)
酒助诗兴,诗以酒成,在陶渊明这里,诗与酒皆成“自娱”之具,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澄明浃洽之境。这样的诗酒人生,既不负“即时一杯酒”,又成就“生前身后名”,酒的烈性被诗的高雅归化,带给人的是与物无伤而又一往情深的真醇与静穆、闲适与欢乐。《庄子·天道》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应该就是这种境界吧。(第191页)
刘强以富有灵性、诗意、哲理的美文为主色调,又时以当下的词汇,以风趣出之,竟别有一种韵味。如“刘伶的外形与精深发差极大,‘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这在崇尚容止之美的魏晋属于标准的‘废柴;但他偏偏‘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似乎竟是一个精神上的‘巨无霸”(第172页)。“废柴”“巨无霸”放在此处,风趣传神,毫无违和感,作者写至此,读者读至此,想必俱莞尔一笑也。
在我看来,刘强之所以胜任《世说新语》的解读,除了其二十余年长期浸淫其中,对《世说》“可谓一往有深情”(《任诞》第42条),故钻研日深,颇得三昧外,更与其贯通儒道佛思想、出入文史哲学科教研(观其论著、授课及指导的博士论文即可知)所形成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素养有关,还与其服膺儒家守中达权的淑世情怀、交游广泛,且深察世道人心的阅历、饮酒赋诗以文会友的雅好、真诚洒脱的个性以及儒雅清通的气度有关。换言之,《世说新语》的上佳研究者,当浸淫既久,沾溉益深,久必与之俱化,融合为一,恰如庄周与蝶,不可分也。
《世说新语通识》封面印有“通魏晋文化,识名士风流”十字,我想这既是本书的主旨与亮点所在,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共同期待。一本优秀的通识著作,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常识,更是传递一种文化精神,昭示一种人格气度,强化对经典的高度、深度、温度的切实感受。借用《世说新语》名言,以收束本文,兼以共勉——“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