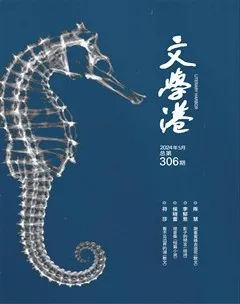归宿
2024-06-15邱引
邱引
喝酒会喝死,这一点我绝对没想到。去酒吧上班的那天晚上,我化了妆,本来我不喜欢涂眼影的,但好几天了,我睡眠不足,黑眼圈儿和熊猫似的。我化妆的时候,同居舍友李雯在哼唱林忆莲的歌儿。再过几天,林忆莲要来鹊城开演唱会。万一林忆莲想找个歌迷唱两句,万一林忆莲选中的歌迷是李雯,而李雯在那么多人面前唱砸了,肯定有损鹊城的形象。李雯那几天有空就练歌,嗓子都哑了。我涂好了眼影,抹上了蓝色的口红,一边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一边问李雯,要不要去酒吧喝两杯。李雯说不去了,她要好好练歌,过几天她要和我去看林忆莲的演唱会。我出门时,李雯没忘了嘱咐我,尽量少喝点。
那天晚上,酒吧里格外热闹。有个富二代过生日,酒吧里的酒水他全包了。来喝酒的都很亢奋,敞开了肚子喝,毕竟机会难得,和中彩票差不多。我陪几个广东佬喝酒,他们个头都不高,肚子也不大,甚至有几分清秀,但他们就是喝不醉。我们先玩了个“海上升明月”的游戏,酒杯倒满,再打一个鸡蛋,蛋清和白酒如海水,蛋黄如明月,看上去很雅致,其实很坑人,酒喝起来没那么呛了,觉得白酒不过如此,但一连喝几杯,头就晕了。我溜到卫生间,抠了喉咙,吐了一地,回来继续喝。几个广东佬又和我玩“深水炸弹”,啤酒杯里放白酒,两轮下来,我扛不住了,肚子里火烧一样,脑袋感觉比篮球还大。我平常不这样,应该是那几个广东佬在我酒里动了手脚。我又跑到卫生间,手指伸进喉咙,这一次我没吐,倒把嗓子捅破了,鲜血从嘴角流出来。我只能先喝几口水,漱漱口。地上有一摊水渍,我没注意,脚下一滑,摔倒了,脑袋磕到了地上。我觉得脑袋嗡嗡直响,一根因为饮酒过度熬夜伤神而处于崩溃边缘的血管就等这一刻了,它连声招呼也不打,崩了。
酒吧里还是那么热闹,没有人知道我出事了。我躺在冰冷的地面上,陷入了昏迷。如果这时候有人打急救电话,我或许还有救。一个女同事进了卫生间,她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喝多睡着了,洗了把脸,她出去了。此后,陆续有人进来,她们都没管我,只有一个和我有过节的女同事踢了我两脚,骂我狐狸精,她补了补妆,穿着兔子制服的屁股一扭一扭的,留给我一个销魂的背影。我想大声呼喊,救救我啊,喉咙像被人卡住了,发不出一丝声响。我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看见一大片草原,很多只羊低头啃草,没有一只抬头看我一眼。我的身体慢慢变凉,血从我颅底骨折处流了出来。直到酒吧打烊,领班问同事们我去哪儿了,有个同事说我在卫生间睡大觉呢。领班火了,他冲进女卫生间,揪住我的耳朵,想把我提起来。这时候的酒吧很安静,所以他的尖叫声就很瘆人,同事们跑过来,她们看见领班的手上沾满了血,不停地抖。
没救了,医生说。医生早知道我没救了,但各项检查一项也没落,血常规、肝肾功能、头颅核磁、胸片、心电图,做完检查,医生给我开了颅,这时候我的瞳孔已经放大,医生叹息着把我的脑袋缝上了。我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身上还带着难闻的酒气。李雯放声大哭,她年龄小,还从未见过一个活生生的人说死就死了。领班忙着给医生解释,他说我是喝酒喝死的,酒吧一点儿责任也没有。李雯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她说我死了,让我父亲赶快来鹊城。父亲是在房顶接的电话,他的脚下是一片晒得金黄的红薯干。李雯的声音清晰地传进父亲的耳朵,他的头顶上是蓝色的天空,一群大雁喊叫着向南方飞去。听到我猝死的噩耗,父亲异常的冷静,他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父亲从房顶上下来,梯子年久失修,他的脚踩到梯子上,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父亲挎着黑色的皮包,在村头拦了一辆货车,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闭上了眼睛。我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他瞧不上我的职业,陪男人喝酒,这与那些卖笑的女人有何区别?父亲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我偶尔回家,他也不正眼看我。父亲坐在货车上,一脸的平静。货车司机问父亲,进城干啥?父亲说,接孩子回家。我和父亲三个月没见了,上一次见面还是我奶奶过生日,他亲自下厨,做了两桌子菜。在酒席上,父亲除了祝福我奶奶,没怎么说话。饭吃得差不多了,我去上厕所,撒完尿从厕所出来,父亲在厕所外面抽烟,他看着院子里的石榴树说,王家庄有个修车的小伙子,人不错,你去相相吧。这么多年来,父亲对我的终身大事不管不问,他冷不丁让我去相亲,我一时不知道说啥好。我瞅了瞅父亲,他鬓角的白头发更多了。我说,好的,我去。我当然没去,我去王家庄赶了个大集,买了两斤莲子,回到了鹊城。没想到我和父亲再一次见面,竟然天人永隔。他掀起我身上的白布,看了看我的脸,然后又把白布盖上了。医院的工作人员问父亲,要不要联系殡仪馆,父亲说,先不用了,家里人还没见见她呢。
父亲雇了一辆车,他抱着我,一步一步走出了医院。父亲常年抽烟,他身上有一股烟味儿。以前我总是闻不惯他身上的味道,而现在,我的魂魄飘在空中,贪婪地呼吸着他的味道。我死去已有一天了,身体变冷变硬,有好几次,父亲就要抱不住我了,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手上再加把劲儿。有好心人想帮忙,父亲都拒绝了。他脸上的汗珠落下来,滴到我的头发上。父亲雇的是一辆面包车,他顺平我的身体,我的脑袋枕在他的大腿上,他搂着我的肩膀。别人看上去,以为我睡着了。
我奶奶和妈妈在村口等候多时,车还没停稳,她们哭喊着跑过来,司机赶紧刹住车。我奶奶不相信我已经死了,她摸着我的脸,喊着我的小名,一口老痰憋在嗓子眼儿,差点背过气去。我妈红肿着眼,一滴泪也流不出来,她在我的大腿上掐了一把,我当然没反应。小时候我惹她生气,她就掐我的大腿,疼得我龇牙咧嘴。这时候我妈确信我已经死了,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边说边骂,埋怨我不听她的话,不好好找份工作,非要去陪酒。在父亲的指引下,司机开着车,往我家走。路两旁站着不少人,他们叽叽喳喳,说啥的都有。我活着的时候,没几个人注意我,死了却享受到夹道欢迎的待遇。
面包车停在了我家门口,我家的黄狗摇着尾巴,冲司机狂吼。父亲给了黄狗一脚,黄狗钻进狗窝,瞪着小眼睛,看着父亲把我从车上背下来。一张灵床停放在屋子中央,我躺在了床上。舒服。我小时候睡过土炕,上高中睡过铁板床,住酒店睡过席梦思,哪张床都没有灵床舒服。我四仰八叉地躺着,奶奶把我的胳膊腿归拢好,她倒了盆温水,蘸湿了毛巾,脱下我的衣服,给我擦身体。我身上有了尸斑,她怎么擦,那些尸斑也擦不掉。她急得哭了,又不敢用太大劲儿,好像生怕弄疼我。我妈从衣橱了找出了一件旗袍,奶奶说,穿旗袍不合适,露着大腿呢。我妈说,她就喜欢穿这件旗袍,过年还偷着穿呢。还是我妈懂我,我买的衣服可不少了,我最喜欢的还是旗袍,我的腰细,腿长,只有旗袍能放大我的身材优势。
我叔是我们村的村主任,负责我们村的红白事,他指挥着几个男人扎灵棚。狗窝旁边有一堆高粱秆,正好派上用场。扎灵棚的男人嘴闲不住,争论我是怎么死的。长红鼻子的男人说我被入室抢劫了,舍财不舍命,让歹徒掐死了。秃头的男人说我给一个大款当小三,被大款的老婆找人活活打死了。灵棚扎好了,烧水做饭的锅台也盘好了,院子里人来人往,很热闹。我叔和我父亲商量,是不是雇草台班子,念念经,吹吹唢呐。父亲说不用了,他去了村委会,拿了一个大喇叭,再打开我的手机,循环播放林忆莲的歌儿。父亲对我叔说,孩子好听这一口儿。
临近中午,大锅菜做好了,白菜猪肉粉条丸子乱炖,香气扑鼻。我就爱吃大锅菜,谁家有红白事我都往近前凑,目的就是混一碗大锅菜吃。乡亲们端着菜,啃着馒头,吃得很香,我真羡慕他们。一会儿的工夫,一大锅菜见了底儿,锅里只剩下几片白菜。一个老女人摇着轮椅,进了院子,她谁也不搭理,来到锅台前,眼巴巴地瞅着锅里仅剩的一点油水。父亲赶紧把锅里的剩菜盛到碗里,又从笼屉里拿了个馒头,递到老女人手里。老女人真饿了,她一口下去,馒头少了一半,她张开还剩几颗牙的嘴,白菜汤喝得哧溜作响。这个女人叫张翠兰,是我们村的低保户,她年轻时是民办教师,长得漂亮,给她说媒的不少,可她谁也看不上,别人说她太挑剔,她说她长得好看,又有文化,就该找个好人家嫁了。张翠兰的梦想是找个好人家嫁了,可惜她一辈子心愿未了。当了几年民办教师,转不了正,她辞了职去了广州。几年后,她衣锦还乡,穿着超短裙,戴着墨镜,胳膊上挎着名牌包。乡亲们问她,是不是找到好人家了,她用粤语说梗系啦,当然啦。后来她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乡,知情人说她在广州给大老板当小三。她的名声坏了,找婆家更难,有些人拿她开涮,见到她就问她,张翠兰,找到好人家了吗?张翠兰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志向却很坚定。前几年我在镇上见到她,她在卖糖葫芦,我和她聊了几句,她嘱咐我,千万别将就,一定要找个好人家嫁了。
张翠兰吃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看样子没吃饱,她伸长了脖子,看看锅里,锅底还有半碗汤。父亲从厨房里抓了半碗肉丸子,放塑料袋里,给了张翠兰,让她拿回家吃。张翠兰说,谢谢,谢谢。她是我们村唯一用普通话说谢谢的人。张翠兰摇着轮椅走了,去年她摔了一跤,髋骨骨折,做了手术,余生只能坐轮椅了。她刚才吃得不少,人却没有力气,轮椅走得蜗牛一样慢。她的脸焦黄,推几下轮椅就咳嗽几声。我叔对我父亲说,老婆子没几天活头了。父亲说,咋不送养老院?我叔说,送了,待了两天就回来了,她嫌那些老头老太太脏,没文化。
吃过了午饭,乡亲们回家午休了。父亲坐在灵棚里,看着我的遗像出神。我很少照相,父亲在我手机里扒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张。他只好找出我的大学毕业照,送到镇上的照相馆,请人翻修,放大,做成了遗像。毕业照上的我也没化妆,咧着嘴傻笑,一副对生活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的遗像上落了点灰尘,父亲用袖子擦了擦。不知道父亲想起了啥事儿,他落下泪来。父亲正难过,从门外走进来一个男人,五六十岁的样子,白白胖胖的,留着背头。来人父亲认识,是父亲在镇棉纺厂上班时的厂长,此人姓付,别人喊他付厂长,他不乐意,他说他明明是正厂长,怎么就成了副的。他让别人喊他厂长,不要带姓。父亲说,厂长,你来了。付厂长悲伤地点点头,握住了父亲的手说,节哀。付厂长随了五百块的份子钱,父亲说,太多了。付厂长说,不多。
父亲给付厂长点上一根烟,付厂长问父亲,孩子怎么回事?父亲说,陪客人喝酒,喝多了。付厂长说,索赔啊。父亲说,孩子签了合同,喝酒出了人命,不管。付厂长说,就让闺女一个人走?父亲说,那还能咋样?付厂长说,配个阴婚吧。父亲说,也想过,没有合适的人家。付厂长说,我家明明走了两年了,你应该知道。父亲说,知道。父亲明白付厂长的意思,他想让他的儿子和我配成一对儿。付厂长的儿子很有出息,官至副处,两年前跳了楼,检察院从他家里找出几千万现金,这事儿鹊城人都知道。父亲说,我和孩子她妈商量商量。付厂长不乐意了,他说,还商量啥?我儿子配不上你闺女?付厂长退休好几年了,说话还是那么霸道。父亲说,是我闺女配不上你儿子,你找别人吧。父亲的口气很硬,他头一次和付厂长针尖对麦芒地说话,付厂长面子上挂不住,他笑着说,行,行,你和弟妹商量商量,这种大事儿必须商量。
付厂长走了,我妈说,刚才来的人是付厂长吧?父亲说,是,来配阴亲的。我妈说,咱闺女可不能嫁给他儿子,贪污犯。父亲说,不能。我妈叹了口气说,现在活人找对象不容易,死了的也难,马家庄的一个傻闺女,好几家抢,听说有户人家出了二十万。父亲说,柳堡去年是不是死了个小伙子?干水电的。我妈说,是啊,电死的,那小伙子不行,是个哑巴,咱闺女要是嫁给他,在那边连个说话的也没有。父亲叹口气说,那算了。
天蒙蒙亮,乡亲们都过来帮忙。放羊的老刘跑到我叔跟前,他说,不好了,不好了。我叔问,啥事?老刘说,张翠兰死了。我叔吐掉了烟蒂,问老刘,真的假的?老刘说,我今早上给张翠兰送了碗面条,看见她嘴里含着一颗肉丸子,我叫她名字,她没反应,我摸了摸她的手,冰凉,半夜的时候可能就死了。老刘一边说,一边哭。村里人都知道,老刘从年轻的时候就暗恋张翠兰,张翠兰一心想找个好人家嫁了,老刘家里穷,张翠兰看不上老刘。我叔一皱眉头,他招呼几个男人,赶紧去张翠兰家,给她处理后事。
吃过了早饭,陆续有人来吊唁。来的大多是亲戚,哭几声,放下份子钱就走了。这几年,亲戚之间走动越来越少,只有红白事,亲戚们才冒头,即使来了,也不是心甘情愿,之前有人情往来,不掏份子钱不合适。我的同学没有一个来的,可能不知道我死了,或许知道,也不来,毕竟我身份低微,不愿意和我有瓜葛。李雯来的时候,提着几个火龙果,我最爱吃的水果就是火龙果,她把火龙果和林忆莲演唱会的门票放在我的遗像前。我和李雯合租了一套两居室,她在一家奶茶店上班,每天用各种高科技勾兑奶茶,看着少男少女们喝她做的奶茶,她就觉得自己作了孽。她心眼好,哭得稀里哗啦。父亲留她吃饭,她摆摆手,哭着走了。
我的命的确是老余救的,如果不是他当年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我妈肚子里了。老余在我们镇的棉纺厂当过厂医,我父亲那时候是厂里的维修工,他经常偏头疼,少不了去找老余开药。一来二去,俩人就熟了,老余没事就来找我父亲喝酒,下棋。我妈那时候已经怀上了我,她挺着大肚子,给我父亲和老余炒下酒菜。眼看我妈就要生了,父亲想把我妈送到医院。我奶奶不干,她是我们那儿有名的接生婆,她不只是给人接生,马啊牛啊她也管,从未失过手。我奶奶训斥了我父亲一顿,把我妈送医院就是瞧不起她的接生水平。我父亲不敢忤逆我奶奶,只好让我妈待在家里养胎。我妈分娩那天出了事,难产,疼得我妈就要昏过去了。我奶奶傻眼了,她一手的血,没办法,只会念阿弥陀佛。再送医院也来不及了,我父亲一下子想到了老余,棉纺厂曾经有个女工早产,是老余给她接生的。父亲给老余打了电话,老余来了先洗了手,然后对我父亲说,得罪了。半个小时后,我父亲在屋外听见了我嘹亮的啼哭。
老余有恩于我,我父亲也知道。但老余要结阴亲,父亲不大愿意。外面下起了小雪,地面湿了。我叔拍打着头上的雪花,走进了院子,他让枣树下闲聊的几个人快去帮忙,张翠兰的坟还没挖好呢,雪说不定就下大了。这时候父亲暗淡的目光一下子亮了,不知道他想到了啥,他拍了一下桌子,对老余说,就这么定了,明天来迎亲吧。父亲突然就同意了,老余高兴得腮帮子直哆嗦,他说,好的,好的,场面一定排场。
天还没亮,十几辆豪车在我家门口一字排开,锣鼓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几个扭秧歌的老太太脸上涂着胭脂,挥舞着手里的扇子。乡亲们都来看热闹,有个大娘说我命好,死了去那边享福了。父亲换上了笔挺的中山装,胸前挂着大红花,我妈挽着我父亲的胳膊,她化了妆,脸上的脂粉盖住了黑眼圈。鞭炮声响起,老余乐呵呵地捂住了耳朵。父亲抱着骨灰盒,踩着满地的纸屑,上了一辆豪车。
两天后的深夜,父亲摸黑起了床。他进了西厢房,打开柜子,从里面取出我的骨灰。一只半夜觅食的老鼠窥破了父亲的秘密,它看见我父亲用包袱将我的骨灰包裹了,挎在了肩膀上。我家的黄狗听见了父亲的脚步声,它刚想叫几声,父亲跺了跺脚,它立即不吱声了。父亲骑着电动车,出了家门。在村头的大槐树下,我叔扛着铁锹,等我父亲。他们往东走,过了一座小桥,来到了一片白杨林。树木之间是一个个的坟头,李伟的父亲坐在李伟的坟墓旁,看见我父亲和我叔,他扔掉了手里的烟头。一具漆黑的棺材躺在坟底,里面是李伟的骨灰。李伟的父亲打开棺材,我父亲把我的骨灰和李伟的骨灰放在一起。棺材盖合上,三个人都不说话,往坟墓里填土。半个小时后,墓地里添了一座新坟。他们三个坐在坟前歇息,李伟的父亲说,过几年,给俩孩子树块碑。父亲说,老余还不知道,我给他的骨灰是张翠兰的,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我叔笑着说,张翠兰这辈子就想找个好人家嫁了,她的心愿终于达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