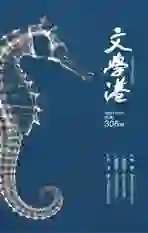访谈: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
2024-06-15
朱夏楠:李老师好。你出生在余姚,那里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记是什么?
李郁葱: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是他个人的财富,就像是一个百宝囊,当我每一次把手伸进去翻捡时,不会知道最终呈现在面前的是什么:它是暗中的源泉。很多时候,我藏在那里。这两年,我写过一本关于童年的散文《童年的月亮》,这里不妨摘录几段:
“老家说起来就在四明山下,但其实对于四明山,我基本上是陌生的,更多的印象来自于书本。孩童时,有过去山上的经历,但记得不特别清楚,四明山对孩子而言,过于广阔了,像老家,说是属于四明山区,如果站在村里,是不会感觉到处于山地的,而只有身处宽阔平原的感觉。
……
余姚人文荟萃,最知名的人物有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等诸先贤,在我少年离开老家时,从感知和内心而言,他们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只是一些名字,像是曾经在土地上吹过的风,当你想抓住它时却无影无踪;又像是我们在田野中漫步时,隔着远远近近的庄稼,远远地看到那些面容模糊的人,依稀是认识的,又觉得非常遥远和淡漠。
随着年岁的消磨,这些名字却变得熟悉和亲切起来,每每提起,往往有与有荣焉之感,而这种感受,让你对他们的旧事生出去探究的兴趣。这可能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在根深蒂固的意识里,我们的身体里装着一个给你有归属感的地址。我们把这称为乡愁,就像是时间里的一滴泪凝结成了琥珀。他们带给我们的影响却是一生的,在暗中滋润着你……”
有着地方属性的童年游戏,萦绕于耳便觉得亲切的乡音,在风中传播的乡间故事,以及,一个又瘦小又倔强又无比偏执的孩子,爱着他的爷爷奶奶等,这些构成了我最早的朴素的世界观。
朱夏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诗歌的?
李郁葱:从时间上来说,大约是在1987年前后。我至今保留着当年一个女同学所抄写的一本笔记本诗集,偶尔整理杂物时翻到,忍不住会笑起来,不是笑话当年的幼稚,而是为当年的某种认真而笑。关于这本手抄诗集,没有更多可以生发的故事,就是正好座位相邻,因为写作者固有的炫耀心理,我每每向她展示我的作品,而她收集起来,之后交还给了我。如果没有这个笔记本,大概不会想到我还写过那么多青春期的呓语,以及,对人生空中楼阁般的描述,包括爱情。
那些都是写作者正常的练习阶段,有些人熬不过这个时期,或者走不出这个过程。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事例不胜枚数。但这个阶段的练习其实远远谈不上创作,最多可以把它称之为爱好,真正的写作是自觉的,有它自洽的内核和哲学。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带点谦逊又能够毫不羞愧地把自己称为写作者。
写作者和写作是两种概念,幸运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成为了一个写作者。
朱夏楠:这个笔记本诗集可谓是你诗歌练习阶段的具象化。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确立“写作者”身份,对你而言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李郁葱: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实际上也并不是很清晰,当然从许多年后的现在回头去看,其脉络还是非常清晰的。具体到我个人,自觉写作大抵是在1994年前后,尽管在这之前,在盲目投稿的情况下,一些重要的杂志,如《人民文学》《花城》《江南》等,因为机缘巧合,发表了我最初的一批诗作,并且得到了一些赞美。但回头去看,当时的诗作更多的是出于个体对文字的敏感,也就是凭借着写作者的天赋,它们处于一种蒙昧而自发的状态。这个时期的作品,后来结集了薄薄一册《岁月之光》,那里面有很多原生的东西,但大多数属于练习曲。
写作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慢慢教会你去观察世界,从某种角度去看,它带有一种矫正的功能。也就在那段时间里,对朦胧诗、第三代诗、欧美现代诗(主要是由查良铮、郑敏等翻译)的沉浸阅读让我对诗有了另外一种认识:它不完全由灵感所驱使,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门手艺,但这种写作虽然清晰,表达出来却不容易,它需要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
这个过程于我是漫长的修行,需要摒弃很多东西,像一位与我有知遇之恩的前辈(他从以麻袋装的自然来稿中挑出了我的诗,并以最快的速度给予大篇幅刊发)语重心长地写信告诫我,不能按照这样的路去写,要回到抒情的路子上去,我的禀赋在于抒情。我喏喏,但不知悔改,可能让他失望了,直到四五年后,他重新选载了我的小长诗《眼镜片的幻术》和另一首《和平时期的可乐》,但直到他驾鹤西去,我都没有问过他是否认可了我所选择的路。
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没有结集出版诗集,总是在犹犹豫豫中,但自身对写作的定义越发明确,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一时,彼一时》的2011年,我40岁,我觉得可以确立自己是一个写作者了:他需要时间的雕琢,并且需要自我的定位。
朱夏楠:有没有参加哪些诗歌社团?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李郁葱: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是多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啊,这主要是一种相互取暖的渴望。1988年前后,参加了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所办的青年诗社,当年那种对文学的热爱至今想起来历历在目,当年社员中的很多人如今还在写作,但大抵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写作之路。那时的交往,更多的是在交流中得到对外部世界的勘探:当时的交通,朋友间的联系,阅读的可能性等,与今天无法同日而语。从某种角度而言,诗社为我打开了当代诗歌的门,我知道了诗的丰富性。
20世纪90年代,诗歌社团风起云涌,呈现出一派繁杂和热闹。在稍后一点的时候,我加入了由韩高琦等人所创办的原则诗群,但开始并没有形成社团,只是几个有相似的诗学理念的朋友相互间的来往,并把各自的诗作打印交流。因为不在同一个城市,我们的交流更多的是通过书信和电话,从创作的角度而言,这种朋友间的鼓励和赞赏,有时候也会有意见相左时的争执,它坚定了我个人的一些诗学理念:无论如何,在一遍遍反复的思考和争辩中,我让自己水落石出。
近年,和杭州(也有外地)的朋友组了杭州诗院,更多的是一种雅集的形式,我们并没有统一的诗学观念和美学标准,相互间是一种促进和学习。
朱夏楠: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你影响最大的诗人有哪些?
李郁葱:这名单可以有足够的长,足以构成一本书。从谢灵运、李白、杜甫、王维到当代的北岛、张枣等,也可以从但丁、叶芝、艾略特、拉金、奥顿到布罗茨基、希尼、沃尔科特、米沃什、博纳富瓦、勃莱等,在不同的时期,我受惠于他们,从他们那里得到过启发。
但一直影响我的诗人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是美国的田园诗人弗罗斯特,有一段关于我个人对他诗歌阅读的轶事。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他那种略微显得平淡保守的风格抓住了我,而我当时醉心于所有的先锋艺术,醉心于各种炫技式的写作,我的这种阅读选择让当时的很多朋友感到困惑:你为什么会喜欢弗罗斯特?
我对弗罗斯特的阅读热情一直持续到现在,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即使经过翻译的过滤和消解,在他偏保守的语句中,依然充满着坚硬和澄澈的质地,这就像陶渊明的豁达和剔透,就像李白的豪迈与铿锵,就像杜甫的沉郁和热情……
在向这些巍峨的山峰借鉴或学习之时,我们需要做的也许是如何脱离他们的阴影:他们太强大了,以至于他们的声音统治了我们个人的,而学习最终的目的是,我可以找到有别于他们的自己的声音。
朱夏楠:很多人认为诗歌是不能够翻译的,对此你怎么看待?
李郁葱:并非如此。很多观念都是似是而非的,说诗是翻译中被渗漏了的那部分,这尽管很诗意,但并不是现实。在唐诗的巍峨高峰之后,宋人别出机杼,创作出了为后人称道的词,但宋人当时颇为迷茫,他们称词为诗之余,也就是诗所剩下的才是词。诗能否翻译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主要是看读者站在哪一个角度上。
就像当代汉诗的写作,常常会有人说翻译体,那么请问,什么叫翻译体?是文字不认识,还是不能理解诗句中的意思?我们总是急于去判断,去抢占话语权,这更多的是出于急功近利,不能沉潜下来去真正理解诗歌的本质。
好的翻译,比如我们所读到的汉译外国诗,那些能够打动我们的,能够一遍遍沉浸于其间的,这些诗,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之间并没有隔阂。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有些诗是不能翻译的,和有些诗不给人阅读是同样的道理:它们是作为文本的存在。
朱夏楠:诗歌在你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李郁葱:它几乎就是我的生活。这样说,也许有些夸张,充满了诗人修辞上的浮夸,毕竟,我还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在做。但事实上,经过三十多年的诗歌训练,无论自己愿不愿意承认,我对生活的看法,我的交际圈,我处事的方式,甚至我的思维方式等,都是被诗所修正过的。
这就像我的家,装修时,我和设计师说,客厅、书房,跃层上下凡是可能有空隙的地方都要装上书柜。设计师说,可以可以,但图纸出来后,我说不行。设计师是按照常规的观念去设计的,也许他多加了一些书柜,但完全不是我所期待的,于是我越俎代庖,让设计师按照我的思路重新出了一份图纸。
生活大概就是被装修的这房子,而诗歌是固执的主人。
朱夏楠:你对自己的创作有怎样的期许?
李郁葱:写作最初需要是热情,一种对语言的敏感和对世界探索的欲望,但能够支撑个人长久写作的,将是阅读和忍耐。有时候我们无法摆脱顾影自怜所带来的个人满足感:生活是一种伤害和修补,文字也是。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会同时活动着多重性格的彼此迥异的“人”,人性上的分离使得表现在肉身上时,所沉浸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像天空里的阳光和月光一样混淆融合。在它们的边缘,一个野心勃勃的幻想家创造出了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畏惧、紊乱、宁静、勇敢和日益磨损的爱所组成。
当写作跨度还不够长的时候,写出的诗常常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怀疑:我的诗,它能够代替我说话吗?但现在,当有着足够的宽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会发现,诗是一种启示和发现,它早于我们个人的智慧。而一个人写作的训练,如果他把写作当作一件自己的事业或工作去从事的时候,一般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自己技巧和言辞上的准备,而在剩余的时间里,他可以营造自己的世界。
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的奖励了。如果说到对自己的期许,或许是,当用文字说出自己所看见的世界,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认可它,如果这些文字能够让他们在这浮世中有所慰藉,那么我的写作就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