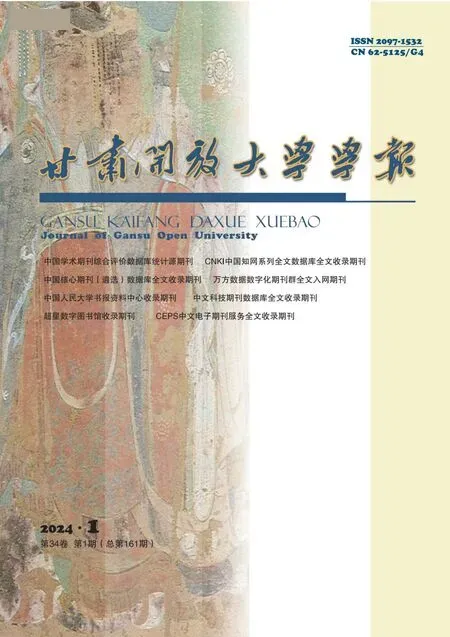苏幕遮兽面背后的西域神话
2024-05-27张同胜
张同胜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一、苏幕遮中的兽面究竟何谓
苏幕遮是粟特语smwtry’或sumdr 的音译,或者说是记音字,这个粟特语来自梵语samudra,翻译成汉语是“水神”之意。[1]婆罗遮、苏莫遮、悉磨遮、娑摩遮、飒麿遮、飒么遮、苏莫者、乞寒胡戏、乞寒、泼寒胡、泼胡王乞寒戏、泼寒等都是对苏幕遮的不同记音或称谓。
苏幕遮的所指,今人多认为它是词牌名或曲名,或以为是胡人的娱乐或中亚的乞寒习俗,还有其它理解,如王明清认为它是“西域妇人帽”[2],杨慎认为苏幕遮即“舞回回”[3]3,葛晓音说它是印度北部的祭祀仪式[4]86-96,刘宗迪认为“所谓‘飒么遮’,当为‘塔穆兹’之音变”[5],……
笔者以为,苏幕遮就是水神节。祆历八月是水神之月,每月的十日是水神之日,故八月十日为粟特人的水神节。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国农历十一月份。苏幕遮水神节期间,西胡举行庆祝活动,包括交互泼水、载歌载舞、假面表演、女子摔跤、两队打斗等,展演的是水神与旱魃的鏖战,以此来祈雨。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6]224唐代和尚慧琳在《一切经音义》卷41 中云:“苏莫遮……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做种种面具形状。”[7]事物的本质是通过表象来把握的,就像狮皮、橄榄棒是赫拉克勒斯的标志性身份符号一样,我们可以依据苏幕遮表演中的狗头、猴面等兽面及其背后的仪式故事,探讨其神话的文化意义,或许能够通达苏幕遮事实的真相。
苏幕遮活动中胡人为什么戴“狗头、猴面”?葛晓音认为,狗头、猴面为男女歌舞者戴的假面;“狗和猴也都与湿婆和女神祭有关”,湿婆三面之恐怖相与不洁即狗相关,而杜尔迦女神庙又被称为猴庙;“或许也与十胜节还有纪念哈奴曼这类活动方式有关”[4]86-96。葛晓音的猜测有一定的道理,她关注到印度神猴大将哈奴曼;但是,其间动物、神祇及其表演活动之间的关系缺乏逻辑论证。例如,狗之不洁,此乃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而琐罗亚斯德教则不作如是观,在琐罗亚斯德教神话的叙述中狗是神圣的,因此湿婆恐怖相与狗有关系云云其实是后世很晚出的意识或观念。
苏幕遮在中国中古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土,主要表现为胡人乞寒的娱乐游戏,“裸体跳足”“挥水投泥”“亵比齐优”[8]3052。它在中亚、西亚是具有神话性质的水神节表演仪式,因此解读祈雨活动中的狗头、猴面等兽面之意义就应该从大西域神话本源故事中去探寻。
二、狗头:蒂什塔尔、阿娜希塔、得悉神
夜晚天宇中最明亮的那一颗星,就是天狼星。在波斯神话中,蒂什塔尔是天狼星的化身。天狼星是阿拉伯语,相当于英语中的Sirius。天狼星,波斯人称之为Tīr,Tishtar 或Tīshtrya,也就是说,蒂尔、蒂什塔尔、蒂什特丽亚、Sirius 都是天狼星的不同称谓。天狼星在波斯神话中为雨神。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人认为,天狼星能给大地带来雨水,驱除干旱。天狼星“蕴含着水种”,能够兴云致雨,从而被北非、西亚、中亚等地区的人们看作是“星辰雨水”之神。古埃及人每看到天狼星偕日升,就欢欣鼓舞,因为从此时起尼罗河河水开始上涨。在伊朗高原上,雨水极其重要,关乎农业的收成,从而蒂什塔尔又被看作收获之神。当地民众专门设立蒂尔甘节(Tiregan,又被译作特里甘节、星节)以祭拜她,祈求风调雨顺。在西亚的波斯神话里,雨神蒂什塔尔与旱魃阿普沙(又被称作阿普什)鏖战三天三夜,后在阿胡拉·马兹达的帮助下,借助于祭祀之力,最终战胜旱魃,带来降水。蒂什塔尔打败了旱魃,从而被波斯人视为所有妖魔鬼怪的克星,于是蒂什塔尔又成为其战神、战士之神、胜利之神。
水神阿娜希塔最早出现在古花剌子模地区的阿维斯塔语中,在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圣经《阿维斯塔》中被称作“阿雷德维·苏拉·阿娜希塔”(Aredvï-Süra-Anāhitā,Arədvī Sūrā Anāhitā),意为“纯洁而强大的河流”[9]106。古代波斯对阿娜希塔的颂歌称为《阿雷维德·苏拉·内亚耶什》。阿娜希塔是大地上所有江河的庇护神。
阿娜希塔在波斯语中为“纳希德”,意谓“金星”。金星是一位女神。在苏美尔神话中,娜娜是金星之神。伊南娜是性爱、丰产和战争女神。波斯帝国时期,波斯人将阿娜希塔与蒂什塔尔、娜娜等同起来[10]31。因而,“娜娜可以和伊南娜、伊什塔尔相联系,可以视为不同名称下的同一位神。”[11]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蒂什塔尔与中亚祆教胜利之神韦勒斯拉纳(又被称为得悉神、瓦赫拉姆或巴赫拉姆等)混同为一,它们都为张弓之武士形貌[12],因为它们毕竟都是战神。
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浣溪沙》,记载了胡人泼寒胡戏在中土的存在状态:“忽见山头水道烟。鸳鸯擐甲被金鞍。马上弯弓搭箭射,塞门看。为报乞寒王子大,胭脂山下战场宽。丈夫儿出来须努力,觅取策三边。”[13]其间的“弯弓搭箭”与上述蒂什塔尔、韦勒斯拉纳的武士形象完全一致,他们在战场上冲杀,表明苏幕遮表演确实呈现为“军阵势”“战争象”(吕元泰语)。
中亚是世界上波斯、印度、中国、突厥等多文明的交汇之地,文化接触频繁,从而当地的神祇具有古代印度、斯基泰、波斯甚至希腊、罗马神话影响的因素。当蒂什塔尔与韦勒斯拉纳接触并被混同之后,她们旁边还有一条猎狗。这是为什么呢?天狼星属于大犬座,它旁边就是小犬座,天狼星和小犬座形影不离,从而中亚壁画上的雨神、水神、战神,总是与狗相伴。二郎神的原型为得悉神,因而他总是与哮天犬相伴。
琐罗亚斯德教《创世纪》写道,犬是“从大熊座的北斗七星之处产生,融合了善端动物与人的优点,乃为保护善端动物而生”[14]。《闻迪达德》认为,如果没有家犬和牧羊犬就不会有家宅可言。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们死后,丧仪中必须举行犬视。如果丧葬仪式上不举行犬视,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琐罗亚斯德教从自身善、恶二元斗争的思想意识出发,将所有动物分为善与恶两大类。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视犬为神圣动物、至善的动物,认为犬可以作为神灵的助手驱逐恶魔、拯救人类灵魂;犬从午夜至清晨一直在巡视,能杀死一千种恶灵。它帮助斯罗什神抵抗谎言。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必须经过“裁判之桥”即钦瓦特桥,桥头有两只犬,帮助密特拉审判人的灵魂。
在波斯人的丧仪中,必须有四眼狗进行犬视,也只有四眼狗才有资格进行犬视。四眼狗要么为全身白毛,两只耳朵黄色;要么就是两只眼睛上面还有两撮毛。黄耳朵四眼犬或许是由于火的颜色为黄色,而琐罗亚斯德教崇奉火,波斯人又尚白,因此教徒们将黄耳朵白犬看作是神圣中的神圣。他们认为这一类四眼狗是大神亲自饲养的,用来保护初人,制止恶魔。
如前所述,在波斯神话中,雨神蒂什塔尔打败了旱魃阿普沙,兴云致雨,“疾风将云、雨和冰雹传送到七个国家的农田和村庄”[9]154。在印度神话中,因陀罗杀死了旱魔沃利特罗,解放了云牛,从而天空沛然降雨,因此因陀罗又被称为“播雨者”。而因陀罗身边总是伴有一条猎狗。蒂什塔尔与因陀罗是何其相似乃尔,或许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共享同一个雅利安人神话的缘故。
黎国韬认为,中国神话中的二郎神的原型为雨神蒂什塔尔,形象与维什帕卡完全一样。[15]侯会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二郎神的原型是雨神得悉神[16]。从星座来看,蒂什塔尔是大犬座,旁边就是小犬座。笔者认为,正因为蒂什塔尔与韦勒斯拉纳相混同,因此韦勒斯拉纳的身边也总是带着一条狗,从而二郎神身边总有一条狗,即哮天犬。此可作旁证。
三、猴面:维什帕卡、湿婆、伐由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中的猴子大将哈奴曼,其父为风神伐由(Vāyu),从而可推知古印度神话中风神形象之一应该是猴子。苏幕遮是伊朗神话中的水神节,因此苏幕遮中的猴面表征的就是伊朗人的风神维什帕卡。
琐罗亚斯德教并不以相说法,然而中亚的祆教可能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却是利用图像弘法。贵霜人的风神Wesho,其替身为印度的湿婆[17]。洪巴赫考察了粟特神祇中的印度因素,认为粟特人的察宛借鉴了印度三大神之一的梵天形象,而阿摩采取了印度的因陀罗造型,维希帕尔卡尔被刻画为印度的湿婆模样[18]。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粟特人的风神维什帕卡的形象与印度的湿婆形象相似,都是三头四臂,手执三叉戟,都是战神的形象。中亚地区是多族群文化的大熔炉,因此神祇的杂糅性非常突出。即以战神而言,就掺杂着西亚、南亚等地的神祇,从而得悉神与蒂什塔尔、维什帕卡、湿婆、因陀罗等都有着文化上的渗透和交融。然而,粟特人的风神维什帕卡为什么不采用印度人的风神伐由的形象呢?印伊神话是同源的,它们都是雅利安人神话的分支。
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湿婆,被佛教借入后成为护法,即摩醯首罗天。由于祆教在中土从不主动向教外人即非粟特人弘法,故古代中国人往往将其混同为佛教的摩醯首罗。韦述《两京新记》误以为胡祆祠里的胡天神就是摩醯首罗。由此可知,唐人韦述是祆教教外人士,也分不清摩醯首罗与湿婆、维什帕卡的区别,故将维什帕卡与摩醯首罗混为一谈。
Katsumi Tanabe 认为,贵霜王朝金币上的Ohdo 并非湿婆,而是风神伐由。[19]伊朗神话中的风神有两位,他们是伐由和伐多(Vāta)。贵霜王朝时期,风神与战神混同起来,后者形象的塑造采用的是伐由,而不是印度的湿婆或希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而伐由也是三头六臂,手持三叉戟,与韦勒斯拉纳的身体造型完全相同。
维什帕卡是风神,而刘海威认为:“Weshparkar 神在波斯历法中指代火星,正合火德星君的身份。”[20]波斯神话中的火神是阿扎尔,印度神话中的火神是阿耆尼,它们其实本来是同一位神祇,只不过读音不同而已。阿耆尼骑着山羊;一说他也与马有关[21]。维什帕卡之所以具有火神的身份,是由于风神、火神都是战神的缘故。
战神韦勒斯拉纳与湿婆身边往往有一头白牛所不同的是,它身边带着一条狗。从神祇伴随的动物来看,维什帕卡的形象应该与古印度神话中的风神伐由的形象相一致,即都是猴子的形象。风神也有可能是公绵羊、公山羊或公鹿的形象,古代雅利安人因为风之迅疾,故将其与上述动物长于奔跑在相似律上建立了关联。
苏幕遮本为粟特人水神节的祭神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表演风神、雨神,以及雨神与旱魃之间的战争。猴面表征的是风神,从而猴面出现在其间是必然的。苏幕遮的战争场面,见载于唐人吕元泰给皇帝的谏书中。《新唐书·吕元泰传》载大唐神龙二年(706年)吕元泰上疏议“泼寒胡戏”云:
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何必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22]
日本平安初期的《信西古乐图》,绘有苏莫者舞者。这个人戴着角状的兽面帽套,身上披着毛皮状蓑衣,貌似猴子。《龙鸣抄》卷下“苏莫者”条写道:“在(序乐)间歇的时候,一个金色猿猴样貌的(舞人)左手持拨登场。”[23]此处的金色猿猴样表演者,应该就是中亚苏幕遮中的“服狗头、猴面”之猴面,猴为金色猕猴,不是猿猴。印度恒河猴即猕猴,又被称作黄猴。日本保存了苏幕遮的某些样态。
林屋辰三郎在《天王寺舞乐的历史意义》中说:“苏莫者,《续古事谈》说:此舞除天王寺舞人之外不舞,是天王寺固有的舞踊。圣灵会上必定上演此舞。原来是中亚细亚胡人的音乐,装扮成金色猿猴的样子。用左手拿着拨子,披着黄色蓑衣上场。演出时,称为‘京不见御笛当役’的、在宫廷内看不见的一个笛人在舞台下吹笛。”[24]日本苏莫者中的金色猿猴或披着黄色蓑衣戴着猴面倒是保留了印度猕猴的形貌。此舞踊为天王寺所独有,也表明大西域神话的故事背景。
葛晓音认为,“飒磨遮真正的起源——湿婆教的杜尔加和卡利女神祭”[4]86-96。笔者不敢苟同,认为苏幕遮实乃雅利安人的水神节,表演的内容为雨神、风神与旱魃之间的斗争。其间的“猴面”表征的是风神伐由,粟特人风神维什帕卡的形象应该是取自风神伐由而不是湿婆,因为哈奴曼是神猴,他父亲是风神伐由,从而风神伐由的形貌肯定就是猴子的形象,至少是猴面。印度的Durgā音译为杜尔迦(又写作杜尔加、杜尔嘎、杜迦),意译为难近母,她是湿婆的妻子。她是复仇女神,生气时前额生出卡利女神,露出恐怖相,她最大的功绩是杀死了牛妖、罗刹,与罗摩、哈奴曼没有关联。这与苏幕遮的祈雨有何逻辑关系?杜尔迦与波斯人的雨神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她们都是女神。
四、其它兽面:马、羊、牛、驼、鹰等
如前所述,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苏幕遮中还有包括兽面在内的种种“面具”,但是没有一一列出,那么乞寒胡戏中的兽面还有哪些?这些兽面与鬼神以及种种面具,其背后所言说的就是水神节的神话故事。
祆教中的战神、胜利之神,就是圣火之神、火星神巴赫拉姆,他又是动物保护神,还是祆历11月和每月2 日的保护神。玛丽·博伊丝说:“他骑在马背上,形象高大威武,身边跟着两个身着白衣和绿衣的随从。”[25]
根据波斯《阿维斯塔》,巴赫拉姆有十种化身:一头公野猪、一头长有金角的公牛、一匹长有金耳和金蹄的白马、一匹发情的骆驼、一阵猛烈的狂风、一个十五岁的青春少年、一只韦勒斯拉纳鸟、一只尖角的野山羊、一只弯角的公绵羊和一个武装的战士。[26]雨神蒂什塔尔、水神阿娜希塔同时又是战神,因而苏幕遮即水神节的庆典活动中,这些动物在苏幕遮其间的表演我们也可以说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一)马
在雅利安人的神话中,马与河流、雨水之关系皆为密切。在波斯神话中,雨神蒂尔塔尔的形象就是一匹白马,江河女神阿娜希塔驾着四匹马。旱魃阿普什,它是一匹“秃耳朵、秃颈、秃尾巴的黑秃马”[9]152-153。白马与黑马在河边鏖战。最初,白马失利,这是神话中的一个母题,即初战失利。后来,白马借助于阿胡拉·马兹达的帮助,以及祭祀牺牲之力,最终战胜了黑马。
雨神与旱魃即白马与黑马的斗争,颜色成为伦理身份的表征,即白为善,黑为恶。在很多民族例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至今仍然以白色表征善,黑色表征恶。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马是雨神的化身,而黑马是旱魃的化身也就很好理解了。
《诸神颂·水神颂》写道:阿特宾之子法里东向阿娜希塔献祭“百匹马、千头牛和万只羊”[9]115,请求赐予他力量。《隋书·西域传》“曹国”条记载国内祭祀得悉神,“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27]。从中可以看出,西域人祭祀水神的规模之大。从西亚、中亚到中土,祈雨的仪式中所用万羊也就渊源有自。例如,中国古代巴蜀灌口地区每年祭祀雨神二郎神用羊四万口,也是源自西域。
据唐人记载,苏幕遮表演时“骏马胡服”,从而可知当时的苏幕遮表演中有骏马参与,那也可能不必采用马面之面具演出,而是西域胡人直接骑着马上场参加彼此的打斗。
苏幕遮传入中土后被禁断,潜入中国古代的祈雨风俗中,依然留有雨神与马之间的密切关联。例如,《龙城录》记载,赵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尊者,见于波面”;《常熟县志》写道:“会嘉州水涨,蜀人见雾中乘白马越流而过,乃(赵)昱也。”嘉州,亦称眉山、灌口,即今四川乐山地区。《新搜神记》则谓“后运饷者见(赵)昱乘白马……俨若平生焉”。如此等等,都是作为雨神的白马在中土祈雨风俗中的无意识表现。[28]
(二)羊
祆教圣火祭坛台座有长着翅膀的公羊座脚。Vāyu与rām,二者为一。《阿维斯塔》有一首诗歌是献给风神的,同时与Vāyu 并置的则是Rām,即公绵羊,也就是说祭司是将它们看作同一的,都是胜利之神的化身。《阿维斯塔》说,伐由“所向披靡”。巴赫拉姆的十大化身之一就是“一阵猛烈的风”或“一阵骤风”,从而伐由被认为是战神,身披金甲,乘坐着金车[10]80。
在《吠陀》和《阿维斯塔》中,伐多是具体有形的风神。因为风能够带来雨,“英勇的伐多”成为雨星神蒂什特丽亚等古伊朗神的助手,帮助他们散播云雨。印伊神话中的风神为伐由,它是“最迅捷的神”[10]79,因此古代雅利安人依据相似律和关联律而将它与公羊联系起来。伐由的颂神书为《哈曼颂》(RāmYast),人们音译Rām 为“哈曼”时就遮蔽了风与公绵羊之间的联系,从而不知所以然。其实,Rām即公绵羊,赞颂公绵羊就是赞美风神伐由。
既然风神是雨神的助手,风雨同行,它们是同一阵营。因陀罗是雷电雨神,被称为“摩录多护卫的大帅”,而摩录多是风神。同理,伐多与蒂什塔尔、维什帕卡与得悉神也是如影随形。它们又都是战神,由此可以想见,在水神节的表演中,风神是站在雨神这一边的,绝不可能是风神与雨神大战,其形象当为公羊的面具或猴面。从而观众所见,一定是猴面、羊面、狗头、鹰首等组成一个雨神阵营,与旱魃敌方(队伍由蛇、黑马、虾、蛙、鱼等组成)作战。
(三)牛
一说,苏幕遮是祭祀苏摩神。在雅利安人神话中,苏摩神常被看作是一头公牛,活动在象征着母牛的水中。苏摩Soma,与Haoma,Sauma 通用。印度神话中的苏摩,在伊朗神话里被称之为豪摩,其实是同一物或同一位神祇。乾达婆将苏摩送给了瓦切,瓦切是因陀罗众多妻子中的一个,即河流女神,被称作“母牛”。
在印度神话中,苏摩神是月神。在《吠陀》和梵书系统中,苏摩即月亮。在雅利安人神话里,月亮与牛存在着一种同一的关系,密特拉屠牛表征的是月亮的生殖功能,或曰公牛的角与月牙是相似律的逻辑。在婆罗门教神话中,苏摩汁即甘露(amr·ta),喝了之后可以长生久视,不再轮回。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写道:“母牛永远是幸福之根。……她们带给人类甘露这神奇的不死之药。她们也是甘露产生的源泉,因此广为三界所崇仰。”[29]
在印度神话里,苏摩又被当作一种神奇的饮料,因陀罗正是因为喝了苏摩才威力无比,杀死蛇妖弗栗多,破坏99 座城池,因而苏摩作为表征也被看作一个武士。苏幕遮表演中的武士是不是来自苏摩神话?或许是巴赫拉姆的化身之一“武装的战士”?在吠陀神话里,因陀罗是风暴之神、雷电雨神;在史诗里,他与雨神波阇尼耶相等同。他曾骑着赤兔马,身边有一条猎狗。后来,他的坐骑改为大白象。苏幕遮,即祭祀苏摩神,苏摩神如同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故而苏幕遮之酣歌醉舞与希腊的酒神节类同,怪不得粟特人在敦煌用酒祈雨。《安城祆咏》诗云:“朝夕酒如绳。”粟特人以酒祈雨,这很有特色。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波斯经历过希腊化阶段,从而波斯神话里留有希腊神话的影子。
美国学者沃森在《苏摩:不朽的神圣蘑菇》中认为,苏摩指的是嗑毒蘑菇“毒蝇伞菌”,吃了它之后就会产生如醉如仙的幻觉。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从明教教徒迷信吃“红蕈”可推知,红蕈即西域神话中的苏摩。于是,信徒将苏摩神圣化,称其是圣树、神圣的植物或神力,吃了它后迷幻如痴,集体狂欢,裸体敬神,相互泼水,以此祈雨,欢庆水神节。
苏摩常被看作是公牛,雅利安人喝牛尿,他们认为牛尿就是苏摩,尤其是如果牛吃了红蕈,人喝了其牛尿就会产生如醉如痴的状态,信徒们以为是通神了。优腾迦故事也表明,神灵的便溺就是不死甘露,也是苏摩,后演化成中国神话里的不死之药。雅利安人榨取苏摩汁的仪式很神圣,筛网象征着天空,汁液就是宝贵的雨水,于是苏摩成为“众水之主”[30]。而苏幕遮是雨神,从而牛,无论是公牛还是母牛的面具表演者,就都有可能出现在节庆的表演队伍之中。
蒂什塔尔每个月有三次化身:少年、公牛、白马,其中中旬的化身为公牛,《阿维斯塔》写道:蒂什塔尔在每月中旬的晚上化身为“一头金犄角的牛”[9]150,在星光中飞驰。这位雨神恩赐她的赞美者以“健壮的子孙”“强壮的牛群”和“矫健的马群”,从而可知教徒们对蒂什塔尔的内心期望。
退一步,假设西方学者所说的粟特风神的形象的确是吸收和借鉴了印度的湿婆形象,那么,湿婆的坐骑为一头大白牛,从而粟特风神随从的形象之面具的表现形式不排除也可能是牛头。从而可推知,苏幕遮活动中,种种兽面之中无论如何肯定就有牛头之面具。
山西介休祆神楼中即有牛灵头像。天水石棺床,其中编号为9的石屏风画像,就有从神牛口中不绝地淌出酒的图像。而牛出现在祆教神话及其物质性文化中,表明它在祆教中的重要性。得悉神的十大化身之一为牛,雨神蒂什塔尔的化身曾为金犄角之牛,从而牛头马面的面具极有可能出现在表演队伍中。
(四)骆驼
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主琐罗亚斯德,词义为“黄骆驼(或老骆驼)拥有者”[9]402。如前所述,琐罗亚斯德教将动物分为善的与恶的,至善的动物如狗、骆驼、马、牛等为信徒们所珍视。《阿维斯塔》极力赞美骆驼,认为骆驼是大神的奖赏:“阿胡拉,正确告诉我,我如何能获得你的公正命令的奖赏:十匹配上牡马的母马和骆驼。”[31]韦勒斯拉纳的化身之一就是精力充沛的公骆驼。
蒂什塔尔与阿普沙大战的时候,首次败北,于是向大神阿胡拉·马兹达求助,大神赐予她“十匹马、十只骆驼、十头牛、十座山和十条适于航行的大河之力”[9]152,经过艰难的苦战,终于战胜了旱魃。从中也可以看出,琐罗亚斯德教对骆驼的看重和珍视,祆教祭祀仪式中往往有骆驼。
祆教的火坛,便安放在骆驼塑像之上。这是因为,祆教教徒认为骆驼是至善之动物。海力波认为:“受婆罗门教与祆教影响,西域除神牛崇拜之外,尚有神马、神骆驼崇拜。”[32]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6]224走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他们要过大漠,一般需要骆驼;但从敦煌壁画来看,毛驴更多。
如果说苏幕遮表演的是雨神与旱魃的战争,那么得悉神的化身是都有可能出现在苏幕遮歌舞表演中的,如此一来,骆驼自然也在其中。
(五)鸟
韦勒斯拉纳鸟是巴赫拉姆的十大化身之一。斗战神的颂歌,有多节是赞颂韦勒斯拉纳鸟的,例如第19节写道,斗战神“化成一只Vareghna 鸟”向求救者飞来,它是飞得最快的鸟,身手矫捷,战斗力强。
玛丽·博伊丝是研究琐罗亚斯德教的著名学者,她在《拜火教研究经文史料》中,将Varaghna/Vareghna鸟翻译为鹰(hawk)。有人将Vareghna鸟翻译为渡鸦,有的译作乌鸦,王小甫认为:“将拜火教神话中斗战神的化身Vareghna鸟比定为隼雀从而与中国古代的鹖鸟勘同是非常合适的。”[33]
库车考古出土了一个7 世纪的佛舍利盒,上面绘有假面舞会:敲鼓的,吹号的,弹琴的,武士、鹰、猴子,以及诸色人物、动物的舞蹈者,或携手踏舞,或单人旋转,或双手鼓掌,表演内容极其丰富。程璐瑶在《〈苏幕遮〉研究》中提到唐代传至日本的苏莫者,其表演者的面具上有鹰图案的刺绣[34]。此处的鹰应该是韦勒斯拉纳鸟之一种表现形式,日本苏幕遮所保留的鹰冠面具表明博伊丝对Varaghna/Vareghna 的理解是正确的,或者说大多数人将其理解为鹰。
日本水原渭江认为《苏莫者》来源于中国,但是源头在西藏:
今天,在传到日本的乐曲——《苏莫遮(者)》中,类似山猿的猿神,头上就戴模仿鹰颈的鸟冠。着这种鸟冠仍然残存于西藏的太平乐的四人舞中。……这一西藏的舞蹈是先流传到了撒马尔干(康国)之后又传到长安的。[35]
从现存日本的苏幕遮表演道具来看,黄色的蓑衣表征着金色猕猴的皮毛,又可以防水;猴面、鹰冠则依然言说着风神与巴赫拉姆的鹰化身;笔者不认为苏幕遮始自西藏后传到康国,恰恰相反,藏戏中的鹰冠倒是极有可能从康国传入青藏高原的。也就是说,中亚的苏莫遮传入西藏、新疆,然后传入中土。
日本有一种名《乞寒》的戏剧,又名吉简、吉干、桔槔。日本人说它来自高丽乐,在相扑宴会上表演。双方各有蛙王一人,各带领随从十人相互攻击。由此可知,日本的乞寒,可能是苏幕遮由雨神与旱魃分别带领自己的人马对垒打斗本土化为蛙王互斗。苏幕遮在日本的表演,除却无力蛙,还有无力虾、无骨蚯蚓等,它们都属于龙族。
中国藏族认为:“龙神类的动物有鱼、蛇、螃蟹、青蛙、蝌蚪等。”[36]从而可知,蛙王的部属当包括上述动物,从而在苏幕遮的表演中它们的面具也就出现了。如果日本人也将青蛙视作“龙神类的动物”,那么日本的苏莫遮或乞寒就有可能来自藏族,而不是汉民族。这一假设如果成立,那么中亚的苏莫遮之域外传播的路径以及中国戏曲的源流就需要重新予以考量。
(六)龙
探讨一个文化事件,一般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作发生学的研究,也可以从后往前看,即做渊源学的考察。考镜源流,目的是为了把握其究竟为何物。从中国古代文献所留有的关于苏幕遮及其变异之后的民俗大致能够了解苏幕遮的本相。苏幕遮表演活动中有龙或“龙神类的动物”的兽面形象吗?
宋人张唐英《蜀梼杌》卷下记载:“(广政十五年)六月朔,宴,教坊排优作灌口神队,二龙战斗之象。须臾天地昏暗,大雨雹。”[37]从“须臾天地昏暗,大雨雹”可知,这种表演其实就是在祈雨。在苏幕遮中,旱魃阿普沙的形象是一匹黑马。然而,苏幕遮流传到中土后,马就演变为龙了。
在西域神话中,龙一般是恶的表征,它控制着水。在印度神话中,因陀罗杀死的弗栗多,就是禁锢云牛的巨蛇。在波斯神话中,龙也是恶兽。这与中国古人对龙的情感偏向截然不同。阿日达哈克是波斯神话中的蛇王,他有三个头、三张嘴、六只眼睛,是最凶残狡诈的恶魔。印伊神话中的蛇王就是我们说的龙王。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人表演的苏幕遮实乃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据上引《蜀梼杌》可知,苏幕遮表演仪式中雨神与旱魃的斗争,正是通过“二龙战斗之象”来展演的,从而苏幕遮的兽面中自然少不了龙的面具。
任半塘以为:“此戏当演灌口二郎神率天兵天将,收伏二龙,并穿插二龙之互斗。”[38]任半塘的理解,其实是不确切的,过于想当然,因为灌口神队的表演,其实是苏幕遮在中土的在地化。上述二龙战斗,其实就是苏幕遮中的白马、黑马之战在中土的变异。二郎神的原型是西域战神得悉神;二龙互斗,是两马鏖战的变相;从而教坊娼优所表演的,不是二龙被二郎神收服,而是二郎神帮助雨神之龙打败旱魃之龙。
苏幕遮中其他戴面具或不戴面具的参与人员,据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新疆昭怙厘佛寺发现的舍利盒上面的图像可知,载歌载舞的人们中还有年青的武士、将军、老者、鬼脸兽耳等,其中的将军、武士可能与战神有关,因为得悉神的化身中有十五岁英俊少年、全副武装的武士;而“兽面有鹰、猴、狗”[39]。笔者认为中土的苏幕遮应该还有虎,《柳塘词话》岭南竹枝词可以为证,词云“碧油油衣苏摩遮,盘旋岭南不采花。红豆乱糁去打鼓,少时聚头来抟虎”[3]3,虎可能也是苏幕遮在地化的结果。苏幕遮表演中还有女妖,《阿维斯塔》云:蒂什塔尔“与众女妖交手,大获全胜”[9]156。女神与女妖捉对儿厮打,或许裸体女子相扑即源自于此?……从而可知苏幕遮歌舞表演时似乎并没有规定必须有多少兽面、人面,只要是有雨神、风神、旱魃等面具穿戴者彼此能够相互战斗即可?在时间距离中,兽面舞容也多有所变异,例如日本的苏莫遮就已经不再见到“绣装帕额宝花冠”。而大唐及其羁縻之地则多见,因为花冠乃三大胜之一。
五、后生命:寒乞、相扑、祈雨、词牌等
苏幕遮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土,最初在宫廷内演出,后来成为街市上的公众表演,最后由于与汉民族的礼仪文化格格不入而在大唐开元元年被禁断。
南朝《宋书·后妃》记载,宋明宗曾经在宫里举办“外舍家寒乞”,妇女裸身露体,众人大笑,唯独王皇后以扇障面不看。今人或以为这不是乞寒胡戏。但是,从“外舍家寒乞”“裸妇人形体”云云来看,不排除它就是苏幕遮在中土的在地化。祆教反对苦行,规定教徒每天“三分之一是饮食、享乐和休息”。祆教提倡享受人生,节庆时“酣歌醉舞”;康国乞寒,“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40];况且,雨神乃女神,苏幕遮演出中有女妖,她们也“浑脱”;从上述引文可知,刘宋宫内“裸妇人形体”是苏幕遮的一部分表演。
《北周书》记载,北周大象元年(597 年)十二月,天元皇帝“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41]。此处文字直白,故后人无争议,皆认为是泼寒胡戏,于是学术界一般将中亚的苏莫遮之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定在北周大象元年。
《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十二月丁未,作泼寒胡戏。”[8]141“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己丑,御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8]149从而可知,在大唐开元元年敕令禁断之前,皇帝、皇室成员、官员多以观看泼寒胡戏为笑乐。
苏幕遮由于赤身裸体之表演与中土礼乐文化相冲突而被大唐朝廷所禁断,但是它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而是遁身于民间祈雨习俗、火神节、女子相扑等活动中,甚至经朝鲜半岛流传至日本。冀鲁豫火神节、四川和江淮地区的“雨戏”、地区小戏、勾栏瓦舍中的说唱、文人笔记中的志怪书写等都仍然能够见到苏幕遮的踪迹。
晚至北宋,似乎依然尚能见到苏幕遮表演的影子。司马光曾经给皇帝上书,请求停止裸体女子相扑。清代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九曾对此作过阐释,他说:“《司马温公集》有《请停裸体妇人相扑为戏劄子》,盖皇帝御宣德门,百戏之一也。此即唐人泼寒胡戏之遗意。”[42]俞樾此论,指出苏莫遮演变后的形式之一竟然是相扑。
域外文化的隐性影响,一般说来难以做精准的考索。但是,蛛丝马迹无论如何也透露了文化接触、文化融合的印痕。海力波关于苏幕遮的在地化指出,粟特祆教仪式的华夏化在唐前期为泼寒胡戏,中晚唐体现在《庐江民》对泼寒胡戏的变异描述中,到宋代成为“打野胡”,贵池的《舞回回》中仍有流风余韵。[43]此说很有道理,上述诸多现象仍然保留和言说着苏幕遮的后生命。
现在一提起“苏幕遮”,人们将其解释为曲名或词牌名。其实,它在中土经历了一段演变的过程。如上所述,最初它就是西域胡人欢庆水神节的泼寒胡戏,刘宋皇宫里、北周的宫廷里、日本的天王寺里都曾表演过苏幕遮。在大唐开元元年,苏幕遮表演中的不雅观由于与衣冠文化的道德教化相冲突而被朝廷禁止。于是,为了生存,它经中土汉民族礼仪文化的过滤,不再在公共场所裸体泼水打斗,潜入祈雨民俗,演变为音乐中诸如《娑摩诘》《感皇恩》《万宇清》等曲名。到了北宋,它就成为《苏幕遮》词牌名。宋代教坊演出、民间祈雨祭祀风俗中仍然留有苏幕遮的痕迹,如“二龙互斗”“两牛相斗”等二郎神故事就是力证。晚至《宋史》,人们误以为“妇人戴油帽”,便是苏幕遮。于是,中土的人们就不再见到“狗头、猴面”等种种兽面打斗了,偶尔所见,则是戴着衰老帽走街串巷的老胡。
六、结语
苏幕遮是雅利安人的水神节,从而其起源之诸说如“波斯说”“康国说”“龟兹说”“北印度说”等都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波斯人是雅利安人后裔,康国的粟特人是东部波斯人,龟兹人也属于雅利安人后裔,因而可以简要地说,苏幕遮起源于古代雅利安人的神话。
苏幕遮在西亚、中亚为祈雨而祭祀水神的仪式及其表演,后来在中亚地区演变为特里甘节。特里甘节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祈雨,二是比武。其实,比武也是为了祈雨,它不过是雨神与旱魃之间的战斗之仪式化表演罢了。它传播到西域、长安、太原后依然由胡人在水神节时表演。由于在农历11月份或12月份,从而被汉人称之为乞寒胡戏。在表演仪式中,展演的是雨神方与旱魃方的斗战,用油囊相互泼水,用银筒或鍮石筒“贮水激以相射”,“或持麿索搭钩,捉人为戏”,从而就出现了狗头、猴面、牛头、马面、狮子、鹰冠等西域神话中的多种兽面。面具是伦理身份的标志性表征,言说着雅利安人欢庆水神节时的神话意义。
从以上对苏幕遮兽面背后神话故事的考索,发现大西域的苏幕遮在与汉文化的接触和过滤之后,仅仅在词牌、曲名和祈雨习俗中留有遗痕,而其具体的表演则通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苏幕遮从中亚到中土,又到日本,在其文化旅行中经历了在地化以及表演仪式和文化意义的加减乘除,它体现了不同地域族群文化的反向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