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纪录片的审美流变与价值取向
2024-04-25李红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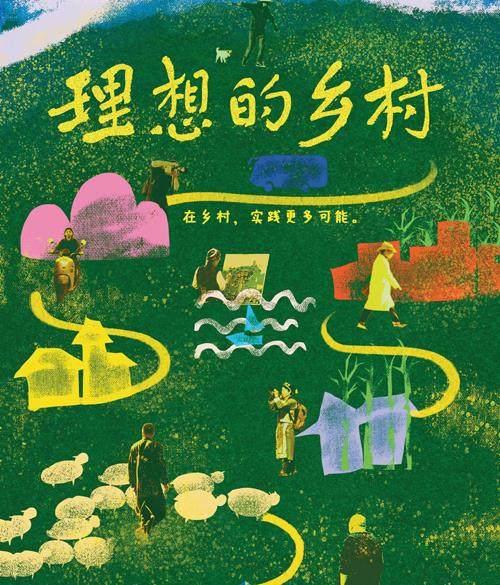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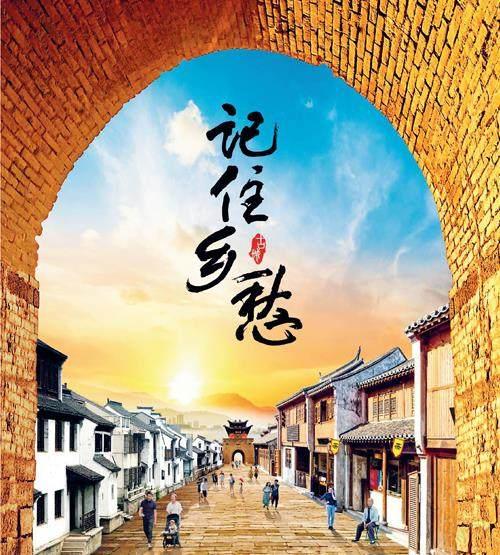
乡村兴则国家兴。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乡村振兴政策的衔接与落实已是一种必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由此可见,乡村振兴已是当今一项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而纪录片以其真实性的特质常常被视作一种时代与社会的镜像和表征。“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时代是纪录片创作的终身命题。”[2]以乡村振兴为题材的纪录片融合了文化消费与主体塑造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今时今日的纪录片不再单纯地仅仅专注于对于革命、阶级等话语的阐述,转而走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纪录片从宏观上又从属于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以国家体制为制作依凭、在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它们展示出引领社会风潮、塑造社会认知、整合社会文化乃至于服务于国家政策等多种多样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展现出符合时代发展话语的审美流变与价值取向。
一、审美流变:“参与式文化”下的多元化影像书写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审美的流变是伴随着媒介环境的特点而产生的。技术环境的变化与文化语境的变迁,媒介内容的受众不再是纯粹的消费者,而是产销合一的主体。在这种情形之下,受众不再甘于处于观看者的角色。他們更希望以某种方式介入到媒介内容之中,即亨利·詹金斯所言的“参与式文化”。这一概念源自詹金斯于1992年出版的著作《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其诞生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粉丝的集结和与之造成的文本重写现象。詹金斯将这种文化现象定义为“对普通民众参与障碍较低、艺术表达障碍较少、能够大力支持创作和分享、具有非正式执导、经验与知识传授的一种文化”[3]。用户不再只能观看节目,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传播甚至是节目的创作中去。
为了适应这一媒介环境的特点,乡村振兴纪录片积极地改良自身的创作范式,不再局限于宣传片式的内容模式,注重进行多元化的内容呈现与影像书写。例如,在《田园中国》①中,纪录片与真人秀的模式被结合到一起,场景的变动实质连通了观众与影像中的人物之间的心理空间,锻造了情感意义上的纽带。观众既获取了关于乡村的信息和知识,又以一种替代性的方式进入到想象中的乡土空间,对于影像文本的消费与生产同时存在;《了不起的村落》(黎振亚,2017-2019)②的主创团体则在社交媒体上创建了人格化的账号,通过定期与受众进行互动,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纪录片的观看从一项文化消费行为升华为维系情感的手段……在这些互动式、参与式、开放式的文本建构中,受众亦被转化为纪录片的推广主体。他们积极地在社交平台上转发、评论,最终形成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二次传播和破圈效应。基于此文化基底,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的审美流变从表现内容与表达形式等多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具有新时代新面貌的乡土美学。
(一)构建新时代乡土美学
在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中,乡土社会被赋予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建构。这种价值从本质上而言是对城市话语的解蔽。这类城市话语运用二元坐标式的思维,既将乡土定位为欠发达的落后地带,而这种观念也通过制度、媒体、教育等,对身在其中的人们进行规训,使其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观念,在经济上“城市化”的同时,也逐渐完成了思想上的“城市化”。[4]将乡土挤压至一个失语的位置,又从中汲取着文化资源,或者说,在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以乡愁抵抗城市生活所滋生的焦虑,以城市中心主义为透镜来审视乡村的言论,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已屡见不鲜。而在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中,乡土不再被固定地刻画为一个满溢怀旧气息,猎奇与落后并存的空间,地方性的生活、文化与历史亦摆脱了次要的地位。被“线性的进步主义观念”①所否认的乡土,在这些影像作品中得到了另一种形式上的承认。但与此同时,在承认传统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这些纪录片并不排斥发展的意义。新旧并存成为这一类纪录片中乡村风貌的关键词。
在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中,乡土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是不可缺少的叙事内容,同时它们被创作者们赋予了一种悠然恬淡的审美体验。不论是对于各种景观的展演,抑或是对于人物行动的描述,区别于城市生活的“慢”特质成为纪录片中的主要节奏。乡土的时间被赋予了奇妙的流速,乡土的空间亦承载着时间的厚度。例如,在聚焦“三农问题”的纪录片《瓜熟蒂落》(宋满潮,2021)②中,二十四节气作为轴线定义着影片时间的流动,三个情况各不相同的瓜农家庭随着时间的变动经历着各自的难题、困境与喜悦、幸福。作为一种民俗,二十四节气渗透着中国人关于土地与自然的思考和智慧。而当这种民俗文化被调用至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中时,一种别具一格的国家意志与人民生活的互动悄然达成。生产活动既依据着二十四节气的民间意义上的安排(清明种瓜,立夏卖瓜,立秋种辣椒),又被归纳至追寻小康、振兴乡土的宏伟蓝图当中。因此,在这种框架的表述下,乡村振兴既是自发的,又是自觉的,更是一种官方和民间的有序合谋。
然而,在《瓜熟蒂落》中,起到支撑作用的国家意志并未展现出强烈的在场感,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影片放弃了旁白解说的纪录片范式,并未一味专注于对政策的解读和阐释,反而是聚焦于个体的心理与活动:梁斌运用科技手段来促产增产;强强为了家长里短而颇费脑筋;满仓整日地奔波于乡野与办公室之间。占据叙事时间的是吃饭、闲谈、种植、商量、乡里人的生意经,详略得当的瓜农生活主导了纪录片的价值内核。于是,乡村振兴战略在影像的塑造中从一项国家层面的宏伟蓝图被转置为乡土住民们发自内心的殷切盼望。
与此同时,《瓜熟蒂落》在示意美好前景之外,还积极运用当地的文化资源,为重泉村予以审美维度上的建构。主创者们采用了对称的水平构图法来记录大棚内的成排的西瓜,绿意森森的西瓜在秦腔的配乐之下被塑造为一种近乎乡野器官的视觉符号。西瓜的藤恰恰又是家庭的隐喻。于是,围绕着西瓜这个关键的符号,《瓜熟蒂落》将发家致富的理想、乡村振兴的前途与合家团圆的愿景融合在一起。也正是在这种复合的、多维的叙事当中,乡土生活不再被视作城市生活的附庸。城乡所固有的中心边缘结构得到了颠覆。乡土的潜力与尊严都收获了承认。乡土被灌入全新的内涵,田园牧歌式的农耕传统与现代化意义上的发展合铸了新时代的乡土美学。
“情感具有社会功能,通过情感能够进行社会动员,调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共同完成社会任务。”[5]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提供关于乡村的种种话语,不论是想象中的返乡、对乡土发展的期望,抑或是对自然风貌的渴望、对农耕文化的向往……最终作用于受众的内心情感,并驱动他们主动参与到纪录片的协同传播过程中。而在这些行动当中,受众通过互动的仪式链条重新确认自我与他人的身份,并最终将这一身份归纳至国家话语的层面之中。
(二)在“逆向流动”中塑造乡土人物
塑造好典型人物是讲好时代故事的关键所在。对于当今时代的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来说,仅仅展现当地住民的人物形象是不够的,在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大策的背景之下,书写“逆向流动”的人群成为一项必要之举。2020年上映的电影《一点就到家》(许宏宇,2020)便做出了这样的示范。这部影片书写了三个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云南乡村创业种咖啡、开快递服务站的故事,成为了年度话题之作。他们不仅将大山里的云南咖啡带向全世界,还将网络购物这种便捷的生活方式带入村民们的生活中。影片在末尾汇集了对现实中离乡打工的年轻人的采访,一种浓烈的离乡之愁将文本与受众串联起来。近年来的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也采取了此做法,在微观之处见宏观,以一个个与乡村有关的年轻人的故事构建当代乡土故事。
在纪录片《理想的乡村》(张华/丁祥/杨骊珠/洪嘉宝/郝雨竹/王悦阳/艾琳/甘梅颖/陈亚女,2022)①中,人物成为叙事的线索与题眼。十个不同的人物指向十个不同的故事,最终融汇于乡村振兴的大命题之下。这些人物包括当地村民、返乡青年、志愿者、乡村医生、建筑师、艺术家。以先发带动后发的互助叙事既承认了在现代化潮流中遭遇发展危机的乡村不可忽视的地位,又彰显出独特的中国特色。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理想的乡村》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返乡话语。不同于城市生活所催生的怀旧式的乡愁情绪,在《理想的乡村》中,乡村被具象为一个切实的存在而非虚无缥缈的情感载体。自愿回乡创立图书室的吴利珠、致力于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的傅英斌、在艰苦中办学的更确木兰,这些人物在短小精悍的篇幅内被塑造成为一个个逆向流动的典范。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颇具奉献精神与人格魅力的人物的背后,存在的是一套中国关于乡村发展的本土经验。吴利珠、傅英斌等人并不是个例,他们的行动被统合在“共同富裕”的执政目标之下。人物回到乡村参与建设,助力乡村的振兴,更改了想象中的文化空间的位置關系,弥合了传统和现代、落后和发达之间断裂性的鸿沟,规避了现代化话语中线性进步主义的弊端,并再次肯定了基层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重要价值。
在纪录片《记住乡愁》(2015-2021)②中,人们的返乡则是受到了乡土底蕴的感召。《记住乡愁》的叙事线索在于对传统礼俗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的有机整合。乡村的传统在如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精神价值。返乡不仅是一种对于故乡经济意义上的助力与奉献,同时也是人物找到真我,收获慰藉的必要之举。在第一季第二集《孝道传家》中,本在上海从事厨师工作的舒志新在而立之年回到了家乡,他给出的原因是“家有老人”。“孝”作为一种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屏山村内成为了被广泛认可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又予以村民们安宁的精神境地。于是,经由这些典型人物的示范,乡村振兴题材类的纪录片讲述了双重形式的反哺:城市反哺乡村的经济,乡村反哺城市的精神。大众媒介视觉图景中城乡对立、乡村落后的刻板印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人物的逆向流动将大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乡村,“人往高处走”式的成功学叙事被“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这类更为平等的话语所取代。
在这样的媒体传播进程下,一方面重新唤起了从乡村走出的年轻人重回乡村寻找自身价值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对乡村特色的宣传吸引人们来到这里体验本地的风土民情。“乡村游”逐渐形成了近年来的旅游主题风潮,观众得以介入影像美学之中,并以自己的实际游历实践纪录片的表达,由此形成创作与受众的合流。这可称得上是阿诺德·贝林特所说的“使感知者与世界在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中结合在一起”[6]的美学,即在上文所述的参与式文化中,环境、纪录片与受众这三者不断轮换着“文本”与“传播者”的角色。纪录片不再只是风景宣传画,而是真实地走入了人们的生活中、记忆里,甚至引领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风潮。
二、价值取向:关注现实境况,梳理文化脉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提及乡村振兴战略时指出,乡村振兴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以及组织振兴。由此可见,文化振兴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而以乡村振兴为题材的纪录片恰好有着形塑乡村文化、提升乡村形象、培育乡村精神的种种功效。以乡村为创作意象,以乡村的发展为叙事脉络,以生活于乡村中的人物为叙事主体的纪录片一方面向社会大众传递乡村发展的境况,反映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落实情况,另一方面又为当代的乡村在文化生态中寻觅到一个位置,弘扬主流价值,讲好中国故事。
“剖析一部人文纪录片的价值要以历史和现状为前提,从文献历史、艺术审美、人文传播、社会影响、产业开掘五方面审视其综合价值。”[7]可见,在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中,价值取向的建构呈现出以下的特点: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统摄下,结合恋地情结、传统礼俗、人文风貌与经济发展等多重维度,并有意识地规避城市中心话语,因地制宜,将实际的乡土生活与他者化的“乡愁”式的乡土划清界线,以平易近人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方式,拉近乡村生活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并力图塑造广泛的传播效应,以纪录片的播出和放映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开展。下面笔者将结合具体的乡村振兴纪录片从乡土建设与乡土文化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聚焦乡土建设,关照发展进程
作为时代之镜,纪录片需要切实反映时代的变迁,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亦是如此。“乡村纪录片积极阐释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像阐释体系,担负着建构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使命。”[8]在这种时代语境之下,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积极地围绕乡村建设这件大事展开了影像叙事。在诸如《淘宝村》(焦波/李梦龙/孙超,2019)①《了不起的村落》等一系列纪录片中,各式各样的关于乡村如何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故事被囊括至影像当中。
以《淘宝村》为例,作为国内首部聚焦于乡村与电商的纪录片,以详实的细节记录了乡村住民在应对信息化浪潮和互联网时代的阵痛、迷茫、奮斗以及最终的收获。电子商务被嵌入乡村的经济生活当中,彰显出技术的普惠性,从而通过影像和事实否定了技术具有排他性的观念,又对抗着城市中心主义独占先进技术的话语。淘宝园区的创立又标志行政力量对资源的分配和调动,于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被整合进入公共行动之中。纪录片中所描述的一切都与数十年前乡镇基层信息网络的建立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乡村振兴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被界定为一项符合公共利益的集体主义战略。
可以说,对乡村建设的呈现是一种关于乡村现代化的另类经验的描述。它示范了路径、过程、困境以及结果,同时为大众关于乡村的想象破开了一个口子,使之能够容纳更多现代化的要素,使传统与现代不再是格格不入的,并构建了一种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内涵被广泛地扩充,要振兴乡村绝不能单纯地依靠老路子。此外,纪录片所挑选的事件和人物不仅是现实中乡土建设的参与者,同时亦被置于大众传媒的领域之内,被塑造为一种关于如何实现乡土发展的知识信使。这些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既为同处于乡村、渴望发展所在地的人群做出了良好的示范,又向社会大众展示了乡村发展的状况,甚至能够直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例如《花开河洲》①对村镇诗意化的影像书写直接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业走向昌盛,《舌尖上的中国》②背靠央视的权威性推动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在这种良好有序的互动之下,乡村振兴有别于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
我们发现,乡村振兴纪录片不仅仅可以反映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落实情况,同时推动着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纵观涉及乡村振兴题材的纪录片,大多数影片的创作方都属于官方组织。创作主体的身份赋予了这些纪录片极强的权威性,有助于树立品牌形象,建构社会大众的议程。作为压舱石、定盘星的主流媒体对乡村振兴纪录片的投入映证了其隶属于主流话语,并在国家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建构。乡村振兴被指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故事,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被勾勒为一个与所有国民息息相关的事件。对其重要性的确立有助于引发扳机效应,使乡村振兴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挖掘乡村文化标识,重构乡村空间概念
在当代大众媒介所提供的视觉图景中,城市往往占据着一个牢不可破的中心位置,而乡村则被不假思索地抛至边缘,并蒙上了一层猎奇的色彩。在这种由逐利的眼球经济逻辑驱动下,乡村被界定为一个文化与视觉上双重匮乏的空间,并与传承了数千年的关于乡村生活的诗词歌赋中的形象相去甚远,随之而来的便是乡村的失落,首先在社会的表征和想象的层面上被确定了下来。费孝通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9]这种文化自觉重在找回失落的乡村文化传统。尽管乡村确实面临着人口出走等种种困境,但仍在当代生态文化中不断转型以寻找适合自我的定位,它们所缺少的是一次在视觉文化图景中得到广泛展演的机会。纪录片《记住乡愁》就是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作品。
《记住乡愁》系列纪录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发起,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组织拍摄。作为一部从国家层面出发的纪录片,《记住乡愁》展现出独树一帜的关照视角与真诚态度。秉持着“一集一村落,一村一传奇”的创作方针,以丰富的细节联系了古与今、人与景。“所谓细节,就是构成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情景、自然景观的最小组成单位。”[10]青山绿水的乡野风光、古香古色的传统建筑、淳朴和睦的乡风民风,这些细节要素的提炼为乡村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
以第九季中的《黎寨稻香茶意浓》一集为例,影片以茶农们的具体生产活动为切入点,娓娓道来的旁白提纲挈领式地强调着纪录片的叙事线索:茶农们如何与土地互动,如何处理橡胶林的难题,又是如何地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乡村被勾勒为一个极具活力与生命力的生产空间。与此同时,传统的生活方式也焕发着勃勃的生机:黎族人一起进山狩猎,得到的猎物不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有一份。不论是采茶、晒谷子,还是进山捕猎,这些活动和行为只能够发生于黎寨,它们本身便构成了黎寨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记住乡愁》以一种官方媒介式的权威让这些活动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使生产活动成为黎镇日常的主轴,并凸显了生产活动本身的崇高价值。它以有力的姿态驳斥了消费语境中乡村文化的匮乏,佐证着乡土生活的底蕴及其丰富性。
在《记住乡愁》第一季中,“敬畏之心不可无”“孝道传家”“讲和修睦”等村镇主题将绵延了千年的中国礼俗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主题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既表述了“千村千面”的事实,又鲜明地指涉着乡村振兴的核心不只牵涉到经济层面,还理所当然地包括了人文层面。在这些颇具人文气息的叙事线索的指引下,乡土的精神空间得到了较好的阐释。而在影片外的舆论场中,人们对于乡村失落的概念恰恰起源于一系列乡村中道德文化沦丧的印象。因之,以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生命力,《记住乡愁》实现了对于乡土生活的价值再构。
纪录片对于乡村文化正好起到了一种促进和增补的作用。人乃是文化的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是中华民族在激荡的世界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所在。对于民俗接递的呈现,在影像的范畴内促进了文化自信的生发和乡村文化的振兴。
结语
乡村如何实现现代化,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更是世界上一切渴望发展的国家要处理的难题。以乡村振兴为题材的纪录片基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传统文化和自身国情,既表述了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向世界发出了中国之声,又号召人们将目光投向乡村,兼顾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我们必须讲好乡村振兴的故事,传播出乡村的好声音,才能让乡村振兴的步伐不断向前延伸、迈进。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河北慰问困难群众并考察扶貧开发工作[EB/OL].(2012-12-30)[2023-12-20].https://www.gov.cn/wszb/zhibo547/content_2314098.htm.
[2]陈红梅.描绘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的影像特色与价值表达[ J ].当代电视,2021(04):60-67.
[3]Henry Jenkins.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9:5-6.
[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修订译本)[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9.
[5]段峰峰,匡蓉.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的话语建构[ J ].中国电视,2023(03):73-77.
[6][美]阿诺德·贝林特.艺术与介入[M].李媛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
[7]赵月枝,龚伟亮.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 J ].当代传播,2016(03):51-55.
[8]刘忠波.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纪录片的文化使命和审美观照[ J ].中国电视,2020(07):6-11.
[9]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6:196.
[10]高鑫.电视艺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8.
【作者简介】 李红梅,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大学戏剧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影视艺术、融媒体教学研究。
①《田园中国》是中国首档乡村振兴融媒推介节目,2020年在山东卫视首播。由青年人组成的“田园推荐团”和由专家组成的调研团以找寻“幸福时刻”作为主线,将乡村振兴带来的人民幸福感作为表达的重心,以短视频为表现手段,深入当地生活,展示拍摄对象在乡村振兴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②互联网微纪录片《了不起的村落》以山乡奇景与东方文化为核心,存档东方100个村落,2017年第一季在今日头条、B站、腾讯视频等网站上线;2018年上线第二季;2019年上线第三季。
①这里区分“线性时间”和“进步主义”两个概念,对后者的批判往往是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认为,“时间”是上帝创造的,是属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恒定不变的。瓦尔特·本雅明认为,“进步主义”的流行依靠于“线性时间观”的奠定,他批判这种线性的进步观,认为在这种进步观的视野中,历史用“进步”的叙述话语来掩盖人类现实的苦难,从而造成人们对于苦难的漠视乃至遗忘。“这种观念不可否认的是对人类社会倒退的冷漠”。参见:[美]阿伦特编.《启迪: 本雅明文选》,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71页。
②《瓜熟蒂落》2021年9月25日在CCTV-17首播。
①《理想的乡村》2022年4月8日在CCTV-9首播。
②《记住乡愁》2015年1月1日在CCTV-4首播。
①《淘宝村》2019年7月26日在CCTV-9首播。
①《花开河洲》2021年8月10日在CCTV-1首播。
②《舌尖上的中国》2012年5月14日在CCTV-1首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