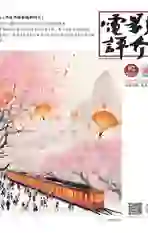现实抒写传统的缘起、置换与批判
2024-04-25张阳
张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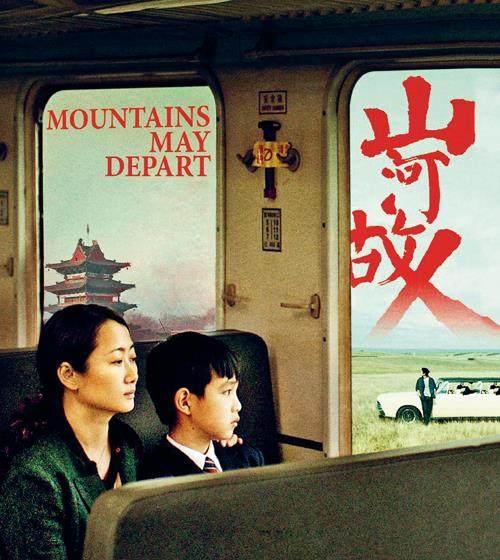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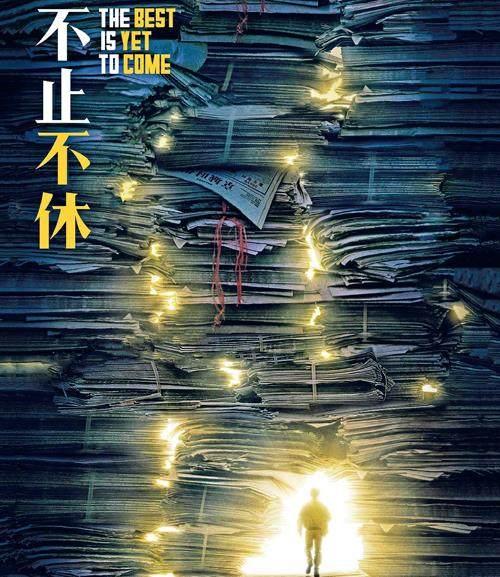
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在法国发端的文学艺术运动,这一运动以法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奥地利精神病理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为哲学理论基础,主张通过梦境、幻觉等“超现实”的方式,展现出超越现实的、真实的客观事实。超现实主义对传统艺术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于艺术的创作方式和目的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探索。因此,它也经常被简称为超现实主义运动,其影响深远,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一环。[1]超现实主义电影的表现手法与视听形式经常由于其“超越现实”的特性给予人深奥晦涩的印象。20世纪20年代,法国先锋派电影人士发现电影的照相本性和蒙太奇对列技巧使它成为超现实主义最理想的表现手段。[2]这一观点始终流行在反传统的影片制作者中间,产生了《贝壳和僧侣》(杜拉克,1928)、《一条安达鲁狗》(路易斯·布努艾尔,1928)、《黄金时代》(路易斯·布努艾尔,1930)等作品。这些超现实主义作品受到当时诸多先锋欧洲绘画流派的影响,呈现出由创作者梦境、潜意识、混乱状态而加工演绎而来的奇幻景象,在世界电影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中国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电影书写传统中,“超现实”的电影传统源于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迅速接纳并成功融合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经由“第五代”导演的系列实践进入电影中,在更多新生代导演的实践中与中国电影融合在一起,并朝着更为广阔的方向发展。
一、现实与超现实抒写传统的缘起
从早期秉执影戏观的早期社会派电影,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电影,再到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都是中国电影艺术家表达思考、为时代画像的主要方法。发轫于社会转型与思想转系之际的中国早期电影出于回应和反映现实的需要,形成并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电影美学传统,这一创作原则和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中依然成为发展的重要倾向。早期的中国电影作品如《难夫难妻》(张石川/郑正秋,1913)、《孤儿救祖记》(张石川,1923)、《玉梨魂》(张石川/徐琥,1924)、《姊妹花》(郑正秋,1934)等作品都默契地遵循一种从疏离现实、贴近现实到批判现实的发展路径。这些作品在展现社会现象和人物性格方面逐渐深入,逐渐在电影美学中融入关注现实社会的手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这部分影片往往在场景展示部分以远景和全景镜头方式向观众展现自然和现实主义画面,在高潮段落时则使用蒙太奇镜头唤起观众情绪,由冲突的画面(用爱森斯坦的术语说即“吸引力蒙太奇”[3],激发观影者的一种创造性反应,使他/她结合主人公的处境产生深刻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美学中的“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写实主义”,这一阶段的现实抒写传统基于“影戏观”产生,其重点与其说是再现现实本身,不如说是唤醒观众对“社会”及“历史”两个现实维度的关注,从而唤起观众的社会责任;导演抒写现实的手法也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战后现实主义等电影流派使用深焦镜头、长镜头有所不同。在关注中国早期影片对真实生活关注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这批“影戏”作品主题表达上的故事性、人物性格、情感表达等因素来更为深刻地理解电影的艺术表达。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思想艺术领域的开放,中国电影界重新认识到现实主义对于中国电影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期,电影作品如《小花》(张铮/黄健中,1979)、《生活的颤音》(滕文骥/吴天明,1979)、《苦恼人的笑》(杨延晋/邓一,1979)等开始结合蒙太奇手法与现实题材,回归早期中国电影中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传统。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學迅速接纳并成功融合以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典型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借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成功创作出许多中国式的魔幻小说,如莫言、贾平凹、张炜、陈忠实、扎西达娃、余华等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电影界也引发了改编热潮。例如,在改编自莫言同名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红高粱》(张艺谋,1988)中,影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高密东北高粱乡这一真实的时空基础上,通过极度夸张的手法将变形、极简、极繁、高对比度的事物呈现给观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张艺谋在影片中注入自己的主观情感,通过时空穿越的方式,将过去和未来几十年间大大小小十来个故事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不仅展现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也将这一带有风格演绎实践性质的现实主义“改写”代入电影中,在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上都对中国电影创作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21世纪后,第六代导演如贾樟柯等以“纪实主义”风格扛起现实主义电影的大旗,这些影片以平民化视角、真实社会场景和主人公的故事,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与此同时,他们又热衷于将意象做特异、不合逻辑的安排,以表现潜意识的种种状态,展现角色内心情绪或表达隐喻内容。例如《三峡好人》(贾樟柯,2006)讲述一男一女在三峡库区分别寻找自己的妻子和丈夫,故事本身是极为贴近现实的;但影片中却出现了地面上的建筑拔地而起飞向太空、天空中神秘的飞碟掠过、走钢丝的人游走在两栋废弃的大楼之间,圣人般凌驾于众人头顶上等“奇异”景象;《山河故人》(贾樟柯,2015)通过一场小城中的爱恋展现出中国几十年间的社会变迁与阶层生活,带着妻子与儿子到墨尔本生活的煤老板与生活困苦的矿工,互为“故人”。如果说《三峡好人》里一架突然冲天而去的宇宙飞船显得太过魔幻,而这部电影中沈涛去给梁子送请柬时,一架农用飞机莫名其妙地坠毁在沈涛面前,而后面镜头里同样的位置有一对母女在烧纸;扛着关刀行路的少年身后是10年后变成的青年,还有反复出现的《珍重》、一闪而过的新闻画面等细节丰富了观众感官体验,也令写实电影更加真实,允许观众们从各种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特异式的表现主义造型亮点是影片内在叙事性和艺术表现力的独创性合成,超级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中的特异式超现实主义造型,在风格异化中既突破现实主义又不排斥现实主义,是一种富有创新思维和革命精神的有限度的诗性自由。”[4]
二、“现实景象”与“虚构景观”在超现实影片中的置换
中国电影通过深入挖掘本土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不断改写现实的呈现方式,也在对单一“现实主义”的改写中不断创新和进步。近年来,不同类型的现实电影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手段,继续在“现实”和“超现实”的纠缠中不断提升自身质量和竞争力,将“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记忆、幻觉、想象等要素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以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展现出世界的另一层“本质”与“现实”。在这一过程中,真实与虚幻可能发生混乱、混淆甚至颠倒,但这也是超现实主义电影的意义之一——它启示观众通过想象不可见的神秘摆脱一切“现实”束缚,最真实地显示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
获2023年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的科幻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孔大山,2023)就在“科幻”的背景下展现出一个亦真亦幻的故事。影片主人公唐志军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执着地经营着宇宙探索杂志社。在影片的前半段,导演和编辑反复地强调编辑部众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唐志军心怀探索宇宙生命的理想,多年来始终坚信外星人的存在,过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生活;但严酷现实却经常提醒他生活的窘迫,编辑部甚至一度连暖气费、交通费与出差采编稿子的经费都凑不出。但在影片中部开始,摄影机画面开始在现实场景与虚幻的设想之间徘徊:在山中寻找信号源时,曾目击“外星人”的孙一通忽然消失,唐志军等人进入深山内一间废弃的石制品厂中,这里摆放着许多无人看管的石狮子和佛像。导演通过展示“神圣之物”的肖像渲染出神秘氛围。作为一部讲述落魄天文学者(或更多人眼中的“民科”)追寻外星生命为主要故事的“科幻片”,《宇宙探索编辑部》不仅展现出主人公试图以超验经验“超越”人生的尝试,更多则表明人类对现实的超越与对超现实的追求——一心执着于寻找外星生命的唐志军,其实也是一位背负丧女之痛的普通父亲,他终生未曾明白为何女儿会采用极端方式离自己而去,身为父亲的骄傲与失败令他无法面对这一问题,使得他在潜意识中将这一现实性问题置换为外星生命是否存在的问题;他“自欺欺人”地追寻着一个可以囊括宇宙万象的“终极解答”来为自己解开女儿离世的心结。随着谜团渐渐揭开,观众会发现该片在探索宇宙的外壳下其实包含着一个朴素至极的,甚至不包含戏剧性的现实故事,那就是唐志军如何面对并接受女儿的死亡,并在经受丧女之痛后继续生活。对于现实主义电影理论而言,关于“现实”的展现并非关于在场的,而恰恰是因为不在场的。在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看来,“肖像摄影”或一切看似写实之物都并不再现现实,它们的对象而是“幽灵般的影子”或“令人不安的在场”,而人们只能以“渐进线”的方式无限趋近于客观性[5]。
中国超现实主义电影中的超现实主义书写与西方电影不同,西方的超现实主义起源于诗性的文学与绘画艺术,崇尚以诗性、狂乱的思想和奇异的梦境;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首先是由诗歌形象最初的概念所支配的。超现实主义影片也将自身作为连接梦境与现实的隧道,让观众在放松的条件下能够获得某些启示,使人将现实中差别很大的理性与感性元素融合,由此重新认识世界。中国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则连接了现实与意识大胆的想象与对现实规则的悖反,它沿着现实主义电影的脉络一路发展而来,在将镜头当作现实的渐近线的同时,对超越现实的景象保持着独特的东方式理解。例如在《不止不休》(王晶,2023)中,韩东手中水笔的漂浮代表了他个人梦想的起飞;而电视中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是一个宏伟梦想的实现,影片的韩东看着电视屏幕中航天员的笔能摆脱引力自由漂浮,也想象着自己手中的笔能够摆脱沉重的现实引力,给人带去梦想、希望和力量。在电视荧幕内外、国家与个人的尺度上,导演试图把宏大的民族梦想和个体的梦想建立起一种对应的联系,表达一个国家需要宏大的理想,也需要每一个个体的理想;民族的进步与社会的前进,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个体努力实现梦想,去促进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好。影片站在2023年回望纸质媒体的黄金时代,画面中,2003年的一名刚转正的小记者的梦想与野心显得格外遥远而珍贵。在纪实与幻想的双重维度下,空间成为电影的第一主角。王晶用类似新闻采访实录的镜头语言、去故事化的叙事手法、慢节奏的场面调度构建了两个空间,在没有削减现实力度、也没有用力过猛的前提下成功完成一次对现实的表述。在沉重的“采访空间”和轻盈的“电视空间”中,记录类型与超现实风格等两种对现实的处理方式背后隐藏着对待世界的不同态度。在沉重与轻盈的对比中,为观众带来具有作者感和对比性的二向空间:沉重的一侧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受到真实歧视的状况,与记者为报道真相而面对的压力;轻盈的一侧则是逆境中新闻工作者演绎何为真正的新闻理想。“轻”“重”的结合体现了导演立足现实、脚踏实地、独树一帜的超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三、电影影像与语言表达的拓展与批判
电影语言的主要功能不是言说,而是呈现那些自己本身不能言说的事物。“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一种风格追求。它是一个灵魂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人性的问题。”[6]超现实电影中对无理性行为的真实性、梦境的重要意义、不协调的形象对列的情绪力量、对个人快感的强调与追求显现出另一种未曾被认识的“真实”的力量,而超现实主义电影则让观众以独特的视角感知它。在独树一帜的、对现实事物与人類思想感情的理解下,诸多魔幻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形式被分解和重新整合,这使得一个富有生趣的新世界的创造成为可能;而这种更带有创意性的行为本身也激发创造性的自觉探索,同样也批判性地促进电影艺术的发展。
电影不显现世界,但世界通过电影显现。电影影像所再现的现实事物以及再现它们的方式之后,必然存在着超越单纯视听范围的、更加宏大的象征性意义。例如受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电影《长江图》(杨超,2020),影片讲述了发生在长江上的两个时空交错的魔幻爱情故事,通过逆流而上的货运航程,将高淳和安陆的爱情故事融入到对历史英魂和长江文化的叙述中。影片的正序时间始于高淳黑鱼供父,他在长江入海口上海偶得一本诗集,又在江阴接货后开始了行程。但不知从何处开始,电影的现在时空开始慢慢地坍塌虚幻起来:高淳在长江图旅途中不断遇到一名叫安陆的女子,出现在各个码头的安陆年龄不同、身份未知、去向不明;高淳跟年轻船工发生冲突,而老船工又不知所踪。高淳和广德号逆流而上,而神秘的安陆沿江而下;没有出现的高淳父亲与没有点破的安陆父亲成为形式上的对位呼应,又仿佛神秘诗集的主人。这部电影打破了传统叙事逻辑,让观众在人物的交合与分离中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与人生的无常。长江上发生的故事有时候好像是真实的现在,有时候仿佛主观幻想,有时候俨然是对诗句的魔幻演绎。但就画面而言,看到的依然只是一艘货船在长江上飘荡,每当读完一首诗,广德号就在水雾氤氲的江上远行五百里。那些具有关联性的、更加宏大的象征意义,建立在对于影像创作的语境及认知用途的理解上。这些象征性表达必然依赖表达语境,即图像与外部文化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源于图像的独特性本身。
在《长江图》中,关于长江、自然与世界的叙述通过某种抵抗性表达与人们相遇,而这种表达不一定是这个世界的坚实肌体。电影不显现世界,但世界通过电影显现。图像的独特性指在视觉层面上,图像与主题之间存在着普遍性认知原则,这些认知原则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是相同的,它标示着日常视觉感知对此类事物的认识。导演杨超对此的解释是:“即使在西方,展现这种魔幻内核的故事时,也是要有相对应的物理提示的,比如,穿越时空的旋转门等等物理实体,让你知道到哪个点,我需要有一个准备,这里要魔幻了。但《长江图》则不然,它首先有一套自己完整的叙事逻辑,在这里魔幻即现实,这让电影很疯狂,也很傲娇,但恰好,我喜欢一切颠覆的东西。我要的是虚实相生的气质,实和虚之间做无缝连接的感觉。观众以为它是虚的时候,它就实了,当观众觉得它实了的时候,忽然又不可理解了。”[7]
电影影像表述的内容并非完全是关于在场的,而恰恰是因为不在场的,人们只能以“渐进线”的方式无限趋近于客观性。在现实主义电影观念看来,一切现实影像都并不再现其自身,它们的再现对象是幽灵般的影子与一切令人不安的不在场。如果要拍摄一部相关主题的具体影片,现实主义的常规做法是首先通过剧本的慢慢修改逐渐描绘出故事轮廓,特别是主要人物的形象,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会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中被体现出来;而中国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则并非如此。《宇宙探索编辑部》从一开始就隐藏了这一最“基础”的事实,让拍摄和剪辑过程一点点地为人物和故事赋予具体的视听形式,在超现实主题下以真实细节(20世纪90年代的老破小楼房、满口玄学的乡下骗子等)填充整个故事,在近乎“玄异”的高潮后又重新一点一点地拆出角色并重新分析,让一场关于人类终极命运与宇宙形式的奇旅最终落地;而《不止不休》以纪录片式的平拍摇摄配合中景构图,将个人与国家/社会两个层面的故事同时呈现在一个画框之中,在真实與幻想之间制造一种感官上的奇幻效果;但是这种奇幻又是真实存在的,呈现的就是2003年纸媒崛起期间最真实的社会生态,不由让人由衷地感怀那一批对自身与未来都充满自信与梦想的人,一个纸质媒体与新闻力量的黄金时代。这些电影图像的主要功能不是指向在某时某地明显可见的事物,而是意指其他缺席却“必然存在”的物体,高明的镜头会在画框内外构成一个意蕴丰富的影像世界。展望未来,中国电影需要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径。[8]这种现实主义必须立足于本土化和民族化,只有这样,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美学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道路。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观众需求变化,中国电影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以适应时代需求,继续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
结语
总之,中国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超现实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电影及其手法的影响密不可分。中国导演在借鉴世界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超现实主义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照搬,而是深刻地契合中国电影传统中原本根深蒂固的现实基因,以及一代代创作者突破乃至批判陈旧的电影观念、呼唤新风格、新美学的迫切需要。“虽然我们在创造图像时可以去描绘那些实际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的个体,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将之作为最终的目的。”[9]超现实主义电影固然“超越现实”,但其本质亦是源于现实。在商业发行的故事片领域,超现实主义并不构成独立流派,它的影响仅见于影片的个别镜头或段落。
参考文献:
[1][2]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107,5-6.
[3][苏联]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M].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15.
[4]王丽君.现实中的超现实——当代中国电影美术的表现主义活力[ J ].当代电影,2021(05):54-59.
[5][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焦雄屏,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10.
[6][英]布鲁诺·赛维.伊里奇·门德尔松[M].万书元,译.伦敦:建筑出版社,1982:164.
[7]黄亚利.艺术电影的诗性复归——以电影《八月》《路边野餐》《长江图》为例分析[ J ].传媒观察,2018(12):89-92.
[8]本刊编辑部.电影如何讲述历史[ J ].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2022(03):6-25.
[9][英]保罗·克劳瑟.视觉艺术的现象学[M].李牧,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29.
【作者简介】 张 阳,男,山东泰安人,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电影管理和版权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