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赋形、场景重塑与影像书写:抗美援朝题材网络电影的创新性探索
2024-04-25王义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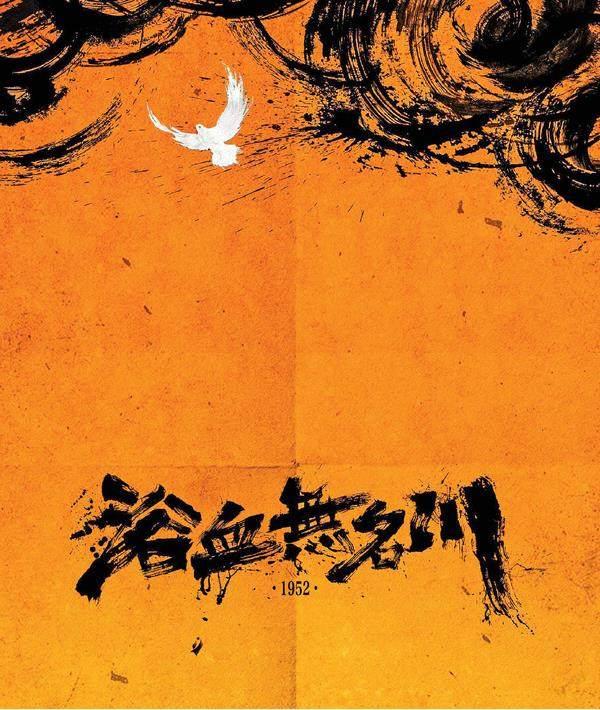
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际局势的深刻演变,塑造大国形象、提升民族自信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背景下,抗美援朝题材成为网络影视创作的焦点,其凝聚的国家属性与战争属性决定其在国家形象构建与民族认同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体的迅速崛起与网络受众规模的不断扩大,一系列聚焦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的抗美援朝题材网络电影如《浴血无名川》(翌翔,2021)、《血战狙击岭》(李志文,2021)、《特级英雄黄继光》(周润泽,2022)、《狙击英雄》(海涛,2022)、《浴血无名·奔袭》(翌翔,2023)等纷纷涌现。相较于同题材院线电影的宏观叙事与震撼影像,网络电影在叙事层面上,以成长型叙事模式展现抗美援朝精神的锻造历程,为志愿军战士的砥砺成长进行生命赋形;在场景塑造上,强调人与武器的相互作用及战术配合,呈现出以“人的力量”为本质的动作美学特质;在影像呈现方面,则通过将专业影感与游戏化网感相结合,创造了战争影像实践的新路径。总之,抗美援朝题材网络电影凭借其对网络媒介特性和受众审美偏好的敏锐把握,成功实现了对抗美援朝精神表达的创新性转化,深刻阐释了人民志愿军“为何而战”的核心意旨与“钢少气多”的精神优势,以“人民性”与“英雄性”的高度统一,进一步深化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情怀,呈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生命赋形:成长型叙事模式下的精神锻造与情感升华
抗美援朝题材院线电影通常借助革命叙事或伟人传记,将英雄个体的独特性与成长历程融入广阔的历史叙事之中。在这种叙事模式下,英雄人物常被呈现为“白璧无瑕”的理想化形象,体现为宏观群体式的英雄典范。这一趋势逐渐导致英雄形象标准化与典型化,削弱了观众对人物的认同感,同时也限制了观众对历史背景与叙事脉络的深入理解。因此,这些电影常显得意识形态输出过于单一,缺乏情感上的共鸣,进而与观众之间产生距离感。相对而言,网络电影通过聚焦人物的成长历程,将成长型叙事模式与实际战场情境相结合,赋予英雄属性多维度的解读空间与成长过程,致使人物形象在丰满的同時逐渐显现出英雄本色的最终特质,从而激发观众的共情效果,实现了对英雄主体的底层深描,并通过更深入的价值引导重新阐释了历史中的英雄瞬间。
(一)成长历程彰显信仰高度
“剧作家为人物编织的情节网要想发挥效用,就必须使人物在穿越每个情节链条的同时获得成长。”[1]抗美援朝题材网络电影在弱化宏观背景的情况下,以小人物的成长经历折射大时代的战争命题,聚焦英雄主体的个人叙事,深刻挖掘人物的内心困境与心理转变,描绘出个体在战场中的砥砺成长,彰显出精神信仰的感召与深层价值的引领。
一方面,网络电影赋予英雄人物个体化的欲望动因与行为驱动,使得英雄人物的形象跃出二维的历史书写,在影像中显现出更为饱满多元的人性轮廓。例如《狙击英雄》中的任东风加入“特射班”的目的是为班长报仇雪恨;《特级英雄黄继光》中青年黄继光参军入伍是为了成为战斗英雄;《浴血无名川》中的娃娃则梦想成为一名狙击神枪手。这种个体化、理想化的目标愿望与现实的战争环境形成强烈对比,个人与群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人物在军队体制中呈现轻微的分离以及有限的越轨,迷茫与困境成为其成长历程的转折点,缺陷的暴露反向构建了大众化语境中的平民英雄形象。与此同时,成长主题下的历史人物与当下青年实现了心理层面的连通,片中成长路径的曲折与压力有效贴合了青年观众的审美体验与生活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观众对片中人物因共同经验产生深刻共情之时,战场中血与火的残酷环境却压缩了片中英雄人物从“小人物”进化到“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在极限的生存选择中,他们往往能够快速走出成长痛苦,直面死亡恐惧。例如《狙击英雄》中的任东风因自己的鲁莽行为而暴露了坑道,报仇的冲动与自私的行为换来了更多的伤亡,也间接导致了战友王清的牺牲。在经历了血的教训后,任东风逐渐褪去了鲁莽的行事作风,树立了为民族存亡而战斗的人生信念。英雄人物的快速成长打破了观众在影片平民叙事基础上产生的共情节奏,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审美体验,此时,英雄人物的选择与他们身上的正义与完美更能打动观众,影片于无声中提升了观众的精神高度,起到了良好的艺术教育效果。
另一方面,网络电影对英雄行为的塑造与阐释,也呈现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差异化个人选择,这打破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中相对固定的英雄行为导向,“英勇牺牲”不再作为唯一的“高光时刻”,“智勇作战”与“人性光辉”成为英雄行为的别样标注。在《特级英雄黄继光》中,黄继光与肖登良发现前线部队正遭受猛烈攻击,人员伤亡惨重。在此种形势下,黄继光选择持枪加入战斗,而肖登良铭记自身任务,返回总部通报前线情况。战场的残酷性与特殊性赋予了人物极具本色的价值选择,展现了差异的性格特征与思考逻辑,但不同的选择路径最终汇聚为“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肖登良及时将情报传递给总部,完成了战术支援;黄继光加入战场,成功击退了敌人。电影中两人不同的价值选择,呈现出差异的成长路径,却共同指向更高的目标,完成“保家卫国”的使命任务。由此可见,电影中对英雄行为路径的差异化表达,将冲突情节场景演化为人物个性的延伸,使矛盾化解指向成长过程的主体逻辑,更加贴近战争现实的人性描摹。
(二)情念结构深化家国观念
抗美援朝题材网络电影将视角聚焦于个体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将亲人之爱贯穿于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之中,以微观且具体的情感视角赋予英雄更动人的亲情属性,使得英雄不止存在于战场,还显现于家庭之中。
“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情境化的体验空间中呈现的。这种体验情境是在观众面前自行展开的,观众只需以感官进入即可,并不需要调用太过复杂的知识结构。”[2]而以感官调动的情感体验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情念性。“情念比情感(emotion)更强调一种带有激情的东西作用在“我”的身上,进而促使“我”产生行动的过程。”[3]情念指向那些具有恒定性的情感类别,且在固定的情感关系中不断深化其情感的表现维度,这种情感关系能够穿越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沉淀。
亲情作为一种恒定的情感关系,是一种具有穿越历史时间的深切感受,这种情念的沉淀同时作用于亲人双方的行动过程,并在残酷的战争离别中产生巨大的情感张力。《特级英雄黄继光》描述了黄继光从参军入伍到壮烈牺牲的整个过程,其中穿插着黄继光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成长经历:从参军时母亲的一句“参军光荣”到身在前线时母亲在信中的问候“仗打完了吗?啥时候回?”再到在危急时刻黄继光梦回故里时母亲的一句“疼不疼啊?儿?”当得知儿子牺牲时,母亲的深情独白“我失掉了一个儿子,却拥有了千千万万个儿女。”无时无刻显露出母子之间的思念之情。
由此可见,电影将情念性作为叙事结构的核心,并以母亲与孩子的双重视角勾勒出一条贯穿于英雄成长的感情线,强调情念维度与家庭伦理的内向观照。在残酷的战争场景中,脆弱的母子情念转化为英雄本色的原始驱动力,母亲形象与国家意象的重叠,彰显出守护家庭与保卫祖国的意义连结,以滋生于内心的力量突破人物的生理极限与生存困境,促成了黄继光从一名普通战士向特级英雄的身份转变,彰显出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与此同时,电影以母亲的视角将万千子弟兵与“我的儿子”同构,实现了从个体情感到集体记忆,从英雄牺牲到精神永存之间的具象转化,以深刻的母子情念缝合了家与国的同构关系,揭示了英雄本色的深刻动因与英雄行为背后深远的家国意义。
二、场景重塑:强调以“人的力量”为本质的动作美学
相较于同题材院线电影,抗美援朝题材网络电影淡化了宏观策略的对抗和重型武器的交锋,而是将焦点汇聚于朝鲜战争中“冷枪冷炮”的相持阶段,呈现出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志愿军的个体行动路线为主观视角,展示了志愿军个体的真实反应与战术默契,并巧妙地将人与武器的使用及战术协同相结合,凸显出以“人的力量”为本质的动作美学特质。
(一)人与武器的细节化呈现
“军人”“武器”“战场”是战争题材电影作品的三大审美要素:“军人与武器是战场审美表达的要素前提,武器是军人参与战场的审美介质,而战场是军人与武器结合时进行审美表达的特定场所。”[4]在现代战争中,军事工业伴随着工业革命迎来迅猛发展,巨大的战争机器取代人类成为战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武器的在场成为战争场景的视觉主体。而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被称为一场伟大的胜利,是因为这是我军在交战双方实力极不均衡情况下,展开的首次现代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再次成为冲锋陷阵的第一战斗要素,在网络媒介的“小银幕”中,这种“人的力量”被细微地凸显出来,与他们手中的武器一起再现历史的同时,彰显着舍生忘死的抗美援朝精神。
“战争不仅触及了各个民族的生活,也触及了思想。这些神秘程式的富有吸引力的暗示越是含混不清,就越具有威力,非物质力量才是战斗的真正方向盘。”[5]人的情感与精神作为主要的非物质引导力量是战争走向的最终解释。对于抗美援朝题材影片而言,网络电影聚焦于个体化的作战形式使“武器”这一审美介质的“伤害性”表现属性被逐渐弱化,而“使用性”的操作属性被强调、突出,“人的本质力量”在想象性的动作奇观中被重新激活。
影片《狙擊英雄》中,主人公任东风在使用武器瞄准目标时的呼吸节奏与具体场景的射击时机,对应着他从鲁莽冲动逐渐转变为冷静自信的成长过程,人与武器的结合从这些细节之处体现出来,经历了多重考验与磨合,伴随着人物内心的变化,呈现出动态发展态势。人与武器的关系也逐渐延伸出不同阶段的作战表现,并最终通过人的意志完成对武器的精神赋值。
同时,武器的传承也在战争场域中形成特殊的审美价值,武器成为持有者的“精神火炬”,在一任任的交接中,生命的陨落增加了使命的重量,武器转变为一种精神性的传承符号。《狙击英雄》中的任东风接过牺牲战友的狙击枪,枪托上包裹的布条印出斑斑血迹,武器在这一时刻不仅成为战友情感的联结,同时是促成主人公成长转变的关键因素,完成从个人复仇到集体精神的具象化表现。此外,在影片高潮的射击场景中,任东风与班长高占奎因各自负伤,采用一人在前用肩扛起枪管瞄准,一人在后扣动扳机的方式完成对敌人的射杀。这种双人共持一枪的动作设计贴合网络受众游戏式的审美体验,通过对历史场景的想象性重构,创新性地表现出人与武器的作用关系,并以一种艺术化的动作设计对“人的本质力量”做出具象化解构。正如恩格斯曾说过:“枪是不会自己射击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去使用它们,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武器。”[6]网络电影通过人与武器作用关系的细节化审美表达,生动诠释了志愿军“钢少气多”的精神优势,形成一种基于网络媒介属性的动作美学奇观。
(二)战术配合的微观化视角
“战争追求的是胜利,美追求的则是‘人这一尺度的价值衡量。”[7]在同题材院线电影中,猛烈的射击火光标志着对峙势力的在场,宏观战场则成为战略成败的关键节点与意识形态交锋的重要场所;而在抗美援朝网络电影中,武器演变为人的力量的延伸,而战场的审美价值则指向人在特殊场域中的力量显现与精神升华。具体来说,战场的宏观战略属性被消解,生成了以运动倾向、射击角度、配合时机等以“人的力量”为主体表现的具体化,微观化的战斗场景。在这种场景中,武器火力的强势在取胜的重要性上逊色于人的反应能力。
电影《狙击英雄》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作战环境与单一的故事线索。在以争夺美军基地为目标的前提下,设置了美军处在高位,我军处于低位的地理关系,并采用中景与近景景别将整体的作战环境细分为以土坡、营地、坑道为主体的作战环节,更加贴近个体对于环境的观察方式与行动选择。与此同时,影片以美军狙击手与我军特射班同时共在的叙事方式,将双方对峙的细微过程通过镜头的剪切表现出来,营造出一种意识快于子弹,时机决定成败的心理对决。影片中,任东风与王清在深夜采取行动,被美军的狙击手发现而被迫躲在土坡后寻找逃生的机会,此时美军的狙击手却通过夜视仪对土坡进行实时盯防,双方展开了一场以时间为主的拉锯战。当第二天的太阳缓缓升起越过山边的一瞬间,刺眼的阳光使狙击手的视线形成盲点,两人抓住时机逃离现场。这种微观化的战场景观塑造,通过人在具体环境中的观察与配合,展现出一种智慧与精神层面的较量。
与此同时,在电影《浴血无名川》中最后的高潮片段,由于我军的弹药短缺,只剩两颗子弹。杜川在危急时刻,以肉体身躯作为娃娃的“第三颗子弹”,率先站起吸引敌人视线,而当枪口指向杜川的时间差,娃娃则将敌方一举击毙。杜川的牺牲成为了娃娃击毙敌军的“第三枪”,也成为志愿军精神延续的“第三枪”。由此可见,在这种微观化的场景视角下,“人的本质力量”转化为一种场景化的动作配合,“钢少气多”的精神优势体现为一种具象化的战术胜利。这种微观化的战场建构与运功性的战术设置展现出以集体主义精神为底色的中国智慧。此外,在微观视角下人物新奇化,场景化的动作设计也拓宽了战争美学的表现形式,不仅迎合了网络受众的审美偏好,同时也对我国志愿军的精神性力量做出了创新性诠释。
三、影像书写:打造“影感”与“网感”相结合的战争质感
“新媒体作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力量,倒逼着创作者在“更改”作品由内及外的文化形态和美学样式。”[8]伴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网络电影作为影响青少年的重要文化形式,逐渐成为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场域所在,一系列的革命战争题材网络电影应运而生。其中抗美援朝题材成为建构国家形象与实现民族认同的关键内容,其庞大的创作体量、丰富的文本内容、统一的价值导向,使其成为网络电影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何继承传统电影的战争质感、如何创造以网络受众为主体的视听网感,以及如何平衡影感与网感的关系表现,成为抗美援朝题材网络电影影像实践的创作要点与难点。
(一)专业性细节提升视听影感
“影感是指电影叙事具有内在逻辑性、制作精良,而且有类型探索和引导正确价值观的艺术追求。”[9]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银幕电影,其自身已探寻出一种固定的具有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的基本美学样式,比起其他影像呈现形式,在专业细节方面的把握往往更受观众认可。在长期的观影行为中,观众不可避免地将这种审美经验代入到网络电影的观影评价体系中。所以,网络电影创作者需要在题材、叙事、制作、视听、价值导向等层面凸显出创作者的艺术功底与独具匠心,进而通过细节的逼真度与逻辑的一致性说服观众,使观众调动起一种关乎影感的心理预期与想象体验。
电影《特级英雄黄继光》详尽地罗列了志愿军与美军的武器型号、军队番号、驻屯炮营。在武器方面,分别呈现了志愿军使用的莫辛-纳甘步枪、PPSh-41式冲锋枪、轻重机枪、M3A1冲锋枪,以及美军使用的M1A1式155毫米榴弹炮、M1式8英寸榴弹炮、M2A1式105毫米榴弹炮;在驻屯炮营方面,展现了千佛山炮兵阵地、甘风里炮兵阵地、城住舰炮兵阵地;在军队番号方面,呈现了志愿军的15军45师135团团部、美军的第8集团军,步7师。这样完整全面地对交战双方的火力配置进行考究的细节展现,体现出创作人员谨慎地创作态度与专业的创作能力。
在听觉层面,影片将不同武器的声效与操作方式进行了细致且专业的描写,并且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将声效进行重组,真实还原了战场上阵地战的战争质感,抛弃了原本嘈杂不堪、持续猛烈式的声效堆积,呈现出有节奏、有层次、有结构的听觉效果。例如PPSh-41式冲锋枪发射时,因连发火力的调试使得弹道平直、射速较快,从而形成“冷枪冷炮”式的音效;重机枪以杀伤力强、装弹数量多、火力持续性久为特征,所以在射击时常常出现“压制性”的火力音效;51式手榴弹形成“爆炸式”的音效以及土地树木被摧毁的音效;战场远处与近处的音效区别等等,多种不同的武器声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听觉效果的增强,完善了叙事效果。
在视觉层面,影片基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仅考虑到双方的武器差距,同时也考虑到使用习惯和武器磨损,以及实地操作时会遇到的故障情况,并将其融入整体的叙事情节中。例如PPSh-41式冲锋枪,是我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具有标志性的自动武器,以可靠性著称,但是在高强度的战斗中,尤其是美军强火力轰炸下,弹鼓本身容易形成故障,如易吃土,供弹口部位易变形等。电影中多次通过细节将战士武器排除故障的情节融入叙事——指导员在紧急关头给步枪排故;黄继光冲上前线慌忙将弹药进行上膛;战士调节机枪射击模式的情节;此类基于武器状况的展现,将艰苦的地理环境与残酷的战斗场面通过武器使用的细节而呈现出来,以真实且专业的细节设计,将一个具有现场感与体验感的战斗环境尽可能完美地营造出来,形成一种特别的影像质感,从视听层面完成对网络电影的影感升级。
(二)游戏化思维提升视听网感
“在互联网语境下,‘网感更多的是一种源自网络经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是一种从观众角度出发,强调观众至上的互联网思维方式。”[10]具体来说,是“能够理解互联网上网民的行为逻辑,并能根据其内在逻辑,设计出符合网民意愿的表达方式,让他们能够接受品牌和产品创意的一种能力”[11]。在网络电影的创作中,“网感”影像的构建与Z世代①观众的审美偏好存在一定的关系。他们热衷于追求网络游戏中的可操控性和可视性,习惯于将游戏元素移植和拼贴到影像中,同时喜欢具有游戏属性的影像模式。
在影片中,创作者不仅通过多样的职业选择对影视剧本进行改编,还推演出更为详细的战场职业划分,对不同职业之间的默契配合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例如电影《浴血无名川》中对冲锋员、狙击手、侦查员、队医等角色的塑造。同时,根据不同职业的属性与能力进行情节设计,将不同人员的配合融入战场环境中,发挥出协同作战的战斗效果。这种战斗情节的设计还原了电竞游戏中的操作与配合意识,通过第一视角与第三视角结合的拍摄与剪辑方式,为观众带来影游结合的观影沉浸感。例如《狙击英雄》将战争场面聚焦于小范围的狙击阵地战,在狭小的环境中营造尖锐的矛盾冲突,采用游戏中“对枪”的战斗机制,简化战场上其他战斗因素,只表现两个狙击手之间的技术对决,通过第一视角与全知视角的结合,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清晰明了的战术路径,融入“拉枪线”“抢时机”“打掩护”“道具战”等青少年熟悉的游戏化元素。
此外,网感影像的创新还体现在游戏化的创作思维与视听表现中。在射击游戏中,高度虚拟化、真空式的环境设置激发了玩家对于战术配合的想象力,并通过实际的按键操作增强用户的体验感,逐渐形成对游戏空间的精准把握与多维想象,这些通过拟真的游戏引擎带来的游戏化思维,进而形成基于游戏空间的网感审美。在《浴血无名川》中,就出现了运用游戏思维创作战争场面的视听内容。影片中,杜川与美国狙击手的对决,采用了“拉枪线”式的游戏思维,通过上帝视角将三角形的位置关系进行全景展示,慢放游戏空间“对枪”的时间差与目标差,并依据子弹悬浮与弹道路径剪辑视听画面。影片充分利用了年輕受众熟知的游戏元素进行互动设计,对于战斗过程的游戏化编排结合现实题材与虚拟想象,使受众在视听层面的多个维度上产生共鸣,完成了视听的网感升级。
结语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彪炳千秋,同时也警醒着当下人民树立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要铭记历史、铭记英烈,同时锻造不畏霸权、锐意进取的民族血性。抗美援朝题材网络电影在“英雄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中描绘了普通人的英雄壮举,深化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同时,影片立足于网络媒介特性,以成长型叙事模式聚焦个体生命,展现出以“人的力量”为本质的动作美学特质,并结合受众审美进行影像创新,以专业化的影像质感与游戏化的视听网感,打造出具有真实感与想象力的战争影像,进而向更广泛的观众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
参考文献:
[1]张智华.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96.
[2]王娅姝.战争记忆的影像化建构:以“新主流”电影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书写为例[ J ].电影评介,2022(08):13-19.
[3][法]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影像·历史·诗歌:关于爱森斯坦的三场视觉艺术讲座[M].王名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37.
[4][7]张晶,石宕川.刀锋之美:艺术媒介视域下的战争美学建构[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03):83-90.
[5][法]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M].孟晖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76.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81.
[8]张卫,陈旭光,赵卫防,梁振华,皇甫宜川,张俊隆.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 J ].当代电影,2017(01):4-18.
[9]路春艳,张琳瑜.影感与网感的平衡——“年度精品网络电影”创作特征分析[ J ].艺术教育,2019(06):107-109.
[10]齐伟,王笑.寄生性、伪网感与点击欲当前网络大电影的产业与文化探析[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05):9-14.
[11]徐茂利.网感的养成[ J ].国际关系,2015(05):8-9.
【作者简介】 王义仁,男,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艺术与网络影视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节目研究”(批准号:17ZD02)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Z世代,也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通常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参见:人民网.九州激荡四海升腾(百年大党面对面⑨)[EB/OL].(2022-06-02)[2024-01-11].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20808405/533aYdO6cr3_z3kATPaJxf_1My6RMNWq7bLVUrBzzqIP0XOpR57sVIE97pkv-_h3GA6Fs5dvLtUb2eb7FUlF7PUPces1QKpxnHb_UC7By7rl-dw2ms8c59c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