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入王土:北宋前期南方族群的治理与王朝统治
2024-04-24裴艾琳
内容提要 北宋前期对南方族群的治理虽皆以“羁縻”为原则,但在荆湖、川峡、岭南等地区的统治实态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与各地区族群发展水平相关,更深受宋廷对族群边地所毗邻核心区域治理深度的影响。宋廷在统一南方并重建地方行政体系与军事体系时,基于南方地区治理与猜防的双重考量,兼顾各地区社会秩序、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等因素,采取了不尽相同的统治措施,造成宋廷统治力在各地区的不均衡分布。这直接影响了各区域南方族群的政治抉择,进而迫使宋廷不得不因应不同地区的边地族群采取各具特点的治理措施。廓清北宋前期羁縻统治的区域特点及其原因,不仅能揭示边疆与内地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可增进对宋代羁縻制度丰富历史内涵的认识。
关键词 北宋 羁縻州 族群治理 行政体系
裴艾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北宋前期,随着五代南方诸国逐一纳入王土,荆湖、岭南、川峡等地土著族群纷纷“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1]。宋廷延续了唐朝的羁縻制度,在这些地区施行具有差异性的羁縻统治。
有关北宋前期南方族群治理的研究,多聚焦羁縻制度的多元形态与族群特性的关系[2],较少关注羁縻制度的地域性特点以及王朝统治与族群治理间的交互影响。对北宋前期地方治理的区域差异,既有研究一般笼统地概括为“重北轻南”[3],对南方各区域间的差异未及讨论,尤其是对荆湖、川峡、岭南等地宋朝统治力量的不均衡分布及其成因等相关问题尚未有全面梳理。实际上,各族群地区在地理上与宋廷直接治理的州县毗邻,在经济上受益于沿边贸易体系,在军事上无论叛服皆受宋廷控制力的影响。因此,考察南方族群治理的区域性,就不能简单地从族群自身的差异性入手,还需要结合宋廷对南方相邻区域的地方治理实态,综合地开展对族群治理的区域特点及其生成因素的分析。
本文拟在梳理宋太祖、太宗两朝南方诸路政治、军事体系重建形态的基础上,考察北宋前期羁縻统治的区域差异,廓清从中央到边陲统治力分布变化的部分实态以及边疆族群治理与王朝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宋朝边疆治理和族群融合等问题提供一些新线索。
一、“通于中国”:宋初与南方族群的交往
乾德元年(963),北宋先后用兵武平、荆南、后蜀、南汉诸南方政权,建立起对南方地区的全面治理体系[1]。在此背景下,南方诸族重启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历史进程。前人已据族群、羁縻州等分类方式,初步归纳了相关族群与宋朝建立交往的史实[2],但各族群行动的历史背景以及与宋朝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关联,仍有待进一步梳理。北宋对南方诸族羁縻统治的重建期间,宋廷对不断拓展的南方疆域版图,采取各类地方统治的措施,逐渐影响了南方诸族的选择。
随着宋廷在南方政权的持续巩固与深入,羁縻统治范围亦随之扩展,所以结合对西南族群动态与王朝统治扩展的考察,可以描画出诸西南族群逐渐纳入王土的概貌。
其中,湘西南北江地区的大族田氏与北宋关系的迟滞与发展,即能表现出宋廷统治地图的拓展对南方诸族抉择的影响。田氏是颇具影响力的大姓,前文提及的田汉琼便是南江田氏的一支,据有锦、懿、奖、洽、峨、波等州,距离控扼沅水上游山地诸族的辰州较近[1],故在湖湘易主后,迅速与邻近的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赟一起奉表归顺[2]。
与南江田氏不同,北江田氏首领在同一时期大多未见有所举动,这或许与北江诸田的所处地理位置与势力范围有一定的关联,可以印证前述有关南方族群的政治行动受宋廷南方统治版图拓展影响的推断。田氏在北江地区可考的41个羁縻州中占据14个州,且都位于酉水上游,与酉水下游据有20州的彭氏,呈分庭抗礼之势[3]。北江田氏之中,率先向宋廷奉表内附的首领,是乾德三年的珍州[开宝元年(968)改名高州]刺史田景迁[4]。宋初珍州位处酉水上游,地理上远离宋廷控扼沅水流域的辰州,受到宋廷政治的直接影响要晚于邻近的辰州。值得注意的是,田景迁内附的时间在宋廷平定后蜀的乾德三年,说明在北宋打通湖湘至西蜀的峡路通道后[5],田景迁不得不调整因应中原王朝的策略。因此,田景迁的来朝,应当视为宋朝政治军事力扩张的伴生结果,印证了族群关系与地方治理建设的密切关联。
虽然没有足够的史料以还原持观望态度族群的全部想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少首领应非因信息闭塞而盲目决定对宋朝的策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湖湘梅山诸族的种种记载。在宋初,王朝政治力量主要侧重于应对沅水上游的诸族,梅山地区相对受忽视,当地族群曾多次入寇宋境,大肆劫掠。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廷派兵出击梅山,荡平各族据点。就在清理诸族“巢穴”时,宋朝官兵发现了数百封土著族群与潭、邵等州大吏、“富人”的秘密往来书信[6]。书信的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可以想见的是,南方诸族与相毗邻汉地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梅山诸族在“不通中国”的时期,正是主动通过这些沿边州县的官吏商贾,建立了搜集宋朝信息的渠道;相信当时南方各族也各有其搜集信息的渠道,以便追踪并掌握宋朝中央与地方的动态,为其政治选择提供资讯和参考。
随着宋廷在地方的控制力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对荆湖西部山地诸族的羁縻统治,从辰州一隅扩展至包含南北江数十羁縻州的广阔地区。北宋在军事上击溃梅山诸族以后,当地族群为避免与宋朝再起冲突,转向西部山区拓展,直接威胁了南江舒氏所据的富州和向氏所据的叙州[7]。于是,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受梅山势力挤压的诚、叙、富、晃、鹤等南江地区诸族首领,纷纷来贡请命,成为北宋羁縻统治下的一员[8]。将南江地区诸族的举动置于北宋平定梅山的时空背景之下来看,就可以理解南江诸族应对中央王朝的策略在太平兴国时期所以改弦更张、转向积极建立与宋廷往来,都是因为宋王朝的影响力在荆湖西部山地的持续扩大。
与荆湖西部地区主要依靠军事实力的较量不同,宋廷对西川地区的控制与渗透,更有赖于经济文化等软实力的运用。据统计,黎州外诸族往来宋朝的频次,在宋太宗时期有了明显增加。其中山后两林蛮在太祖时两次来贡,间隔约六年之久,但是到了太宗时期,该族平均每一年半便派遣使团来宋。究其缘由,一方面,与宋朝有意招徕沿边诸族有关[9];另一方面,则受到朝贡贸易的影响,地方族群赖此为衣食之源[1],貿易的吸引成为北宋制约西川外诸族的重要手段[2]。
比较而言,岭南地区诸族群与北宋的往来显得有些冷清。宋初君臣认为岭南是遐荒炎瘴、风俗乖异、族群繁盛的异域[3],并不完全适应中原的统治传统,故而对地方族群团体以宽松羁縻为主[4],在岭南既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未曾创造经济往来的丰厚条件,所以除了南丹州莫氏屈指可数的几次来朝请命,以及雍熙中招安寇边抚水州首领蒙令地、蒙令札[5],其他族群团体的朝贡皆未见记载。
可以认为,北宋初年统一南方背景下重建羁縻统治的过程中,宋王朝的政治影响力、军事控制力、经济文化吸引力等皆对南方诸族是否并入“王土”的抉择产生了影响。
二、“辟土既广,吏员多阙”:北宋前期南方官吏的选任
总的来说,北宋前期南方行政体系的建立有两个重要背景。其一,在统一南方以后,统治疆域急剧扩张、治下人口迅速增长[6],加之南方诸地财富充盈,使得宋廷不得不盡快完善治理体系[7],甚至采取裁撤州县行政机构的方式,以减少官吏阙员之压力[8]。其二,北宋前期君臣基于唐五代的经验,奉行“强干弱枝”等基本国策[9],严厉限制地方势力做强以避免割据覆辙。尤其是对于南方诸国残留势力,宋廷更是严加防备其重新崛起,以往对南唐入宋君臣的研究就充分展现了宋廷对诸国旧势力的猜防[10]。
因此,宋初朝廷在重建南方行政体系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对诸国旧地治理的“治-防”博弈,而南方官吏的选任与行政体系的确立亦在此博弈中不断发展。
在接管南方政权之初,宋朝多以行营武将为地方长官[11]。这些武臣成为地方长官便于地方的接管与稳定,也有利于后续的军事调配。宋廷为长久稳定地控制南方地区,采取了废除各国旧有节度使制度,派遣京朝官直接管辖重要的州郡,推进南方藩镇的州郡化[12]。但京朝官人员有限,小郡州县只得适当继承武平、后蜀、南汉旧有的行政体系,留用旧国官吏,以维系南方疆土的统治。
而在“治-防”博弈下,宋初朝廷针对旧国官吏,依其在故国官僚体系中的地位,采取了不同的措置方式。其中最为主要的策略,是将各国旧有上层官员迁离原籍[13],以防止制霸一方的变动发生,但仍会适当留任旧有基层官僚,以维持地方行政的稳定运行,所以宋初诸国入宋官吏的传记中,也不乏“仍旧职”的地方官员[1]。
留用旧国官吏的目的,是为有效利用荆湖、川峡、岭南人才以释缓统治压力[2]。基层官员的留任只是权宜之策,并不代表宋廷消除了对这些官员的猜忌与防范。宋太祖就曾下诏在荆湖、川峡“伪命官”任知州的各州,逐处设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以制衡,“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得施行”[3]。一般认为,此后影响北宋地方行政颇深的通判之职,设置的初衷就是钳制宋初大量任命的前国旧官。易言之,通判之职首先在南方荆湖、川峡等地出现,可视为北宋对南方旧国官吏猜防政策的一种体现。
同时,北宋为了防范旧国官吏,还屡屡将官吏调离本籍,再行任用。在后蜀留任的官员中就有数起仕宦荆湖等地区的例子,如后蜀宰相毋昭裔之子毋守素[4],兴州裨将赵彦韬[5],原施州刺史龙景昭[6],衡阳县令周某等人[7]。宋朝一方面冀望选任旧国官吏以平稳地方行政,另一方面则着意选任不同层级的官员迁调其他地区任职,以削弱地方势力。
此外,宋太祖曾下诏要求地方注意搜访“有怀才挺操,耻仕伪庭者”[8]为宋廷所用,以起到制衡旧官吏的作用。苏轼外曾祖程仁霸就是在此政策下出仕为官的。宋平蜀后,他在地方上被推举担任摄眉州录事参军[9]。在“遐荒炎瘴”的岭南地区,更普遍任用“习其风土”的本地人出任摄官,或选任旧南汉所设诸小郡及州县官[10],以便宋廷加强统治。
宋初在荆湖、川峡、岭南各地重建政治体制的过程中,针对各地情况施以不同政策,形式各异的官员选任举措均反映宋初南方地区“治-防”博弈的影响。宋廷通过留用旧有官员、异地任官、增设通判官等措施,一方面尽力保障地方行政的有序开展,另一方面使用层层手段降低地方官员复叛的可能。
即便如此,同样的政策在荆湖、川峡、岭南却遭遇不同的境况而产生差异性结果。相较而言,荆湖地区是当时官员赴任时较易接受之地,其他二地各有弊端,所谓川峡多“贼乱”、岭南多“瘴疠”,皆是宋朝官员不愿赴任之所[11]。
正如叶梦得所言,宋朝初定西蜀时,“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土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远不测为惮”[12]。川峡地区在宋初接连发生兵变、民变,且为免北方官员赴任后擅权不法,宋廷禁止任川峡职事者举家前往,这都使官员畏于蜀行[13]。
至于岭南,因其气候与中原殊异,当时到任的京官和三班使臣生还者十无二三,朝廷为鼓励官员南下不惜抛出丰厚俸禄和赏赐,酿成贪冒之徒纷纷愿往的恶果[14]。对此,不同的官员均提出措施以减小危害。如开宝四年,知邕州范旻提出只有本地人士才适合长久居住,在岭南不必依照岭北的政治体制遍除职官[15]。又如淳化二年(991)九月,王化基在上奏中请求“自今以往,西川、广南长吏不任负罪之人,则远人受赐矣”[1],以避免其为害远方。由此可见,地理、风俗上的差异,造成官员选任结果的差别,特别是川峡、岭南长期是行政体系建设的薄弱地区。
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广开科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吏阙员的问题。《宋代登科总录》中记载了太平兴国二年、三年(978)、五年(980)三榜共42人的初授官情况[2],绝大多数是初授官于南方地区,尤其集中于长江沿线。而且,也反映出宋廷在南方地区治理程度的差别:初授官地点中,淮南、江南等地区共15人为最多,其次分别是川峡四路共13人,荆湖南路共8人,荆湖北路共2人。其中,升州、鄂州、宣州等通判,均为榜首所赴任之地,说明了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北等路的重要性;荆湖南路除羁縻州以外的11州中有6州在太宗初年设通判,于各路中设通判比例最高;任职川峡者则遍布蜀地,说明在蜀地派驻京朝官,亦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宋初荆湖的衡州、邵州、澧州和川峡的泸州、戎州等近“蛮”地区,已成为朝廷重点治理区域。
太平兴国年间开始大量进士进入南方,其初衷固然有改善南方基层治理体系困境的考虑,但通过三者之间任官人数的显著差异,可以窥见毗邻西南族群聚居的荆湖、川峡、岭南三个地区中,宋廷的关注多集中于荆湖,其次为川峡,岭南则未受到同等的重视。从宋廷的治理理念而言,南方地区的治理各有侧重,而政策的差异导致了地方行政体系的完善程度和王朝统治贯透力的区域性差别。
三、“重西北而轻东南”:北宋前期南方地区的军事部署
军事控制力是影响南方诸族抉择是否接受羁縻统治、宋廷能否维系边地安宁的重要因素。既往的军事史研究,已经从宏观上揭示了北宋前期的军事部署,及其在两重维度上的轻重之别[3],即一重是中央与地方的轻重之别,通过聚天下精兵以强京师,削弱地方州郡军队势力[4],从而形成“强干弱枝”的格局[5];另一重是不同区域之间的轻重之别,因拱卫京师、抵御边患等原因而形成了重西北而輕东南的格局[6]。然而,在此宏观维度下的荆湖、川峡、岭南三地军事部署详情,仍需要进一步解明。
北宋前期,南方各地的军事部署虽深受国家总体军事政策的影响,但仍有其显著的区域特点。从“强干弱枝”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解散原南方诸国的兵士、放归务农,另一方面拣选兵员纳至宋朝的军队,并将其整编入北宋禁兵迁出原驻地。宋初共整编后蜀降卒入虎捷、奉义、怀勇、怀爱四军,计约12个指挥合计6千人,并将奉义、怀爱两军驻泊京师附近,怀恩驻泊荆湖北路。此后,将地方军队整编为禁军的行动,也时有发生。比较典型的事例,是淳化四年(993)王小波、李顺起义后,为防止蜀兵响应,北宋从川峡威棹、克宁两厢兵中选拔编入禁兵,分别立为川效忠、川忠节、川桥道[7]。由这些旨在“强干弱枝”的军队整编过程可见,宋廷不断从地方抽取合适的兵力以充实中央禁兵,同时减少南方地区叛乱的可能,削减叛乱的烈度。不过,宋廷虽防范了新纳疆土的叛乱,却削弱了对南方地区的军事控制力,因而北宋前期的西南军事部署中始终蕴藏着“治-防”博弈的理念。
从“重西北而轻东南”的角度考察相关军事的西南区域性,可以发现为因应南方的治理需要,太祖、太宗两朝东南军事部署采取的策略是:主要由厢兵轮替屯驻,辅以在核心区域部署相应的禁兵驻泊,从而形成控制地方社会、削弱地方军事实力的双重效果[1]。
值得注意的是,禁兵与厢兵、土丁等武装力量的协同模式,在宋廷对西南各地军事控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荆湖地区,宋初驻泊禁兵有怀恩、雄武、归远、虎翼、雄略等[2],皆具有巩固边地的积极意义。怀恩兵由后蜀降卒整编而成,主要驻屯在北路荆南府、鄂州两地。雄武兵的主体是乾德三年太祖整编的诸道州兵,日常驻屯京师及其附近[3]。开宝年间,因用兵南唐,故屯戍荆湖南路邵州等地。开宝八年(975)五月,李继隆曾率雄武三百人屯戍邵州,应系更戍禁兵[4]。邵州屯戍人数虽然不多,但处北邻梅山的军事重地,所以仍有控扼边地的效果。至于归远、虎翼、雄略等禁军,曾长期屯戍于荆湖北路的蕲黄州、荆南府等地,在景德四年(1007)宜州陈进起义时,宋廷遣此三军远赴桂州[5],平定岭南的叛乱。
虽然驻泊禁兵对南方战事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其兵额数却是相当有限的。依据诸军番号,结合《宋史》所载,可大略推估宋初荆湖地区禁旅的概况:怀恩兵在荆南驻屯2指挥、鄂州1指挥[6],归远兵应在鼎、澧、荆南驻屯共约3指挥[7],雄略兵在荆南驻泊约5指挥、潭州约4指挥、鼎澧二州各约2指挥[8]。概言之,荆湖禁兵驻泊集中于长江两岸,总兵数在20个指挥以上。
论及川峡地区,其特殊之处在于因此地宋初兵变频发,故而成为禁兵驻泊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宋初驻泊川峡地区番号可考的禁旅,有虎翼、广武、神卫、忠勇。虎翼是宋初设立的禁兵番号,又号“雄武弩手”,是以弩手为主的禁旅;广武则为淳化二年从各军中挑选强壮善射者组成的禁兵,与虎翼均在宋初驻泊川峡,至太平兴国年间主力转戍京师[9]。此外,忠勇军是在咸平五年(1002)从易州调兵组建的禁兵,驻泊成都府[10],至迟在宋朝前期属侍卫步军司的神卫兵,亦曾驻泊成都府等地[11]。
依以上考证,推算宋初川峡地区驻泊的禁军不过十几个指挥,且主要驻泊在成都府及附近区域。此外,北宋英宗治平禁军军额,在湖南为8300人,湖北为12000人,福建为4500人,广南东、西为1200人,川峡三路为4400人[12],北宋中期的状况也可逆推、佐证北宋前期南方军事力量的区域差异。
由于只有少量精锐禁兵驻泊,南方地区的长期稳定主要依靠州郡厢兵维系[13];宋初从厢兵中选拔精锐整编入禁兵后,留在本城的厢兵所辖事务庞杂,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14]。虽然《宋史》对厢兵的记载较为简略,但大略可知各地厢兵番号,如川峡地区至少有克宁、威棹两番号的厢兵[15],荆湖、广南皆有水军,广南有以静江、忠敢、澄海为番号的厢兵[16],还有诸州所设的壮城、牢城等[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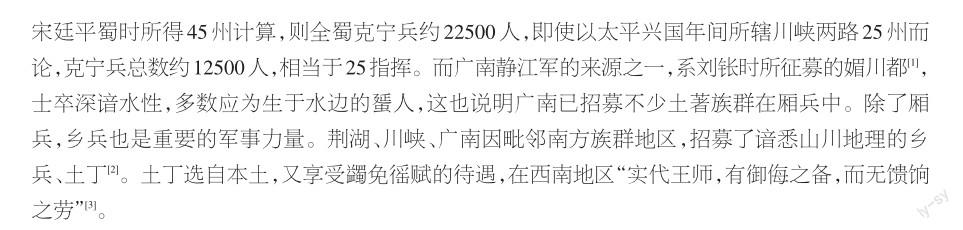
苏轼曾总结说,宋初沿边要害地区,通过厢兵屯戍、禁兵交锋、土丁保境构建起沿边的防卫,尤其是平日保卫与防御,须专用“极边土人”[4]。这一说法,对西南边防同样适用。一方面土丁熟悉土著族群的生活区域与交通要道,掌握控制各族的方法;另一方面土丁能适应当地气候风土,不像一般的宋军会出现饱受瘴毒之苦的状况[5]。
有关宋初南方土丁的招募情况,如果以辰州为例进行考察,可以得知,太祖平荆湖以后,提拔傜人秦再雄为辰州刺史。为便于控扼沅水上游诸族,秦氏训练了一支能披甲渡水、善于翻山越岭、“捷如猿猱”的军队[6],士兵极可能皆来自当地土民。到仁宗庆历二年(1042),荆湖北路的土丁仅屯驻辰、澧二州,就达19400人,而荆湖南路全、邵、道、永四州,总计5153人[7]。仁宗时期,南路四州的土丁人数尚不及太祖时期辰州土丁的一半,而北路辰、澧二州是南路四州总数的三倍有余,说明北宋中前期大量招募土丁以防备辰澧州上游南北江地区的事实。
宋初在川峡地区有义军,亦是以土著族群为主的军队,雅州曹光实父子就是后蜀控扼邛崃、百丈的静南军的首领。王全斌率军入蜀后,得到曹光实协助相继攻克雅州、黎州,宋廷曾封曹光实为义军都指挥使和权知黎州兼黎、雅二州都巡检使[8],不过随着禁兵、厢兵的设置,曹光实所率静南军渐为永康军、静戎军替代,西川的这支义军遂消失于历史记载之中。
四、“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北宋前期对羁縻州的治理
宋廷和荆湖、川峡、岭南等地土著族群交往的深度,与行政体系完善程度、军事部署强度间呈正相关性,表明了华夏政治对于边缘族群的吸引力与控制力深受相邻核心地区综合实力的影响。但宋王朝统治下的州县行政体系如何含纳地方的族群治理,尚需从具体史实中进行考察。
宋朝前期对南方族群主要采取宽松的羁縻政策,但如果仔细梳理针对西南的官封、朝贡、“因俗而治”等具体措施的施行,则这一认识仍值得斟酌。宋朝在南方诸地实行羁縻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南方政治、军事体系建设相类似的状况,即在荆湖、川峡和岭南地区呈现区域性的差异。
但是,宋朝的官封往往具有区域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一类是延续唐代羁縻制度,以各羁縻府州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可世袭;另一类是延续唐代授封蕃官的习惯,以武散官授以首领,“以授蕃官”[2]。通常授以刺史的诸族群首领,主要分布于湖南、岭南诸地,及西川的保霸州,其封授的基础是以羁縻州为主要形态的政治体,通过仿以地方职事官授以刺史等职,来确立其首领的名分。授以将军等武散官的诸族群首领,则主要是黎州外诸族、西南五姓蕃、环庆州诸蕃、党项、吐蕃等[3],虽不能尽说全无特例,但大致符合这两种分类。由此对比两种封授官职,既与是否具有羁縻州实体有关,也体现出不同地区土著族群政治体在政治上宋朝化的程度差异。
羁縻统治的区域性差异,同样体现在宋廷对族群实际治理的介入深度。从原则上来说,宋廷一般不介入族群地区的内部冲突和权力斗争,只是接受各族群权力制衡的最终结果,所谓“树其酋长,使自镇抚”[4],作为王朝治理边地的代理人。
当然,宋廷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南方族群地区的权势更替,特别是在毗邻行政、军事要区的地带,如南北江地区,随着地方统治的稳固和当地重要性的提高,宋廷时常会采取直接干预其族群事务等多种措施,加强对当地的控制。此外,宋廷对于可能引起地方动荡的羁縻州首领,利用其入朝的机会,将之迁于内地。乾德五年(967)十月,太祖下令将身为酋豪的溪州彭氏的彭允足、彭允贤和珍州田氏的田思晓迁至濮州、卫州、博州各处任牢城都指挥使,隔绝其与本地的关系[7]。这种将酋领迁至内地的做法,一方面可以维系地方的稳定,另一方面将羁縻州首领迁至京畿附近之牢城,对当地诸族起到了震慑作用,增强了宋廷的在地政治影响力。
除了册封羁縻州首领、平衡地方势力、内迁安置部分蛮酋,宋廷还重用熟谙边情的土著官员,以增强对南北江地区的控制。魏泰指出,“太祖既下荆湖,思得蛮情、习险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当时有傜人秦再雄骁勇可任,太祖特召至阙下,任为辰州刺史,命其镇抚南北江诸部[8]。宋太祖在川峡也同样任用熟悉边地族群民情、军事上勇猛可信的曹光实为权知黎州,兼任黎、雅二州都巡检使,以控扼边地[9]。开宝六年九月,因岭南接连发生族群扰边,曹光实被任命为诸州都巡检使,捕斩叛乱分子,平息了动乱[10]。此后曹光实又参与对西北的战争,成为北宋前期的重要将领。
在华夏边缘区,羁縻统治的建立实际上如中央势力逐渐进入南方地区建立州县统治体系的过程一样,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和区域特性。在荆湖的南北江地区,宋廷的处理较以往显得更为积极进取,不仅接续了晚唐以来的羁縻制度,依靠土著领袖对南北江诸族建立统治基础,而且注意利用大姓势力间的争斗维持地区平衡,还以内迁的方式拔除可能影响北宋统治的地方势力。在控扼南北江地区的辰州等州郡时,选任熟悉西南族群风俗的官员,以军事力量稳定边域社会。但是这种环环相扣的治边政策,在川峡、岭南都未曾完整体现。在川峡地区,虽有招徕各族酋长内附等行动,但宋廷显然对参与诸姓争夺无甚兴趣,始终以维系宗藩关系为要务。这一时期,岭南地区诸族群与宋廷的关系显得最为薄弱。
五、结语
在宋初的南方边地,羁縻统治与州县体系相伴而生,使得族群边缘区与内地核心区的交汇地带,内政与治边往往呈颉颃之势。宋初羁縻统治建立伊始,南方诸族的政治决策便受到宋朝政治影响力、军事控制力、经济文化吸引力等因素的复合影响,而宋廷对南方诸族治理的深入程度,亦受到内地核心区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制约。因此,宋廷对荆湖、川峡、岭南等地的治理差异,与三地羁縻统治的区域分别,呈现紧密的相關性。
这种相关性的背后,透露出中央统治贯透力的区域差异。羁縻统治与州县治理体系固然差异甚大,但某种程度上而言,羁縻地区可以视作宋廷政治力向外延展所能达到的末端区域[1],故宋廷基本采用不直接介入的方式,而利用地方权力参与其中。可是,宋廷政治力的辐射范围,必然与其核心区的政治巩固程度息息相关。宋廷对于统一后的南方诸地,重视程度各不相同。以毗邻族群地区的荆湖、川峡、岭南三地而言,三者无论在军事、政治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宋廷在荆湖路不断增强文官选任以改变当地政治形态,但川峡、岭南则渐行“定差法”放权地方[2],说明南方各地区在政治上有轻重之别;另一方面,荆湖位于南方诸路通衢,是军事战备、交通往来的主要区域,是南方禁军驻屯的核心区域,而川峡、岭南虽有防备兵变、边患的需求,但禁军军力有限,主要依靠厢军和土丁加以防卫,体现出南方军事上的区域差异。
正因为政治、军事力量在南方各区域分布得不均衡,羁縻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落实于实际的过程中呈现区域性的特点。与川峡、岭南多秉持羁縻原则不同,宋廷借由相对完善的地方行政体系与较为雄厚的军事力量,对荆湖西部山地诸族的治理程度比较深入,已经出现针对地方酋领的种种直接干预的新措施,显示出宋代羁縻政治的时代特点与地域特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朝既是中国经济重心南迁的关键时期,又是羁縻制度向土官土司制度发展转型期[3]。由南方族群治理的区域化特点所揭示出的宋初治边与内政之间的交互关系,预示着此后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南方诸地统治体系的完善、治理水平的提升,宋廷在南方地区的政治贯透力与影响力日渐增强,对南方诸族羁縻统治的介入程度亦随之深化。这使得宋代羁縻统治呈现多元化的面貌,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羁縻制度转型的基础。
〔责任编辑:史拴拴〕
[1]《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209页。
[2]吴永章:《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発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6年版,第125—226页;R. L. von Glahn, The Country of Streams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s in Song Times,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1987, pp.72-79;吴永章编:《中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178页;安国楼:《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2页;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2页;刘复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46—267页。
[3]安国楼:《论宋朝的“轻南”政策及其影响》,《学术论坛》1997年第3期。
[1]刘复生:《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裴艾琳:《唐宋之际南方边地的华夏进程与族群融合》,《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2]张雄:《中国中南民族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241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三月壬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7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七月乙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8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正月丁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六月辛亥、七月戊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3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六月丁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5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六月是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9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开宝七年七月丙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0页。
[1]南江地区是以沅水支流的辰、?二水为主,南至郎溪,东达澬水,北与溪州相邻的族群生活区域。参见马力:《北宋南江地区羁縻州考》,《文史》1992年第34辑。
[2]《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72页。
[3]马力:《北宋北江羁縻州》,《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七月乙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5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正月辛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5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八月癸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0页;《宋史》卷二七四《翟守素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63页。
[7]《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96页。
[8]陈曦:《虚实之间:北宋对南江诸“蛮”的治理与文献记载》,《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
[9]《宋大诏令集》卷二四〇《山后两林蛮王归德将军勿尼等进官制》,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43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丁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5页。
[1]《宋史》卷三〇一《袁抗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02页。
[2]贾大泉:《宋代西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雍熙二年九月乙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9页。
[4]孟凡云:《羁縻与经制:宋朝在南丹州地区统治政策变迁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
[5]《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205页;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838页。
[6]《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3—2094页。宋代史籍中所载数目略有差异,参见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133页。吴松弟指出了宋初平定各国时难免因战乱等导致调查数目存在差异的情况,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2000年版,第116—117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八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7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七月壬子;卷一三,开宝五年四月庚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7、282页。
[9]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9—284页。
[10]伍伯常:《北宋选任陪臣的原则:论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10期(2001年),第1—30页。
[11]《宋史》卷二七一《张勋传》、卷二七四《王继勋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89、9535页;药永图:《前磁州刺史药公墓志铭》(太平兴国九年四月二日),国家图书馆藏拓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六月丙午、乾德四年七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2—174页。
[12]闫建飞:《唐后期五代宋初知州制的实施过程》,《文史》2019年第1辑。
[13]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页。
[1]《宋史》卷二七七《卞衮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34页。
[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3]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65页。
[4][5][6]《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赵彦韬传》《龙景昭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893页,第13888页,第13888页。
[7]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二,俞钢整理,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三年正月丁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页。
[9]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10][1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06页,第806页。
[11]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3页。
[12]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侯忠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0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闰八月己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8页。
[15]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九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2页;郑文豪:《“恶弱水土”员阙与宋代两广官员选任》,《武陵学刊》2018年第3期。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九月庚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22—723页;《宋史》卷二六六《王化基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86页。
[2]龚延明、祖慧编著:《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程民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
[4]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九《兵制》,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597页;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9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5]堀敏一:《五代宋初における禁軍の発展》,《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3年第4册;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79页;小岩井弘光:《宋代兵制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第29—50页。
[6]李觏:《李觏集》卷一《长江赋》,王国轩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页。
[7]《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中華书局1985年版,第4595页。
[1]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七《总议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8页。
[2][6][7][8][9][10]《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95—4597页,第4595页,第4596页,第4597页,第4595页,第4596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十一月庚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五月甲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0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六月乙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72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一月甲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80页。
[12]《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77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05页。
[13]龚维玲:《宋代广西兵制探微》,《社会科学家》1990年第4期。
[14][15][16][17]《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39页,第4656页,第4642页,第4645页。
[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九月壬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7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五月丙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3页。
[2]石亚洲:《宋王朝的政策与土家族土兵的形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5][7]《宋史》卷一九一《兵志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41页,第4741页,第4742页。
[4]《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26页。
[6]魏泰:《东轩笔录》卷一,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闰八月甲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6—177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一,元祐五年四月丙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620页。
[10]《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74页。
[1]刘复生:《岷江上游宋代的羌族羁縻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
[2]李林甫:《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2页。
[3]郭声波:《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
[4]《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71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六月是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4—305页。
[6]《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200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十月丁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6页;《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73页。
[8]魏泰:《东轩笔录》卷一,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十月己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0页。
[10]《宋史》卷二七二《曹光实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15页。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2]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206页。
[3]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