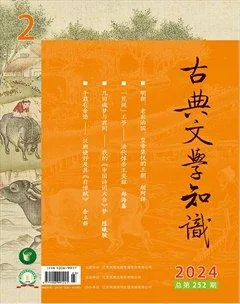中国早期小说的“名实”与“离合”
2024-03-25宁稼雨
宁稼雨
中国古代小说从起源时的萌芽状态到现代成熟状态,中间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按当代小说文体概念的基本要求,作为叙事文学文体形式的小说,大致应该包含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虚构成分,以及三者所需要的叙述描述语言。不过用今天小说概念与早期小说状况对比,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中国早期文献中,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文字材料与今天的小说文体概念比较吻合,但它们却没有被赋予小说的名称;另一方面,很多被赋予小说名称的文字材料,用今天的小说文体来衡量却很难被认可收纳。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体变化过程中,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逐渐淡化消除,从离到合,完成了小说自身的良性发展。
早期与“小说”沾边的几种情况
早期与“小说”沾边的文献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早期历史文献中对于“小说”这个概念的表述,二是史志小说家门类的著录,三是当时被冠以“小说”之名的现存作品。这三个方面汇总整合,大致能复现出当时“小说”的概貌。
最早使用“小说”这个名词概念的人是庄子。他在《庄子·外物》中通过两个钓鱼的例子说明境界胸怀远大的好处。一个是任公子,他用五十头牛做鱼饵,在会稽山能把鱼钩甩到东海,钓来的大鱼做成肉干够浙江、湖南一带人饱餐一顿。另一个是有人用小细绳、小细棍做成小鱼竿,在小河沟只能钓到小鱼小虾。后者如此狭隘局促,却还要“饰小说以干县令”(用琐屑无聊的话语获得美好名誉)。庄子认为这种做法“其于大道亦远矣”(即与任公子那种恢弘气势、胸怀大道相去甚远)。因为战国和西汉文献中未见其他人使用过这个词汇,所以可见这时候“小说”一词还只是庄子为抬高自己学说地位,有意贬低其他学说的一种修辞手段,并不是一个普遍常用词。很清楚,庄子这里使用“小说”一词是指与“大道”相左的琐屑言论,与今天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其中“小说”所体现的琐屑言论,还是与后来的小说观念有一定联系的。
到东汉时期,桓谭对于“小说”一词又有了更加细致深入的理解和阐述: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新论》)
从桓谭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小说”一词到东汉时期已经比庄子时代有了巨大进步和提升:“小说”已经自成一家,这一家的表达方式是采用“合丛残小语”“以作短书”的形式,通过“近取譬论”来说明世人在“治身理家”方面的正确做法。而且与庄子的不屑态度相反,“小说家”被认为有“可观之辞”。不过,这里的“小说家”仍然还不是一个现代文体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以表达思想观点为宗旨的诸子文章的末流。
汉代之后,文献中“小说”的表述开始分化:一方面继续沿袭传统观念,视“小说”为琐屑小语,与“大道”相对。徐干在《中论》中说: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谙于远数。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体骛乎俯仰折旋之容。(《务本第十五》)
徐干向曹丕进言治国之道:身为帝王,如果“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就会乱国亡国。这可以说是把对“小说”负面作用的蔑视否定推向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另一方面,“小说”也开始作为一种文艺性文体概念为人们所使用: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
这条故事大约可以作为上一条引文的一个笺释,曹植喜闻乐见的“俳优小说”,正是徐干极力警示曹植他哥哥万万不可为的亡国之道。
宋代之前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子部中设有“小说家”门类的有《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过对这些史志小说家门类中编著者的按语和所收小说作品性质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时段人们对“小说”认知的一个侧面。
《汉书·艺文志》是最早在诸子略中设立“小说家”门类的史志,班固对“小说家”做了这样的概括解释: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番话在进一步肯定小说“必有可观”的社会价值同时,比较突出的新意亮点是指出了小说家的背景来源是“盖出于稗官”。不過尽管如此,“小说家”在诸子略十家中,仍然是唯一不“入流”的一家。因为其他九家都是学有专攻的独立思想学派(儒家、道家、法家等),唯有小说家不具备这个条件,而只是从民间采集一些有益启迪人生的道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所著录的十五家作品虽然多已亡佚,但从班固的描述介绍和残存佚文(如《青史子》)来看,汉代人心目中的“小说家”还只是带有世俗风格的议论性话语,与今天文体意义上的小说相距较远。
与《汉书·艺文志》相比,六朝时期目录学著作中小说家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从残存的阮孝绪《七录》分类表可以看出,其“子兵录·内篇三·小说部”中收有小说书六十三卷。这些作品中,《语林》《世说新语》等一大批记述真实人物故事等与现代小说文体很接近的小说作品进入《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的子部小说家门类。这说明“小说家”这个门类从早期远离小说文体的议论性文类开始向带有小说叙述性质的门类转变过渡的走向已经相当明显了。
早期没有“小说”之名的作品
与早期具有“小说”之名但缺乏“小说”之实的现象相伴随,早期很多文献载记和作品,虽然没有被冠以“小说”之名,但实际上却与具有“小说”之名的文献相比更接近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庄子·逍遥游》中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学界一般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齐谐”是一位专门搜集怪异故事的人。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后来兴盛繁荣的志怪小说的早期经典用语。志怪小说成为超现实题材小说的种类名称,“齐谐”也是志怪小说的代称,可见其内涵与现代文体概念的“小说”相当吻合。
类似情况还有,被胡应麟称为“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和被其称为“古今纪异之祖”的《汲冢琐语》,很长时间内也没有被视为小说。班固将《山海经》列入《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刑法家类,《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将其列在史部地理类。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被收入子部小说家类。《汲冢琐语》在《隋书·经籍志》和两唐志中均被列入史部杂史类。最突出的是,很多同类志怪小说(如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等)也都是同样的遭遇,被拒在小说家大门之外。还有,从《庄子》开始,子部各家的很多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含有数量很多、故事情节色彩很强的寓言故事(像《庄子》《韩非子》等)。最明显的就是《汉志》子部儒家类所收《晏子春秋》,以及《说苑》《新序》。三部书其实是以讲述故事为主,只是故事结尾加上了作者想通过这些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但他们仍然没有“小说”的头衔。
两者从“分离”到“合流”的完成
总体来看,宋代之前“小说”的观念走向还是从远离和隔阂逐渐向今天文体意义上“小说”概念逐渐靠近的。大致脉络走势是:一方面,具有“小说”之名的作品,不断被剥离其原体中非现代文体小说意义的成分,逐渐向现代小说状态走近;另一方面,那些早期不具备“小说”名号的作品,在保留坚持其符合现代文体意义上小说要素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其小说文体价值不断被社会接受认可。这两股力从早期分离很远逐渐走向合拢。在这个由分离到合成的过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
首先是六朝后期,人们已经自觉用“小说”这个名称来命名自己写下的符合现代小说文体概念的作品。这个时期出现了三种以“小说”作为书名的作品,分别为刘宋时期刘义庆《小说》,南北朝无名氏《小说》,还有南朝梁《殷芸小说》。其中前两种已经亡佚,《殷芸小说》大体尚存。《殷芸小说》所收均为历史真实人物,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通过对《殷芸小说》的粗略考察,大致可以看出,到殷芸所在六朝后期,人们不仅摆脱了汉志时代视小说为子部大家宏论之下琐屑小论的传统认识,而且把小说作为“史”的附庸来认知,从而把小说的基本功能由议论一下子转入叙述方面来。这是对小說文学功能的重要发现。同时从该书内容可以看到,志怪题材和志人题材,这两种以前分别书写,所以在史志中分别著录的故事,可以一揽子收在这部名叫《小说》的书中了。该书以其编纂实践,完成了将以往分离的二者合流为一的重要工作。
其次是这个合流最终也在史志著作中得到正式确认和表述。最重要的转变是,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大量志怪小说,在《隋志》和《旧唐志》中还被列入史部杂史类,但是到宋人所编《新唐志》中,终于统一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了。从此便结束了大量志怪小说被排除在小说大门之外的历史。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终于走出混沌状态,开始明确向文学性方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唐代传奇的繁荣盛行,并非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