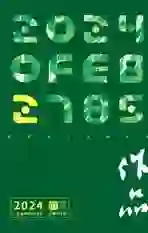仲肯快跑×老狗(短篇小说)
2024-03-19江洋才让
江洋才让
1.仲肯快跑
仲肯一下子从墙上跳过来。
不小心踩了野狗的尾巴。
野狗汪汪汪地哀叫几声,龇着牙。
即使天还没亮透,也能看到它牙上的白和雪山上的雪不同,也和墙上垒着的白石头不同,更不用说那糌粑口袋里的白糌粑,这最耐饿的粮食,还有混合在糌粑里的白砂糖。即使狗叫过了,收拢口袋布般耷垂的上嘴皮,呆愣一小会儿,望着仲肯摇起了它的狗尾巴。尾巴像是一根牛尾掸子,在空气中扫扫,要说它能净化空气很难,可要说它吸引了仲肯的一部分注意力倒是真的。
仲肯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把手指竖放在自己的嘴唇上,脸上焦急的神色暴露了他是逃出来的。你呀,别再叫了。这要是让村里人看见,我该怎么办?仲肯脸上的表情即使被天的黑掩住,可野狗却是闻出来了。要不怎么说,它能闻风辨色,嗅着那道轨迹它能追着你跑上一天,不不不,整整一个月也追着你。仲肯突然意识到这点的时候,脚已经把他带到了路上。脚板一前一后,轮番交替,声音啪啪啪的一点也不矜持,不像是悄悄逃出来的。更不像是一个仲肯,也就是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做派。嘻,还哪门子做派不做派的。要知道祸到临头,大事不好,哪还有什么心情管什么做派不做派的,就差没有插上翅膀,恨不得飞起来,飞走。
仲肯看着野狗,跟在他后头,就骂咧咧地赶走它。所谓野狗在这里指的是没有人豢养的狗子。所以,打它一石头不会有主人找上来。可问题是一石头下去,野狗肯定会哎哎地叫唤,叫唤声肯定会引起其他狗子的狂吠。其他狗子一狂吠,肯定会把村里的牛吵醒把村里的羊也吵醒。村里的牛醒了羊醒了就会踏圈,那蹄子噗噗噗地激起带着灰尘的声音,很快就会吵醒屋里头的人。人醒来肯定会去牛圈里看看,去羊圈里看看,然后,听着狗的狂叫会好奇地走出院子,再看,就看到仲肯站在石板路上,就会上前问,仲肯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走呢?很快就要开格萨尔说唱现场观摩会了,你可是我们村唯一的仲肯,你要是跑了,这场观摩会其他仲肯来了,你这不是丢咱村的脸嘛?仲肯想到这里,赶紧噤声,捂住嘴,然后,朝野狗踢踢腿,向村外走去。他想到老婆这时候还睡着,刚才出来的时候,他悄悄地看看她,再看看她被窝里三岁的儿子。再看看屋里的陈设,而后看看自己的说唱帽子仲霞。说唱帽子仲霞就在立柜的橱窗里待着。一看到仲霞,仲肯转变方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打开橱窗,立时,他感到仲霞动了一下。
仲肯吓得不轻,如果说仲霞动了一下,那说明自己脑子有问题,他把仲霞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就听到仲霞说话了。
仲霞好像感到了他的处境,轻声说,你怎么能走呢?你走了,后天的盛会怎么办?仲肯愣了一下,嘴里轻声说道,我不走难道要待在这儿丢人现眼?丢人现眼还不是丢我一个人的脸,全村的脸都会被我丢了,所以,你就别说话了。我知道一顶帽子说话必是我的臆想,回归你的橱窗待着,老老实实等我回来。
仲肯确实想出去躲几天,等到现场观摩会结束后再回来。他赶走野狗后,一个人沿着村里的石板路走到了村头的土路再由土路踏上了蜿蜒的山路再下山来到了全是路的地方。天亮了,太阳把光洒下来,问候第一个看到他的人。仲肯觉得自己绝对是那第一个。刚才,他看到太阳露头的时候,就问候太阳来着,你早,请把你的光带给全世界吧。太阳越升越高,他突然觉得自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肯定是不可以的。他回想着自己到底要逃向何处,既然到了这里肯定不能没目的地瞎走,像一头走丢的牛和一只走丢的羊甚至像一匹可怜的马。
仲肯想起来了。
仲肯想起了什么?
太陽轻轻地将光丢在他的肩上、额头上。仲肯想起自己的窘境。当一个仲肯突然发现脑子里的格萨尔王说唱被清空,那意味着什么?这对于一个仲肯来说绝对是噩耗。
那一天,村长找上门来。村长手提一串檀木念珠,嘴里刚开始哼着一段民歌的曲调,见到仲肯立马转换成语重心长的话语。
村长说,这次格萨尔说唱现场观摩会很重要,在我们村召开,县里投了不少的钱,还请了电视台的人拍电视,你可要为我们村争光啊!
村长见仲肯呆愣如羊,又说,你要好好地说唱,这几天,可要保护好你的嗓子,不要吃辣子,到了那天用你清亮的嗓子把全场给震一下!
仲肯记不起格萨尔王说唱的所有内容,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如果有人问这是为什么,他无言以对。他想了好久,决定搞失踪。太阳把他的身子晒得暖融融的时候,仲肯已经从那片全是路的地方走到两山之间的一片草场。以前,他放羊的时候,时常光顾这里。现在不常去了,却还记得那时候自己放着羊惬意的走动。他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在搞跟踪。仲肯有了这感觉心里立时慌张起来。他想象也许是村长也许是自己的老婆或许是村里别的什么人,想到这儿,他猛然回转头。脑后的世界立时变成眼前的世界。什么也没有嘛,如果说有什么人跟上来,肯定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曲塔才仁。这家伙考学考不上质疑人的本事却见长。他时不时就会找仲肯,仲肯记得他总是问是谁教会他格萨尔王说唱的?仲肯回答,没人教。只不过是放牧时睡了一觉,做了一个梦,醒来后大脑里就有了很多部的格萨尔王说唱。可现如今,脑子里好像是刮起了一场风暴,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仲肯有点恨曲塔才仁,当然他更恨自己。猛然间,就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宛如一群藏野驴踏地而来,颤动从地表过电一般传递他骨头上。
仲肯一惊,然后反应过来,还没等他向青草掩着的土洞跑去,那条野狗突然汪汪汪狂叫着蹿出来。仲肯揪着它的头皮将它拉入洞,钳子般的两只大手箍牢狗嘴,不让它发声,嘴里小声说道,你这黑皮白斑狗,真的好无赖,我不是让你别跟着我嘛,你怎么又跟来了?
野狗嗓子里发出哎哎的嘶嘶声,试图从他的左臂下挣脱出来,仲肯夹得更紧了。他听到那阵宛如藏野驴踏动地表的脚步声,停在土洞的上方。这样,这些追来的人就站在他的头顶开始说话。有人说,肯定不是走了这条路,一开始我们就追错了方向。还有人说,就你能,难道你是狗,能闻到仲肯的味道不成?又有人说,不是这儿,从这看过去一览无遗的,也没发现个人影,更不要说早早就跑掉的仲肯。
随后,他听到了曲塔才仁的声音。方才我明明看到一条黑皮白斑狗过去了,可转眼之间就消失了,难道它钻到了地缝中?更让仲肯想不到的是,老婆的声音也冒出来,昨晚,村长告诉我,你老公状态不对,你可要留意了,别让他出什么事。没承想,这一大早的,他就消失了。
仲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怎么说呢,老婆一定很紧张,心里绝对像是下了一场白茫茫的大雪。刚开始,他确实想写几个字,留到桌上,可后来一想,老婆一定会把纸条交给村长,所以,他只能咬咬牙跺跺脚,心一横,什么也没留。仲肯继续竖起耳朵听洞外的动静,老婆和曲塔才仁的对话变得稀碎,好像被一阵风带走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身上的力气就泄了,整个人好像瘫软了下来。他拉着野狗的身子爬出土洞,太阳在天上散射着热焰,草原上的草似乎被烤得发出细密的声响,嘶嘶嘶的,好像什么在漏气。老话说得好,谁直视太阳的眼睛,谁就是在给自己的眼睛找麻烦。
仲肯低下头,忽然看到野狗一点声息没有似的静静地躺着。他扯了一下野狗的后腿。又一下。野狗紧闭双眼,一动不动,皮毛被风吹得抖颤,好像它的灵魂溢出了身体。
野狗死了?仲肯一下子慌张起来。他提起野狗的前腿,将它的身子甩来甩去,醒醒,喂喂喂,你怎么不汪汪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汪汪也不会暴露目标,可现在你却闭着眼闭着嘴,好像吃了万能胶把嘴给粘上了。太阳静静地照着一切,万物闪闪发光,有些时候,只有安静下来才可能获得一些灵思。
仲肯哇哇大哭起来,他不是哭野狗,而是哭自己怎会如此的倒霉,不但忘记了脑子里最金贵的东西,还背上了一条狗命。太阳掩在了一朵云里,他开始用手刨一个坑,眼泪哗啦啦地从脸上滴下来,滴到自己刚挖出来的一个浅坑里。这个时候,他又发现自己出了状况:竟然忘记了口诵的经文。换在平时,他时不时会咕哝上那么一段,可现在看着野狗的尸体嵌入浅坑,而自己却念不出半句超度的经文。
仲肯又哭了起来,直到哭得嗓子有点哑了,他才把土掩在野狗的身上。这么一个浅浅的坑,却让他晓得自己不只是忘了格萨尔王说唱,而且还在忘记自以为记得最牢固的东西。
仲肯再次想哭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了眼泪。干号刮擦着空气,刮擦着自己的耳膜,直到干号从嗓子眼里撞上岩壁而后回弹到身上,再飞向眼前的三间土房。土房是在路口出现的,要知道这儿本来是一个小卖部,早年间,阿爸瞅准了这个地方。仲肯记得阿爸拉着他的手,那时他还小,鼻涕条从鼻孔里探出来,好像一只躲在山洞的绵羊走出来。那時候,阿爸就说过的。你看,这里有三条路,每一条都通向一处要紧的地方。左边是通往萨麻的,右边是通往萨闹的,这一条嘛,却是通往向尼敦德的要道。仲肯不但记得阿爸使劲地将一口痰吐到青石头上,还记得阿爸在路口撒了一泡尿,像是一条野狗在自己的地盘打上气味的记号。果然,没多久,阿爸就在这儿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人把那个小卖部叫作司机解忧部,也有人把小卖部叫作欢乐牧人之家。反正,仲肯记得阿爸自从干起了这营生,家里的活儿全落在阿妈和他的头上。这一干,就是好多年,直到有一天阿爸觉着自己干不动了,加之仲肯也不打算继承,所以就把店盘了出去。现在,这面貌算是升级了。也不知转手了多少次。总之,现在这家店不仅是小卖部,还是饭馆,还算是一家旅社,因为有一间客房可以提供。仲肯突然明白自己算是被潜意识揪着来到这里的。
仲肯说,我又来了。仲肯说这话的意思当然是在说明不久之前自己刚刚来过,而且还认识店主人怪大叔和怪大婶。怪大叔和怪大婶这外号不是仲肯起的,而是他从店里的意见本上看来的。你看这一句,怪大婶今天表现不佳,阿卡包子里的油明显没前几次足。还有这一句,怪大叔脾气冲,态度蛮,人最起码要做到始终如一,不能一天阳一天阴,凉了大家伙的心。当然了,油腻脏污的意见本依然挂在墙上,瑟缩在仲肯的背后,黯淡无光。仲肯意识到自己的后脑勺对着意见本,而鼻子正冲着怪大叔。怪大叔没意识到仲肯的来临,和一个月前的目的完全不同。
一个月前,他纯粹是被怪大叔请去说唱《格萨尔王传》,这间店子里坐着十来个人,仲肯就给他们说唱了一段《霍岭大战》,这是老段子了。可现在,说出来怪大叔完全不会相信,怪大婶也不会相信。当然,也没有必要对他们讲出来。
仲肯买了一堆的零食,算账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乘法口诀,五七得多少来着?原本除了说唱,他最拿手的是乘法口诀,可现在他一点也想不起乘法口诀是什么时候从大脑中逃逸出去的。仲肯想哭,怪大叔见状用犀利的眼神盯着他。仲肯说,我想不起乘法口诀了。怪大叔说,这怎么可能,你的脑子里能够装下二十部格萨尔王说唱,怎么会容不下那么一点点的乘法口诀?仲肯说,我还想不起全部格萨尔说唱的内容了。话不经意间飘了出来,仲肯抽了一下自己的嘴,就听得怪大叔和怪大婶异口同声,怎么可能呢?你又说笑了。说完,他俩面面相觑,交换眼神,只见仲肯尴尬地将那堆零食装到糌粑口袋里。也没多少,就是一把水果糖,零散的小饼干,五颗巧克力,四根棒棒糖。刚开始,他把糌粑口袋藏到藏袍里,做到了好像他没带任何的食物。要知道他并不是喜爱吃零食,而是紧张的时候,他需要不断地往嘴里塞一些嚼着,嚼着,好像能分散注意力,不去想那些让他痛心的事。
店子里又进来一些人,车子在店外激起的灰尘从门里进来,落在店里的桌子上,手指一划就能在桌面划出一道痕迹。几个人围坐着一张方桌,确切说是四个人,为首的显然是那个女的。女的戴着一副眼镜,她不动声色地叼了一根烟。坐在旁边的一个长发男赶紧用打火机打着火,帮她点上。另两个男的也是长头发。倒是这个女的是短发,深深地吸一口烟,而后缓缓地将烟雾吐到空气中,好像要置换店子里的空气。
仲肯耳朵里立时传入这些人的谈话声。一个男的说,这次我们出来已经做足了前期准备,绝不能再输给二组。又一个男的说,就是,上次主要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所以让他们领先了。另一个男的说,别说了,背后议论人没什么意思,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行了。短发女发话了,也不要搞得跟上前线似的,正常工作,心态一定要好。
仲肯的耳朵里立刻塞满了他们的话语,也不知这些人是干啥的,单从外表上猜很难猜出来。仲肯付了钱,耳朵却警觉地听着,好像一匹临河而立的马听着河水的动静。他装得心不在焉,转身就看到那三个男人中最瘦的那个,好像变戏法般地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个文件袋,女人转过头来喊,怪大婶,给我们来十斤阿卡包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带走晚上吃。说着,那个瘦男人从文件袋里拿出扑克牌厚度的一沓照片,一张一张地在桌子上铺开。仲肯显然没见过如此的阵仗,耳朵里又传进瘦男人的声音,导演,你看看这次观摩会上仲肯们的照片,你想想,我们应该从谁那儿开个头?
仲肯算是听明白了,这些人是电视台摄制组的,打算给仲肯中的代表人物各拍一个十分钟的专题片。那一张张的照片里也不知有没有自己的。仲肯看着怪大叔,怪大叔看着仲肯。这些人却专心看着桌子上的照片,好像看着扑克牌通缉令上的伊拉克战犯。
谁是那个老K,谁是那个A,谁又是接下来依次出现的二三四五六,仲肯感到好奇,怪大叔也感到好奇。他俩面面相觑,而后又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们的动静。
女导演吐了一口烟,而后拿出其中的一张,显然这个人就是她认定的仲肯中的老K,就从他开始拍。女导演又吐了一口烟,烟雾散去后,仲肯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她手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照的,一脸的严肃深沉,似乎凝视着深渊中的黑色浪花。
仲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他拔脚就从店子里跑了出来,就听到身后怪大叔说,跑出去的那个就是你们手中照片里的那个仲肯。仲肯听到他们在身后喊了一阵话,因为跑得太快,话语很快在耳边变得稀碎,好像一锅冒泡的稀粥。他像一只蜜蜂凭着感觉选了一条路,也不知是通向萨麻还是萨闹,更不知是不是通往向尼敦德的。反正,他快速跑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啊,跑啊,跑啊,心里还一个劲地埋怨自己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如果没有忘记格萨尔说唱,这一切该有多美好,可现在却变成了毁掉自己的噩梦。仲肯跑得气喘吁吁,他忽然明白自己的出走变得毫无意义。不是吗?眼前的大地竟然随着自己的呼吸一起一伏。头顶的太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嗡嗡作响,好像一群蜜蜂环绕在上方。一个女人的声音,好像从空中撂下来,砸在仲肯的脚面上。
要知道自己从店子跑岀来的那一刻就被盯上了。一架有着摄像喊话功能的无人机从店子的门口扶摇直上,一切尽在俯瞰之下。
突然,他感到自己的裤管在急剧的拉扯下撕开了一条口子。那个声音好像把自己的心也撕扯了一下。他摔倒在地,爬起身来就看到浑身沾满土尘的野狗冲他龇牙咧嘴。看来,野狗没死,那浅浅的坑困不住它。这时,高空中女导演的声音更加的响亮,声音不仅砸在仲肯的脚面上,还砸向耳朵的最深处。
仲肯,回来。我已经知晓了你逃跑的真正原因。怪大叔和怪大婶刚才向我讲了你已忘记全部的格萨尔说唱,这对于我们摄制组而言更有记录的意义。如果你不回来,依旧选择逃跑,那我会用无人机拍下你逃跑的全过程,你逃无可逃,藏无可藏,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仲肯不由感到一阵晕眩。他看看正抖落皮毛上尘土的野狗,又抬头看看悬浮在天上嗡嗡作响的无人机。一种愤怒从脚跟猛然窜上了头顶。
仲肯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使出吃奶的力气向无人机扔去。
2.老狗
他们说我一到夜里就哭。黑夜沉沉,只有门口黑皮的老狗似乎要定住夜晚,几颗星星眨巴着小眼睛。烟囱里飘出烟子,整个县城都似乎被熏染了一番。
夜里的板房,炉子上烤着的土豆焦黄。
他们知道,我守着个场子。冬天,我披着破皮袍在这片圈起的地,简易的木头杆子缠着老麻绳,一拉一松,便完成拦车杆的起降。
晚间,停车场里的车子,稀稀拉拉。我像一个老牧人。门口的老狗,快变成铁疙瘩了。我像是点数牛羊一样点数车子。
面包车是羊。
卡车是马。
越野嘛就是牦牛。
山在不远处黑咕隆咚的地方卧着,时不时向我耳朵发送响动。
嘎哒嘎哒,好像一截冻土段持续冰冻。我的眼撞上一丝凉,一点也不明白这也算是考验。考验就考验呗,于是我眼睛瞪圆。场子很可能是一片牧场嘛。
其实,我知道停车场是停车场,牧场是牧场。车子的四个轮抵不了活物的四条腿。有些时候,夜深了,所有人都去了梦乡——只有我,披着皮袍。皮袍是祖传的。夜里的老狗,在门口蜷着身子,时不时闷出低沉的吠叫。场子里的车都睡了。头顶的一根木杆上悬着的黄灯泡把我照在一边:耷拉着袍袖。
气氛快赶上天葬场了。
我紧赶着将一个盛饭的铝盆放入空地。老狗闻着味儿,慢悠悠醒转,低眉順目,好像说:谢谢噢。我的皮袍完全罩住小板凳:不用谢。
老狗矜持地站一会儿,良久,才吧唧吧唧吃起来。
我说,慢点,当心噎着。
天黑压压,暗沉沉。几丁星光起不了什么作用。老狗似乎在示意:要不你去睡觉,这儿有我盯着。我抬抬眼皮。一丝睡意竟然像一粒火星嘶嘶嘶漫在瞌睡的草地。睡意让我挪动步子,倒在床上。身子一躺平,却又睡意全无。脑子里指不定会出现几个人。他们中的好些人一生气,便称呼我为其根:老狗。
我耳朵里这样的声音冒上来,便不在乎多几个。夜里时不时就有风吹来。他们问起话,一点礼貌也没有。
其根,你有老婆没有?
我摇头。从来就没有过?
我继续摇头。
可悲,一把年纪了白来这世上走一遭。
白来就白来呗,这又能咋样!
我不断地在床里沉下去。老狗的吠叫,带着点数星星的意味。我听得出来,夹杂着隐隐的不安。——板房的门,突然被推开。悬在屋外的灯,晃悠悠地照着推门人的后背。
一股酒味混合浓烈的香水味,呛得我朝三个方向打了好几个喷嚏。
我使劲揉揉鼻,打开屋里的灯。眼前的一幕竟然吓得我往后退了退。一个年轻的姑娘敞开呢子大衣站在那儿,光生生的大腿,白晃晃的有些亮眼。
我裹紧老皮袍。
她钻进屋。
夜,真要把我脑子里的不一样逼出来。他们肯定打赌了。一方说,其根经不住这姑娘的诱惑。没有另一方。另一方是我自己。我抬眼猛扎扎看到她的红嘴巴,把夜烫个窟窿。
老眉下,老眼中:呢子大衣扑啦啦落在积灰的角落。角落堆着好多药瓶,失效的药片早已死在瓶中,做不得见证。一些凌乱的诊断书被揉得皱巴巴扔在那儿。有了呢子大衣遮盖,这一切一点都不重要。
眼睛继续往前看:姑娘像从天而降,眼眶涂得乌青乌青,脸瘦得有些脱相。只是,我一点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她要在我体内烧一把火。
我脱下袍子,套住这姑娘。皮袍简直像是扑上去,紧裹住她,皮袍上经年的膻味,肯定会打消她的念头。她双手撕住袍襟,试图脱掉皮袍。她一拉,我一收。她拉的时候使足了力。我一收,也用了九成气力。来来回回。
她喊,你拿开。
我说,天冷,你披着。
她喊,其根,他们凑钱雇我陪你过夜。
我说,你穿上我祖传的皮袍,就算过了。
所以,只要套上皮袍,陪我就变成坐在场子的小板凳上。
四周,那些稀稀拉拉的车子盯紧她。我袒露着上身,溜肩上下行的空气拔凉拔凉。老狗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形,说不出什么,干脆,趴下来下巴贴着地。狗头指示的方位:五菱之光与金杯面包车在前,之后是牛头霸道。北京吉普在更隐暗的角落盯着。桑塔纳独自沉思,一个轮胎竟然瘪了下去。皮袍完全像和她达成了一致。
他们肯定想不到,姑娘竟然当着我面哭了起来,刚开始是抽泣,后来变成号啕大哭。他们表示不能够理解,只不过是穿了其根祖传的皮袍,事情怎会变成这样?我不明就里,手足无措。哭吧,有人不是说我一到夜里就哭嘛,也许是皮袍起了作用,哭到不想哭,心也就通透了。
白天,老狗早早就离开场子。整整一天,它都会在县城里晃荡。
晚上,它带着县城的烟火味儿准时出现在门口。那里,铺着一块干羊皮。只要羊皮嘎嘎一响,一召唤,老狗便会蜷成一团缩在那儿。
我啪啪啪拍去白天的土尘。其实,看一个老式停车场也没什么复杂的,不过是一辆车停进来,一辆车开出去,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轮又一轮,一波又一波。我总是重复着升杆降杆收钱的动作。到了夜里自然也就缓下来,慢下来,时间也不像白天那般匆匆,一切都不急不缓。我不住地看着老狗坚硬的狗头,好像听到它慢吞吞道出县城的事。他们总是讲,老狗的说道其实是我自己的编排。当一个人习惯在一只狗面前自言自语,必定会将言说转变为头脑中的对话。
老狗慢悠悠地走进来,依然是吃完我倒在铝盆中的剩饭之后,趴在离我三尺开外的地方。老狗好像在说,我在县城看见那天的姑娘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这都过了一个月,你还没忘掉这档子事。老狗又好像说,有些事情没那么好忘,比如一个号啕大哭的姑娘,要知道我现在都想不明白,她哭什么哭嘛?
我披着皮袍时不时对着场中的车子问一问。问多了显得我很傻。我傻不拉几地说着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得了魔怔。不信你看嘛,我一个人盘腿坐到场中央,似乎要给场中的车子开一个会。会议的议题,一提出来就整得我自己窘迫。
我的老脸沉下来。夜也沉下来。老狗也从鼻孔里喷出几声哼哼。身后传来恰如草丛中的异动。这也怨不得谁,时不时我就会想场子就是片牧场,而草丛中的异动不就是那个姑娘的到来,她来了,明显地换了种活法。头发不再凌乱而卷曲,而像是溪水垂下来。眼眶涂抹的乌青不见了,薄薄的鸭绒衣穿上身,黑色的长裤衬托着双腿,嘴角挂着浅笑让我觉得我是不是认错了人。
我转头看老狗。
老狗点点头。
真是她?不要搞錯。
老狗眼神流露,怎么会嘛,不信你听她说什么嘛。
我有点恍惚,耳朵里被丢进来的是不是一个声音?
我不敢重复,只有在心里酝酿。眼看着这姑娘在我的板房里忙活起来,擦擦桌子,扫扫地,把桌子上的缸子移到床头柜,又被我挪回来。
他们确实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这个姑娘慢慢就和我混熟了,和老狗混熟了,和场子木杆上吊着的灯泡混熟了,和缠着老麻绳的拦车杆混熟了。
我知道混熟后的后果,她可以看我的身份证嘛。身份证上的我板着脸,嘴巴撇得好像不屑于来到人世。眼睛圆溜溜,像挂在舞靴上的铜铃铛。耳朵嘛,不大不小的像捏了河边泥,做出来也就这样。发型和现在毫无二致,是无发型,不长不短,自然生长。
她惊呼,你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其根?
我说,开玩笑,哪有人叫老狗的?
她喊道,你居然叫曲赤,小狗。可现在却成了老狗的年岁。
我只好解释,这是父母亲怕难养活,取了贱名。
她继续喊,哦,原来是这样。那我给你介绍对象如何?
第一个对象是一位厨娘。厨娘胖乎乎臃肿地移步场子。
我知道她看不上我的外形,而且不一定配备了有趣的灵魂。两个人的外形都不过关,拼拼灵魂看看能不能撞出火花。没火花,甚至连烟都没冒。
第二个对象是开肉铺的。老狗好像时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唠叨。
我看这第二个还不如第一个。
我说,何以见得?
老狗在我脑海里说,她常带着亲友蹭停车费,不给钱。
我说,那些钱后来都是我垫的。
老狗继续在我的脑海里说,不要和她来往了。
他们当然记得我刚来县城的情形。
我背着用绸腰带绑成一团的皮袍。眼睛里闪动的火苗,那么小,那么小,那么小,眼看着就要熄灭。他们不要看我眼里的火熄了,其根,所以说,你看场子的工作是我们给你争取的。
炉子上的土豆嚼在嘴里变得稀碎。
牙齿上沾着只有我自己看不到的黑屑,像虫洞。
时不时,夜的边界上醉汉们又开始喊起来。场子的拦车杆总是拦在那儿,好像一条界线。醉汉靠上来,扶住拦车杆呕吐。只要老狗舔了这污秽,它也会醉一夜。
老狗一醉,就变得恹恹的,它趴在羊皮上,把头缩在前爪上,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倒不是说老狗不想什么,而是老狗想什么我压根不知道。只要老狗醉了,场子里的车子就变得烦躁起来。我听到车子无故发出咔嗒,或者叮叮的响声。或者,警报会奇怪地响几声。
我披着皮袍,神情紧张,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拿在手里。
他们清楚我后来松了口气,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地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个醉汉。醉汉裤兜里的手机开始叫唤。一只老狗吠叫的彩铃撕开场子的静谧。重复,不断地重复,重复到好像要把狗叫送到石头里去,送到车轱辘里去,送到车子的机器里去。我赶忙从醉汉的裤兜中掏出手机,接通。
耳中立时出现一个大牧场,好像一下子就在我的脑子里画出界钱。真的,很大很大,有这么这么这么大,总之很大很大很大,大到让我想到我耳边的手机里有天地。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突然冒上来。
小女孩说,阿爸,你在吗?
我看看醉汉,你阿爸睡着了。
小女孩说,他今天很累吗?要在平时他不会这时候睡觉。
我说,他来我这儿玩,所以今晚会睡在我这里。
小女孩说,你那里是哪里?
我说,我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小女孩说,我这里叫一百个帐篷牧场。你那里的停车场叫什么?
我说,可以叫藏獒停车场,也可以叫老狗停车场。
小女孩说,怎么有两个名字?
我说,两个名字,就是大名和小名。
我听到小女孩在笑。
笑聲还未散去,就听到她继续说道,阿念(爷爷),请您转告我阿爸,我阿妈原谅他了,让他快回来。
我点点头。早上醒来,却发现醉汉不辞而别。
我后悔地直跺脚,哎呀呀,怎么能这样?
我摇摇头,披上皮袍,自责的情绪竟然绵延了很多天。
我还能干什么?这点事都干不好。
我坐在小板凳上,突然看到一个穿皮袍的小女孩看着我。她的脸蛋红扑扑,嘴角挂着的笑意让我觉得很亲切。
这不是做梦吧,小女孩朝着我走过来,挥动小手。她站在离我有二十米远的地方。
开始喊起来,阿念,我阿爸回家了。阿爸和阿妈复婚了。我又有阿爸啦。阿念,欢迎你到一百个帐篷牧场来玩。
我兜不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不住地告诫自己:
要稳当。稳当。稳当。
我稳如老狗。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