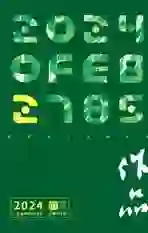让虚构与更高的事物交往(评论)
2024-03-19陈培浩
陈培浩
一
王幸逸才华横溢,叙事老练,已经初具自己的语调。他的五篇小说,题材和写法颇不相同,确是具有炸裂潜质的超新星。让我感兴趣的不止于此。我想他的个性中也蕴藏着某种共性,他希望面对现实,又难以摆脱对梦的迷恋;还有低欲化叙事,与低欲望社会若合符契,王幸逸笔下的人物总是倾向于节制情欲,而非释放荷尔蒙,这无疑呼应着当下的低欲望社会语境和佛系青年文化。这些特征在当代青年写作中,其实是症候性的。我愿通过他,既观察青年写作的内面,也探讨青年写作的某种可能。
且从作品谈起。
《登仙》是一篇具有某种玄幻性的现实型小说,虽然这种玄幻性在叙事上占比并不大。但是,它却是具有症候性而耐人寻味的。通常而言,有现实主义追求的小说非常慎用玄幻元素。因为,玄幻通常是一种类型文学制造阅读快感的手段,它瓦解而非加强了小说的现实感和精神深度。当然,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经过重构了的超现实性,成为小说内在意义生成的要素,这也并非没有。格非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隐身衣》就借助了某种惊悚的哥特式元素,这反而拓宽和深化了小说的现实主义表达。
那么《登仙》呢?这是一篇从儿童视角出发的小说。其中牵涉非常具体而真实的大时代背景,比如香港回归。这个真实历史事件镶嵌于此,绝非可有可无。它是小说现实感非常重要的支撑,也是我们观察当代青年作家现实书写的重要通道。在人们所熟知的“铁西三剑客”的作品中,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工人生活现实得到了反复地表现,与之相关的则是重新书写90年代现实的写作尝试。《登仙》显然同步于这种尝试,通过一个孤独儿童的经历和内心,试图去触及一个逝去的时代。只是,不同代际的作家的现实书写和历史想象,显然大为不同。
小说中,“我”的父母原为春谷县(这个虚构的县名,不知是否为今安徽繁昌县,古称春谷)氮肥厂的职工(也是90年代工厂职工的故事,似可窥见“东北三剑客”的影响)。母亲工作兢兢业业,父亲沉浸于影视文化而好幻想。90年代正是港台流行文化的全盛期,香港电影寄托了改革初期内地民众对现代化和外面世界的无限想象。贾樟柯电影《小武》中的县城青年,正是这个时代的青年。贾樟柯的电影最早以新现实主义的方式展示了90年代真实的中国县城的面貌。那其实依然是一种日常主义式的现实表达。但是,到了“新东北作家群”,关于90年代的现实表达镶嵌了某种新的历史感。这是一种重审和反思发展主义的历史人文视野。贾樟柯的电影可贵之处在于对真实小人物的重视,这在彼时已经十分难得,我们不能强求他当年便能拉开足够的历史视野,观照到身处历史进行时的县城普通人的命运漩涡。多年后,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并非比贾樟柯更有历史感,而是时间的后见之明。但相比于同代人,他们依然是先行者,而王幸逸,显然紧跟着他们的步伐。这不奇怪,共性才折射出症候。
回到《登仙》的故事。早年父亲虽在工厂,却过着街溜子的生活。1995年,氮肥厂大修。父亲试图好好生活,戒掉了打梭哈的习惯,而且借钱在县城买了房子。此后,父亲还和朋友们去广西养蛇谋生,母亲因有孕未能同行。1996年,氮肥厂倒闭。同年,“我”出生了。与父同行的朋友们都已回家,父亲却从此杳无音信。父的缺失,成了小说具有隐喻性的情节设置。“我”成长在没有父亲的不确定感中。为了照顾母亲和“我”,奶奶来“我”家,并拉着母亲去尼姑庵拜佛,老尼为母亲算卦,说“云隐苍梧”,有些事情未必去刻意寻求,缘分到了自然会发生。1997年,在香港回归前夕的喜悦氛围中,母亲一度怀疑父亲去了香港而不是广西。过了两年,母亲在昆仑商场做导购,为了监督母亲的生活,奶奶常带“我”去突袭商场。一次,发现母亲请假未上班,奶奶怀疑母亲在外面有了新的感情生活。经历了跟踪事件后,她发现一个开着蓝色奇瑞QQ的男人是母亲的男朋友,于是奶奶让“我”表演苦肉计,试图用眼泪留住母亲。我九周岁的生日那年,母亲在新世纪大酒店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宴会,但回家后“我”仍然感觉孤独,门外也不时传来奶奶和母亲的争吵,此时的母亲已改嫁。在睡梦中,“我”来到了一个仙境,见到了父亲,父亲给了“我”一面镜子,说它与家族有缘,让“我”好好保管。醒来后,“我”渴望再次进入仙境,远离现实世界,但耳边响起了母亲催我起床的声音。通过镜子上“金华牧羊儿”的故事,“我”悟到:凡人不见的白石,正是他所寻求的羊;“我”像白石一样静卧,等待四十年后被人唤醒。
《登仙》隐藏着这样的信息:青年一代并未进入仇父乃至弑父的模式。弑父往往来自于一种更加具有冲击力和爆发性的文化时期。譬如在80年代余华等先锋作家的笔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仇父、弑父并取而代之的冲动,而新一代的青年,他们活在父缺位的无尽哀伤中。他们感到的是父及其确定性、安全感的缺失带来的惶惑,而不是一种想要重立天地的愤怒。八九十年代,我们在崔健处听到愤怒;在莫言处看到蓬勃的才华,在王朔处看到满不在乎的调侃,在王小波处看到机智的解构……而现在,我们在青年作家处更多看到的是孤独和感伤。一篇关于现实的小说,却导向梦中的镜子与仙境。这不是王幸逸一个人的方式,而是一代人的方式。与其粗鲁地怪责他们缺乏力量,不如再想一想,他们的感伤究竟有何文化意味?为何关于现实的表达,却纷纷导向了梦的表达?我想起最近桂林乐队瓦依那的《大梦》的流行。梦是什么?梦有时是现实的更高版本,更多时候是缺失现实的补偿。以梦为喻的现实,梦表达了现实,是否也部分遮蔽了现实?
二
《忽闻歌古調》是关于爱的篇章。
青年人怎能不书写爱?青年人如何理解爱、想象爱和书写爱,大有意味存焉。想当年,莎士比亚尚且年轻的时候,他写《威尼斯商人》时,对友情和爱何其乐观,他深信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之间的兄弟情深,他相信巴萨尼奥和鲍西亚之间的情侣真情,他相信真诚和真情可以战胜嫉妒和误解!即使巴萨尼奥将鲍西亚送予他的定情信物送给别人,也不会瓦解他们之间的信任。可是,到了《哈姆雷特》《奥赛罗》,他对爱的信心简直跌入谷底。
《忽闻歌古调》写的不是行动的爱、激情的爱、实践的爱,而是感伤的、残梦般的爱。
她,25岁。上大学时,是血气激荡的文艺青年,加入南岳大学的校报《燧石》,关注学校的各种问题。大二下学期,《燧石》编辑部重组,她顺势退出,专心研读古典文学去了。她被大夏大学殷和玄教授的《世间谁有不平事?》吸引,因此决定考研,毕业后顺利地从广州来到上海。在殷教授对学生们青春激情的鼓励下,她开始尝试爱情,于是有了几段爱情经历:初恋来去匆匆,疫情期间的网恋倏忽即逝,然后是与他的相遇。他乖顺、温吞,有过几次短暂的恋爱,到二十六七岁时通过网上认识了她。沪漂几年后成功考上了老家的公务员,所以与她告别。在他临走前,二人决定进行一场真正的亲密接触,然而终究未能如愿,这时,一阵朦胧的歌声闯入房间,忽闻歌古调。
大概每个青年作家都要写一段自己的水晶之恋吧。令人感慨的是,这对在我们看来正是如花盛开的青年,却已有了中年人的壮志消磨和意兴阑珊。他们纷纷在寻找着安全的堡垒和港湾。这在《忽闻歌古调》中是古典文学专业,是公务员的职位;在陈春成那里则是一艘潜行万里,却又封闭自足的“夜晚的潜水艇”。小型封闭空间隐喻着当代青年的精神结构。他们退守到一个最低的位置,守望着一个透明的梦:
一番话使她钝钝地明悟过来:是她沉溺在一个叫作亿万斯年的梦里。面具、争吵、谎话里的一点真心,其实已经很珍贵了。她却始终不满足,反而把一切都葬送掉。
她的自省,透露着当代青年的心法:往后退,退到梦中去。这样的心理,是不会产生把爱作为政治维度来实践的观念的。就像阿兰·巴迪欧那樣。在《爱的多重奏》中,巴迪欧召唤当代人像爱真理一样去相爱,在爱的持续性中去无限靠近永恒的真理。巴迪欧批判了一种将对象他者化的爱情观念,并充满洞见地阐述了爱的可能:“正是在爱之中,主体将超越自我,超越自恋。在性之中,主体最终不过以他者为媒介与自身发生关系。他人是为了揭示实在的快感。在爱之中,他者的媒介是为了他者自身。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爱的相遇:你跃入他者的处境,从而与他者共同生存。”
在青年写作中,我们邂逅了一个又一个返身入梦的青年主体,这是一种现实。但我依然相信,写作者应书写这种现实,但更应与其周旋、博弈,以写出另一种更高的现实。
三
《罗马玫瑰》是关于梦碎和妥协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小说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80年代是中国重新拥抱世界的时代,是一个人们充满激情和梦想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接下来的90年代,虽然开启了与80年代的人文主义者设想完全不同的市场化道路,并引发了“人文主义大讨论”,但是,整体上,90年代的文学想象是非常有力而明亮的。90年代文学中,日常、反讽、肉身等元素纷纷粉墨登场,如今看来简直堪称生猛有力,野气横生。简言之,90年代的书写可能琐碎,甚至向下,但既不绝望,也不感伤。90年代还不懂得讲述梦碎的感伤。所以,还是那句已经变得滥俗的话: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出生于1998年的王幸逸,把八九十年代感受为一个梦碎的故事、妥协的故事,这同样意味深长。当他写老右来祝贺“我”考上友谊小学语文老师的时候,我忍不住轻笑出声。大概只有考编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时代,考上友谊小学语文老师这件事才值得祝贺吧。这是王幸逸的失误?他把自己生长时代的意识投射于故事的时代中去?可反过来想,80年代不也是一个铁饭碗大过天的时代吗?如此来看《罗马玫瑰》,倒发现了两个互照的镜像。80年代,人们纷纷从铁饭碗中走出来,跳进更大的市场海洋中去;而时过境迁,越来越多青年人做了谨慎的选择,重新为铁饭碗投寄了巨大的热情。《忽闻歌古调》中的那个“他”正是选择回家乡当公务员。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幸逸,只能携带着他的时代潜意识,去进入更遥远的年代。这种当代潜意识与历史产生的缝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透镜。
回到《罗马玫瑰》中来。小说安排了两条线索:“我”和她都是80年代的文学青年、先锋爱好者。80年代的北京,虽只见过几次,已有了肉与肉的碰撞,鱼与水的欢愉。她说自己是维纳斯,临走时不小心遗落了印有“罗马玫瑰”字迹的戒指。她走后,我每天都想在人群中邂逅她,但终究无果。另一条线索则来自老右,一个在历史大潮中经历命运跌宕起伏的人。老右曾因家庭成分不好,在特殊时代遭遇命运的重压。他的一个堂叔镇反时就被打成了敌特,他父亲又是“摘帽右派”,但老右的父亲救过母亲和我的命,所以父母对老右很好。哥哥死后,也只有老右还和我做朋友。哥哥曾是红卫兵,“我”的名字赵红卫就是哥哥取的。拨乱反正后,“我”的家庭也遭遇一系列变化:哥哥被打死,之后,父亲死去,母亲改嫁。老右在广州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很快买了三大件,还安了电话。老右这个人物,是中国当代史上的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家笔下都出现过,譬如莫言的《等待摩西》,又如魏微的《胡文青传》。可是,《罗马玫瑰》的重点不在老右身上,也不在“我”身上,而在罗马玫瑰所表征的失落的、遥不可及的梦上。
一天,老右从南方回来,打电话叫“我”去德清饭店,要介绍一个朋友老胡给“我”认识。老右一反常态,西装革履,也点了很多丰盛美食,说明他的朋友老胡是个尊贵客人。老胡还没来,老右说应该在和女友拉扯。其间,老胡劝“我”去南方做生意,“我”未同意。老胡来了,带着她一起出席。觥筹交错间,“我”借故出去,缓解悲伤心情。回来后,酒桌已散,“我”对老右说她就是那个戒指的主人,老右反问什么戒指,你没有给我看过戒指。“我”愕然,不知哪个是真实。最后,“我”同意和老右去南方。
颇有意思的是,90年代的主导意识曾经体现为飞往南方,但在这里,去南方被叙述为梦碎之后与现实无可奈何的妥协。不妨对比一下,莫言写的《等待摩西》,涉及当代史,落脚点不在历史,而在生命的感悟;魏微写的《胡文青传》,雄心就在历史。她试图通过这个人物去理解历史的起伏。效果如何,各花入各眼,但目标指向是了然的。但《罗马玫瑰》虽借助了当代史的背景,目标却不在历史,而在一种主体情绪的感伤和喟叹。
一方面,我们看到王幸逸试图把小说之船驶入自我经验之外的海域;另一方面,我们依然要说,在主体情绪如何与现实感、历史感融合上,青年作家仍有路要走。
四
我们知道,有的小说家,一辈子只能写一种小说,那就是从“我”出发的小说。他只能在自己经验的领地,以自己习惯的那种语调去讲述。这种剑走偏锋的小说家,不妨说聊备一格。但是,小说家之为小说家,小说家独特的魔力,就在于他必须能够讲述自我经验之外的生活。这种虚构能力,对于青年作家而言尤其是一种挑战。但是,王幸逸显然试图不断超越自我经验,把虚构的抓手伸到更辽阔的地方去。《胧月夜》就将虚构的触须伸进了历史。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但“我”却是美国记者史密斯。1948年,受华盛顿总部指派,“我”到日本搜集尾崎秀实的信息,因“我”与尾崎秀实是老相识,便欣然前行。尾崎秀实(1901—1944)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出生于日本东京,共产主义者、记者、日本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特派员、中国问题专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秘书、佐尔格间谍案中的重要人物。这当然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王幸逸要去挑战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平衡木,委实令人期待。
尾崎秀实死于1944年11月,是日本七名A级战犯中的一员。二十年前,尾崎秀实是大阪《朝日新闻》在上海的特派记者,“我”是合众社上海分社的记者,二人常借着工作的机会去咖啡馆闲聊,“我”尤其喜欢听尾崎秀实讲神话故事。日本侵华战争后,二人在上海有过短暂见面。日本入侵中国以后,尾崎秀实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暴得大名,他当时预言了中共的崛起。后来,人们发现他是佐尔格事件的核心成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佐尔格、尾崎秀实被捕入狱。尾崎秀实在狱中一共给妻女写了上百封信。川合贞吉是尾崎秀实在情报事业上的同志,几经辗转,“我”联系上了他。在露天市场外碰头后,“我”把他请进了公寓。喝着白兰地,川合贞吉向“我”讲述尾崎秀实的温和可亲,对文艺的热爱和强韧的乐观。
显然,王幸逸并未将以尾崎秀实为主人公的作品写成谍战小说,他试图在虚构的通道中恢复这个历史人物更丰富的精神面貌。《胧月夜》在王幸逸作品中,显然具有更强的肯定性。有趣的是,小说显然试图理解尾崎秀实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革命的人生理想。但与以往对革命者的想象不同,小说通过尾崎秀实更多呈现了清冷、朦胧但又温和、乐观的“趋月性”,而非一般革命者的“趋日性”。我想说,青年作者王幸逸已经开始透过历史人物完成他对世界的理解,建构他的精神叙事。这是成为小说家的必由之路。略微引申一下,当年尼采推崇酒神精神而贬抑日神精神。尼采的日神精神从内在属性上其实跟王幸逸的“趋月性”相近。这种历史错动,颇堪玩味。
《异闻》是对《聊斋志异·长清僧》的故事新编。原小说短小精悍,旨在通过老僧人死而魂不散,魂寄纨绔公子之身的故事,表彰一种坚韧的心性。“异史氏曰: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聊斋志异》作为古典小说,其价值确认直接而坚定。但在王幸逸的《异闻》中,禅师魂寄公子的故事,却充满了现代性的诘难和张力。
这边厢,瑾少爷坠马后得了失心疯,禅语不断,无人能懂。那边厢,少奶奶异梦频发,梦见自己化为狐妖,被僧人追赶。有意思的是,作者还让老僧和少爷不断展开禅辩,而老僧竟辩不过少爷,最后竟痛下杀手。当人们发现被斩成数截的少爷时,那刀就掉在已气绝的和尚身边。和尚面带微笑,看着不像犯过杀戒后的样子,反而显得修行高深。此后少奶奶也离奇失踪,毫无踪迹。此案敷演成鬼狐故事,流传开来。魂与身的重新结合在蒲松龄那里似乎毫无障碍,但在《异闻》却困难重重,甚至已经构成了魂的强行附身以至暴力弑身。这个极其玄幻的身心对抗故事,却以隐喻的方式而具有现实感。从中我们是可以看到作者的小说才华和能力的。
五
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说: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今天很多人说:大学中文系不仅可以培养作家,也应该培养作家。关键不在于判断,而在于产生判断的时代。杨晦说话的当年文学还为万民所敬仰,神州大地放眼望去,多的是地瓜型作家。所谓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是说,作家用不着大学中文系来培养。及至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春风拂面,神州大地到处都是生意人。越来越少人写小说了,怎么办?只好大学动手来培养盆摘型作家了。于是创意写作兴焉。
作家可以培养吗?写手可以培养,作家无法培养。通过培养走出来的作家,要么他不培养也会成为好作家,要么他只是被吹捧成好作家。
作家的养成,特别有赖于一种暗经验的滋养。阳光经验是一种常规经验,只要阳光经验的作家,只能有太阳系想象力;具有暗经验的作家,才可能具有宇宙想象力。
作家自生于旷野和大地,见过白骨埋于荒丘,穿行过无人的黑夜,听见过不远处若隐若现的哭泣声。仰观过宇宙,俯察过品类,不是从小背着书包上学,规规矩矩走路,在阳光雨露滋养下茁壮成长的作文优等生。
作家是什么?作家是文明人中的莽汉,是闯进瓷器店的豪猪,是一流办公室里的二流子,是上流阶层的痞子胚,也是底层世界的同路人。
我们谈的是一种理想的作家,不是iso体系认证的作家。
以上似乎俏皮了些,我们好好说话。虚构的小说能给予我们什么?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的一段话可能提供了启示,他绝不将虚构当作一种消遣或自娱,而保持着一种对小说完成自身文化使命的乐观:
通过认真阅读小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了认真对待生活。文学小说显示,我们实际上具有影响事件发展的能力,我们个人的决定可以塑造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生活。在封闭的和半封闭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是有限的,小说艺术处于落后状态。但是只要小说艺术在这些社会得到发展,它就会邀请人们思考自己的生活,而且它能实现这一点就是通过小心翼翼地构造有关个人的人格特性、感知和抉择的文学叙述,开始阅读小说,我们逐渐感到我们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选择可以和历史事件、国际战争以及国王、帕夏、军队、政府与神祇的决定一样重要——而且更为不同凡响的是,我们的感知和思想拥有的潜能比所有这些都更有趣。我在年轻时饥不择食地阅读小说,感到一种惊心动魄的自由和自信。
关于小说的功能,中国学者陆建德也有精彩的论述:“作家通过创作一部小说来创造一个世界,我们阅读小说,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认识了一些新的人物,熟悉了一个新的环境。阅读以后,我们把书合上,就好像神游一番,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家里,但会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滋养,而且身上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在小说的影响下,一些变化在我们身上出现。这就是小说移入的力量。诗歌、戏剧都具有这种魔力,但是小说包容性强,力量最大。”“小说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到无数具有挑战性的地域去旅行,那是审美的旅行,也是伦理的旅行。”(陆建德《现代小说与心灵旅程》)
帕慕克和陆建德各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阐释了小说完善心灵以及想象伟大事物的功能。可是,这显然是从理想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的小说和虚构都堪担此任。很多小说不过是白日梦,作者也自觉地扮演造梦者的角色;也有一些小说并不甘于作为白日梦,但作者尚未掌握与更高事物交往的方法,所以常常沦为自我情绪的宣泄。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抱负,其次是方法。在我对90后特别是95后青年作家的不完全观察中,他们的写作似乎普遍表现出一种精致的感伤。精致是因为他们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文学教育,其间已经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写作资源,他们天然地掌握了一种更精致、微妙的文学语言。感伤则是他们作为写作主体普遍的现实反应和精神状态,青年人既容易激情满怀,也容易失落感伤。感伤还带有某种浅层次的审美性,很容易让青年作者和读者沉溺其中。感伤者有情,感伤也表达了对现实的某种疏离和审视,当代青年作家越来越懂得用精致来装饰感伤,但是感伤绝非一個理想的文学位置。因为今天很多青年写作的感伤其实是景观化的。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有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景观的起源是社会统一性的丢失”。我们也可以说,景观的产生是更高的冒犯性的丢失。景观社会的繁复景观背后还镶嵌了一套编码系统,让每个“作者”投身于景观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以,景观是独一无二的套版,是一种无个性的个性。或许,感伤在最初是有冒犯性的。但是,当感伤变得越来越精致,感伤在景观化的过程中便成为失去活力的语言。所以,青年写作者,谁率先从共同景观的统治中醒来,谁率先提供一种未必精致,却能撕开缺口的语言,谁时刻心系重大的事物并心心念念于寻找丢失的统一性,谁就能走得更远。
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教训青年人。我们同样置身于景观中,我们同样是景观的一部分。所以,从景观中醒来,让虚构与更高的事物交往,不是青年作家才面临的难题,而是我们,所有写作者都必须直面的难题!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