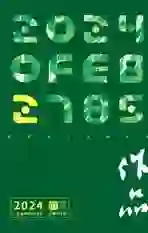繁花(散文)
2024-03-19陈元武
陈元武
一
三月给人以舒心和愉悦,因为春天大抵是如此的诱人,像一枚盛满了荷尔蒙的花朵子房,给人一种迷醉和甜蜜的感觉。柠檬花的香气格外的清新,有时在庭院里,能够被它持续的浓郁的香气所陶醉。普鲁斯特笔下的神秘花园,在一个独处的小院里,隔着无采光窗孔的高墙,有两棵树叶发黄的树,将紫色的柔和的天空托住。他听到滴水罐沿淌下的水滴的声音,那底下有一片瓜叶菊组成的草坪,他甚至想象着隔壁花园里的情形:一个红头发的美女,坐在高背椅上,看着书,头发扑过花粉,是薰衣草的那种幽紫的蓝色花粉,扶手椅一边放着咖啡壶和杯子,在院子角落放着一架拨弦古钢琴,在一张蜗形脚桌子上,放着插满瓜叶菊的蓝陶花瓶,墙上挂着古老的镜框,里头一样有一个女子的幽灵,头发扑着花粉,插着几朵蓝色花,手持一束石竹花。他走到了长廊的尽头,一堵无门的实墙对他说:“现在该往回走了,但您看到,您其实根本就没走动过。”而他无数次尝试着在夜里赤着脚走来走去,未装百叶窗的窗户对于他只是个摆设,它对他说,其实,我们都一直在陪伴着您,一动不动。普鲁斯特在虚构一个密闭的空间:小房间,对面的墙,无法从那里逃出的窗户,隔壁的花园和美女,蓝色的瓜叶菊和持续不断的滴水声音。他更想象另一个更大的花园:长着各不相同的种种睡眠,如同陌生的花卉,有曼陀羅、印度大麻引起的迷幻的睡眠,乙醚引发的梦呓,有颠茄、鸦片、缬草产生的迷醉,这些花永恒不开,直到“由灵魂注定得救的陌生人来触及花蕾让其盛开,并在长达几小时的时间里,在一个赞叹而又惊讶的人身上,释放出它们的特殊的梦的香味”。普鲁斯特是想象力的大师,他的心灵花园里永远是如此神秘和芳香迷人。
繁花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生命最直接的符号和标志,在户外草地上,不难碰到成片的野花,星星点点,掩在草叶间,密芾的树叶构成了花朵的神秘背景。当早梅凋谢后,长出满枝的新叶,柳树的米芽也纷纷绽放,纷繁芜杂的世界,多半是不可知的,像普鲁斯特所说的那种无采光窗孔的高墙阻隔着的无数小世界里,无数的花朵秘密开放,在量子的意义上,纠缠着的物质的镜像因子,隔着遥远的距离互相对应着并产生作用力,像中微子、波色子、强子和弱子、费米子,在质子般的世界里以微皮米的距离闪挪着,互相迷幻重叠。花朵的香气进入我们的身体,产生了迷幻的电流,并通过脑中枢产生无限美妙的感知。这种电流反馈给了我们的鼻子、眼睛和各种感知器官、神经末梢。地上布满了花朵的碎片,有些凌乱无序,酢浆草的花无一例外让人欣喜,粉红、嫩小,却格外显眼,田字形的叶子也似乎像规整的文字符号,但它们却只是叶片叶子,中间的暗深色叶斑让人想象成了田字。野荠的花简单,明黄色,像菊科的千里光,马兰花则像白色的童谣。蒲公英的花高出叶簇数寸,很好辨认,刺蓟的花野蛮而硕大。食草的羊只喜欢野荠菜一种,对于其他的花视而不见。山羊俯下脑袋,摇晃着颔上的长须,啃着地上的荠菜,门牙切出清脆而持续的啮啮声。羊似乎是花世界里的知己,像蓝堇的苦味,酢浆草的酸味,紫花地丁的清香微苦,和野蓟的多汁鲜辣,婆婆丁的大苦,毛地黄的微苦鲜香,羊的竖形眼睛能够从阳光里看到另一种紫外的光线,它能够在花朵上产生异样的光泽。也许,在羊的眼里,我只是一个移动的长着两条腿的木桩,浑身沐着紫外的光芒。像德·盖尔芒特夫人喜欢的圣赫勒拿岛的宽叶杜英一样,在阳光底下的城堡花园里摇曳着白色多瓣的花朵,夏尔·博尔德的圣热尔韦歌唱团的音乐一般充满着阳光和梦幻的意味。五月的阳光落在院中的柚子树上,新展开的宽大柚叶泛着革质的光泽,因此,将阳光片片反射向四面八方,柚花硕大绵密和杜英花相似,在叶簇间闪烁。柚子花带着甜橙的香气,而杜英花则充满着神秘的幽兰气息。羊的眼睛可以看到散射的阳光中紫外线的部分,蜜蜂的复眼则可以看到更多的偏振光和极紫外光。幽蓝色的花和纯白色的花一样,能够反射极紫外光和紫外光线,人的皮肤能够反射一成的紫外光,衣服则更多。在画家雷米·艾融的眼里,紫外光世界是无比奇特和唯美的,他据此将光和物体分割成若干不相干的部分,重新组合成奇妙的复合体,它将绘画雕塑化,立体化了光和影的效果。花朵一样具有可分割和重组的可能。他说,每一朵花都可以构成一个光的世界,同样,每一缕光都可以改变一个视界的感观。他将云、树木、房子、墙壁和管道打乱后重新组合,由“大部件组成的世界里,需要无数的小部件来充实”。纯红色的光代表着太阳的本色,橘红色的光代表着太阳的温度,而黄色和蓝色则是太阳内部核子的光色,波长随着光谱越来越短,直到紫光以外。红光基本上被植物完全吸收,而部分绿光和黄光则被植物反射出来,白色的花朵则将所有的光反射出来,因此,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与羊眼睛里的或者蜜蜂眼睛里的完全不同。也许,野蓟的紫花在羊眼里,只是一片深色的蓝紫斑块,包括它的叶子,这颇刺激到了羊的食欲,羊甚至会将人的衣服反射出来的紫外光当成美味的植物,羊咬住了人的衣服。
二
木荷的花同样是米白色的,厚厚的花瓣则意味着有更多的反射面和吸收光线的能力。木荷树在山冈上站立成孤兀的样子,秀颀而高,但木荷的花让人感觉亲切而迷人,它的香气淡淡的,像含笑花。森林里许多木兰科乔木,木荷是山茶科植物,而厚朴和鹅掌楸则是木兰科,山木兰的花米黄带紫红的蕊芯,萼托也是紫红色的。厚朴花与木荷花期相近,在初夏开放。在山上独行时,除了山风外,蕨草的微腥气息加上松脂的气息,让山风多了些异样的味道。竹子微带着青草的香气,地上的桃金娘也应时开放,桃红色的花轻浮在叶丛表面,梭罗说,这些植物的花朵是地球上最美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繁殖过程优雅得像诗歌和音乐。蜜蜂或者其他昆虫触发了这样的接触,当花粉触及柱蕊上黏性的表面,一部分花粉化为基因的携带因子,与之结合并融为一体,遗传物质交换融合,子房迅速在发育壮大。这个微观的过程能够被紫外光详细记录下来,当蜜蜂看到一团紫外光的污渍残留在某朵花之上时,就知道,已经有同伴来过,并且带走了绝大部分的花粉和蜜汁。
德·康布勒梅夫人喜欢在正午的花园里采花并收集一些羽叶植物,像肾蕨,一些铃兰的长叶子,绶带草的修长叶子能够编织一顶不错的花冠,石楠的猩红色嫩枝、鸢尾花的柔弱蓝色、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和玫瑰,加上一些罗勒和迷迭香的针状尖叶,柠檬树的嫩梢和香茅草,当然,不能缺少橄榄树的枝条。她应该是盖尔芒特城堡里的特别讲究装扮的贵妇之一。然而,她只是一个不算贵族的贵族,或者说是落魄的贵族。于是她极力向往剧场里的包厢,以及包厢里的王妃周围的女人们。她站在那儿,瘦削的身板,细而尖的长腿,她活像只山羊般孤独。公爵夫人们以及王妃的亲信在一旁交谈着,闻着仆人送来的刚刚采摘的鲜花。夫人们因为兴奋而潮红着脸,眉飞色舞着。阳光从不远处的穹顶的曙窗上射进来,彩色玻璃让阳光变得极其复杂而陆离。剧场里昏暗的氛围因为舞台灯光和穹顶的阳光而稍稍改变。猩红色的天鹅绒大幕披垂而下,仿佛红色的盛装大氅,或者是红色的瀑布。星星点点的微光从布幕上反射出来,像满天的星星。亚历山大·加布里埃尔·德康的东方主义绘画中经常表现的那种神秘的,带着朦胧光晕的花朵,在幽暗的林檎丛间闪烁。天幕间堆积着幽晦而泛着微红光的层云,局部松散出一些幽蓝色的天空,但仍然蒙翳着一层薄云。
直到毕沙罗和莫奈的印象主义盛行之后,花卉成了光和影的双重奏,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而主观。柯罗在指导毕沙罗绘画时,给他明确的忠告:你务必在绘画时忘却一切美好的细节,但你必须抓住每一瞬间的光和影。毕沙罗后来的绘画多半是严格的柯罗风格,但他不想完全遵照柯罗的印象主义主张,他更进一步诠释了印象主义的绘画,那就是主观的印象决定了绘画的本质。在莫奈、毕沙罗和塞尚、高更以及凡·高等人的努力下,印象主义的风格得以发扬光大,后印象主义画家们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将一些非必要的元素去除,而只留下重要的“结构和形式”。像修拉的针点式绘画和凡·高的变幻的曲线条和颜色重构,塞尚的立体结构和高更的重彩色块排列。后印象主义更加强调了主观的元素,不是印象给人怎么样的效果,而是他主观给人什么样的印象表达。凡·高的《向日葵》系列是他勇敢实践的杰出成果,当柠檬黄色和木乃伊褐色,以及铬黄、铬红和纯蓝纯灰纯白相间时,向日葵便鬼魅般复活了,即便过了一百多年,站在它面前,依然能够感受到凡·高的精神漩涡如此复杂而强烈。它是暗示,是无名的诗歌或者音乐,是狂飙式的精神火焰和暴風骤雨式的洗礼。
三
我站立的脚下,是一片松散而泥泞的土地,红色或者灰褐色的泥浆像吸盘似的让我寸步难行。只好远远地看着一片在夏季风暴过后盛开的罗望子花,它浓烈、猩红,星星点点,在类似于金合欢树枝叶的棘刺间闪烁着,这是一片晚云映照过的树林。南方的夏和春天是瞬间转换完成的,因此,春末的时节,暴雨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刺桐花和凤凰木都开过了,夏天便正式到来。合欢花的香气彻夜彻昼地弥漫,甜腻到了极点,蜂鸟和叉尾太阳鸟不时在屋檐底下的阴影里歇息片刻。紫藤的浓荫下还聚集着别的动物,比如我的猫。橘猫仰头盯着紫藤架上的小鸟,似乎在盘算着怎样下手。莲雾树和蒲桃已经谢花结子,只有石榴树半花半果地延续着红色的主题。林风眠先生是花卉绘画的高手,水粉画花卉一直是美妙而永恒的精品。他喜欢画百合、鸢尾花、美人蕉、木兰和水仙,他的荷花系列更是绝妙如梦幻,没有太多的技巧,也不讲结构,更不像莫奈那样,为追求光和色彩变化而将画面变得极其复杂。他的荷花清新淡雅,白的荷和墨绿的叶,盘盘,旖旎、磊磊落落。鹜鸟、三五水禽,芦苇和铅灰色的天幕,远山依依。林氏的画风简洁而不失于清旷。
南方的四季,多半是阳光炽烈,空气清新,紫外线强烈的户外,大地呈现出一种深邃的铅青色,荔枝林、龙眼林、芭蕉园、棕榈树,在山坡上的青冈栎、楮树、木荷等,将大地的赤色掩映尽失。正午阳光烤着柚树和柠檬树叶,散发出青柠檬的香气,刚刚谢蕾的柠檬果墨绿色,泛着油质的光泽,柠檬皮上有许多气孔组织,外皮的赘生物让其颇为丑陋,但很快它就长开了。南方人称柠檬为带花的水果,它总是芳香迷人,从花开始。那些被人遗弃的老式旧房子像废墟般陷于时光之井,在坡地的村庄旧址上仍然存在着,逐渐被藤蔓蒙络湮没,无处不在的罗望子树和构树会湮没任何一处空屋和无人的村巷。苔藓像风里的花粉般浸漫在每一处空墙上,和石头、砖头融为一体,幽绿或者昆黄,而后在不经意的一场雨里沆瀣成泥,或者迎着风暴抽出细小的苔米,绽放成细小的白花。沿着干涸已久的废弃水渠边走着,马樱丹开得颇为热闹,这种外来的野草长势喜人,不会因为干旱而枯萎,肾蕨类在石缝里长得绿意盎然,佛牙草成片地占据着道路边的空地,微微挺着细小的茎蔓,偶尔开出黄黄的碎花。空墙上的苔渍更像是水墨丹青的写意,皴擦洇染,黄宾虹在与友人论画的书札里说,徽州的民居白墙上多有苔渍,如画般美妙。那是层层皴擦上去的,并不容易区别其层次,或者多层相互洇渗,互相纠结,终成那斑驳的样子。这其实与石涛所说的大皴擦是一样的道理,石涛用一个字来形容“化”,一切有形有态的物,都是可化开的,山石如此,溪流如此,树木花草如此,甚至是人。一个化字,甚是精妙:将边缘模糊化,物与物就融合在一起了,再染出层次,从淡墨到浓墨再到焦墨,从留白到沆瀣一片,无不尽其妙。汤显祖《牡丹亭》中有段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道是无晴却有晴,人总是这般矛盾僵持着纠结着,内心里无限的繁花美景,到头却总是凌乱、憔悴和无奈。像黄宾虹的画,有人嫌它太污了,一团污黑,画面凌乱,而他们并不知道,恰恰这凌乱之处,方显出繁花点点。只是眼光的不同罢了。
世上总是存在着有意和无意两种花,比如这漫山遍野的花,谁人有意过它们?一树树李花白似诗句,紫云英艳如云霞,不过转瞬宛尔,一阵风过,纷纷扬扬,都似下雪,紫云英过春分即成片凋萎,成为泥淖中的一抹残红。有意的花,却长开不败,花不需多,一二足矣,千利休的侘寂艺术,以枯草、干花入景,瓶中常开不败,像枯荷的莲蓬,枯了,却定了,不再改变,像是超出五界之外,在侘寂艺术的插花风景中,枯枝、干的芦苇芒、干的满天星、五角槭、枯的藤蔓,甚至是用白石子营设出的枯山水,一江水痕,一帆一桨、一舟一人,石上尽是纹理,无一处生机,却处处生机。“浑似江天尽一粟中,纤细委婉,尽在虚无之间呈现无限妙趣。”无意的花就是天然之花,无尽意在其间,一念生则万物生,有些风景确实可以靠想象而得,欹则的梅、野渡的芦苇、舟楫、旷游的白鹭,水凫和鹈,闲云生于岩岫山林,纯属无意,一松一榛亭亭于水中孤岩上,无意之妙,像水中的藻荇交织,曼妙如舞裾,无意之妙。比如拈花一笑,看似有意,却是无意,无意者得之,有意则枉然。《景德传灯录》里记载了一些禅宗故事:“有康、德二僧来到院,在路上遇师看牛次,其僧不识,云:‘蹄角甚分明,争奈骑牛者不识何!其僧进前,煎茶次,师下牛背,近前不审。与二上座一处坐,吃茶次,便问:‘今日离什摩处?僧云:‘离那边。师曰:‘那边作摩生?僧提起茶盏子。师云:‘此犹是蹄角甚分明。那边事作摩生?其僧无对。师云:‘莫道不识。便去。”这便是有意与无意的辨认。赵州和尚说“吃茶去”,就是破了有意与无意之争,云在青天水在瓶,都是无意之意。“毗卢顶上起寒涛,没手泥人斩怒蛟,聩耳千程闻蚁斗,失明万里见秋毫。”岩上起苍苔,也起禅机,一梅著花一梅落,各是天真各自然。
四
猫对花是不太喜欢的,猫的瞳孔是竖着的,对光线极为敏感,因此,对明色调的花并不太喜欢,猫喜欢躲在花荫里睡覺,偶尔看到蝴蝶飞来便有了兴趣,起身扑蝶,结果,蝴蝶没扑着,将一树花弄得一地憔悴。猫虎着脸,瞪着远方,似乎远方才有它喜欢的东西,有它想知道的答案。猫主人往往容忍了猫的造次和鲁莽,花开了败了,日子浮在阳光底下,在叶子之间,像偶然闪现的云翳,没有什么是恒久的和重复的,日子也一样,但猫是个例外,它日复一日待在同一个地方,百无聊赖地看着某一处,墙上的老藤上抽出一截新芽,像绿色的蝴蝶似的舒展开,这吸引了猫的关注,也许,在猫眼里,它就是个能灵动的昆虫或者花朵。猫眼是色盲,或者说是昼间的色盲,到了夜间,只需要红外反光的猫眼,像夜视仪似的看清黑暗里的事物。因此,猫通过嗅觉和听觉来了解世界,和主人沟通,它喜欢主人的身影,喜欢主人的一切,包括臭鞋子。猫经常将主人的臭袜子藏起来,让主人一阵抓狂,或者将粑粑弄得很臭,腚沟里沾着猫砂就上了主人的床头,让主人注意到它的存在。猫眯缝着眼睛往光处看,偶尔惊讶地瞪圆了眼睛,看着主人做让它惊奇的事情。一本书打开着,一行行字像蚂蚁似的列队,灯光柔和地照着书页,它看看桌上的一切:除了书还是书,一个长音箱偶尔幽幽地响起音乐,音乐是主人喜欢的吉他曲,偶尔换成了古筝或者古琴曲,弦切音和弹拨的音符,像不连贯的水滴,甩向虚空,也甩向了多维度的时间深处,像淌向了水缸里,或者是水井里的水滴。有一朵花开在这音符的串珠上,白色洁净,微微透明。猫似乎看到了那朵花,在灯光的柔和照射下,书页上也映出了对应的花影。一朵玉兰花,乡村称它瓣兰花、玉簪花,这不是春天时的玉兰花,南方的玉兰花也指夏季开放的形如玉兰的白兰花,它是常绿乔木,叶子宽大,浓荫蔽日,树形修挺,白兰花就缀在枝叶间,不甚起眼,但香气浓烈,一棵白兰花树足够让方圆数十米都浸沐着它的甜香。那种香气不轻浮,反而有些内敛,猫喜欢在树底下酣睡,风吹树叶沙沙响,仿佛是它的摇篮曲。
三月底,花基本都开完了,只剩下了荼蘼花还在继续,木香花是荼蘼花的一种,蔷薇科的木香花和玫瑰、月季一样,延续着漫长的花季。那幢楼在一排老式的洋楼之后,过去是某个富人的别墅,现在被收归某机构作为办公场地。院里有一棵流苏树,三月底,流苏满树白花,细长如檵木的花,缀满了枝头,风一吹,满树摇曳的花影,洁白、宁静,在阳光底下如同一首圣洁的赞美诗。墙头附着一层毛茸茸的绒苔,沿着砖缝写出一个个方形的文字,老式的百叶窗总是关闭着,偶尔开着一条缝,猩红色的窗帘就被风挤出窗框,在窗台外鼓成一个球形。老式的木楼板被重新铺设后,已经失去了木质的吱呀吱呀声响,但女人走过时仍然咚咚地响起,女人的高跟鞋就是敲响地板的鼓槌。有时候,有人高声唱歌,歌剧里的美声唱法,从另一幢老洋楼的窗户里飘出,院子里的香樟花弥漫着清新而纯粹的香气,这种比玉兰花更甜美的香气,足够让一切都变得极其美好,比如这歌声,女高音加上钢琴伴奏,理查德·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和朱塞佩·威尔第的《阿伊达》。埃及王手下战将拉达梅斯率部出征,迎战埃塞俄比亚国王阿姆纳斯洛。此时埃及王的女儿阿姆涅丽斯公主爱恋着拉达梅斯,而拉达梅斯的心上人却是阿姆涅丽斯的女仆阿依达,而这个女仆不是别人,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阿依达公主。盛大的欢庆场面映衬着凯旋广场上武士们列队整齐,迈着胜利喜悦的步伐。阿依达却在俘虏中发现了成为囚犯的父亲,他伪装成普通的士兵。埃及王和公主忙于准备赘婿招夫,拉达梅斯陷于痛苦的纠结中,他不愿意娶埃及公主,同时又为身处险境的阿依达担心,最后,他放走了阿依达和她的父亲,却惹怒了埃及公主阿姆涅丽斯,报告了埃及王,将拉达梅斯判处活埋之刑,阿依达决定和他同归尘土。女高音忽而高亢的声音仿佛有着强大的穿透力,在阳光斑驳的树荫下,这金属般的高音回荡着,世界因为有了爱情和悲剧而变得丰富而深刻。钢琴伴奏毕竟缺少了点丰富的交响乐的感染力,只是替女高音做了衬托和渲染。前院有个咖啡馆,也同时是茶馆,院里有一棵紫薇树、一棵广玉兰和数棵香樟树、紫薇树和广玉兰并不大,应该是刚刚种下没多久,而香樟树则是和洋楼同庚的事物。古老的香樟树撑满了整个院子的天空,唯独向西的一角留下一方空间,这里恰好被紫薇和广玉兰给填补了。铁艺的栅栏和铁门给花留出了想象的空间,店主人不时会让一些应时的花卉在铁艺门和栅栏上攀附出一种小资的情调。像三角梅、铁线莲、炮仗花、紫藤,当然,细花蔷薇和木香是首选,像欧月藤本之龙沙宝石、黄金庆典、夏洛特、金雀、甜蜜马车、达·芬奇、玛丽皇后。光和影在花墙上充分融合,剩下的就是诗一样的时光在慢慢流淌,缓慢的时光沿着墙角的阴影一点点地往上延伸,太阳也一点点地往西坠下。下午三点多,喝咖啡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那只橘猫似乎受到了情绪的感染,变得风情万种。不时在墙头和花台之间跳上跳下,或者在台阶边伸了个懒腰,打个哈欠,竖着尾巴,走着优雅的猫步。
客人很安静,或者面对着阳光,或者背向阳光,浑身被光线剪出一个动态的身影,金色的光成了他的最优美的边际线,面对阳光的脸上,满是生活的宁静和艰难荟集成的憔悴和苍老,难掩的疲态,他努力保持着优雅的姿态,不让随时想张开的嘴发出一声哈欠。他或者看着手机,或者手里有本书,棕色封皮或者灰色封皮,有着缬皱的浮雕修饰和烫金的书名。文字或者潜藏于咖啡和微风挟带的香气里,远远地只能够看到一行行细小的灰黑色的文字沿着米黄色的纸页爬行,像蚂蚁一般。在一张胶片唱片的发烧友家里,看到一套杜比音响的Arkroket黑胶片唱机,整整占据了半个墙面。胡桃木色外壳在柔和的灯光下显得像艺术品似的完美无瑕,播放着《Title:In the Wee small hours》。弗兰克·辛纳特拉的带着南方口音和烟腔调的爵士乐,他和艾拉·费兹杰拉的二重唱使得爵士的魅力像浓稠而香甜的咖啡一样香气四溢。
五
夜晚之前,客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子夜前后,来喝酒的人比喝咖啡或者茶的人更多,但院子里反正冷清了,院里几盏昏黄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灯照着三五斜靠着高背椅背的青年男女,不锈钢勺子碰着杯沿叮当作响。几盏射灯照着老洋楼的红砖外墙,也照在老香樟树的叶荫下和树干,幽幽的绿光染得香樟树魔幻失真。空气似乎也被灯光染绿了,斑驳无状。偶尔升起的香烟气慢慢扩散开,像图腾似的在院子的空间里展开。有些人影也似乎被投影到墙上,高大而失真,像蒙太奇。橘黄色的射灯让洋楼的墙重新焕发出一种民国式的情调,相信过去的人喜欢音乐和咖啡,喜欢在院里种满花卉,在半幽暗的维多利亚灯具照明下,独自品味着那微苦而香气浓郁的拿铁。应该有个人在念某些诗歌,或者轻吟某个歌曲的唱词。男男女女眼带微醉,明眸波光盈盈,浅笑低语。丁香茉莉是一种有着浓绿叶子的花卉,在初夏到深秋的夜晚,它的香气总是幽魅般袭来,白天,它的花收拢成憔悴的模样,到了夜晚,就绽放开,洁白得像一朵朵栀子花或者茉莉花,它的蕾密集,有着修长而宛尔的长萼和花柄,像丁香。丁香茉莉在铁艺栅栏的花格上攀附成藤本形态,和木香、蔷薇月季融合为一体,彼此互不相干地开着花。洋楼咖啡馆的主人喜欢这种混色的藤本,也喜欢玫瑰花的甜香和丁香茉莉的幽香混合,不分白昼和黑夜。雨季时,地上总是落着树叶和细小的枯枝,地砖缝隙里偶尔也有绿苔的影子,但总能够在白天到来时,收拾得干干净净。女主人偶尔自己来冲洗院子,拖地刷来回刷着地上的苔藓,那些青石板和方砖表面总是洁净如初。
五月底的福州夜晚,已经像盛夏的情形,燠热潮湿,白天的太阳留下了全城桑拿般熏蒸的感觉,直到后半夜,才有微凉的风从江面吹来,吹在身上湿哒哒的,让皮肤黏腻不适。但晚睡的人越来越多,在江边的公园里,长椅上东倒西歪着一些光着膀子的市民。洋楼咖啡紧邻着一条马路,隔着马路和江边公园形成一个毫不相干的风景。这边的人衣冠楚楚,虽然燠热会让他们浑身汗涔涔,吹着摇头电风扇也无济于事,但他们绝不会光着膀子,在院子里大呼小叫。爵士音乐也和江边公园里嘈杂的广场舞音乐或者喧嚣毫不相干,院子里会受到马路汽车和江边公园里的噪声的影响,但似乎,在他们的内心里,只有爵士音乐和柔和的灯光,树影摇曳,夜晚如此美好。内心就是世界的全部,当然,那些江边的人也一样,他们有着他们的世界和快乐。
在公园的花格砖外墙外,一排幽加里树正在开花,俗称柠檬桉的幽加里树花在五月盛开,恰好和银桦树同时开花,幽加里树的花像蒲桃花,米白色,微带亮黄的花芯,四下舒张。远远地看,又像是银合欢花。柠檬桉的清香带着桉叶油的刺激气味,强烈覆盖了别的花香。银桦的花像是深橘黄的缬边,连缀着在羽叶间和枝丫底下,仿佛长出的菌类。合欢花也正在开放,像槐树的叶子,羽绒状的花序,粉红到粉白,分不清花瓣和花蕊,洋合欢的花带着浓烈的幽香,这些树都是过去闽江边使领馆的洋人们带来的,现在扎根下来,成为本土的风景。过去这些旧洋楼的外墙都被改造过,抹上厚厚的水泥白灰,刷上涂料。写上若干大铁锈红的标语,铁艺也全部拆除,砖墙凌乱颓圯,几为人忘记,如今重新修葺复原,恍如隔世。在旧法国使馆的洋楼里,旧的百叶窗仍然保留,重新刷上浅绿色的油漆,楼顶安放一个高卢鸡造型的风向标和避雷针。院门口的左右门柱上安上铁艺的猫造型,一只橘黄色的猫和一只黑色的猫,据说这是当年公使夫人最喜欢的猫,猫去世后,公使夫人要求按猫的颜色和形状做一只猫形门柱标志。
那只橘猫懒洋洋地睡过门房外的过道旁,紧挨着一盆垂花茉莉和一棵鱼尾棕榈树。洋楼外的阳光已经有些强烈,往年这时候,每张咖啡桌上都会支起一把阳伞,香樟树的浓荫都抵挡不住阳光的强烈,加了遮阳伞之后,仍然有些闷热,但毕竟可以或坐或躺,抱着一本书,点一杯咖啡,看一下午。橘猫跑过来,大概是闻到了甜点的味道,仰着头,摇着尾巴,给了它一块甜点后,它就立马跑开了,回到了花盆边上,垂花茉莉的香氣大概是它最迷恋的气味了。五月底香樟籽开始成熟,逐渐变黑,不时掉落,砸出星星点点的渍斑。香樟的清香气味,使空气变得清新美好。外边马路不时飘过来的油烟气和汽车尾气的味道,但这不影响院里的空气保持着清新自然的状态。下午三四点是闽江涨潮的时刻,江水浑浊起来,浪花拍打着岸边的石墙,像节奏器似的。泛船浦大教堂那边,总是游客如鲫,放风筝的人手持风筝,迎风追跑,五颜六色的风筝升在百米高的天空中,像开到天上的花朵,长长的线就是花的柄。银杏树高而修长,没有旁枝侧丫,写生的人专注着眼前的风景,灰色的教堂屋顶,落满了层层的积垢,似乎永远无法清理干净,这多半有苔藓的缘故。它现在纯粹只是一个网红打卡点,门永远关闭着,褐色的木门似乎跟灰色的屋顶一样陈旧而落灰。尖穹顶的彩色玻璃窗上,映着一轮夕阳,阳光似乎支离破碎,分割成若干明亮的小块,或许,在教堂内的地上,留下了五彩五花筒般的光影。但这只是猜测,在门后边,是永远的谜。当年的法国驻福州公使克洛代尔·P是法国诗人、剧作家,他在《福州印象》里这样写道:“这个南中国最美的城市里,总是不乏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热衷,他们有着像塞纳河一样的闽江,有着上千公顷的茉莉花田,在城市的街道边,还种着无数的著花乔木,像紫薇、玉兰和含笑,他们对玉兰的喜爱甚于茉莉,当然,一些从郊区来的女人们会挽着花篮子,装着串成串的茉莉花和玉兰花的花环,他们习惯将这些花环挂在胸前、手腕上,或者在屋里的任何地方,那种完美的香气弥漫着整个夏天的夜晚和白昼,若干天后,将干枯的花摘下来,泡在杯子里,当成了茶饮。”作家郁达夫来福州时,就住在烟台山下使馆区的洋楼里,他说,福州这地方真是奇妙的城市,不仅有摘不完的花,茉莉、丁香茉莉、白兰花和桂花,这里的桂花竟然四季常开(四季桂),大户人家里总有不断的鲜花采供,从洪塘那里过来或者建新村过来的花沾着新鲜的露水,有荷花、白兰、茉莉,成串的茉莉和白兰在花妇手里拎着,见到行人就喊:要茉莉花不?刚采摘下来的!那些妇人脸上挂着谦逊卑恭的神情,希望每个坐黄包车的老板都能赏一两块铜板,将花递过去,然后满心欢喜地走开。向晚的闽江边,拥挤着运货的驳船、水工船、渡船,码头上同样拥挤着过渡的行人,郁达夫说,他们或衣衫褴褛,苦力则光着上身,只穿一条宽而污黑的大裤衩,光着脚板,肩上扛着卸下来的货包匆匆往街上走去,少数坐在黄包车里的老爷太太们衣着光鲜,黄包车旁不时挤着一些小乞丐向他们讨钱。船夫们的衣裳是蓝色粗布的宽襟衫,便于干活,自然打着若干补丁,码头边洗衣的妇人,则趿着木屐,走在石板路上,橐橐作响。她们挽着袖子,脸上满是汗水和燠热产生的红晕,她们身材高大,福州女人的脸相骨骼分明,不像苏杭妇人那样,圆脸盘,眉眼全在一张包子似的脸上。
五月底,福州陷入漫长的雨季,水稻已经抽穗开花,郊区的荔枝已经半红带绿。洋人们怕热,老早就坐着滑竿小轿上了鼓岭,一队仆人帮着驮运行李,大箱小箱的,往山上走。鼓岭海拔在一千米左右,气温凉爽宜人,湿度较大。美国人加德纳的别墅是纯石头垒成的,加一个简易的杉木歇山式屋顶,铺着灰瓦,院子也用石头垒成,没有院墙,也没有篱笆,顺着山势搭出几级平台,底下是孩子玩的秋千架和花园,上边是他们喝茶休憩的平台,加德纳夫人弹着钢琴,她妹妹在一旁唱着诗。加德纳则和朋友们在屋外泡着清香的茉莉花茶,一边聊天。鼓岭上因为寒冷,只有石楠花和杜鹃,还有高山木荷,夏天时,柳杉长着一串串长花序,幽幽的杉木香气弥漫于周围。茉莉花开得比山下稀少而小,高山木荷则满树白花,甜香悠远。他的猫是长毛的缅因猫和本土的虎纹猫,大约有四五只,山上的猫野性勃发,目光炯炯,照片里,除了缅因猫表情忧郁外,其他的猫眼神里带着野性的电光。一年中,鼓岭的花总是常开不败,像铃兰、白兰和垂花茉莉,野花开时,夜晚的山野间,浮着虫声和萤火虫的微光,雾气不时拥塞过来,白茫茫的一片。
六
四月底的雨像任性的孩子,瓦屋像一架琴在雨中弹响。向晚的雨淅淅沥沥,欲续还休,黄卷上的字在灯下发出一种柔和的墨光,纸质的表面,是无数次摩挲留下的痕迹,而墨迹也稍稍漶开,透入纸里,岁月留下了墨香之外的陈腐的霉味,微微地酸沤,恰好是一本书最好的味道。文人之所以酸腐,与此不无关系。文字像干枯的花夹在书页之间,乍一看,并不太入人眼,再细看,仿佛往昔的容颜浮现。关于茶的文字不少,我喜欢雨夜独饮,酌与饮似乎相通的,只是酌酒使人昏,而饮茶使人醒。如此雨夜,断不可轻率地就寝。帐幔之外,可以烛光摇曳,也可以是青灯黄卷,禅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有关于禅与茶的故事甚多,饮茶如我,则无需烦琐过程,一盖碗、一壶一杯一茶洗即可,水预先烧好,茶如乱龙入宫,在盖杯里摇一摇,晃出香气,水冲下去,嗞嗞作响,茶叶便苏醒过来,茶水旋即红酽,倾出,杯里满是幽幽的香和柔和的色。石乳茶和白鸡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茶种。白鸡冠长于峭崖之上,少水少土,长得极艰难,茶叶带微白绒毛,泡出来的茶味清而淡,持久,而石乳长在谷间乱石间,虽有烟岚水泽,然其性烈如肉桂,香如碧醴,味浓烈而冲喉,一杯下去,浑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无不张开,味如石乳者,此茶而已。因此,有些花树长得细瘦,是因为环境使然,寸土难得,涓流难觅,茶是灵秀之木,少了水,自然滋味寡淡。而禅者,无分别为第一要,饮茶有浓淡,参禅无始终。仿佛雨滴打在芭蕉叶上,时急时缓,时重时轻,像古琴曲《半山听雨》的音韵节奏。参禅或者需要内心的清净,略闭目,听茶铫中水砰然作响,炭丸微红,散着热气,炭木的香味随之飘散,水从铫嘴里溢出,化作一团浓雾,倏然就升华了。而闭眼之间,宇宙不再是那个庞大无极的时空了,就在眼与心之间,仿佛有一些光明出现,续而光愈明亮,内心仿佛就被彻底照亮了,纤毫毕现。有时怯懦、茫然无措,失意怅然,惶然如失,或者有所心动窃喜,继而癫狂,如宇宙间的星系、恒星、行星,错综复杂,一时萦系纠缠,互相盘桓逐斥,时而合而为一,时而纷斥星散,土崩瓦解。“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金刚经》)一合相是宇宙的总称,众尘和合为一世界,而世界本身就是空无一物的,连微尘都没有,所以说是非一合相,而无即是有,众生妄执以为实,故非一合相就是一合相,这好比花的正面和背面和侧面,花瓣重叠合而为一,无数的花汇成一个世界,而在虚空中这其实是虚幻的,并不存在,像万花筒变幻出来的景象,要看,那无比纷繁复杂,却只是虚幻的视觉。从无限远看到的星系,只是它数亿年前发出的光,这影像也是它数亿年前的样子,现在的样子谁也说不清了,这就是我们所感觉的和真实的区别。闭着眼睛听雨,就有无数种感觉袭来,雨仿佛滴滴可见,又仿佛连成线,汇成流,持续撞击着屋瓦,在树叶间砸出持续的声音,忽大如涌,忽轻如诉,时而急湍奔岸,时而轻风细雨,轻重缓急,不正是音韵琴律?初夏的夜,有些闷,需要开着微风扇,吹着周身,才不觉黏腻,风是一味良药,驱散了污浊,也驱散了室内的异味,风是通窍的,五行中无风一说,而风其实是属于五行之外的一种介质,是五音和十二律吕,张炎《词源》说:“十二律吕各有五音,演而为宫调……黄钟宫(均),黄钟商(调式),黄钟角(调式),黄钟变(变徵调式),黄钟徵(调式),黄钟羽(调式),黄钟闰(闰宫调式)。”宫音高大响亮,长远以闻,商音嘹亮高畅,激越而和,角音和而不戾,润而不枯,征音焦烈燥恕,如火烈声,羽音圆满急畅,条达畅快。《蠡海集》云:“萬物之所以为生者,必由气,气者何?金也,金受光顺行为五行之体,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冬至起历元,自冬而春,春而夏,夏而长夏,长夏而归于秋,返本归元而收敛也,逆行为五行之用者。金出矿而成革,于火以成材,成材则为有生之用。然火非木不生,必循木以继之,木必依水以滋荣,水必托上以止畜,故木而水,水而土,是则五行之类,土以定位。”不唯我们片刻离不开气之畅达,而风助火,风助金,风也助水、土,唯一伤的是木。气之为炁,是结合了五行和五音之起承转合,本身就是一曲无上的雅音。《乐书》里说,辛公善埙,《拾遗记卷》里说“疱牺灼土为埙”,古人知风入窍而作鸣响,埙是风与泥土最好的碰击之音声,泥土经过水与火的抟炼,化为陶,具有了金石之质,埙之鸣,则是最原始的音乐,古琴是更进一步的乐器,伏羲闻凤凰之鸣而定音律,造琴瑟。木与丝弦的共振,形成了雅音,看似少了风的参与,而实际共振形成的音波,正是风的一种形式。雨落江潭,似乎是水与水的碰撞发出的声音,而雨落携风,撞击形成的声波涟漪,也是风的一种形式,唯雨落瓦上、石上、树上,则是水与石,是柔与刚的碰击,落在叶子上,似乎是水与木的碰击,这些自然形成的声音,无一不与炁有关,自然的炁,就是阴阳之变,就是风。断断续续,淅淅沥沥,若有若无之间,自然之炁便在流通中,并融入了我们的身体。人本身是一合相,自然也是一合相,人和自然不可区分,互为交融,音声、气流振动,萦回羁縻,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混为一体。因为,入定时的感觉,仿佛身在虚空中,如临不测之渊,如立万仞之山,云来云往,周围全是那种宇宙的信息,似乎有琴声,有啼鸣,有私语,有微澜如莲涌,有异光如幻彩。便不觉虚空,人如在水中,万流穿身而过。
七
香道中有一种浸花香道,最早的香道讲究艾蒿、香花、香叶等植物笼取,薰香之囊谓香囊以避秽驱疫,后来改为燃香,增加了木质香和动物香料如沉香、檀香、木香和水樟香、柏子香、苏合香、没药,加上龙涎、冰片、麝香、灵猫脂、海狸脂,《离骚》里提到了许多佩香的习俗:“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南方以香蒲、菖蒲为蕙香,以泽兰和艾蒿为菌桂,以八角、香榧、花椒为申椒,以水樟、月桂和桂皮为菌桂。浸花香道以鲜花为料,取当日初放之鲜花,放之酒精中,淬取其香,取其浸液,蒸馏,得香水,以大马士革玫瑰、白兰、茉莉、栀子、桂花、苏合子、月桂皮、辛夷花、荷花、花椒子、香樟花、荔枝、龙眼花、兰花、羊蹄甲花、薰衣草、迷迭香、罗勒、薄荷、柠檬花叶、橙花、柚花、橙皮柚皮、香柏子等诸香,香水中加入龙涎定香,南方的豆蔻花,也就是艳山姜花,其全株皆可浸香。燃香则多为木质香和香料植物的混合物磨为细粉,以特制香道器具,在香炉内燃点,室内雅香阵阵,人置身其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山野之间,必有香树香草香花,南方多烟岚瘴气,瘴气是南方春夏季大地上浮着的一种水汽,夹杂着病毒细菌微生物和霉腐潮湿的气味,在太阳升高之前浮于地表,吸者有胸闷中毒之感,气促心慌,呼吸不畅,或者因中瘴而昏迷倒地。河流中也有瘴气,多发于晨昏之际,河水鼓沸,毒瘴泄发,沿河面飘浮如雾,闻者立倒不起。河中行舟者多燃香草以避之,嘴里含鸡舌香,燃艾蒿,烟气蒸腾,则毒瘴不能侵。毒瘴为暑湿之毒,犯人心肺,使昏厥失志,腿脚无力而失足河中。季夏南方,河水潴滞之处,水色异样,初绿如漆,继深褐如浓酱,再漆黑发臭,令人掩鼻。老人走近河边之前,必以石投之水,激起河底瘴气,待风吹散,方可近前。鸡舌香、豆蔻香可破瘴气,艾蒿可驱蚊虫,而清心之物,必有鲜花,以豆蔻、香柏子、桂皮、花椒为常用物,悬栀子、茉莉、白兰、柠檬、香茅、薄荷、菖蒲等香袋,那河中的臭味就逊减不少。山岚也能致人疾病,山居时,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是燃香,一是花茶。菖蒲可燃炙起香,花椒、水樟、月桂树枝叶、檀香树枝叶、香樟、枫香树、泽兰、杜蘅、白芷、川芎、当归、山胡椒、辛夷、松香、桧柏,随地可拾的松枝,燃起来,香气弥漫。山里人烧火,首选松柴,枫香、柏枝、香樟叶、月桂枝叶,燃香柴时,屋舍外十里皆闻其香。山民们制枝香,以香蒲和桂叶、樟叶为主料,晒干磨粉,杂以少许木香、檀香、柏香粉,做成各种枝香。檀香气沉稳难散,樟香通窍提神,柏香令人清心去浊,桂香令人愉悦轻松。
农历五月,端午后,气候炎热难耐,午后昏昏欲睡。燃起一炷香,屋里顿觉清凉。弘一法师在闽南时,也感觉南方炎暑难熬,他自制了一种饮料——清心茶,即茶叶里加了少许荷花之蕊,杂以荷瓣,茶水隐隐有荷花香,味清凉而沁入心肺。佛家忌浓香,而屋外可以种诸香花,茉莉、栀子、玫瑰、香柏、香樟、散沫、豆蔻、丁香和薄荷,然师仅远闻而不近嗅,而一身无异味,始终清香如甘露。师禅房里无一物,简陋如闲房,只一床一帐一几而已,小桌上摆只油灯,地上一蒲团,有时在地上打坐,有时在床边,室内清新如芝兰之室。夏月,荔枝红熟,信徒送来荔枝供奉法师,弘一闻之甚喜,只尝数粒即分与弟子同品。有弟子善香道,以荔枝壳、核为香料,加之茉莉、栀子等物,以菖蒲为提香料,做成正香,燃于室外,众人欢喜,以为法香,请弘一法师提一名,弘一法师不以为然,说,此并无香可闻,只觉法香袭人,如沐甘露。荔枝壳、核香甚微,茉莉和栀子并不宜燃闻,香气淡而幽,如竹林下,桂树下的风,觉其不香而甚香,这是精神界的香气了,是常人体会不到的异香。
诸花如花而非花,诸香如香而非香,像法师所说的那样,无分别心,何处无繁花?心香处即花香处,禅结于心,而香在身外,禅向内求,彼岸此岸,何处着花?
责编:鄞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