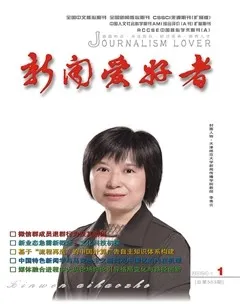媒介空间生产与主体权力让渡:新型派对游戏中的“双向规训”
2024-02-23戴元初陈怡然
戴元初 陈怡然
【摘要】2022年年底,一款派對游戏《Goose Goose Duck》短时间内迅速吸引了亚洲区玩家的眼球,这也正是网络游戏开发者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媒介空间生产的一次成功探索。研究发现,与传统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相比,这类新型派对游戏迅速爆火的背后是游戏设计者与玩家作为媒介空间生产的共同主体“双向规训”的关系建构逻辑。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出发,探寻新型派对游戏中蕴藏的空间权力结构及其暗含的“权力幻觉”,有益于对深度媒介化时代现实社会关系建构方式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关键词】媒介空间;空间生产;权力让渡;双向规训
2022年年底,以“狼人杀”桌游为前身、受《Among Us》启发创建的派对游戏《Goose Goose Duck》在游戏玩家中被追捧,成为Steam(全球较大的综合性数字游戏软件发行平台)有史以来峰值在线人数最高的派对游戏。这款小成本无宣发计划的派对游戏展现了新型派对游戏的共同特征为:游戏规则相对简单、玩家自由度高、社交属性强、盈利模式多为内购。如果仅从这些表面特征看,无法解释这类游戏市场穿透力的来源。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的建构可以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答案。
一、空间媒介化:媒介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关于空间的讨论在学术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哲学家将“空间”这一概念赋予了物理学意义,认为它是可感可知的。而进入近代以来,空间逐渐实现了从客观环境到社会关系的转向: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空间还被理解为一种“生产的物理环境”;齐美尔则摆脱空间的物理局限,认为客观物质空间因为心灵与互动而具有了社会意义;列斐伏尔与福柯关于空间生产与空间权力的理论则正式将空间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发展引入转向阶段。[1]自此,社会学研究中“空间转向”的基础理论奠定,其他各学科也纷纷加入“空间转向”时期的热潮。
空间——特别是虚拟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媒介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意指,其传播就成为这场关系建构的动态过程。在网络时代,媒介不断建构虚拟空间的同时,又在虚拟空间的基础上重构着新的虚拟空间[2]。这也恰好印证了列斐伏尔对空间本身生产的思考。列斐伏尔在揭示空间的生产内涵时,发现空间还附带着隐蔽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他在空间的权力结构分析中延续了马克思的批判性色彩,并在社会空间内强调了征服、整合和反抗的关系。福柯在阐释空间规训理论时也提到,权力话语对空间进行了精妙设计、构造与生产,从而达到对个体监视和改造的目的,同时使其服从于管制及规范[3]。
游戏空间正是虚拟空间最早以及最成功的化身,而空间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也在虚拟游戏空间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游戏空间作为一种可盈利商品在生产活动中必定受到资本权力的驱动。
二、解构空间权力: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类游戏中的“单向规训”
追溯游戏发展的历史,Alemi将目前的游戏确定为三个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简单的在线游戏。第二类是MMOGs(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它的特点是几乎没有预先编写好的故事情节,以及玩家在游戏中的化身很大程度不是由游戏开发者预先确定,而是由玩家建造属于自己的虚拟世界。第三类是MMORPG(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它让玩家沉浸在预先编写好的复杂可变的环境中,通常故事取材于英雄幻想或科幻小说。玩家在游戏开发者创建的角色和提供的游玩元素基础上进行游玩建造[4]。
(一)固定角色,规训的开始
早在2012年,René Glas就全面地分析了《魔兽世界》这部游戏背后的控制机制和程式化设计模式,指出这款虚拟游戏对玩家高度的角色控制权[5]。固定的游戏角色不但加深了现实世界中本身的职业符号化印象,也是虚拟游戏空间中空间权力的象征。在MMORPG类游戏中,固定的游戏角色意味着固定的虚拟社会关系与固定的主线任务,这是玩家无法通过在虚拟空间中的其他劳动改变的。而玩家能否沉浸并扮演既有角色的过程,是产生化身认同的过程。当认同发生,虚拟游戏化身会在游戏空间中取代玩家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自我,玩家用真实的游戏数据充实该空洞角色的血肉,将其真正变成设计者所预想的虚拟人物。而当玩家不认同该角色却被迫扮演其身份并说话行事时,玩家会产生巨大的消极情绪进而导致退出游戏与空间生产或迫使自我强化认同沉浸游戏两种选择。由此看来,无论玩家对其固定角色认同与否,都是设计者在虚拟游戏空间中规训玩家、压迫玩家的权力运行过程。
(二)任务与奖励,规训表面的“玩乐场”
角色的固定意味着任务的固定,而任务则控制着玩家的议程,奖励推动着玩家完成任务。任务的存在让玩家在游戏空间中保持着无限忙碌的状态,玩家在一个又一个任务中沉迷,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任务是游戏不断保持玩家留存的手段,也是不断榨取玩家剩余时间的利器。虚拟游戏空间作为表面上的“玩乐场”,为了督促玩家完成任务也都各自具备完善的奖励体制。比如在《生化危机:启示录2》中,游戏会记录玩家在任务中使用的道具、击败敌人的数量,以此作为奖励机制的衡量标准,并按照不同标准为玩家颁发金、银或铜奖章。不少竞技类游戏也会设置排名榜以激励玩家积极参与任务刷经验、精进装备、提高技能点等。虚拟游戏空间利用任务与奖励刺激玩家在不知疲倦的状态下进行高效率数字劳作,迫使玩家在虚拟空间中持续生产,隐藏其压榨玩家的本质。
(三)数字“玩工”,规训背后的“劳作场”
虽然任务和奖励机制隐形奴役玩家进行生产,但仍不乏有游戏爱好者在游戏空间中深度探索并进行创造性生产,这既使游戏节省了后期研发与创新的费用,又增加了游戏的吸引力和创造力。而这些不受外部压力(如生活所迫)驱使,又不是单纯进行休闲活动的游戏爱好者被称为“玩工”,游戏“玩工”在探索游戏中的一系列劳作过程也正是虚拟空间再生产的过程,“玩工”们不仅是商业平台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还是以剥削自身为目的的广告商的帮凶,这使得再生产的过程呈现出了双重生产性与双重剥削性。“玩工”概念的出现表明游戏已经从最初休闲娱乐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在资本的介入与剥削下由“玩乐场”异化为了“劳作场”。但在游戏“劳作场”中,劳动的虚拟工人并不能像现实生活中一样获得工资或报酬,反而还要向游戏公司支付货币购买游戏以及用真实货币购买虚拟空间中的虚拟装备等。
三、再现权力让渡:新型派对游戏中的“双向规训”
(一)短轮次,自主意志的提升
对于新型派对游戏来说,一方面游戏轮次耗时短是其类型的一大特色,也是相对于传统MMORPG游戏玩家自主权提升的显著表现。比如《糖豆人》类跑酷游戏单局游戏时间在3—15分钟。平均十几分钟的单局游玩时间给予了玩家更自主的游戏时间选择,也减轻了游戏的退出阻碍。另一方面,轮次交替频繁也给予了玩家更换角色的权力,如在《Goose Goose Duck》中每一局游戏玩家都会被分配或自主选择角色,而每一个角色的属性、阵营、获胜方式和附带的虚拟社交关系都是不同的,这就避免了固定角色所造成的强迫角色认同。在新型派对游戏中,设计者实际上将部分角色设计权、选择权、控制权让渡给玩家,并通过灵活的退出机制与短小的碎片时间营造了一个由玩家与设计者共同主导的游戏空间。玩家借助游戏评论区与设计者注重的评分实现和设计者无障碍沟通并双向规训的局面。
(二)房间制,玩家掌权的幻觉
由于派对游戏的社交性,设计者深谙玩家更愿意拉上熟人、朋友一起以群体的方式参与,于是独立的房间制成为派对游戏中的基本设置。房间制的出现意味着游戏公共空间中产生了各个独立的新空间,而这些新空间的出现正是玩家开始掌握其空间权力的象征。就《Goose Goose Duck》来说,每个房间都是由一位玩家作为房主创建的,每位房主都可以选择是否向公共领域开放房间、是否设为私密房间、用语音还是文字交流、踢出任何一位玩家以及在房间内设置房规。而在“轮抽模式”中房主还可以设置正反阵营的角色数量与类型,拥有空间内(房间内)的绝对控制权。对新空间(房间)的掌控给玩家营造了一种非常真实的“权力幻觉”,让其在游戏过程中体验“掌权者”的感觉,而正是这种“掌权”的感觉吸引了玩家的兴趣。
如果房间为不向外界公开的“熟人局”,玩家们甚至可以漠视原本游戏规则、违背原本角色任务与属性,在包容性极强的轻松融洽氛围中自创玩法为派对增加趣味;而如果房间为玩家随机社交的公开房,房主的权力就十分显著,房主可以设置专属“房规”打造一个为自我利益服务的空间,且可以无条件将任意玩家踢出房间。惩罚保证了规则的施行,规则的施行确立了权力的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玩家的自我意志在游戏中充分展现,对游戏设计者与空间本身就是一种“双向规训”。然而权力幻觉终究是幻觉,玩家的权力边界即是设计者设置的游戏基础框架与运行代码,其底层运行逻辑仍旧是资本无限剥削玩家完成再生产,“房间”的诞生不过是一种蒙蔽玩家的新型麻醉剂。在新空间中玩家依旧需要在设计者提供的地图上扮演已有的角色,在资本提供的物质生产资料与设计者技术的产物——虚拟游戏空间本体中进行无偿生产。
(三)免费准入,放权下的反向规训
与传统MMORPG游戏付费预购的模式相比,新型派对游戏最大的不同是多为免费内购的盈利模式,免费游玩实现了让玩家无偿享受设计者与资本共建的劳动成果——虚拟游戏空间。在这当中,较低的准入门槛、相对简单的游玩技法吸引着无数对游戏感兴趣又涉入程度较低的人群。可以说免费游戏的存在争取了许多非传统玩家的市场,新型派对游戏也很大可能成了非传统玩家尝试的第一款游戏。而由于玩家经验与房间制规则的不确定性,新型派对游戏很有可能会导致游戏“混乱”局面的产生,而被允许和制造的混乱也正是设计者“放权”的体现。
免费游戏带来新手玩家的不断涌入也改变了传统MMORPG游戏对玩家剥削与压迫的权力结构,即“玩工”的数量与深入程度大大减少。新手玩家大多被简单的游戏规则与准入门槛吸引,对游戏的整体热爱程度一般,大多希望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参与游戏来放松现实工作与生活中的压力,这与朱利安·库克里奇对于“玩工”的定义相悖。这也就意味着投入程度不深的玩家不仅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游玩与退出时间,更能脱离虚拟游戏空间中的规训机制。另外,免费准入与内购盈利的模式也导致了设计者与资本更倾向于考虑玩家的意见从而吸引庞大的路人粉丝并不断改进以增加游戏的留存度,这也是玩家对其他空间主体的“反向规训”表现。
四、结语
在传统MMORPG游戏中,玩家承担着“消费者”“玩工”“生产者”等多重身份,却始终处于资本、技术、社会关系、规则等控制之下,从开始购买的那一刻起便被纳入了游戏公司的权力结构之内,在角色认同、任务奖励、宣传营销的单向规训中一步步陷入“数字劳工”的命运中不能自拔。甚至游戏公司还会通过虚拟空间将意识形态投射到玩家的“本我”身上,影响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形成对玩家隐蔽的数字奴役。
新型派对游戏开放自由的初始设置允许了玩家的自我创造,而玩家的自我创造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向规训着设计者不断更新以共同建造更美好的虚拟游戏空间。虽然在资本与市场的作用下玩家不可避免地存在被占有剩余时间的无偿劳动现象,但相比于传统MMORPG游戏,设计者对权力的让渡使得玩家可以在设计者创建的空间中自主创建新空间(房间)并掌握新空间的空间权力,从而产生作为“掌权者”的权力幻觉。因此,新型派对游戏中较高的自由度和权力的获得感或许是未来更为玩家接受的原因之一。
权力幻觉的研究发现还暗示了媒介空间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旧处在资本控制之下,权力让渡并非所有权让渡,新空间的产生也存在权力边界。至少现在的媒介空间,特别是虚拟游戏空间还未逃脱虚拟空间生产的底层资本规训逻辑。然而新型派对游戏的短暂爆火确是对此规训逻辑的新突破,设计者的放权导致了玩家地位的提升,资本的免费引诱也标志着对玩家的控制效果减弱。同时对媒介空间的受众来说,获得对空间权力的掌控感却是极具吸引力的,随着万物皆媒、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到来,或许适当放权和让渡的行为更为媒介用户所接受与喜爱。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时空视角下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策略与理论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BXW003)
参考文献:
[1]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34(5):38-42.
[2]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際新闻界,2012,34(5):38-42.
[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Alemi,F.2007.An Avatar's Day in Court:A Proposal for Obtaining Relief and Resolving Disputes in Virtual WorldGames,UCLA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11:2),pp.1
[5]Glas,René.Battlefields of Negotiation:Control,Agency,and Ownership in World of Warcraft.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2.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4cg5np.
作者简介:戴元初,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济南 250100);陈怡然,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济南 250100)。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