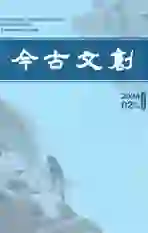《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的生命美学探究
2024-02-02徐杨林丽敏
徐杨 林丽敏
【摘要】《给麻风病人的吻》是莫里亚克小说创作成熟的表现。莫里亚克在《给麻风病人的吻》中主要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在其婚姻悲剧后面隐藏着的是物化的社会,自我的丧失等丑恶现象。这些“恶”恰是莫里亚克生命美学的体现,生命因“恶”而萎缩,莫里亚克期望通过“恶”让世人认清现实,实现个体生命的超越,呼唤个体生命本真的美。探析莫里亚克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的生命美学,有助于对莫里亚克思想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莫里亚克;《给麻风病人的吻》;生命美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2-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2.006
莫里亚克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在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中,他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的婚姻悲剧。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小说中蕴藏着对生命本体和生命意义的思考,注重挖掘人性的矛盾和多面性,关注以“人”为核心的生命体系。
生命美学体系高举生命旗帜,人的全部活动构成了生命的样式。王晓华将生命美学定义为“以人感性的生命活动为言说依据并以生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美学” ①。强调生命的存在对于整个世界的价值,需要从其存在性、发展性、超越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考量。潘知常认为人与世界之间有三个维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意义活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方面着重现实问题,关注的是现实维度及现实关怀;“人与意义活动”这一面超越现实的维度,构成了超越维度的终极关怀。②在此综合以往学者对生命美学的言说,与之对应的人的生命也应有三种样式: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以及超越生命,超越生命意味着在超越现实的层面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独立。《给麻风病人的吻》中自然生命的萎缩,社会生命的失落,超越生命的永恒等现象,正是生命悲剧意识和生命强力的体现。本文试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探讨《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的生命现象,从个体生命出发,挖掘作者对本真生命的思索与呼唤。
一、自然生命的萎缩:精神与欲望的双重压制
自然生命是指作为个体存在最为基本和原始的生命存在样态,小说中自然生命的萎缩主要体现在个体对精神与欲望的压制。
在《给麻风病人的吻》中,处处流露出精神的困顿。《给麻风病人的吻》讲述的是發生在20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家庭的故事,这是一个充斥着金钱铜臭味的时代。让·佩罗埃尔(以下称“让”)是地主的儿子,按理说,在被金钱蒙蔽双眼的时代,让应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大少爷。然而,他生的痛苦,活的压抑。命运给予让丑陋的容貌,他也因此受到来自社会、学校各方面的不公正待遇,被称为“怪物”。他没有朋友,也不敢随意出门,房屋成了他的避难所。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在外界声音的非议声中被同化了,变得敏感自卑。他在一切还未发生的事情,如爱情和巴黎生活面前,首先决绝的给予自己“否定”的心理暗示。长期以来外界的非议以及自我内心的压抑,一步一步腐蚀他,造成他精神上痛苦压抑。此外,让生活在专制的父权制家庭,在父亲长期专断独行的压制下,他丧失了自尊与自信。此外,热罗姆老爷的生命也体现出一种孤立无援的空虚与孤独,他与他儿子共享痛苦,小说中写道“他们的生活正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艰难、忧郁和寂静!” ③有钱无实,精神空虚;整日担心财产会被胞姐抢走,敏感多疑,以至精神衰弱,经常失眠。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负担带给他的绝不会是享受生活,而是在空有其表的生活中苟延残喘。
欲望是生命不可分割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欲望,人才能称为人。《给麻风病人的吻》中,在两个家庭利益的逼迫下,在神父的“热心”撮合下,让与诺埃米结为夫妻。诺埃米满足了让对女人的所有幻想,激起了让的欲望。他疯狂嫉妒并厌恶着身边的英俊男子与诺埃米的交谈,可当他产生不好的思想时,他的脑海里又冒出:“啊,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比我的面孔还要丑恶不堪!” ④灵肉冲突拉扯着让的情欲。青春貌美的诺埃米对爱情、伴侣抱有期许,她也幻想在夜晚意中人“奉献出他们结实的胸膛,用双臂紧紧地搂抱着她们。” ⑤而诺埃米把让当成了蟋蟀,毫无情欲。小说中对情欲的扼杀,在两人婚后相处达到了高潮。让知道妻子厌恶自己,完全不可能接受自己,感觉到躺在他身边的是一具腐尸,给他的吻是昔日给麻风病人式的吻。诺埃米生理上对让感到恶心与排斥,“晚回房一小时,她就少恶心一个小时”。⑥她把对年轻医生的欲望埋葬心底,生命在麻木状态下一天天消逝,最终“她的耳朵、嘴唇和面颊失去了光彩。” ⑦欲望意味着欠缺,欠缺意味着痛苦,情欲本是生命烈火的表现,两位青年男女在爱欲之火燃烧正旺的年纪将其扼杀的一无是处,情欲受到遏制,痛苦无处宣泄,进而造成了人性的扭曲。
《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的让,诺埃米,热罗姆老爷等的生命无不呈现出萎缩状态,在时光的流逝中不断消耗生命的能量与热情,在尔虞我诈的家庭生活中不断透露出生命的虚无感。
二、社会生命的失落:自由与爱的缺失
《给麻风病人的吻》中,莫里亚克探讨的是典型法兰西文化氛围中资产阶级家庭的虚伪、贪婪,人物灵魂的空虚,借此表现生活中普遍意义的绝望,恐惧和孤独,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抑制和变形,呈现出社会生命的失落。
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在诺埃米和让的生命中,他们始终没有把握自己生命的自由。诺埃米始终扮演着“世俗的奴隶者”这一角色。首先,在婚姻上听从安排,与不爱者结合。她父母因为觊觎让家族的财产而与神父联合安排将女儿嫁给让,诺埃米对此几乎没有做出反抗,她从心底默认了“这是我无法摆脱的命运”这一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的观念,在不幸的婚姻中消磨生命。其次,囿于世俗的眼光,放弃爱情,甘当寡妇。在让去世后,诺埃米本可以接受医生的追求,获得重生的爱情。然而,面对强大的世俗和金钱的威力,她不得不亲手扼杀这份新生的欲念,像牢笼一样将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埋葬乃在世俗的眼光中,成为“引以为傲”的寡妇,让生命在麻木慢慢逝去。让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俗的奴隶”。他短暂的二十多年时光全然活在世俗的眼光下,在世俗的议论中不断否定自我,否定自己追求爱的权利,认为自己不配得到幸福直至否定生命的全部。
此外,《给麻风病人的吻》中到处弥漫着以“爱的名义”筑起的“爱的牢笼”,呈现出嫉妒、扭曲、压抑的生命状态,是无爱的人间。诺埃米的父母全然不顾女儿的幸福,并违心地说出“男人用不着长的英俊漂亮,男女结了婚就会产生爱情……” ⑧这样冠冕堂皇的话语,但实则是“人们不能拒绝佩罗埃尔少爷” ⑨。热罗姆老爷为让安排婚姻,是为了保住财产不外流,他从未真正爱过他的儿子。菲利西黛对费尔南的爱是畸形的爱,源于疯狂的占有欲,更是说过“假如费尔南娶亲的话,我那媳妇就甭想活下去” ⑩这样癫狂的话语。让的成长经历实则也是一个爱的缺失的过程:幼时丧母,与父为生,父亲是一个专制又自私的人,生活在无爱的环境中;青年时期,因为“丑”,在学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待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世人认为他不配谈情说爱;再到与诺埃米的结合,实则是爱的缺失导致的悲剧。
爱与自由的缺失,让诺埃米和让的生命呈现出紧张的状态,在顺从世俗中丧失把握生命的机会,丧失生命的自由;在一次次“以爱的名义”成全幸福的过程中失去了生命中真正的幸福。
三、超越生命的永恒:向“死”而生
生命美学见证着人类生命中高层次的精神活动,而“超越”正是美学的价值所在。死亡并不可怕,因为生命终有逝去的时刻,人类在对死亡的超越中,灵魂获得救赎和升华,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死亡并不意味着存在的彻底终结,而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做自己的可能性。⑪主动选择死亡或许不是爱惜生命的表现,但是面对绝望的人生、灰暗的社会环境,死亡或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弃绝生命者渴望用毁灭式的自我牺牲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彰显生命最后的价值。
在《给麻风病人的吻》中,让就是弃绝生命者,他的高尚精神就是超越生命的体现。让在这场爱而不得的婚姻中,他多次“逃离”:故意早出晚归打猎,远走巴黎出差;甚至故意染上肺结核,主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还妻子青春活力,结束对妻子产生的痛苦和折磨。其中有个小细节,让为了防止传染肺结核给诺埃米,他从他喜爱的昏暗的小角落搬到了庭院,临死都在为诺埃米考虑,足以见得其人格精神的崇高。在这里,让·佩罗埃尔的生命有了双重的意义:死亡是个体生理上必经的终点,但同时死亡也是个体精神上新生的起点。
生命的不朽以爱为媒介,向人类短暂的生命告别,将其刻上时间的维度,从而赋予生命永恒的意义。让虽死犹生,谱写了一曲关于生命的赞歌,彰显生命的超越之美,达到了向死而生的美學境界。
四、本真生命的理性呼唤:爱、自由与信仰
“生命美学以爱与信仰为维,以自由为经,以守护‘自由存在’并追问‘自由存在’作为自身的美学使命。” ⑫窥探《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生命美学的意义,在于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美好,意识到本真生命应当是追求爱、自由与信仰的状态。
本真生命呼唤爱与自由。生命美学是人的美学,是生命的美学,同时又是爱的美学,以人为主体汇聚成的关于“爱”的生命核心。诺埃米和让的人生是金钱婚姻所导致的悲剧人生的典型。审视两人的悲剧,可知晓这悲剧是由两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对金钱的病态占有欲而导致的,本质是爱的缺失。莫里亚克期望借悲剧的力量来呼唤爱,因为没有爱的家庭和社会就像牢笼,没有感受过爱的人生注定是悲剧的人生。“真正的人的生命活动,必定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本质内涵,所以真实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生命活动。” ⑬《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的男女主人公的不幸在于没有肯定自我生命的真实。让·佩罗埃尔因为样貌丑陋,认为自己的存在就是错误,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始终压抑内心,郁郁不得志。诺埃米更是把自己当作家庭的附庸,不反抗家庭的安排,也不顺从自己的内心,把原野之火扼杀在生命的摇篮里,最终在家庭的束缚中,在金钱的牢笼中葬送人生的大好年华,葬送生命。
本真生命呼唤信仰觉醒。在《给麻风病人的吻》中,莫里亚克塑造了一位圣母型人物——加黛特,以此反对丑恶的人与事,对生命起到净化以及引领作用。加黛特虽然地位低贱、贫穷,但她拥有着自然状态的生命,有着宗教所宣扬的博爱与同情。虔诚的信仰使她历经生活的苦难依然热爱生命,信仰在此起救赎作用。反观,从19世纪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喊到“内卷化”的21世纪,人类在欣喜现代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孤独与虚无。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似乎成了个体不断追寻却又找寻不到的生命意义。在此,生命美学呼唤个体信仰的觉醒,信仰对个体精神洗礼尤为重要,人类生命对终极关怀的需要离不了信仰,人类追寻信仰是为了寻求个体精神的安定。信仰的定义是愿意相信,真正的信仰不一定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它是个体内心最为坚定的那部分,无论遭遇多大的诱惑,遭受多大的苦难,依然是生命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始终信仰。
五、结语
莫里亚克在《给麻风病人的吻》中,透过荒诞的生命现象书写了生命的悲剧意识,穿插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显示出生命的本真状态。在自然生命的萎缩、社会生活的失落中来回穿梭,并将死亡当成个体对现实生命的超越,死亡亦为新生。小说通过展现人物生命体验促使我们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试图呼唤本真生命的觉醒,追寻爱、自由与信仰,渴望个体从自我与外界双重束缚的沉睡中苏醒。以生命个体为起点,对生命过程与经验加以研究,并最终达到对生命的超越,始终围绕生命进行,而这正是生命美学的精髓所在。
注释:
①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诞生的逻辑因缘与基本维度》,《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潘知常:《头顶的星空:美学与终极关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③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石横山译:《给麻风病人的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④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石横山译:《给麻风病人的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⑤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石横山译:《给麻风病人的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⑥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石横山译:《给麻风病人的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⑦弗朗索瓦·莫里亞克著,石横山译:《给麻风病人的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⑧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石横山译:《给麻风病人的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⑨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石横山译:《给麻风病人的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⑩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石横山译:《给麻风病人的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⑪(德)韩炳哲著,吴琼译:《他者的消失》,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5页。
⑫潘知常:《生命美学是“无人美学”吗?——回应李泽厚先生的质疑》,《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⑬潘知常:《生命美学:从“本质”到“意义”——关于生命美学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给麻风病人的吻[M].石横山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2]徐曙霱.莫里亚克《给麻风病人的吻》主题质疑[J].外国文学研究,2001,(01):78-81.
[3]龚亚琼.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人性的探索[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02):22-25.
[4]乔明文.沉沦,超越及救赎——解读艾略特《荒原》中的生命美学[J].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02):156-157.
[5]刘娟,马粉英.“犯罪-忏悔-救赎”模式——莫里亚克作品的结构主义解读[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2):228-232.
[6]陈矿.挑破压抑的帷幕寻找自由的灵魂[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2):97-105.
[7]范藻.生命美学的新境界——评潘知常新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J].上海文化,2020,(04):118-124+127.
[8]潘知常.生命美学:“以生命为视界”[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06):72-76+60+124.
[9]潘知常.美学的奥秘在人——生命美学第一论纲[J].文艺论坛,2022,297(01):33-41+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