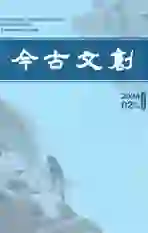从新批评看范仲淹《江上渔者》
2024-02-02杨维罗炜
杨维 罗炜
【摘要】新批评作为西方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本体研究,主张采用细读法,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同时,它又有异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中国古代诗词。因此,基于新批评理论出发解读范仲淹的《江上渔者》一诗,能够在一个新的视角下获得新的启发,产生新的理解,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意蕴。
【关键词】新批评;范仲淹;《江上渔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2-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2.001
一、新批评的构架肌质理论
《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此诗首见于北宋刊刻的《范文正公集》卷三。另外,宋末蔡正孙所撰《诗林广记》题作《赠钓者》,“但”作“尽”,“风”作“涛”,诗末引《翰府名谈》云:“范希文《赠钓者》诗实寓深意,不徒作也。”又引《文酒清话》云:“希文《江上遇风》及《赠钓者》诗语虽同而意各有寓也。”[1]可见,蔡正孙认为此诗蕴藏着“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与新批评派批评家兰瑟姆的“构架—肌质”理论和韦勒克、沃伦的“结构—材料”之说极为切合。所谓构架就是“诗的逻辑核心,或者说是诗的可以意解而换为另一种说法的部分”。[2]38即诗歌的逻辑观点或者能够用散文转述的部分。所谓肌质,就是诗的意象,无法用散文转述的部分。[2]38它是依附于构架,但又不囿于结构、趣味横生的细节,也是诗歌的真正本质与核心。为此,新批评理论家们提出文学活动的本源与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不能分割,并倡导文学本体、结构肌质和语境理论,它们又必须在意义交互的语义场中进行文学细读和分析。
诗的“构架-肌质”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有机整体,基于这样的理论要求,不难发现,《江上渔者》的“构架”(“材料”)非常简单,即通过对比渔者与往来人的生活及其动作、神態,进而歌颂渔者的辛勤付出。但这首诗将“结构”(“肌质”)隐藏在深处,读者无法轻易找到。甚至,这样的“结构”与原意义指向完全不同。而这也恰好为诗的“言外之音”“弦外之响”。所以,新批评的复义、张力、反讽、隐喻、象征等就格外适合这种“结构”(“肌质”)理论,可以从实际操作层面来把握。
新批评理论家们特别强调,禁止在批评中涉及与作家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作家的生平、背景、创作意图、创作感受等,因为新批评是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擅长直接对文本进行分析。这就与中国古典文学独有的知人论世的批评方式截然不同。新批评反对研究作者的创作意图,并认为这是“批评误区”,也称为“意图谬见”,新批评对此有更直接的描述,即“将诗和诗产生的过程相混淆”简单来说就是,不能把作者创作意图中的世界等同于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世界,当一部作品创作出来以后,作品就不再属于作者,也就不能再把作者的愿望等同于作品的实践。在新批评看来,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作品意义是两码事,批评家尤其不能依据作品是否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来判断其价值。[3]160而《江上渔者》也并未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迫使大家将注意力聚焦在文本本身。
二、《江上渔者》的文本细读
此诗题为《江上渔者》,“渔者”即江上以从事渔业为生的人。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非个性论观点认为诗人不能脱离文化传统而真正地具有个性,因为诗人必须承受历史意识,处于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体系之中,不能脱离历史和文化传统。“渔者”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意象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如《庄子·渔父》中“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到“刺船而去,沿缘苇间”刻画的是一位逍遥从容的隐者形象;又如《庄子·秋水》中,庄子面对楚王重金厚币,选择“持竿不顾”,刻画的是一位淡泊名利的渔者形象;再如《楚辞·渔父》中“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劝词及所歌“沧浪之水”,刻画了渔者经历沧桑看透世事后所怀有的通达与洒脱。后代诗人沿着渔者隐逸遁世的传统进一步表达出自己对“渔者”的向往,如唐代张志和《渔父歌》“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代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及《渔翁》“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还有宋代张昪《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等等。不难看出,在中国古典文学里的渔者形象往往象征着“隐者”。上文提到蔡正孙所撰《诗林广记》题作《赠钓者》,那么《江上渔者》《赠钓者》孰优孰劣?“渔者”是源于先秦时期文学作品并作为隐者意象流传至今。而在新批评看来,用“江上”要比“赠”字更具有“内涵”,因为诗题“江上”与首句“江上往来人”起了冲突并由此产生复义,这也符合新批评的基本理论。
英国批评家、诗人燕卜荪在《复杂词的结构》中说过关于“复义”的解释:“复义这个术语,指的是读者感到两种解读都成立,而又多少可以被一种二者结合的意义所取代,这两者被用来构成一个明确的结构。”[2]43通俗来说,复义本身“可以意味着你的意思不确定,意味着有意说好几种意义,意味着能二者之一或二者皆指,意味着一次陈述多种意义”[3]162。新批评对文本在语言层面的深度开掘,发现文学语言具有多义性、含混性。而象征性符号的抽象性产生了这种多义、含混(复义),给诗歌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语义批评中的语言特质,是非指称性的伪陈述。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艾·阿·瑞恰慈在研究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差异所在时指出:在科学语言上我们会要求它准确无误,其语言之间的所指关系较为稳定,这也与科学本身唯一正解有关。与之相反的是文学语言,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含混与多义,文学语言总是试图用有限的文字来表达无穷之含义,有时还不满足于现状,如中国古代律诗、绝句等这类合辙押韵的体裁,要在各种限制之中融入无限意义,让其指向更多的所指,即所谓的言有尽而义无穷。因此,充分发挥出文学语言的含混性和多义性,才能取得这种效果。一个词的词义是指词语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各种意义,包括本意、引申义、比喻义、联想义等等。除此之外,该词被使用的当下语境、特定语境也制约着词义的确定,使其产生特有含义。
在《江上渔者》这首诗中,由于“江上”未明确具体方位,它既可以指江岸、江边或者江中的任何位置,也可以指同一个位置。渔者在“江上”的动作可以是乘船在江面中心进行打鱼作业,也可以是在岸上进行撒网、收网工作,当然也可能是在江岸一角进行垂钓。这样就造成空间位置上的含混,从而引起复义。简单来说,由于“江上”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不仅可以容纳“渔者”,同时也可以容纳“往来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是追求自由隐逸的渔者,一边则是凡尘俗世中的往来人,因“江上”的含混复义,使得渔者和往来人从一种风马牛不相及变成可相互转换的状态。他们同时出现在诗歌当中,这就使得“渔隐”的象征意味逐渐淡化,诗人不再沿着中国古典文学赋予“渔者”以隐者的意蕴继续前进,而是跳脱出来,回归到大众视野,回归到平凡中去。诗歌在这种复义和矛盾下,展现出既紧张对立又和谐共存的关系,共同构筑成诗歌的张力。渔者是归隐的象征,他所追求的世界和目标本该与往来人不同,但由于“江上”的含混复义,渔者和往来人就都有了共同的目标和追求——鲈鱼。
鲈鱼作为意象被纳入文学作品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张翰所作的七言诗《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诗的内容大致是张翰在洛阳看到了秋风吹起的场景,于是怀念起家乡的鲈鱼脍,并说道:“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4]2384于是辞官归隐,“秋风鲈鱼”也遂由此而得。而鲈鱼意象存在着双重意义:一是像李白《秋下荆门》“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杜甫《洗兵马》“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等表达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精神与心态。二是像黄滔《钟陵故人》“一箸鲈鱼千古美,后人终少继前踪”;夏竦《狼山渡口有作》“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直钱”;温庭筠《送襄州李中丞赴从事》“江雨潇潇帆一片,此行谁道为鲈鱼”等表达的是一种淡泊名利的归隐之情。不难看出,“鲈鱼”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指向,鲈鱼作为矛盾的意象既满足了渔者隐世的需求,又满足了往来人世俗的需求。中国古典诗歌讲究含蓄之美,这与之诞生于中国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壤有关。中国古人在创作诗歌时讲究中和统一,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歌,而这种和谐之美与新批评的张力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看似矛盾的意义融于“鲈鱼”上,将本该对立着的意象有机统合成流畅和谐的诗句。此句的“但爱”二字也不能忽略,“但爱”强调一种程度,也就是“只爱”,暗示人内心最本真的渴望,即除了“鲈鱼”别无所爱。与此同时,渔者也展现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意象特征,即“渔者的平凡化”。如果说首句是由“江上”二字含混,造成渔者和往来人之间没有那么明确的分界线,那第二句则是由“鲈鱼”二字的含混,更深刻地表现出渔者和往来人没有任何区别,诗人完成了渔者从“出世”到“入世”的飞跃。
话锋一转,诗人一句“君看”把大家的目光引向了“舟”的位置。舟这一意象原指在水面上自由移动的交通工具,但在历史沉淀之下,它同样被古人赋予了诸般意义。如《书·说命》“爰立作相,王置其左右,命之曰:‘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是一艘仕宦之舟。又如《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是一艘漂泊之舟,俞平伯先生在《读诗札记》中曰:“(柏舟)取喻身世之畸零。”又如《庄子·列御寇》:“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是一艘超俗之舟,王先谦道:“惟圣人泛然无系,譬彼虚舟任运逍遥。”再如柳永《雨霖铃》“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是一艘离情之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舟”多作为诗人航行心灵世界的工具,也是诗人孤独意识的隐喻。而“舟”与“渔”的组合共同创造了独特的渔者形象,如《楚辞·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5]2468屈原未等到山水渔舟的治愈,而选择一条“知死不可让”的决绝之路。《江上渔者》的“舟”为“一叶舟”,“一”字凸显着这艘舟在茫茫江海中的孤独与落魄,而“叶”则更显出这舟的脆弱与渺小,“一叶舟”象征着渔者孤獨弱小的心灵。“出没”作为一个动词,将“渔者”具有的隐者形象彻底打破。“风波”则隐喻着社会环境之恶劣与时事之艰难,而渔者主动放弃逍遥归隐的生活,选择直面风波,也意示着渔者的百般无奈,只能默默承受着命运的安排。诗歌中的“一叶舟”是广阔无垠之江海中渺小的生命个体,“风波”是江海之无限阔大、波涛汹涌,一小一大形成了极具张力的矛盾对比结构。同时,“一叶舟”和“风波”也构成了反讽,这种反讽类似于杜甫所作《春望》诗,“春望”给人一种春天的美好,但诗歌内容呈现的却是山河破碎,表达的是离亲乱世。
当细读完整首诗后发现,除了诗题以外再无他处提及渔者,但渔者的形象却逐渐清晰了起来。邱运华在《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一书中引用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并说到:“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核心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具有怎样的互相关系。”[3]161为使渔者形象更完整,我们将考察的视野由意象扩大到句子层面。第一句“江上往来人”看似不是写渔者,但因为“江上”二字的含混,让渔者脱离了传统的隐者形象而趋向往来人,所以渔者和往来人都可以象征为“人”。第二句似乎也和渔者无关,但经过上文分析,渔者与往来人一样,对鲈鱼同样有热爱和追求,此句可象征为“欲望”。第三句描写渔者的心灵世界,“一叶舟”给大家呈现的是一种孤独和弱小,象征为“失意”。第四句则是诗人留给大家唯一的“渔者”形象,“出没风波里”可以概括为“勇往”。这四句诗每一句都象征着一个关键词,所以,“渔者”形象的四个关键属性“人”“欲望”“失意”“勇往”都被找到。至此,一个生动的、形象的、完整的“渔者”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隐喻背后的诗意
诗人以“渔者”自喻,但不同于前人的是,他跳脱出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所构建的“渔隐”形象。在前人笔下的“渔者”往往是仕途失意,甚至是追寻功名利禄而不得,又不想与浊世淤泥为伍,于是进一步退而求隐。中国古代文人在经历过政治斗争之后,一旦被伤得体无完肤,便选择江湖泛舟、退隐山林,以此抚平内心伤痛。这是他们无法改变现实而做出的主动抉择,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而按照新批评的标准去分析和解读,不难发现,《江上渔者》是被动之隐,是无奈之隐。诗人以“隐”为开篇,通过“江上”“鲈鱼”“舟”等意象含混复义,进一步打破“渔隐”的概念,寻求一种“非隐”,即积极入世的思想。尽管“入世”后被浊世浇了一盆冷水,却也勇往无畏,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正如上文所言“新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反对在批评中涉及一切与作家的社会背景、作家的创作意图以及创作感受有关的分析。”但实际上任何人也无法做到这点,因为分析任何意象与隐喻都需要立足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假设此刻分析的作品为李白、杜甫所作,或是那些耳熟能详的诗人的作品,那大家就必然要接受到中国传统知人论世方法的影响,新批评细读只是帮助了人们发现了其内在结构蕴含的力量。但不管如何,新批评作为西方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文本解读、分析方法,在文艺理论界持续发光发热,至今对诗歌,尤其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具有独到且实用的作用和意义。在新批评理论支持下,批评家们可以跳脱出传统的知人论世模式,对那些缺乏文献史料的作者的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文本分析,也是其价值所在,不仅可丰富文学作品的内涵,也能为诗歌提供全新的解读方式。通过新批评细读法视角解读《江上渔者》,可以发现整首诗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寓意深长,言微旨远。
参考文献:
[1]蔡正孙撰,常振国点校.诗林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邓新华,章辉.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3]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