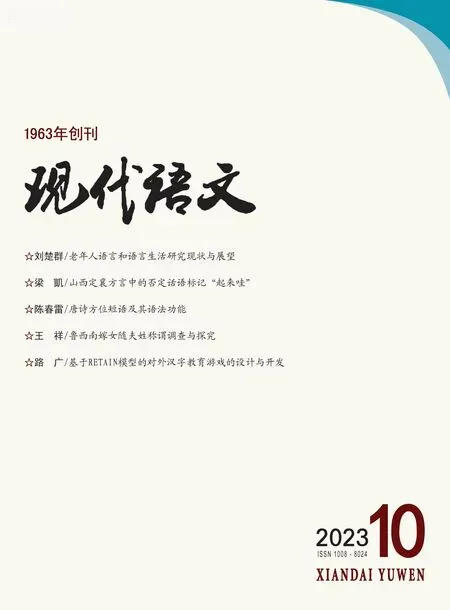《禹贡》“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歧解辑释
2024-01-08宋海燕
宋海燕
(安阳工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禹贡》是《尚书》中的名篇,也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习地理沿革者莫不宗之,被誉为“古今地理志之祖”。《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并依次介绍各州的疆域、山川、草木、赋贡、贡道等。在叙述兖州的赋税等级情况时,此书云“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关于这句话的断句、释义,历来歧解纷纭。有鉴于此,本文对古今学者的注疏、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力图探究出比较符合当时历史语境的结论,以期对此句有更为合理的解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断句
清代学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云,《史记》《汉志》作:“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1](P142)这里无“厥”字,“载”作“年”,为训诂字,“贞作”连读。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云,郑玄从“厥赋”断句,将“贞”连下句读,作“贞作十有三载”,并解释说:“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八州同,言功难也,其赋下下。”[2](P562)清代学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郑康成曰:‘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八州同。’……云‘贞,正也’者,《子夏易传》云:‘贞,正也。’云此州‘正作不休’者,读‘厥赋贞作’为句,以‘作’为耕作也。”[3](P149)谓郑玄从“厥赋贞作”断句,这里的句读“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史记集解》所载不同,已失郑意。清人王鸣盛《尚书后案》亦引郑玄后云:“此‘贞作’自是谓使民自治其田。”[4](P111)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引王先慎云:“据郑注,当连下‘作’字为句……”[5](P257),亦是从“厥赋贞作”断句。
与“厥赋贞作”断句相比,从“厥赋贞”断句的学者更多,如伪孔传、孔颖达、颜师古,宋人刘敞、苏轼、叶梦得、蔡沈,清人胡渭、牟庭、简朝亮等。我们也赞同后一种观点。在《禹贡》中,将全国的赋税和土质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并对兖州之外其余八州的赋税等级情况进行了描述:冀州:厥赋惟上上错;青州:厥赋中上;徐州:厥赋中中;扬州:厥赋下上;荆州:厥赋上下;豫州:厥赋错上中;梁州:厥赋下中三错;雍州:厥赋中下。从《禹贡》的叙事体例来看,八州“厥赋”后皆为等级排序,故兖州“厥赋”后也应为等级介绍,只有这样,才符合《禹贡》自身体例。如果从“厥赋”或“厥赋贞作”断句,以“贞”修饰“作”,认为是“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或者是“谓使民自治其田”,则赋税等级不明。因此,这里的“贞作”应分开,其断句是:“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
二、“贞”释义
在《禹贡》中,冀州、青州等八州的赋税等级均十分明晰,只有兖州的赋等为“贞”,与他州截然不同,因此,关于“贞”字的释义,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东汉学者郑玄将“贞”训为“正”,孙星衍认为《子夏易传》亦释“贞,正也”[3](P149),由于郑玄的学说影响较大,因此,后世学者多从此训。同时,学界对于“正”之涵义的解释也有所区别,大致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第九,赋正与州相当。如伪孔传:“贞,正也。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6](P140)孔颖达正义亦沿袭了这一观点:“《周易》彖、象,皆以‘贞’为正也。诸州赋无下下,‘贞’即下下,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后毕,州为第九成功,其赋亦为第九。列赋于九州之差,与第九州相当,故变文为‘贞’,见此意也。”[6](P140)孔颖达认为,兖州在九州中最后治水成功,州第九,赋亦当为第九,“贞”乃为“下下”的变文。颜师古、林之奇、屈万里等亦赞同此说,这里主要是从治水的角度去论述。今人李长傅《禹贡释地》云:“孔安国说:‘田第六。贞,正也。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兖州地下多水患,故田列第六。贡物的运输溯济、漯二水及河。逆水上溯甚难,故赋最低,列第九。”[7](P40)李长傅指出,兖州的贡道为水运,需要逆流而上,运输困难,因此,赋等列为最低第九等,这主要是从交通的角度论述的。
(二)第六,赋正与田相当。宋代学者刘敞认为:“田中下而言‘厥赋贞’,乃第六,明矣。”[5](P257)苏轼《书传》亦指出:“贞,正也。赋当随田高下,此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赋亦中下,皆第六。”[8](P518)宋人史浩等亦有类似的表述。不过,南宋学者林之奇反对这一说法,其《尚书全解》认为:“雍州之赋出第六,而兖州之赋不应又出于第六也”,先儒“谓兖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者。”[9](P125-126)清代学者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引清人何焯反驳云:“赋乃与田正当,不谓与州也。”[5](P257)清人俞樾亦云:“《广韵》曰:‘正,正当也。’厥田中下,厥赋亦中下,赋正与田相当。”[10](P49)
(三)薄为正,“贞”为下下。《尚书校释译论》引宋人叶梦得云:“九州之赋无下下,赋以薄为正,则贞谓下下也。”[2](P563)蔡沈《书集传》亦云:“田第六等,赋第九等,贞,正也。兖赋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赋为正也。”[11](P45)宋人曾旼、元人黄镇成等亦持此说。不过,这一说法也遭到了质疑,如南宋学者陈大猷《书集传或问》驳之云:“以薄为正,岂他州之赋皆非其正乎?孟子言‘轻于尧舜者为貉道,重于尧舜者为桀道。’故古人以十一为天下中正,岂但取于薄乎?皆未免牵强,故缺以待知者。”[12](P218-219)清代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亦指出:“《蔡传》云:‘兖赋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赋为正也。’(说本曾氏)然则他州之赋皆不正乎?袁良贵曰:‘什一者,尧舜中正之法。重则桀,轻则貉,谓赋以薄为正,殊非大道。’”[13](P78-79)陈、胡均对“以薄为正”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赋税过重或过轻皆非大道,“贞”作“薄赋”,解释牵强。
(四)贞:正出本等,无交错之名。宋代学者薛季宣《书古文训》云:“贞,无交错之名也。九州之赋交正庶土,用相补除。……兖州正出本等,无补除也。”[14](P249)在《禹贡》中,九州赋税等级确有交错者,如冀州“厥赋惟上上错”,豫州“厥赋错上中”,梁州“厥赋下中三错”,这里“错”的意思是上下浮动、杂出其他等级,而兖州“厥赋贞”为无需补除、正出本等的意思。
(五)贞:正、一、固定不变。胡渭《禹贡锥指》云:“韩康伯注《周易》‘贞胜’曰‘贞,正也,一也’。贞训正,兼有一义。厥赋贞,谓十二岁之中,赋法始终如一也。盖禹制五亩之税,视岁之丰凶以为多寡,而兖独有异,受患最深,垦辟不易,禹……宽以待之,至一纪之后,第十三载,然后赋法同于他州,亦视其丰凶以为多寡也。九赋之赋唯缺下下。兖赋至少,固当第九,而经不言下下,何也?兖赋法异于他州,言贞,则其义见;言下下,则其义不见。故不曰‘厥赋下下’,而曰‘厥赋贞’也。……《易·文言》‘贞固足以干事’,是贞亦兼有固义……贞皆其不动不变者,‘厥赋贞’当作此解。”[13](P78)胡氏认为,“贞”应训为正、一、固定不变,“厥赋贞”是说兖州十二年中赋法始终如一,由于兖州水患最重,垦田不易,因此,赋税最低,并且十二年保持不变,直到第十三年,赋法始同于他州。正是因为兖州赋法不同于他州,所以不言“下下”而言“贞”。
除了将“贞”训为“正”之外,“贞”还有其他解释:
(一)贞:卜问,根据往年收入以定赋等。胡渭《禹贡锥指》引朱氏云:“贞者,随所卜而定之之名也。盖兖与他州不同,水患虽平,盈虚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载,历历试之,然后得其一定之法,而赋始年年齐矣。”[13](P79)《尚书校释译论》引近人简朝亮云:“凡岁计之时,赋者问岁之既往而定之,异乎卜者问岁之未来而定之也。”[2](P565)简氏释“贞”与前说稍异,然皆云根据往年收成以确定赋税等级。
(二)贞:侦探。近代学者杨筠如认为:“贞即侦探之侦。《说文》:‘贞,卜问也。’《广雅》:‘侦,问也。’是其义相同。《晋语》‘贞之无报也’,‘贞’亦当为侦。《集韵》:‘贞又作侦。’《周易》:‘恒其德,贞。’《礼记·缁衣》‘贞’作‘侦’。贞、侦盖古今字,由卜问之义引申而为侦察之义也。‘作’,当如‘任土作贡’之作。‘贞作’,即言作赋之事,谓侦察而作也。”[2](P563)由“贞”的卜问义而引申出侦探、侦察的意思,其从“厥赋贞作”断句,谓“贞作”为侦察而作,即侦察相关情况、视情况而确定赋税等级。
(三)贞:终。牟庭《同文尚书》:“赋第九谓之贞者,元为始,贞为终。……赋之终殿为‘赋贞’,其义同也……上供薄少,则人情耻恶,故田可以言下下,而赋独变文而称贞耳。”[15](P170)牟氏指出,元为始,贞为终,“赋贞”即赋终第九等,“贞”是“下下”的变文,因为上供薄少,面子上不好看,所以将它改为好听一些的“贞”。
(四)贞:中。今人黄怀信《尚书注训》云:“贞,同‘中’。《利簋铭》‘岁贞’亦即岁中,皆古‘贞’、‘中’互通之证。中谓中中,第五等。”[16](P67)黄先生释“贞”为“中”,即赋税等级的第五等。樊东《尚书译注》亦云:“贞即‘中’”[17](P24),又云:“赋税是第九等”[16](P25),前后似乎矛盾。
通过上文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关于“贞”的释义可谓是聚讼纷纭。《尚书校释译论》指出:“这是一不易捉摸的问题,尽可由得各人驰骋自己的想法看法。”[2](P565)虽然如此,我们却可以通过《禹贡》体例和相关论述,大致判断其真实涵义。《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九州田地由上上至下下分作九等,除兖州外,其余八州之田地对应的赋等的次序为:冀州:上上错(一等);豫州:错上中(二等);荆州:上下(三等);青州:中上(四等);徐州:中中(五等);雍州:中下(六等);扬州:下上(七等);梁州:下中三错(八等),唯独缺少下下第九等,因此,兖州赋等当为下下。《尚书校释译论》云:“古人有喜欢‘整齐故事’的习惯,对一些本来不那么整齐的事往往要把它编排得整整齐齐,于是九个州便要把它编排为九个等级,这实际是不可能符合客观的,我们不要为它所拘泥。”[2](P542-543)不过,《禹贡》体例确实是这样编排的,冀州、兖州等九州都应毫无例外,就此来说,认为兖州赋等下下是很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将“贞”释为第五等、第六等、卜问、侦探、无交错等义,是值得商榷的。
还需指出的是,虽然很多学者以兖州赋等为“下下”,但都是从“贞”字上探寻“下下”的依据,这种研究方法同样值得商榷。兖州“厥赋”后不言“下下”而言“贞”,“贞”实际上是一个误字。宋代学者马廷鸾《六经集传》认为:“贞字不过‘下下’之误耳,不烦于贞字取义。”[2](P563)金履祥《尚书表注》对它的解释更为详细:“贞,本‘下下’篆文重字,但于字下从二。兖赋下下,古篆作下二,或误作‘正’,遂讹为贞。”[18](P440)金氏指出,在古代铜器铭文中,重文常以“二”作标识,“下下”古篆作“下二”,由于竖体书写被误作“正”,又讹变为“贞”。可以说,这是基于宋代发达的金石学成就而提出的卓见。马、金首倡此说,元人陈栎等又一再称引。裘锡圭指出:“秦汉时代的书写习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表示重文的方法。在周代金文里,重文通常用重文号‘=’代替,而且不但单字的重复用重文号,就是两个以上的词语以至句子的重复也用重文号。秦汉时代仍然如此(就抄书而言,其实直到唐代都还常常如此)。……知道了古人表示重文的习惯,就可以纠正古书里与重文有关的一些错误。”[19]《辞海》释“重文”,曾举东汉碑刻《北海相景君铭》为例:“‘再命虎将,绥元=兮。’‘元=’即‘元元’。”[20](P28)此外,清儒沈彤,近人曾运乾,今人江灏、钱宗武等亦赞同此说。因此,我们认为,“贞”应是“下下”的误写讹传,但“各家震于它是‘经’文,只能顺着它去解释,都成了瞎子断匾似的妄说”[2](P565)。
三、“作十有三载乃同”释义
在“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中,如果“作”连下句读,则无主语亦无宾语。学界通常认为其主语是禹,在先秦典籍中有很多关于“鲧禹治水”或“大禹治水”的记载,只是在年数上的说法并不一致;郑玄则认为“作十有三载”是治州的年数。可见,此句的争议主要围绕在“作”是治水还是治州,换言之,十三年究竟是治水年数还是治州年数。
(一)治水说
《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伪孔传:“治水十三年,乃有赋法,与他州同。”[6](P140)孔颖达正义:“‘作’者,役功作务,谓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赋法,始得贡赋,与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于他州最在后也。《尧典》言鲧治水九载,绩用不成,然后尧命得舜,舜乃举禹治水,三载功成,尧即禅舜。此言‘十三载’者,并鲧九载数之。《祭法》云‘禹能修鲧之功’,明鲧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载’者,记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内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6](P140-141)孔颖达基本沿袭了伪孔传的观点,将“作”释为治水,谓兖州治水十三年后,始得贡赋,同于他州;并援引《尚书·尧典》《礼记·祭法》等,说明十三年是治水的年数,包括鲧之九年和禹之三年。
自宋以来,承袭治水说者不乏其人,仅在计算的年数上有所区别。如《尚书校释译论》引朱熹云:“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年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则此州水平其后五年欤?……禹用功处多在河,所以于兖州下记‘作十有三载乃同’。此言等为治河也。”[2](P566)朱熹指出,禹治水八年后八州平,这里之所以说十三年,是因为大禹在治理兖州附近的黄河上又花费了五年。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云:“《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而不入门。’郑说与《史记》合。马注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十三年,并鲧九年数之,与《史记》说不同。”[1](P142)《史记·河渠书》记载大禹治水十三年,马融云大禹治水三年,皮氏由此指出,《史记》与马说不同,而与郑说合;不过,郑玄所言“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是说十三年为治州年数,实际上,郑说与《史记》亦不合。《今文尚书考证》又引《三国志·高堂隆传》曰:“‘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亦合禹之十三年与鲧九年计之,同《史记》说。”[1](P142)《史记》禹之十三年,加上鲧之九年,合于《三国志》所载的二十二年,皮氏据此认为二说相合。此外,清末吴汝纶据《史记·夏本纪》说禹“劳身焦思在外十三年”,又云《孟子》说禹“八年在外三过其门”,以评马融说之不尽合。凡此种种,都是将传说中鲧禹治水的年数当作信史来推求,皆不足为信。
(二)治州(赋)说
东汉时期,郑玄对“贞作十有三载乃同”的训释是:“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八州同。”[2](P562)已明言十三年为治理兖州的年数。后世学者亦多从此说,如苏轼《书传》:“兖州河患最甚,故功后成至于作十有三载。”[8](P518)林之奇《尚书全解》云:“说者多以十三载为禹治水所历之年……据此文承于‘厥赋贞’之下……是专为兖州之赋而言也。盖兖州之赋必待十有三载然后同于余州,非所谓此州治水必至十三年而成功也。若果谓此州治水必至十三年而成功,则其文势不应在于‘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之下也。”[9](P126)林氏从《禹贡》体例出发,认为此句在“厥赋贞”之后,当是承接赋税而言;同时,《禹贡》前文已云“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后文再言此州治水十三年而成功,亦不合行文逻辑。蔡沈认为:“兖当河下流之冲,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剧。今水患虽平,而卑湿沮洳未必尽去,土旷人稀,生理鲜少,必作治十有三载,然后赋法同于他州。此为田赋而言,故其文属于‘厥赋’之下。先儒以为禹治水所历之年……殊无意义,其说非是。”[11](P45)元人王充耘云:“兖受患最深,水土既可耕作矣,又必宽之十三年,待其一纪之后,岁星一周,天道变于上,地力复于下,然后使供输比同于他州。盖因其受患之深,所以优恤之至。”[13](P78)王充耘将“作”释为耕作,认为兖州水患最重,需要优待照顾十三年,等到地力完全恢复后,才能与他州贡赋相同。至于这里提及的“岁星一周”,乃为占星家之说,是不足为据的。明人王樵亦认为“此句因田赋而言”,并解释说:“‘作’为耕作之‘作’,乃合记田赋之通例。九州通例,记水土平治后,始及田赋,并无田赋之后又言治水。兖地虽最下,亦不应治水独至十三年之久也。注疏附合十三年之数尤凿。”[21](P329)此外,清人胡渭、王鸣盛、孙星衍、牟庭、俞樾、王先谦、王先慎,今人曾运乾、李长傅、屈万里、江灏、钱宗武、樊东、慕平等,亦有类似的表述。
相对而言,我们更倾向于“治州(赋)说”,理由有三。第一,在《禹贡》中,言及“作”者共有四处,除兖州此处外,其余三处分别是:冀州之“大陆既作”,青州之“莱夷作牧”,荆州之“云梦土作乂”。其余三处的“作”皆表“耕作”义,所以兖州此处的“作”亦当为耕作,而不是表示治水。第二,可以结合兖州此节的具体语境进行分析。此段先言“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澭、沮会同”,显然是说治水;随即又言“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接着,叙其土壤、草木、田赋后,方云“作十有三载乃同”。因此,这里所叙当为治州或者治赋,不应回过头来再谈治水。第三,从《禹贡》的叙事体例来看,各州首言疆域,之后叙其山川、厥土、厥田、厥赋、厥贡,厥土有时附其草木,厥贡则附各种不同物产,所有各州都遵此次序,并无一州例外①据刘起釪考证,冀州由于错简、脱简,造成赋在田前,属于州域的“恒卫即从大陆既作”,错简到了“厥田”之后,此外又脱去了“厥贡”的简文。此为西汉时的《禹贡》文本,并非《禹贡》原文[2](P544)。。值得注意的是,“厥赋”等级后一般紧接“厥贡”,两者之间没有其余文字,唯独兖州“厥赋”与“厥贡”间多出此句,因此,黄怀信《尚书注训》怀疑此句为“错简衍文”[16](P67),略过不释,这种处理方式与各家注释皆不相同,值得格外重视。不过,《史记》所录《禹贡》文本已是如此,可见,从先秦传至西汉的本子基本一致。由于此句处于“厥赋贞”之后,因此,它只能是承赋而释,释作治水则是不确切的。综上所述,“作十有三载乃同”的意思是“兖州经过十三年的农作耕耘,赋税才赶上其他各州”。
总的来看,田赋是《禹贡》的主要内容之一。《禹贡》中“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的记载,由于对兖州赋税等级叙述的特殊性,从而造成了断句、释义的歧解。从《禹贡》的体例编排来看,从“厥赋贞”断句,更符合《禹贡》的叙述形式。这里的“贞”为赋税等级,宋代学者马廷鸾、金履祥以丰富的金石学知识为依据,论证了“贞”为“下下”的误字,较有说服力。“作十有三载乃同”一句,由于“作”处于无主语、无宾语的状态,遂引起后世学者治水与治州(赋)的争议,这一问题亦可通过联系《禹贡》文本体例、行文逻辑、具体语境等而得到解决,此句的意思应是“兖州经过十三年的农作耕耘,赋税才赶上其他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