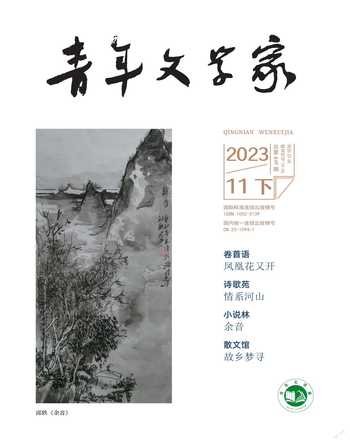陈庭学西域诗的个性特色分析
2024-01-02赵江媚
赵江媚
陈庭学(1739—1803),字景鱼,号莼涘,晚号莲东逸叟,直隶宛平人,祖籍吴江。乾隆三十一年(1766),其考中进士,年仅二十七岁,便已经“以文雄著籍京师”。乾隆四十六年(1781),其因甘肃赈灾案株连夺职,于次年谪戍伊犁。陈庭学寓居伊犁十四年,在西域的交游往来中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诗歌风格。
一、诗风豪迈慷爽,昂扬高蹈
年少为官的陈庭学四十二岁时在陕西道任上因甘肃冒赈案而谪戍伊犁,在其四十八岁时被再次起复为伊犁惠远城仓务,五十六岁时终得归乡。陈庭学一生波折颇多,但即使经历了这样的艰难曲折,他的诗歌中仍怨怼极少,而是以一种豪迈豁达的态度来笑对人生,使其颇具豪爽之气的诗风在诸多“慷慨悒郁以达其悲凉之气”的西域流戍文人中有了较为鲜明的风格。
(一)诗歌中遍布坚毅之风
首先,陈庭学的西域诗从整体情感上来看始终呈向上之姿,其中最重要的缘由的就是诗人十四年间从未放弃的释还东归的坚定信念。从一开始刚进入西域地界,陈庭学就直抒胸臆:“人间惯说他乡远,塞外从知化宇宽。”(《出嘉峪关》)只要心中有信念有希望,他乡即故乡。陈庭学的信念也非常直接地体现在《君恩重尚慎毋忘陟屺歌》中,“万里生还应有日”,即使因罪远戍西域,但不以此抱怨,他相信终有一天还会活着回到中原。在好友庄肇奎因为家信久未到达而忧伤不已甚至难以进食时,诗人劝慰道:“沦落尚希逢雨露,况君绾绶被恩光。”(《胥园迟家信未至,病不欲食,造问谈余,小饮尽欢,归用前韵慰之》)其对朋友和自己的未来都充满无限的期待。这种由衷的安慰与庄肇奎低落的返乡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陈庭学擅长将他人境遇与自身境遇相结合,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归心,在不断地自我暗示中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诗风。当友人东归时,陈庭学不止一次地表达自己东归的决心,“举头便是长安日,试看春回草木光”(《复次前韵答胥园》),“与君天末尤相见,他日重逢自有缘”(《送蓼堂还京》),“天教迁客暂相依,君但能来亦易归”(《蓼堂去后,胥园来诗,归思颇剧,次韵奉慰》)。在得到可以返回中原的确切消息后,陈庭学则更为激动:“我亦明年及瓜代,相期蔗境话金台。”(《秋日送柳南同年还京赋诗四首》)这些真情流露之作正是植根于诗人对自身处境的乐观判断和对复起东归的决心及信心之中。至此,在其诗歌中随处可见的对复起东归的信念成为陈庭学西域诗的一大特色。
(二)超越生死的洒脱
在陈庭学的西域诗中,有一些情感十分真挚的悼亡诗,可以从中看出诗人对生死的超脱之感。《哭高青畴》是陈庭学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为友人高青畴所作的悼亡诗。高青畴,生平不详。这首诗是陈庭学得知高青畴突然病逝,挥笔写就的悼亡诗。诗人在诗作中说,仿佛昨日还在一起喝酒聚会,酒局还未结束,怎么今天就突闻噩耗。诗人的情感也是经过了一个起伏的过程—由感叹、震惊逐渐转为冷静,并在最后询问好友的葬期。在突然的情绪爆发后,诗人也能很快冷静下来,可见其康适的人生态度。
在另一首悼亡诗《哭温弁山同年》中也有相似的表达:“小住溘然逝,一恸太仓皇。”诗人开题即对友人溘然长逝感到悲痛,接着大篇幅回忆与友人过去“与君共门墙”的日子,表达对友人和自己少年岁月的怀念。如今斯人已逝,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只剩下“一语众皆诺,残膏黯垂烬”,一时间悲伤到达了顶峰,只有吟唱哀歌来舒缓内心之痛了。整首诗到这里全都是极度的痛苦,但是到了最后两句,笔锋稍转—“颓光如可挽,一蹶当再振”,在阴霾中突然就有了阳光的透入,诗人自勉道:斯人已逝,活着的人更应抓住光阴、振作起来,有希望、有信念地活着。在面临死別的极痛之后能够迅速平复心情,可见诗人颇有洒脱之气。
二、语言怀抱超旷,情真意切
余集在《塞垣吟草·序》中直接赞叹:“而公徜徉诗酒,豪?之气不减,曩时同年之在朝者已落落如晨星,每一过从辄叹公之怀抱超旷,为不可及。”
陈庭学这样宽阔的心胸与其自身年少时较为顺遂的经历而塑造起来的乐观心态及其对佛学禅理的参悟密不可分。同时,从陈庭学的诗歌中难见不平之词,而多是记录人生喜事来看,他有着极强的乐天知命之感。
(一)善用禅语进行自我净化
佛教作为广大世人追求超脱的主要工具,帮助无数清代西域流人走出精神困境,如陈庭学的《格子烟墩》写到“百年未了世间事,片刻且为空外人”,将禅思渗透进了诗歌的核心。因此,在这样的文化浸润下,做官的心态逐渐由劳形怵心转变为闲情逸致。但陈庭学对待佛教禅学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像大多数贬谪诗人那般暂时地躲进宗教的庇护伞下进行自我麻醉,而是真正将其“空”的奥义渗透进诗歌创作甚至个人的际遇选择中,指引着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至后来陈庭学自伊犁被放归后便开始了颇为闲趣的生活,“日以训课生徒、口授指画为乐……归而享家人之乐……绝不以门第高甲、仕宦得失为荣辱”(朱珪《塞垣吟草·墓碑》)。可以说,这与诗人对佛理的参悟密不可分。
《役旋途次书怀》是陈庭学在交游中创作的颇具禅理气息的代表作。“须弥芥子”,言偌大的须弥山纳于芥子之中,暗喻佛法之精妙,无处不在,如果能明白理事本无障碍,那么这就是游刃有余地理解禅理了。陈庭学用此典故正是宽慰自己、鼓舞心灵,彰显了其宽阔明朗的处世态度。诗歌最后以“收拾归心还努力,莫将岁月付飘蓬”结尾,丝毫不见沉迷宗教、不理世事的颓唐之气,一股雄健之风扑面而来。可见,陈庭学修习佛理禅学并不是为了皈依宗教或暂避世事,而是更好地理解佛门之“空”,来坚定自己的内心,不为暂时的苦难击倒,以达到更宽广的境地。这和同为流放诗人的舒敏有所不同。舒敏,乾隆六十年(1795)被贬伊犁,在伊犁流放四年间,舒敏的西域诗与禅学也有颇多联系,“落日孟城口,秋风扫秃柳。城头眼界空,禅寂破诸有”(《孟城坳》)。舒敏的禅诗表现的是一种与陈庭学禅诗相异的静态,在佛家的“无”中深感寂寥,而这种感情也是颇多中原文人流放西域后最主要的表达,“佛学宽慰自己,看淡自己现在的生活,使得生活中的贫瘠和理想的无处抒发有了寄托之地”(王潇仪《舒敏诗歌研究》)。由此对比可见,陈庭学确实有超乎普遍流人的超脱心态,在对待佛理禅学的态度上也是以净化自身来达到更大程度的开阔心胸、积极生活,因而陈庭学对禅学的态度是超越的。
(二)志喜语言感人肺腑
陈庭学性格直率、心胸开阔,当闻得亲人朋友的喜事时常常兴奋之情溢于指尖,故颇多“志喜”之作。所谓“志喜”,即记录喜事,诗人认为高兴的事情特别值得记录,他以一种纪实性的方法来记录当时发生的喜事和心情。“志喜”不但志远在中原的家人之喜还志周遭朋友之喜,品味志喜语言能够感受陈庭学超乎常人的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视。
1.语言风趣幽默
在志家人之喜时,陈庭学多用幽默之语,充满家人之爱。陈庭学有二子,大儿陈预、小儿陈云。“子预庚戌进士,四川永宁道以军功赏戴花翎。”(陈庭学《塞垣吟草》四卷附《东归途咏》一卷)两个儿子都是通过科举高中进士而授官于朝。陈庭学在伊犁时对儿子颇为思念,多次在诗中记录,拳拳爱子之心溢于言表。
在《得家信知弟举子,大儿预连试首选,次儿云入泮,志喜三首》诗中,诗人提及弟弟的喜事,大儿子考试得了第一名,二儿子也入学了,这些都是值得诗人高兴的,特别是大儿子“连试首选”,让诗人非常骄傲,随即有一丝自得在其中,“汝似吾当日,文场屡冠军”,既夸了自己的儿子,也夸了自己,颇为风趣,最后不忘叮嘱大儿子要好好教导小儿子,一位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2.语言平实,极富感染力
朋友復官,陈庭学特别作诗志喜—《闻溉余、蘧庄两同年复官志喜》,特别是后两句“仆倦忽闻归亦喜,谁言得且住为佳”,语言平实朴素,直白易懂。陈庭学在诗作中极少用典及华丽的辞藻,通常直接表达对朋友即将复官的极度喜悦,在喜悦背后深藏的是诗人对自己终有一天也将复官的信心。诗人的志喜诗,将家人朋友的喜事及时地记录下来,通过其间真挚的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诗人将这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看作自身前路有望的希望之光,是诗人在极寒之地振作精神的心灵良药。在其一首首志喜诗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位不卑不亢、心胸豁达的诗人,在边寒之地自我安慰、鼓励亲属、自得其乐。伊犁十四年,陈庭学始终保持着一颗向前看的理想之心,保留了他有少年般的纯粹和热情。在其志喜诗的字里行间时刻流露出诗人激动期待的心情,他以平实的文字与读者分享这份喜悦。
三、诗歌基调和平温厚,意境宽舒
张问陶直接评价陈庭学的诗歌基调,“每念戈壁风沙,渺如天外,居其地者愁吟苦啸,当如何慷慨悒郁以达其悲凉之气,而诵先生所作则和平温厚,意境宽舒,几忘其为羁人迁客也”(余集《塞垣吟草·序》)。陈庭学西域诗的整体基调温和平实,以浓厚的家国情怀充斥其中,在闲适的生活中展现大雅诗风。
(一)中华一家的理想信念奠定平和基调
陈庭学在西域十四年却少有悲愤不平之作,除其自身宽舒性格之外还有对中华一家思想的深刻领悟。
首先,陈庭学之所以使人“忘其为羁人迁客”,有很大的原因就是陈庭学有一种以贬谪地为“家”的强烈认同感。清代诗人在大一统的社会环境熏陶中,已经把岁岁东风、恩泽遍及边塞的理念根植于心了,能够作出“乡关非近塞非遥”(《放怀》)的壮语。在看到西域的屯田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农业大获丰收时,陈庭学满怀热血地感叹道:“陆耕曾不羡江田。”(《读申瑶泉麦浪诗次韵一首复成三首》其三)。
其次,有清一代,当文人被贬谪到西域时,他们大多真实记录西域见闻,或直接以家书的形式邮寄回家,或以诗集的形式保留下来以供后人阅读,“凡先生书至,必有诗,有诗,笠帆兄弟必与子同展读”(余集《塞垣吟草·序》),或将这些见闻以口述的形式作为朋友宴饮时的谈资,这些的保存或表达都不适合流露出太过暴烈的情感,因此平缓的抒情与白描才是最恰当的表现形式,也更能彰显民族团结、国家一统之风,这样的创作要求再次巩固了陈庭学中华一家的理想信念。
第三,陈庭学深入西域十四年,对西域有了自己独特的感悟,再加上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边界在不断模糊化,陈庭学在周围环境的推动下不再有中原文人的文化优越感,以更平静、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西域景物和自身处境;同时,他对禅学“空”“无”的不断参悟,让他逐渐做到“我亦渐忘身近远”(《霄山过敝居赋赠》)。在这样双重影响下形成的视角写出来的诗歌自然意境宽舒、温润超脱。所以,在诗人和平温厚、意境宽舒的诗风之下是他坚定的中华一家的理想信念。
(二)清雅闲淡的平居生活展现宽舒意境
“至于遭遇虽穷而超然事外,不诬不怼、不矜不挫,发为文词,冲和大雅,使人意消”(余集《塞垣吟草·序》),这是余集对陈庭学诗风的重要评价,亦是十分贴切。陈庭学之所以能够有大雅诗风,正是由于其大多数时候都过着与友人共游登高、参禅悟道的闲适生活,这也造就了其温厚平和的诗风。
陈庭学闲适诗的代表作是《小院》。这首诗几乎就是诗人在伊犁闲适生活的缩影。首联说明自己有一方小院,有稳定的住处,是一切安逸生活的开端。然后开始描绘小院里的景致:架子上有“瓠”,篱笆外有“豆”,充满了田园生活的闲趣。在这样静雅环境中安静地生活,也就注定不会有过多锋利的棱角。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轻松的活动:“花锄闲自课,药裹病新除。命酒棋枰侧,拈毫贝叶余。”(《题于梅谷寄亭与庄胥园同赋》)诗人养花弄草,与人对饮,研究棋艺,阅读经书,参悟佛理,在一片祥和悠闲中享受生活的平静美好。在这片清雅闲淡中隐约透露出一丝淡淡的愁绪,但又很快被“何地不吾庐”(《题于梅谷寄亭与庄胥园同赋》)释怀,留下的仍是阵阵恬淡之风。
总之,陈庭学的西域诗始终展现着诗人独特的超然心态,语言温和平实、幽默风趣。特别是诗歌中一以贯之的禅学思维和中华一家的理想信念更是为陈庭学的西域诗注入了一股坚毅超旷之风,读之“使人意消”(余集《清代诗文集汇编·塞垣吟草·序》),这在当时流放西域的诗人群体中是十分难得的。
本文系甘肃省教育厅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石韫玉诗文笺注”(项目编号:2023CXZX-006)的阶段性成果。